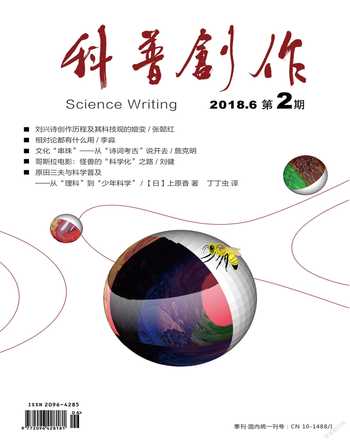科普耄耋老顽童
——刘兴诗专访
2018-09-10姚利芬
姚利芬
这个已是望九之年的老头儿是一个奇妙而多维的存在,他的名片上按照惯例写着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研究员、作家。却在另一张上抛弃了这一切,老老实实标明三种真实的身份:教书匠、爬山匠、爬格匠。背面标注着: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新构造运动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史前考古学、科普创作、儿童文学作家、旅游资源开发或其他杂学。你惊讶于他“变身术”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兴趣的多元。他还喜欢吃奶油蛋糕和做梦,因为“在梦里张开双手,一下子就能飞起来,真好玩极了……”
梦醒时,他是一位勤恳耕耘的作家——“我喜欢不断地重新开始,探索新的可能,也愿意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山野考察里跨出最后一步,或者在伏案写作中度过。”
幻想从现实起飞
记者:你是地质学教授,同时又创作了大量科普科幻作品,无论是童话还是科幻的创作,都离不开幻想,你怎样看待幻想和现实两者的关系?
刘兴诗:我的观点是“幻想,从现实起飞”。科幻小说说到底,只不过是浪漫文学的一种,通过折射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只是幻想,没有联系现实。那岂不就是断线风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以前讲科幻小说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凡尔纳流派,又叫重科学流派;另一个是威尔斯流派,即重社会学流派。根据现在的情况,远远不能这么划分,我现在对科幻小说做三个划分:
第一个是重科学流派,以凡尔纳为代表。这个流派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切实可靠的科学主题,有扎实的科学根据。我很喜欢凡尔纳的作品,很喜欢!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他的作品了。所以有评论家说我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与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有神似的地方。
第二个是重社会学流派。以威尔斯的《隐身人》为代表,这部作品看似荒唐,却讲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个人企图离开社会必然灭亡,在荒诞的外衣内有一颗严肃的心。如果在一个荒诞的外衣里还是荒诞的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很多作品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把这个流派叫作“重文学流派”不是很恰当,什么作品不需要重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流派一定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题。所以我给取名:重社会学流派。
第三个流派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类,以玄幻小说居多。我给它取名叫娱乐流派,娱乐不是不好,生活好了当然需要娱乐,并不是贬义词。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最好不要成为主流,不管科学主题,还是社会学主题,还得言之有物才好。
记者:能谈谈你的代表作《美洲来的哥伦布》相关的创作情况吗?
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前期准备资料和考证的时间花了大概20年,就因为有些问题我没有弄清楚,所以迟迟没有下笔。在我做完科学考证之后,真正开始写作只花了十几天的时间。这篇小说的末尾,完全可以附上参考文献,所有的场景都真实可考。
金涛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说,好像喝了几两海水一样。你要问我,为什么这部小说中的场景描写写得那么真实,你知道我找了多少科学材料,多少文学材料?花了多少时间仔细琢磨透了当地的气候环境,才能如实写到纸上。
兴趣广泛,最喜欢写童话
记者:你的作品语言优美流畅,题材所涉庞杂,科学考证严谨,生活中你是否兴趣比较广泛?
刘兴诗:说到语言,这怕要追溯到我的古典文学和诗词的功底,童子功嘛。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描述的对象本身就很美,人生本身就很美。照实写出来,怎么不美呢?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真实就是美,完全不用矫揉造作,使用一大堆形容词和副词堆砌。
我从小喜欢阅读。小时候我爸给的零花钱主要用来买书了。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南京大撤退,我带的东西就是几本小小的童话书。书名我还记得,《三只小猪》《小老鼠历险记》。到了少年时期,我特喜欢《金银岛》一类的探险小说。
语文、历史、地理一直是我的强项,我喜欢写古典诗词,格律一点也不会错。我考北京大学的时候,数学只有5分。那时候学校自主招生,我得以被录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像西语系的冯至先生,我请教他英国的十四行诗的问题,他说你别研究那些,何不研究中国的古代律诗呢?
很多知识我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刚进北大的时候,教普通天文学的老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几番接触后,他好奇地问我,你这个天文学知识是咋学来的?我告诉他,在中学的时候,我带头成立了南开星空协会,都是我们自学的。戴先生说,我这个课你可以不听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就是了。啊呀呀,想不到在大一的时候,戴先生就不拘一格,几乎把我当研究生徒弟了。有了这些科学和文学的积淀,再写《古诗文中的科学》这类作品,当然就一点不难了。
(1)尾煤泥水一段浓缩。浮选尾煤和中煤、矸石磁选机尾矿进入一段浓缩设备,进行分级、浓缩,使溢流中尽量减少大于0.045 mm粒级含量,减轻二段浓缩设备的负荷;使底流浓度达到20%~30%,满足一段回收设备对入料浓度的要求。
记者:能谈谈喜欢的作家作品吗?
刘兴诗:我以前特别喜欢雨果,包括《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这些作品。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喜欢的作家也很多。现在好多人不喜欢看长篇小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现在谁还会去看《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飘》和《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中有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得——“葛利高里失败后回到家乡,推开家里的木门,那个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嘎吱嘎吱响的声音传来。”我每次回北大,一进西门,就觉得一阵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声音似乎就响起来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喜欢的书很多,什么都看。比如说《圣经》,我现在还在看。《圣经》实际上是传说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圣经》也很有趣,还可以从民俗学研究,不只宗教的视角。我不是宗教信徒,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宗教,我的信仰非常明确——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人民、我的土地,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真正的宗教。
记者:在你创作的诸多文类和作品中,最喜欢的是什么?
刘兴诗:我最满意的文类是童话,还有小说。童话我喜欢唯美主义的那类,自己创作的作品中最喜欢《星孩子》。科幻小说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真正研究出来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很少有人看过的《海眼》。
记者:你写的微型科幻作品也比较多,很有星新一的味道。
刘兴诗:我写的微型小说与现实生活联系也比较密切。《流星雨之夜的梦》,写的是一个小餐厅的姑娘,梦想自己的白马王子。一口气跑上天桥,果然就出来一个白马王子。第二天早上,他来了,原来是给这个小店送煤球的小伙子。凡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不能写啊?难道爱情只能是王子和公主吗?还有《中国足球狂想曲》《“三六九”狂想曲》也是针对现实生活,关于中国足球和房改等问题,有感而写的。我提倡写“ing”,写现在进行时的作品,切中当下的现实问题,为什么非要写和生活不着边的外星世界、外星人呢?
记者:你写的好多故事都跟海洋相关,除了海洋还偏爱哪一类题材?
刘兴诗:我喜欢海洋。另外我还喜欢写动物小说,因为我这一生都在跟野生动物打交道,我喜欢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写的动物小说很多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写《蛇宝石》就受我们在热带、亚热带地方野外考察天天遇见的眼镜蛇启发。
记者:你的小说经常会塑造硬汉的形象,类似海明威笔下的那类硬汉,你对此怎么考虑的?
刘兴诗:这和我自己的人生追求有关,别人对我的评价中就提到我是个硬汉。在野外考察,我经历过很多场面,总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去,撤退的时候我在最后面。“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我的信条,也是我一直践行的准则。我从来没向困难和权势低过头,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社会上的斗争。
勤勉求新,不断归零
记者:《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获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你觉得这本书为什么会获奖?
刘兴诗:目前市面上科普书籍很多,但大多是编著的,仅仅就科学谈科学、就知识谈知识,很难激发学生们的阅读兴趣。《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之所以颇受好评,关键在于“原创”,介绍了我国境内丰富的气候带内的各种自然环境、地域空间和自然现象。有实地考察,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通过优美的文字展开,既通俗易懂,也有浓烈的美学观念,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追求形式。你说为什么会获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对国家、人民的爱写出来了。真实的爱,就是一种特殊的美。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你不要以为科普作品就是干巴巴的科学知识,真正好的科普作品是需要神韵的。
记者:是否考虑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写下去?
刘兴诗:不,我选择放弃。就是做到一定成绩的时候放弃,重新再来,不断创新。创作要求新求变,再模仿写下去就没意思了。一个人抄袭人家不好,抄袭自己也不好。到一定的程度就放弃,来新的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要尝试一下。过去的成绩我已经忘记了,学习女排精神,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现在每写一部新的作品都要改变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成都一个出版社曾出了我3本书,是把20多年前的书改编了3本,他们想让我做宣传,请媒体宣传,签名售书。我推辞不过,读者让我签名,我就写了8个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表示这是陈旧的作品,必须完全忘记,重新创造才好。
曾经有一个编辑说,我的童话写得好美,认为《星孩子》不亚于泰戈尔的作品。这说得太过了,十分惭愧。也有人说,我的一些科普作品和传统的科普完全不是一回事。被读者检验后认可,当然我也高兴,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不断地归零重来。必须敢于设想,敢于怀疑,敢于放弃,敢于再创新才好。
记者:你对当下的科普科幻创作以及出版有什么建议?
刘兴诗:我和很多出版社的朋友交换意见,搞出版的应该做出版家,别做出版商。出版家具有开阔的视野,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出版商却只是跟着市场跑,什么书好卖,就拼命跟风,大批制造。这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怎么可能出好书?千万不要唯市场化。现在的社会很浮躁,沉不下来。在出版和创作这一块里,这个现象也存在。能够沉得下来,不跟风、不浮躁,多出新的、好的、有个性的作品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