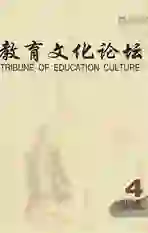女传教士“看”与“被看”模式的文化义理疏论
2018-09-10陶冬
陶冬
摘 要: 以《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为研读对象,并就其中女传教士群体宣教中国西南期间形成的“看”与“被看”文化模式的义理进行疏诠。“看”是女传教士视角的主动投射,在主动“看”的过程中,折射的是女传教士群体的文化心理。而“被看”模式所彰显的,是中国在特殊时期根深蒂固的“男权至上”思想。透过“看与被看”,一方面凸显了两种文化间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无论西方女传教士还是中国西南腹地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里,她们都是“他者”,都是被造成的“第二性”。
關键词: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女传教士视角;看与被看模式;文化冲突;形象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4-0133-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4.027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东人达教授译注本《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记述了张道惠、布莱恩、柏格理、邰慕廉、王树德等英国传教士,在晚清民国时期于云贵川各地从事传教、教育、医疗等工作的心路历程。是书由117篇纪实性文章构成,主要作者为张道惠夫妇。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录了传教士妇女工作者和基督教会妇幼(后文统称为女传教士)群体的工作经历,在宣教、教育及医疗过程中,她们表达了自身体察认知中国的看法。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不仅记录着张道惠、柏格理、邰慕廉等人在西南宣教的种种经历,还记录着女传教士群体的一些经历,她们的活动区域多在昭通、东川、贵州石门坎等地。在这些文章中,以“妇女的帮助者”为题的文章八篇,记录着妇女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以“孩子专页”为题的文章3篇,主要记录苗疆地区的孩子所遭遇的苦痛。而女性传教士所著的文章有11篇,主要记录了女传教士在宣教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样一批人,她们身份特殊,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医生。作为其中的少数人,她们须忍受艰苦的条件,长途跋涉来到西南,以完成所谓的“上帝指派的任务”。这样一群人,她们或带着怜悯、或带有同情,在云南、贵州、四川的部分地区游走,也言说着她们眼中的故事。然而,这样一个群体在当时奉行男权至上的中国来说犹如天外来客,使人惊奇不已。女传教群体用自己的眼光在观察中国时,她们也在被观察着。在这样一种相互的“看与被看”模式下,隐藏的是两个不同文明碰撞所带来的一些冲突。文章以《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为主要蓝本,试图去分析女传教士在西南宣教行中的“看与被看”模式,并探讨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
一、作为注目者的女传教士
与男性不同,在宣教途中,女传教群体所要承受得更多,不仅在于身体的困苦,更在于内心的煎熬。其中,女传教士在言说自己眼中的西南、或脏乱、或美好、或残忍、或仁慈。她们用女性的特殊体验与视角来描绘自己眼中的西南,而在她们作为注视者的同时,她们也在被注视着。这其中包含的“看与被看”模式对比鲜明,但探讨其中却颇有意义。
(一)女传教士眼中的表层中国
初次步入中国,能得到的第一印象是风景。从英国到中国西南路途遥远,而时常要跋山涉水。所以对中国的山山水水,她们的感概是“风景真是美不胜收”。绝佳的山水、奇异的风景,无一不在昭示着这是一片待开发之地。“我希望能够将所看到的风景描述出来,高高的山峰环绕着我们,构成了一个壮丽的体系。”[1]63。这些沿途中的美丽似乎都不能掩盖大环境的脏乱差。脏乱是女传教士口中时常出现的词,环境的脏乱使得异国的女性阵脚大乱。“每一个物件都是肮脏的”[1]60旅途中的客栈也是污秽的,中国的猪也是肮脏的。时局也是动荡的,在宣教途中,云贵川等地多次发生暴动,特别是1910年以后,针对外国人的仇恨情绪一下子上来,很多地方都在敌视外国传教士,所以在这些女传教士眼中,中国的时局是动荡的。可即便是这样,在中国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是亲切善良的。“此时我感到浑身疲惫与肌肉酸痛,而一位妇女就尽量让我靠住她以舒适一些,于是我就半坐在凳子上并倚靠在她亲切、不洁净的身体上,她就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3]。在女传教士群体看来,这些人在内心深处是渴求得到解救的。“我们对于她们可以说无能为力,当离开村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们渴望的眼神”[1]265。从行文中,可以看到女传教士群体的优越感。总体来说,女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她们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男性。用布莱恩女士的话来说,“旅行是令人愉快的,但冗长的路途,对我而言,是沉闷的。”[1]272这是浅层面的认识。风景、环境、人心、时局等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真正能够反映实质的是妇女和儿童的境遇。胡适就曾说过:“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是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妇女和儿童的境遇最能体现最深层的文化特质。
在女传教士的眼里,投射最多的无非是西南的妇女和儿童的遭遇,妇女与儿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被侮辱的与被侵害的地位,从女传教士的眼中透露出的怜悯折射出她们自身的优越地位。或许这无形中透露出来的优越感不是她们主动彰显的,但是这种对比之下出来的优势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
(二)女传教士眼中的妇女和儿童
女传教士群体看到的与男性传教士看到的不尽相同,他们都看到地位低下的妇女、濒临死亡的婴孩。而作为男性群体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职责和道义,而女传教式群体更多展示的是怜悯与同情。这其中有身体与心理的原因。当然也有文化的原因。
被女传教士关照最多的无非就是身处蛮夷之地的妇女和儿童。她们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处于边缘的边缘,是最弱势的群体。而由她们孕育出来的婴孩,更是朝不保夕。溺婴现象的存在、缠足风俗的根深蒂固、一夫多妻制的盛行,加剧了女性被遗弃的风险。而有些女性也是助长这些风气的元凶,丈夫死了的女性,为了再嫁,竟然在刚出生的孩子身上绑上石头,以终止婴孩的生命。说到底,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也是受害者。而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鳏夫,迫于饥饿的压力,竟然将自己的孩子带往天花遍布和流行性感冒发病地区,让这种看似“非人为”的因素夺去孩子的生命,可以说,妇女和儿童随时都是身陷囹圄,不能自救。当肩负“神圣义务”的外国女传教士们目睹周遭的一切时,怜悯与同情油然而生。内心更加坚定“解除那个不幸福国家的疼痛需要基督教的力量”[1]68这种信念。女传教群体由于自己特殊的性别和先天的使命,对这些被侮辱与被侵害的群体加以保护。虽同为女性,但一强一弱对比鲜明。来自西方的女传教士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渊博的学识,拥有男性传教士的坚毅和果敢。而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妇女,从出生到死亡都不曾拥有选择权,由于溺婴现象的存在,有些女性从出生时就注定着死亡。此外,男权为尊的社会,女性只得一辈子依附于男性。低下的社会地位、无法选择的生育权,使得这些东方女性瞻仰着来自西方的“天使”们。而似乎馈赠笑容给别人就是女传教士们的首要任务,多布森夫人如是说:“我喜欢观察妇女的面部表情,时而她们都在哭泣,时而她们全部开怀大笑,看起来总是满怀欢乐与欣慰地回家。”[1]137张道惠夫人在孩子专页那里说到:许多小孩子因为身体虚弱而无法接受食品的营养,在相继离开人世后,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饥饿,也不再干渴。”女传教士们倾听女人们哀伤的故事,并给予她们安慰,尽力去改变儿童的现状。这是她们的任务所需,也是她们的内心所趋。
作为注目者的女传教士,在看到深陷囹圄的东方女性时,试图施恩于这片土地,而这种神圣而仁慈的任务也使她们能够享受到在其所在国享受不到的自信与成就感。女性传教士在“看”的同时,她们也被看。被柔弱的东方女性带着羡慕的目光观看,也被男权为尊思想支配着的男性们看。
二、被“看”的女传教士
在一个男权居上的社会里,一些外国女性的出现、尤其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性出现在这片未开化之地,这无疑在原住民的认知体系中刷新了新的一页。女传教士既被受“男权为尊”思想支配的东方男子们观看,“每个安息日我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被船工观察。”也被身处弱势地位的东方女性观看。“我察觉到,这些妇女从来就没有听过一位与她们自己性别相同的人解读《圣经》,也就意味着她们对教义所知甚少。”[1]206而在被“看”的途中,体现出的是主动观看者的诧异。无论如何,对于这片待开发之地的男男女女来说,女传教士们的出现无疑洞开了他们的眼界与认知。而在这种被看中,更加体现出东方女性的地位低下。
同为女性,地处西南边陲的女性只能依附男人生活,甚至过的是一种朝不保夕、毫无地位的生活。而来自欧洲的女传教士所做的竟是教化育人的工作,这其中体现出的不仅是欧洲白人女性的优越感,还有西南地区妇女的羸弱与无助。无论是这些欧洲女传教士,还是身处西南腹地的女性们,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她们都是被塑造而成的“第二性”。女传教士们在来到中国之前,在自己的原生国家也并没有享受到与男性相等的地位。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也是经过多番争取而来的。甚至于有些女性传教士只是妄求挣脱原生国的处境,才远渡中国。传教这份工作之所以需要女性,也只不过是一策略性的权宜之计。女性传教士的加入,都有利于消解彼时国人对外国人的抵触,尤其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妇女来说,女性传教士不失为一个绝佳的倾诉对象。“女传教士的存在,对于打开女性信徒心结方面的功效,绝对是男性传教士无法代替的。”[2]
19世纪50-90年代,第一次女权运动在西方各国呈现风起云涌之势,妇女解放意识开始觉醒。然而,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为女性赢得多少权力。20世纪初年,英美等国妇女进一步走上了独立。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尽管摆脱了附属地位,她们实质上并没有赢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为此,有些女性试图通过海外传教和投身慈善活动,赢得平等地位和实现自身价值。于是,众多女传教士们远渡重洋赶赴各地异邦,在“肮脏”“混乱”国度中零距离目睹到了遭遇远较自身更悲惨的女性,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在这种双重的被注视中,在东方男女老少诧异的眼神中,女传教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宣教同時,通过创办天足会和开展文化教育等方式,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成就感。她们惊异于异国他乡的女性地位是如此低下,在这种被注目的情况下,女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优越感和自信心,这是在与弱者对视时所产生的。
而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的思想也使得当时两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下立现。在当时的中国,女性尚处于附属物阶段,她们的一生一死都取决于自己的父母和丈夫。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为尊”的社会里,男性权威容不得丝毫撼动,而在目睹异国女性施教于中国的途中,这种畸形的思想立马原形毕露。在女传教士被注目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彼时中国西南腹地民众的诧异、还有恐慌。
三、“看”与“被看”模式下的文化义理
无论是女传教士群体的主动观看,还是西南腹地人民的看客行为。无一不在体现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女传教士时常将《圣经》挂在嘴边,口中时常唱着“耶稣爱我”等歌曲,她们在看的时候,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标准看的,所以对沿途所见的遗风陋俗鄙夷不已,对比她们更弱的妇女和儿童怜悯不已,这是上帝的福音使然,也是一强一弱的对比下强者对弱者所产生的同情使然。正是在这种“看”与“被看”的互动中,东方妇女的生存现状昭然若揭,西方女性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平权思想和男尊女卑同样折射的是两个不同文明的针锋相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3]2波伏娃的这段话很形象的点明了彼时东西方女性地位优劣的由来。20世纪初年的英国,社会开明、思想开放,大都女性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被温柔款待。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女性有着自己的使命感,她们试图挣脱男权的控制,向世人昭示自己的独立与伟大。所以女传教士们在这样一个异邦较大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
反观彼时的中国,民智未启,况且传教士所行经的乌蒙山区更是法外之地。遗风陋俗繁杂,女性缠足的情况时有出现,一夫多妻制的盛行,男权至上思想被奉为圭臬,女性地位的低下。在这样的文明环境下,女性只能沦为被侮辱的与被侵害的。当这样两种文明下的人群集结在一起,高下立现。同为女性,虽都属于生物圈里的弱者,“只是权利的媒介,而不是权利的掌握者。”[3]98然而相比而言,女传教士群体比这些在遗风陋俗影响下的女性则要强大得多,而女性温柔敦厚的天性和上帝指派的任务相结合,女传教群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势必会无限放大。女传教士群体时时关切着西南腹地妇女和儿童的处境,并且力图救她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看似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帮扶,实则是同为女性,作为同一个物种的惺惺相惜。
女传教士在执教中国的过程中,在自己心里勾勒了一个属于她们的中国。脏乱、动荡不安,但却温情脉脉。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对生活了十几年的中国她们也有不舍。从起初的厌恶到之后的同情再到离开时的不舍。女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和西南是复杂的。女传教士在“注视”的同时,她们也被异邦人民所注视。从被“注视模式中又可以看出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也正是在这样的“被注视”下,女传教士得到在自己原所在国所无法得到的成就感。
参考文献:
[1] 张道惠,柏格理,等.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M]东人达,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2] 陳玥.循道公会女传教群体在滇东北宣教活动述论[J].昭通学院学报,2016(38).
[3] 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涂 艳)
Abstract: Examining female missionaries cultural modes and co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ching” and “being-watched”, the Chinese translated version of Southwest Missionary Archives Revealed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watching” is an active projec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missionaries and it can reflec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group of female missionaries. What is highlighted by the mode of “being-watched” has revealed Chinas deep-rooted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a special period. Through watching and being watched,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highlighted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clear that no matter western female missionaries or women in the hinterland of southwest China, in the male-oriented world, they are all “others” and are made “second sex”.
Key words: Southwest Missionary Archives Revealed;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missionaries; modes of watching and being-watched; cultural conflict; imag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