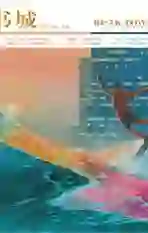中岛家三畸人传
2018-09-06尹敏志
尹敏志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东京文求堂书店总共出版了九部甲骨文专著,昭和八年(1933)五月发行的《卜辞通纂》是其中第四部。书出版时郭氏还被国民政府悬赏缉拿,通过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销售网络,此书才得以销往中国。鲁迅就很快从上海内山书店买了一套插架,花费十三元二角,并录入日记的书账中。
《卜辞通纂》一书大量使用日本收藏的甲骨文材料,在序言中郭氏介绍道:
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去岁夏秋之交即从事探访,计于江户所见者,有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洋文库五百余片(林博士旧藏),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蠔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携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半为罗叔言氏寄赠,半为滨田青陵博士于殷墟所拾得),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氏七八百片,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
文中提到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京都大学自不必论,林泰辅、中村不折、罗振玉、内藤湖南、滨田耕作等私人藏家也都大名鼎鼎,无需赘述,只有“中岛蠔山”鲜为人知。
蠔山真名叫中岛竦,文久元年(1861)出生于东京,字翘之,号玉振道人、蠔山。他不但富藏两百多片甲骨,自己也做文字学研究。昭和九年(1934)六月至昭和十二年(1937)十月间,他的甲骨文著作《书契渊源》在东京文求堂书店分五函出版,共十七册线装白纸石印本,从印刷、用纸到装帧形式都与郭氏著作相近。中岛擅长书法,故该书从题签到正文皆是其肉笔手书,魏碑体字棱角铮铮,苍劲老辣。
由于《书契渊源》每函仅印三百部,后来再未重版,又多收藏于日本各公共图书馆,剩下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水火之厄、战乱虫蠹,目前书市上全本难觅。我只在东京大学南门的琳琅阁书店见过全帙,然而价格不菲。最近半年,我从东京都的两位不同卖家那里购得其中第一函和第四函,虽零帙残册,亦堪宝贵。展读时查阅相关资料,方知埼玉县中岛氏是明治维新以后重要的儒学世家,抚山、斗南、蠔山三父子前后相继,与中国的关系始终绵绵不绝。
一、玉振道人
中岛竦早年以教私塾自给,生活清贫。大正元年(1912)森鸥外曾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名为《羽鸟千寻》。小说的主人公是位曾受過森鸥外关照的青年人,因为贫困上不起大学,顽强地靠自学通过医师考试,进入陆军军医学校当教员,却不幸感染肺结核身亡,逝世时年仅二十六岁。小说以羽鸟千寻写给森鸥外长信的形式缓缓铺开,笔调清冷。在描述自己八岁在群马县乡间所受的启蒙教育时,羽鸟这样写道:
我在八岁时开始受汉文素读。当时在玉村的父亲有个义弟正当县会议长,以他为中心组织了名为“晚翠吟社”的诗社。后来又成立了叫“玉振学社”的私塾,一位名为中岛蠔山的埼玉县久喜人受聘前来执教,我记得他头发很长,结成麻绳一样的辫子,浑名“木食道人”。学校放学后,我总是背着书包去中岛家里,到十五岁时已经依次读完了《孝经》、四书五经、《文章轨范》《十八史略》《唐宋八大家文》。进入中学以后,大家都头疼不已的汉文我却轻松通过了。
在小说的开头森鸥外敬告读者主人公并非虚构,汉学老师“中岛蠔山”当然也真实存在。因为中岛竦没有任何年谱或传记存世,小说提供了其早年经历的重要线索—虽已是明治末年,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争相学习西方文明,将线装书当作废纸卖给古书店时,中岛却选择从埼玉县搬到离东京更北、更偏远的群马县做塾师,教学生读越来越无用的汉文。
中岛竦在群马县究竟待了多久不得而知,只知道一九○二年他受京师警务学堂之邀赴北京担任日文翻译,时年四十一岁。二十世纪初旅居北京的日本人还不太多,除了二叶亭四迷等文人外,中岛竦还与中国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密切来往。青木虽是一介武夫,但也粗通汉学,他见中岛熟读汉籍,就怂恿后者写一部面向日本读者的蒙古志。这种朋友间的委托背后可能有军方授意:当时日本军部对于蒙古地区有浓厚兴趣,苦于对其一无所知,急需全面介绍这里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的著作。
中岛痛快地答应了青木的请求,然而写作的过程极其艰辛。一九一六年《蒙古通志》在民友社付梓时,青木亲自为之作序,介绍中岛为撰写此书“于燕山客舍里,君雪夜呵冻毫,驱溽热以榆荫,拮据经营,如斯前后易数寒暑,无日不翻阅史册,无日不讨究疑义”。他称赞正是这样严谨的态度使作者“贯穿通博,上下二千年,东西三万里,遂能大成此不朽文字”。
据中岛竦本人自述,此书的写作一九○七年九月发轫于北京北城朴园的无尽意轩内,一九○九年四月在南城御河桥北育材馆脱稿,前后历经两年春秋。《蒙古通志》先总述蒙古各部名称区分、清政府统治沿革、盟旗制度与风土物产等基本情况,接下来分漠南、漠北、漠西、回部四编展开叙述。该书体例严谨,内容厚重,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并驾齐驱,被认为是日本蒙古学研究的先驱。所以在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中,中岛竦最早不是作为一个甲骨学者,而是以蒙古史研究者的身份“出道”的。
因为光绪至宣统年间长居北京,耳濡目染,中岛敏锐地注意到这时蒙古地区变化显著。清末开拓边疆之风骤起,“或以巩固边防,或以安插饥黎,或以开发利源,或以启悟蒙民。出洋学生首倡于外,经世论客续和于内,函牍交错,献策售说,一时官场视为终南捷径,利窦已开,孰甘居后”。在那以前,从内陆移民到蒙古的只有河北、山东两省边民,此后无论南人、北人皆成群结队移居蒙古,很多地区被迅速汉化,风貌也发生剧变:“牛羊下括之地,化为禾黍离离之区,毡幕帐庐之乡,转见上栋下宇之家。”他认为这一变化尚处于进行时,以至于《蒙古通志》的内容与实际可能有所出入。
《蒙古通志》写到一半时,慈禧太后过世的消息传出,中岛竦投笔走出书斋,上街观摩了太后的葬礼。他记得那天北京城里狂风暴雨,泥泞满地,但街道上却人潮鼎沸,犹如盛大的节日。层累的污泥被路人踩至糜烂,没过脚踝,送葬人都预先穿上了分发的新靴,然而很快就看不出本来的颜色。狼狈的抬棺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不成队列地送完了慈禧太后的最后一程。目睹这一切的中岛预感清朝气数已尽,很快就会走向灭亡。
在中国待了十多年后,中岛竦受善邻书院之召,回到东京任书院讲师。善邻书院创办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发起人为曾留学中国的宫岛吉美,书院以融合东西文化为宗旨,主张中日两国学生共同学习,增强相互了解。此外日本国内还有昭和八年(1933)成立于东京的“善邻协会”,以进出蒙古为主要目的,协会与书院虽然都名为“善邻”,其实没有相互关系。
中岛竦此后在书院教授汉文、蒙古语,同时钻研甲骨文,《书契渊源》就是精思二十多年的成果。中国学界对此书最早的评论是语言学家严学宭于一九三五年发表于《考古社刊》的短论《读中岛竦〈书契渊源〉后》,严氏在阅读了第一函后认为,中岛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唐兰殊途同归,都是“废部首而不言,顺文字自然发展之理”,但唐氏的方法似乎更为精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都藏有《书契渊源》,但这部书后来基本从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回国后的中岛竦一直住在麹町纪尾井町的善邻书院教师宿舍里,直到生命末尾因病移居老家栗桥。据增井经夫(他是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女婿,东京大学毕业,以研究清史成名)回忆,从昭和十三年(1938)开始他一直去上中岛的《说文解字》讲义课。虽然先生年近八十,但每次讲课前仍然会郑重地梳起浓密的头发,端坐小桌前,然后才开始音吐朗朗地讲学。善领书院校舍嘉树环绕,环境清幽,有一次讲课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清澈的叮叮声,中岛遂弃书辍讲,不安地对增井说道—
“他们这是在锻日本刀呀!”
二、中岛抚山
中岛竦之父名中岛庆太郎,字伯章,号抚山、演孔堂,文政十二年(1829)出生于江户龟户的商人家庭。
在少年时代,庆太郎的汉学启蒙老师是出井贞顺,十四岁时改而从学于龟田绫濑。绫濑是儒学者龟田鹏斋的长子,后者属于江户时代的“折衷学派”大儒。该学派不恪守德川幕府推崇的程朱理学,主张调和儒道,去粗取精,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的狂儒一流。庆太郎亲炙绫濑之教十二年,待先生去世,又受教于其子龟田莺谷。
莺谷名长保,字申之,号学孔堂,他继承家学,博览洽闻,尤好钻研儒家“性”说,著有《论孟集注异说》《学庸章句异说》等,反复修改几十年仍不愿付梓。直到某日他忽然领悟道:“韩愈氏有言:‘汲古得修绠。稽古之道,宜若汲井然,维患绠之不修,不患井之不浅。”故而毅然将自己的心血全部毁弃,一归于“述而不作”之儒家古义。至晚年又考究日本國典,试图调和神道教与儒学,使两者合流,创立“神典圣经一致说”。
受醉心学问的两位老师影响,三十岁时中岛庆太郎已久忘世味,他将全部家产转让给堂弟,自己搬到江户两国町(今天的东京市墨田区)一带,安政五年(1858)创立私塾“演孔堂”。中岛竦描述父亲当时安贫乐道,“独携妻子弟妹,别下帷都门,聚徒授经,日夕讽籀为乐,妻孥告饥,晏如也”。紧随两个哥哥中岛靖(绰轩)、中岛端(斗南)之后,中岛竦也诞生在这个家庭,他后面还有四个弟弟翊、开藏、田人和比多吉。
家中全是嗷嗷待哺的孩子,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恰好庆太郎的同门—在埼玉县开私塾的新井大年和其子新井和卿先后病故,新井的弟子们全部来到江户转入中岛门下,所收束脩勉强可应付家计。
然而此时正值幕府末年,天下将乱:“当是时,幕政失驭,国论鼎沸,各藩就封,江都落莫,纪纲日弛,剽盗昼行,加以凶饥,米珠柴桂,人不乐业,师友四散,各往所适。”考虑到江户人员辐辏、骚扰不安,中岛庆太郎决定带着家人避居埼玉县久喜,修缮当地“迁善馆”旧址居之,这里是龟田家几代人曾经讲学过的地方,馆内鹏斋执笔的《迁善馆记》碑犹在,碑文有曰:
恭惟一乡之人,入于斯馆,登于斯室,闻道承教,而变顽迁善。
明治六年(1873)天下甫安,中岛抚山在久喜自家宅内开设私塾“幸魂精舍”。据现存久喜市斋藤家保存的课表,幸魂精舍的课程安排是每月一号讲读《毛诗》,二号《中庸》,三号《周易》,四号《论语》,五号《古事记》和《诗文会》,六号《孟子》,七号《万叶集》,八号《韩文》,九号《论语》,十号休息,十天过后,再从头开始循环。
没想到开学没多久,学生也没招到几个,私塾就被政府找上麻烦。由于一年前八月日本政府颁布《太政官布告第214号(被仰出书/学制布告书)》以及首部近代《学制》,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全部纳入国家管控之中,东京文部省的官员据此公文认定“幸魂精舍”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合现行学制的轨辙,勒令其停业整改。幸而久喜当地人信任中岛抚山,继续将子弟送进这里就学。幸魂精舍存在了三十多年,走出毕业生一千多名,其中多有在地方议会和县、村政府担任公职者。
对明治新政府的各种干涉,抚山甚为不满,中岛竦回忆父亲晚年“既卑视流俗,不媚时辈,趋舍暌违,不欲与世俯仰,棲迟衡门,裹足不复入都,以故道行于闾里子弟,不为世知,虽有遗著,传之家耳”。中岛家还延续江户时代的传统习俗,不理会明治政府规定必须改过西历新年的法令,继续庆祝农历新年。一九○三年新春之际,抚山作一汉诗云:
七十五年强项儒,讴春沿例酌屠苏。
斯文不坠传家有,自许六经坦递夫。
此诗铿铿有金声,亦可视为斯人之自叙传。明治四十四年(1911)六月中岛抚山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纵观其一生,实际上是以一己之力,将龟田鹏斋、莺谷之学传到明治末年。
他去世二十多年后,昭和十年(1935),抚山的两位弟子增永、吉田写信给中岛竦,表明共同出资出版老师遗著的意愿。中岛竦遂将父亲的《性说疏义》手稿从箧底寻出,在开明堂东京营业所石印几百部,于北海道札幌市发行。此书共四卷,线装两册,卷一卷首云“性说凡十一条鹏斋龟田先生著 门下后进 中岛庆疏义”。该书内容是对龟田鹏斋《性说》的注解,体例是引用一章节,再对之作详细解释,惜之印数极少。
三、斗南先生
中岛抚山的二子中岛端字俨之,生于安政五年(1858),被人尊称为“勿堂”或“斗南先生”。勿堂六岁承袭家学,精通汉文,性格“狷介善骂,不能假人,人亦莫之能假”。中岛端是家中最不耐键户读书的一位。他任侠好剑术,热衷于就政局发表议论,三十三岁时出版第一本书《近世外交史》(东京幸玉堂1891年),署名“图南狂生”。
明治三十五年(1902),中岛端跟随东亚同文书院第二代院长杉浦重刚来到上海。同样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杉浦赏识中岛端的才学,准备为他在同文书院安排一个教职,端却推辞不就,选择短衣仗剑,如侠客般在中国四处游历。
某日清晨,居上海的罗振玉洗漱完毕,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急促敲门,登楼俯视,见“有客清癯如鹤,当户立,亟倒履迎之”。两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来客毫无扭捏之意,他先呈上自己的名片,上书“日本男子中岛端”,接着从怀中拿出笔墨递给罗振玉,双方开始伏案笔谈。那天中岛端意气风发,“指陈东亚情势,顷刻尽十余纸”。第二天罗振玉来到中岛端寄居的丰阳馆回访,才知道他一早就已启程离开。
几个月后罗收到中岛端的来信,称自己遍游吴越各地,已而又来信表示还想继续在此再待三年,询问能否给他介绍工作:“仆有三寸弱毫,不素餐也。”罗笑而许诺,邀请他来自己主编的《农学报》任日文编译。中岛在报馆待了约一年,将泽村真《农艺化学实验法》,草野正行、中村春正《气候教科书》等农学书籍译出,暇时将自己的诗文呈示罗振玉,“雄直有奇,其抱负不可一世”。在上海中岛端还接触刚开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并动笔将德文《资本论》的部分章節翻译为汉文发表。
一九○四年罗振玉转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中岛端也跟着他来南京当教师,但几个月后就挂职而去。此后一年他闲居上海,不事生产,眼看橐囊渐空,遂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繁琐的文书杂务明显与他的性格不合,每日社务之余“平居茕茕,形影相依,言而莫听,唱而不和,郁屈无聊”,他痛感这样下去“日复一日,况能奋发砥砺,有以树立乎”。
熬了三年多,眼看自己年近半百,中岛端下决心不能再以糊口为事:“我赵人耳,今虽惫矣,气力犹足用也,倘故将军不弃我,庶可以自效乎。”
没过多久,中岛端便投笔悬日本刀北上,投奔也在北京的弟弟中岛竦,途中他作有古体律诗数首,其中《幽燕途上》一诗颇有慷慨悲歌之意:
关外雪风吹白草,满天落木燕南道。
五更听尽萧萧声,催得征人一夕老。
同题又一首云:
绝望太行渺翠微,千村万落带烟霏。
秋风嫋嫋秋天迴,无际平沙独雁飞。
抵达北京的那年年底,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宣统帝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清朝政局震荡。中岛端为之欢欣鼓舞,认为办大事的时机已到,写信建议罗振玉上书弹劾正当权的袁世凯,或者干脆“手刃之以泄敷天之愤,仆虽不武,愿袖短剑以从”。文士罗振玉当然不可能去当刺客,更无意得罪当道,只能敬谢不敏。中岛端听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辛亥年初他心灰意冷,离开北京返回日本,没想到走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中岛端有洁癖,终身未婚,不近妇人,回日本也没有稳定工作,生计仰赖亲戚朋友、弟子门生支给。脾气又褊急,动辄骂人,自称:“恶诗恶笔,自欺欺人,亿千万劫,不免蛇身。”在大正、昭和年代那个基本完成现代化的日本,无论他的剑术、汉诗文,还是立场,都不合时宜。如果能早生三十年,他这种江户汉学者气质与国士狂热气质夹杂的性格,或许能在幕府末年的乱局中闯出一片天,但此时只能叹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一九三○年中岛端最后一次西渡中国,年过七旬的他故地重游,慨叹“千年故国无乔木,百里废园只夜螀”。他在大连与老友罗振玉见面,分别时说自己一定会再来,并郑重约定了日期,没想到翌年就在故乡作古。他的遗言辗转传到罗振玉那里,据说是:“吾死后速行火化,散骨灰于太平洋,异日有兵临吾国者,当为神风以御之。”遗族谨遵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太平洋西北角的熊野滩海面。
另据侄子中岛敦回忆,伯父死前还曾手书给他简单的六字遗言:“勿葬,勿坟,勿碑。”这是非常简洁洗练的中文,前来报道死讯的记者浑然不解其义,出刊时居然将“勿坟”误植为“勿愤”(繁体字“墳”与“憤”字形相近)。对于终生郁郁不得志,在不满、焦躁和愤怒中反复挣扎的斗南先生来说,这一无心的讹误犹如天意,多少有几分讽刺的意味。
四、尾声
在《卜辞通纂》中,郭沫若收入中岛竦所藏甲骨拓片八片,并称他为“日本有数的汉学家”。昭和十一年(1936)十二月底,即将七十七周岁的中岛竦手写完《书契渊源》的最后一页,深感体力不支:“余潭思篆籀,数十年于兹……唯是年迈耄及,大命近矣,故所论著仅止此耳。若夫继而成之,余有厚望于时贤来哲焉。”最后又勉强将已出版四函中的文字错讹勘误完毕,这项工作终于宣告结束。
四年后中岛竦溘然长逝。此时战争正如火如荼,他在北平时搜集的甲骨按松丸道雄的说法“不知所踪”。直到一九九六年荒木日吕子发表《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的甲骨片》一书,人们才得知中岛在过世那年已将这批甲骨无偿赠予友人山崎溪琴,现藏溪琴之子山崎忠处。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批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北洹滨的甲骨部分遗失,剩下的发生碎裂,原来的两百片不到变成了目前的两百二十九片,所幸仍存天壤间。
参考文献:
1.森鸥外《羽鸟千寻》,《鸥外全集·著作篇》第三卷,岩波书店1937年;
2.增井経夫《線香の火》,研文出版1987年;
3.中岛竦编《斗南存稿》,文求堂书店1933年;
4.中岛敦《斗南先生》,《中島敦全集》第二卷,築摩书房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