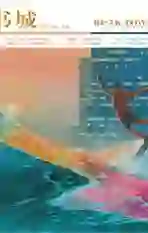中文影响我的一生
2018-09-06周质平
周质平
最近二十年来,“汉语热”成了美国外语教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之后,只有中国人学外国话的份儿,哪儿有外国人学中文的事呢!而今风水轮转,外国人居然也学起汉语来了。五四运动以来,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指为中国进步绊脚石的汉语汉字,在经过近百年的批评、摧残、改造之后,居然屹立不倒,还在世界各地,大出风头。这绝非当年主张废灭汉字、提倡拉丁化的学者专家所能梦见。
汉语汉字之所以由“冷门”变成“热门”,绝非因为汉语汉字的内在结构起了根本的变化。而是因为中国已经由一个被列强侵略的次殖民地,一变而成了雄峙于东方的一个大国,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汉语汉字成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五四知识分子常有因果倒置的论断,以为中国的复兴端赖汉字的改革,而不知汉语汉字的复兴实有赖于中国的复兴。
随着学习中文的学生的快速增加,汉语教学成了学界一个新的关注点。在对外汉语教学这一界,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为数可观的教学研讨会,但至今还没有从学习者的角度探讨过,来谈谈学习中文对他们一生和工作所产生的影响。
怎么教、教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是怎么学、学什么,为什么当今从事中国研究或在中国经商、工作的人需要学中文,学了中文,对他们的一生和事业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始终只能从教的角度来研讨推广汉语教学,那不免还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外国学生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为了打破这种一偏之见,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和我在二0一六年十月筹组了一个从学习者的角度来探讨中文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和事业的研讨会。
在近一年的筹备中,我们请到了当今美国学术界、商业界、法学界、外交界、新闻界和政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卓有建树的学者专家十八人,他们在中文造诣上也是一时之选,中文在他们的学习、研究、工作中都占着重要的地位,我们请他们现身说法,谈谈汉语学习和他们的中国事业有怎样的关联。
受邀的十八位专家学者都在会前递交了英文论文。研讨会分为五组进行:第一组四位发言人,有三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其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的林培瑞教授是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田安(Anna Shields)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lbany)的何瞻(James Hargett)教授是研究唐宋文学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安雅兰(Julia Andrews)教授是中国艺术史专家。这一组由我主持。发言的四位学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史的兴趣,分别是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开始的,在时间上容或有先后,但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经济还很穷困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好奇和知识上的追求,而不是功利的。这组发言强调了中文学习对学术研究以及对认识中美语言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强调了准确的发音和优秀的教师对提高学习者中文水平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组是美国在华的三位商界人士,包括跨国制造企业The Crane Company驻中国的总裁高杰(Geoffrey Ziebart),麦当劳公司前在华高管、曾任美国在华商会主席、现任高尔夫球美巡赛中国区副总裁的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以及《财富》杂志中国前主编高德思(Thomas Gorman,未能与会,林培瑞代为发言)。主持人是林培瑞教授。前两位发言者均以流利、准确、自然的中文演讲,对目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凸显了长期生活在中文语言环境中,对其中文水平特别是口语表达产生的重大作用。高杰认为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使他在工作中能够有效化解中美双方的矛盾,敏锐把握市场变化的细节,实现企业与员工以及中美两国贸易交往的双赢。葛国瑞认为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不但带来了事业上的成长,而且带来了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的丰收,他不但有了美丽、聪慧的中国妻子,而且还有两个在双语、双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混血儿女,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为儿女的未来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组是美国各大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主编,包括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知名撰稿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他的“中国三部曲”曾获得过美国多项纪实文学大奖。张彦(Ian Johnson)目前是《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纽约客》《国家地理》的撰稿人,二○○一年曾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Mary Kay Magistad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记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设立了该广播电台在中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新闻周刊》记者刘美远(Melinda Liu),曾经历了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歷史事件。这组的主持人是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因工作性质的关系,这组发言者的文章、书籍、时事报导,对美国公众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发言者认为直接用中文采访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比借助翻译或者英文往往更能让对方推心置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雾里看花或者转用其他新闻机构的素材进行写作造成的弊端,因而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
第四组是从事法律与政治专业领域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包括纽约大学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柏恩敬(Ira Belkin)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郭丹青(Donald Clarke)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祖若水(Rory Truex)教授。这组的主持人是圣母大学的朱永平教授。发言者认为中美法律体系、政治体制不同,所用术语差别很大,因此很难用英文作简单对应的翻译,由于法律工作的特殊性,从业人员必须对中文有非常准确深入的理解,才能满足工作需要,减少差错。
第五组是在美国各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包括前联合国驻华官员毕儒博(Bill Bikales),他用准确而流利的中文,进行了生动、感人的演讲。葛思亭(James Gadsden)曾就职于在台北的美国贸易中心(U.S. Trade Center),并曾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冯若诚(Owen Fletcher)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目前在美国驻越南使馆任职。朱思敏(Julian Smisek) 现任职于美国驻华使馆。这组的主持人是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发言者认为,美国人需要打破英语是世界上最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各国人民都应该掌握并运用英语与美国人交谈的成见;语言交流的平等,是国家互信和平等相待的基础。学好中文还有益于掌握日文、越南文等其他亚洲语言,在冯若诚看来,中文类似于亚洲多种语言中的“拉丁文”,是日文、韩文、越南文的源头。
在这十八位发言人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都怀有一份温情,用英文来说是一种“passion and love”,正因为有了这一份温情,才能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份敬意和了解。我借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中的“温情”和“敬意”这两个词,并不是要研究者失掉客观的立场,而是希望一个外国的研究者能透过中文,从中国人的角度,设身处地来探讨他所研究的问题,否则就成了“隔靴搔痒”。
在中国从事研究或工作的外国人,如果他日常的行事都必须依赖翻译,其结果不只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尤其严重的是,他所观察到的一切,都不免是“霧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一层也许薄如蝉翼,但真相却常常因此隐去。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在一九六○年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对那些驾驭中文材料能力不足的美国学者,很含蓄幽默地指出,对原文没有透彻的了解,却妄下评论分析,其结果往往是“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之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次大会发言者的共同的经验是,翻译不但不是万应灵丹,有时还可能造成误会,闹出笑话。
以中英文双语写作而知名于海内外的作家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一书中,对中英文的不同,有深刻的观察,他说:
在中国语言里有一种见不着,但却能极有效地改变一个人思维模式的成分。由这些成分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形象和话语的声调,是如此有别于英文。
林语堂所说的这种看不见的巨大不同,是很难透过翻译表达出来的,要感觉出这点不同,必须在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环境中有过长期的浸润和沉潜。
林培瑞在他文章的最后,用园丁种花的生动形象,来说明语言教学带给他的快慰和满足。初级语言课的老师都是播种者,最初播下去的只是一颗语言的种子,语言一般都只被看作是一种工具,但在茁壮的过程中,这个在表面上看来只是工具的种子,会渐渐吸收可观的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也可以是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外交、商业。工具加上内容之后,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的,而这个新的思想和观点,可以为每一位外语的学习者提供一对新的眼睛、一双新的耳朵、一个新的嘴巴。有了这些新开的窍,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所有讲演者在回忆中也都提到,学习中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事业,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商业、外交、新闻各个领域,他们的工作和中国是分不开的。 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往往在他们初次接触到中文的时候,就已播下了种子。
在对外汉语教学这一界里,我们往往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略了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内容。这个内容应该是中国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而不仅仅是节庆、习俗、剪纸和中国结。这次研讨会的十八位发言人为这一点作出了最好的见证。一个真能学好中文的外国人,他必须对中文有一点痴,有一点陶醉。这让我想起林培瑞对相声的热爱,他曾多次在我们家和其他北京来的老师表演侯宝林的《戏剧与方言》,他用几乎乱真的北京话演绎着侯宝林那脍炙人口的片段。在他表演的过程中,与其说是娱人,不如说是娱己。他的那份陶醉是我始终忘不了的。
学好并精通一门外语,需要一点“痴”,需要一点“陶醉”。这点“痴”和“陶醉”我们在十八位讲演者身上都看得很清楚。有几位早年都愿意克服生活上种种的不便,到中国去学习研究。对艰难困苦甘之如饴的态度,这就是我所谓的“痴”和“陶醉”。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两句话里,最关键的一个字是“乐”,“乐”字,相当于英文的enjoy,也就是“乐在其中”。学习任何东西,一旦达到这个境界,就欲罢不能了。
但是这点“痴”和“陶醉”,在我们对外汉语的课程里面却不见踪影。“商用汉语”“法律中文”是不可能让学生“痴”,让学生“醉”的。我们过分强调学习中文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结果整个学习的过程成了技能培训。学生很难从语言的学习中感受到知识的快乐和智慧的增长,结果是只感觉其难,感觉其苦。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柏恩敬(Ira Belkin)在回忆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提到,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全力学习中文,他觉得爱上中文类似于谈恋爱,与其说是一个理智的决定,不如说是一种感情上的爱好,这种不以实用为出发点的学习动机,往往更能持久。他每学一个新的汉字,就觉得又解开了一个谜,又多了一把通向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让他最感快慰的是他说出了一句字正腔圆、用词得体的中文,让他的中国朋友对他忍不住赞叹。我和恩敬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这是一段非常写实的剖白。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教育与善的生活》(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一书中对语言教学的一段话,至今对我们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机械化的文明里,有一种纯粹只顾实用的危险。为了追求所谓“效率”而牺牲了生活中的美感。也许我有点儿老派,但我必须承认,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交流的工具,而忽略了它同时也是美感的承载,对此,我是深感忧心的。
我所说的“痴”与“陶醉”,大多来自语言的“美感的承载”,而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是“有用”,而“美感的承载”则是“可爱”“可敬”“可佩”。学习一种外语,让人感到它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是不难的,但让人同时感到它也是“美感的承载”就不容易了。“交流的工具”,是任何初级入门的学生都能体会到的,但“美感的承载”,即使皓首于外语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能有所体悟。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广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的介绍上,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但我们的关怀似乎过度地集中在普及上,而没有在提高上作出足够的努力。我们这个研讨会带给大家的启示是,提高才是真正力量之所在。没有提高的普及,至多只能形成一个人多而势不众的局面。但提高往往需要长期的投资,默默地耕耘,不能求速效、速成。
在这次受邀的十八位发言人中,他们大多有流利的汉语水平和成功的中国事业,在回忆中,他们也都将中国事业的成功,归功于流利的汉语水平。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在欣慰之余,也别让兴奋冲昏了头脑,以为中文真有了国际语言的地位。这不免又偏离了中文在当前世界上实际的处境。林培瑞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在西方世界,比如说在亚洲协会年会中,一个中国学者用中文来发表有关王阳明思想研究的文章,而与会的其他外国学者,也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提问和讨论?至今在学术界里还弥漫着一种风气—即使是中国研究,也只有用英文发表的学术著作,才是真正严肃的研究。
其实这个会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林培瑞的观察。这个研讨会的总题是:“为什么中国事业需要学习中文?”(How and Why Language Learning Is Useful In China Careers?) 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暗示着,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研究或在中国工作生活是不需要中文的。我们如果把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改成:“为什么美国事业需要学习英文?”(How and Why English Learning is Useful in USA Careers?)大家都会觉得这还用讨论吗?换句话说,这个研讨会,一方面说明了中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体现了中文要成为一个真正国际上承认的通用语,还有很长的路。
二0一八年七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