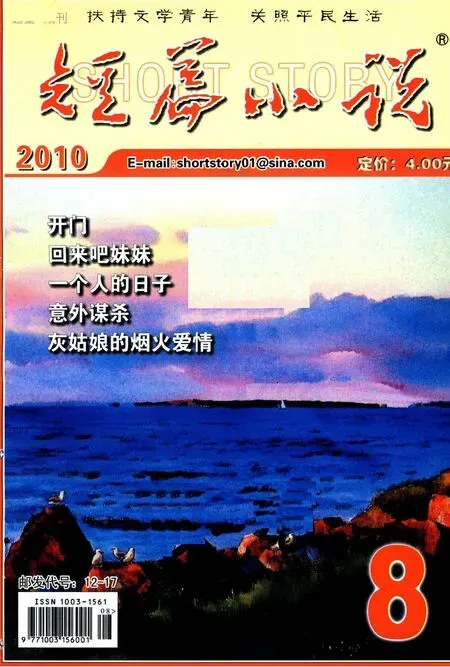坳坳街记事
2018-09-06陈其深
◎陈其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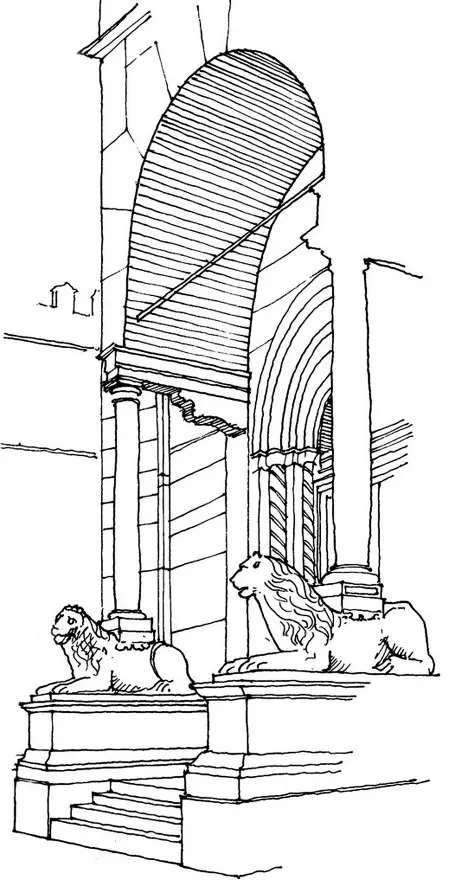
1
最近,二奶奶手腕上没再戴那件宝贝玉镯了,那天她还把半仙堵在家门口,手指头都快伸到半仙的鼻子尖尖了,她带着哭腔骂,死瞎子!死瞎子!骂得半仙脑袋差点都要低到裤裆里了,半句话也不敢吱声。
多年以前,酒癫子毛三少也这样骂过他,但那一骂却骂出了半仙的名气。那天,三少找他算命,半仙摸了摸三少的天门,就把钱递回给三少。算不得。算不得!三少快回吧!三少本就浑,又是一戳就硬的年纪,看着半仙那神兮兮的模样,大骂,你个死瞎子!装!装你个鬼呢!说完跨上摩托车连轰两把油门,箭一样没了踪影。当天夜里,毛三少骑着摩托就冲下了西洋河,再也没有浮上来。
半仙姓夏,因为夏和瞎同音,我们就都省略了夏,整条坳坳街都喊他半仙。
2
坳坳街是三合城里唯一的老街了,总共也只有里把多路长。进街就是陡坡,出街又是坡,只不过下坡是石级,一麻溜四十来步石级直下西洋河,整条街就是一个马鞍的样子。
坳坳街文革时叫红卫河街,现在不喊红卫河了,叫书香街,因为坡顶有小城唯一的图书馆。但不管那些起街名的文化人怎样折腾,我们这些本地土著一直顽固地叫它坳坳街。街里八十年代出了个北大状元,学出名堂后就去了美利坚,虽说在那里发洋财,骨子里到底还是忘不了上坡下坡的日子,网名就是“坳坳街上人”。
半仙当年是坐船来的,在这个青条石彻成的码头上,半仙手执一根青皮竹竿,沿着这四十来步石级,一步一探地爬上了坳坳街。后来,当青皮竹竿不知不觉变成黄色的时候,半仙在坳坳街落了脚,再后来居然还买下了二奶奶屋后的半间偏房,虽说只是一个角落,但到底也成了坳坳街一员,出口也常是我们坳坳街如何如何。
半仙一直是在图书馆的大门口摆他的算命地摊,一张小板凳,一块纸牌子,纸牌不大,是捡来的瓦楞纸,外面蒙了一张大红染纸,五个隶书大字:算命看八字。这几个字是图书馆对面谢先生帮忙写的,半仙是个记情义的人,后来还特意给谢先生送了只老母鸡。刚开始的时候,半仙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可他不急不躁,一个人坐在板凳上,轻轻地吹口哨,吹我们本地的一首民歌,乡里妹子进城来,半仙吹得有滋有味,吹着吹着人就多起来了。
后来图书馆的白头发孔馆长就不乐意了,半仙一副圆墨片眼镜在图书馆前指点人生,孔馆长看过来看过去,就觉得这个实在有点滑稽,有一天孔馆长就蹲在他身边,小声地劝半仙换个地方,说我们这个图书馆也是个书香之地,你这些个封建迷信弄到这大雅之堂来了,是不是大煞风景呢。半仙低搭着脑壳,一边听一边唯唯喏喏点头,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待到孔馆长口干唇燥歇气的时候,才小声接了一句,说,孔叔啊我也是讨口饭吃,我一个瞎子没地去啊,这条街除了图书馆是公家的,那些私人门店哪个准我摆呢。大慈大悲的孔馆长最后直起身子,长叹一声,也是造孽人啊,罢了罢了。
我那时还是个待业青年,整天无事,满街闲逛,整条街上的大哥大姐,叔伯老姨都有事做,都没工夫搭理我,唯有半仙肯陪我说话,而且给我递一块钱一包的香烟抽,我说的越多,烟也递得越多,好像要我把整条街的事都讲给他听。
半仙好像不比我大多少,但看起来却比我江湖多了。有次我笑话他,我说,你在图书馆门前算命是有些荒唐,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就算你眼晴看不见,也要拉起你去游大街的。半仙拉住我的手,认真地说,老弟此言差矣!孔馆长说图书是塑造灵魂的,我这也是点化灵魂,都一样呢!半仙这话当时还真把我说得有点晕,心里头居然还傻不拉叽地跟着他的思路转,好一阵都没转过弯来,难不成这算命也成了崇高的事业哪?
我之所以和一个蹲在墙角的算命先生有如此交谊,最对口味的是他那吹口哨的绝活,每回都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当年有一个夏夜,我和半仙在码头纳凉,河水静静地流淌,远方隐约有捕鱼者,船上传来星星一样的灯火,我说半仙吹一首吧,半仙问吹什么呢,我说随便,半仙说那就吹《在那遥远的地方》吧……
月光下,半仙仰头向天,仿佛天上有人在看着他,那略带忧伤的音调,像水雾一样在河面飘荡,河面是这样的安静,半仙的口哨传得很远很远……
黑暗中有一个人影闻声而来,也是坳街上的老人,在文化馆写诗的古老师,他把半仙的口哨曲大大赞许了一番,大有高山流水之叹。后来据说古老师有几次想推荐半仙上文化馆的舞台,但弄一个算命瞎子上去,大家又都有些顾忌,节目审了几次,还是给刷了下来了。
我在网上百度过全世界的口哨曲,我觉得要是把半仙的口哨弄上去,说不定也是可以火一把的。
3
半仙的主顾大都是从乡下乘船进城的山民,我们坳坳街上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常找他,二奶奶就是一个,有一次家里的宝贝狗跑了也找半仙,半仙伸出三根指头就再无多言,第三天那狗果然自个又跑回来了,只是遍体泥巴,像从泥塘里捞出来一样,原来油菜花开了,二奶奶家的狗也动了春情,追着一条母狗,在乡下的油菜地里,放肆爱爱去了。二奶奶欢喜得不得了,立马给半仙打发了个大红包。二奶奶是个有福份的人,儿子柴干在京城里当干部,她手上那件墨绿色的玉镯就是柴干买的,椐说还是过去从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比金子还珍贵。
在二奶奶眼里,半仙是通灵的,她是从来也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因为半仙的失算而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倒是一直不太相信算命占卜之类,但我对半仙却还是有点敬佩,对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瞎子,靠着自己一张嘴就在我们坳坳街安了身,也不晓得他该是用了多少心思,更何况他口哨吹得那样好,我甚至想,若是眼睛好,半仙说不定也是个人尖。
我在微信上搞了一个“爱音乐”公众号,就一直想把半仙的口哨弄上去,只可惜他一听我说要录音就紧张了,嘴唇就像打了麻药一样,吹出来的声音干涩涩的,几乎不成调,我说不紧张,他也回不紧张,可就是紧张,我还真就弄不明白,一个双眼一抹黑的人,你又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我那天去找半仙就是想和他好好再沟通一番,我绕过二奶奶家的门面房,拐进旁边窄仄的小弄子,就到了二奶奶的屋子后面,紧挨着的就是半仙的两间平房。屋子还是二奶奶手里的老样子,尽管二奶奶当时也卖得烂便宜,但半仙也是拚了老底的,别说翻修,就是稍微装修一下这辈子怕也是很遥远的事。
在我的眼里,坳坳街上的日子好像总是平平静静的,对我而言,年复一年的也无非就是上坡下坡上班下班,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撞破了半仙的秘密,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而且,这事居然和二奶奶有关。
那天半仙家的门是虚掩的,我轻轻推开门,那一刹那间,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我分明看见半仙手捧一张报纸,紧凑在电灯泡下——他在看报纸!只是,与其说是看,还不如说是在闻更贴切,半仙的鼻子几乎要碰到报纸了,那情形又像是要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个抠出来,又一个个丟到嘴里嚼!
但,半仙的的确确是在使用他的那一双眼睛!
半仙终于发觉了我,慌慌忙忙把报纸一把藏到身后,有些恼怒地冲我说,你,你,你怎么……怎么也不敲门呢?
撞破了半仙这样的秘密,我当时其实也很尴尬。旁边半仙的老婆,那个被我们称为“袖珍哑姑”的女人,也似乎有些慌张,咿咿呀呀地叫着,拚命比划着,好像说他是闹着玩的,一个死瞎子又哪看得见什么东西。
多年以前我曾听半仙说过,他原本不是瞎子,十一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眼晴就再也看不见了。看今天这情形,至少还是看得见一点点光的。我不由悄悄瞥了一眼半仙身后的报纸,隐约觉得是份大报,一个算命的看这样的报纸,我就感到同他在图书馆前摆地摊一样,有点滑稽。
半仙最后还是把报纸放到了桌子上,要袖珍哑姑给我搬张板凳,自己又在桌子另一边坐下。我好像还是头一回看到半仙没戴墨镜,那深陷的眼眶里隐隐看到一点点光泽。三人一时都静坐无语,最后还是半仙先打破了寂静,说,都是二奶奶骂的。袖珍哑姑就在旁边指着前头蒋二奶奶的屋子,扳着指头比划二奶奶骂了半仙几回几回。
坳坳街是地头掉根针满街都听得见声响的,二奶奶骂半仙的事其实早已家喻户晓,原由是半仙替二奶奶的儿子柴干算命算拐了场,柴干到底还是摊上大事情。
柴干在北京的某个部里当处长,据说很有实权,下面的市长见他都要预约排队。从去年初开始,坳坳街里就传闻二奶奶的儿子要出事了,有人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中纪委的人都出动了。
传了几个月,柴干什么事也没有,去年冬天风风光光又回来了一趟,还请坳坳街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在坳街老酒楼吃了大餐,柴干说他是这些老人们看着长大的,见着他们就亲切!又说欢迎叔伯老姨来北京玩,来了北京一定要告诉他,他一定派车陪大家好好看一看紫禁城,看看皇帝老儿当年坐过的龙椅。
柴干临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二奶奶领着他到屋后又看望了半仙两口子,柴干问了两人的生活情况,还当即给一个领导打电话,说拜托家乡的父母官一件事,给半仙两口子的低保提一提。柴干的话管用,第二个月半仙两口子的低保就提了一个档次。
但就在上个月初,坳坳街有人从北京回来,说柴干真出事了,两口子都被检察院带走了,据说光从他家里搜出的现金都要用麻袋来装。那几天满条街的人,特别几个看着柴干长大的老人,一个个都惋惜不已。
半仙舍不得花钱,屋子里的小灯泡光线很弱,可此时他的脸色比这灯光还黯淡,他低声说,我对不起二奶奶的,对不起柴干。那次回来,柴干是找我看过命的,你想啊,一个正当火候,太阳正午一样的人,我哪能想到他会出事,我都还寻思着他日后能当部长呢……又说,二奶奶一家都是我的恩人,你看我这事做的,骂死也该啊!
前些日子我也曾听到有人传,说二奶奶领着柴干向半仙问运程,我一直都难以理喻,我们坳坳街那么有水平的人怎么也会相信半仙呢。我说过,我虽然与半仙有交情,但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能解救别人的人生,半仙至多也只是给那些被命运踹过来踢过去的人一点心理安慰而已。现在看来,当初柴干自己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找半仙怕也只是寻求一点安慰罢了。
半仙的内心却是如此的纠结,他抚摸着桌上的报纸,连声长叹,说他这一世英名也算是毁了,要是早关心关心些国家大事,也就不会把柴干的事给算岔了,政府反腐搞得这样凶,一个月捉一个,再怎么着也得给二奶奶提个醒啊!此时,半仙就好像课堂里犯了大错的孩子一样,眼睛都有些潮湿了……
这天晚上我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半仙提录口哨的事,离开的时候,倒是半仙主动说他一定会好好为我吹一曲,只是要我别把他看报纸的事再传出去……
4
半仙到底还是一诺千金,在我的录音棚里,他连续录了两首曲子,《斯卡布罗集市》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中一西,这一回半仙的嘴巴就像水坝开了闸一样,声音畅快而出,两首曲子都吹得十分完美,令人陶醉,还真有点天籁之音的感觉。
正如我预想的一样,我的公众号就因为半仙这两首口哨曲关注量大增,而他的曲子更是不到一周点击量就过了十万,留言也早已爆棚,最让人意外的是,陆陆续续的打赏金额居然过了五千元。我决定一分不少全部交给半仙,半仙怕是一辈子也没能一下挣这么多钱,我也很有几分成就感了,甚至想,兴许半仙哪一天也会像那些个草根名星一样,一夜就火上了天。
我很兴奋地来到半仙的房前,我一连喊他的名字,却没有一声回应,门冷冷地闭着,好像里面压根就没有人。
别喊了,瞎子走了。
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二奶奶已站在我的身后。二奶奶这些日子一下就老得不行了,凌乱的白发,刀削过一样的身子,好像吹口气就会倒下。
都走了,说是要回老家,不再来了。二奶奶似乎有些愧意,一边转身一边又说,我也是老了,也怪不得瞎子,我怎么就骂得那么凶呢……
想想半仙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此时我还真有些失落,沿着石级一步一步走向码头,江面空空荡荡,只见远方有一条船正愈行愈远,我几乎觉得半仙就在那条船上,可船却毫无牵挂地往前奔,一会儿就成了一个黑点。我不知道还能否再见到半仙,因为直到这会儿,我才突然发觉,这么多年了,我们居然谁也不知道半仙是从哪里来的,他似乎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坳坳街,又像空气一样,忽然一下,说消失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