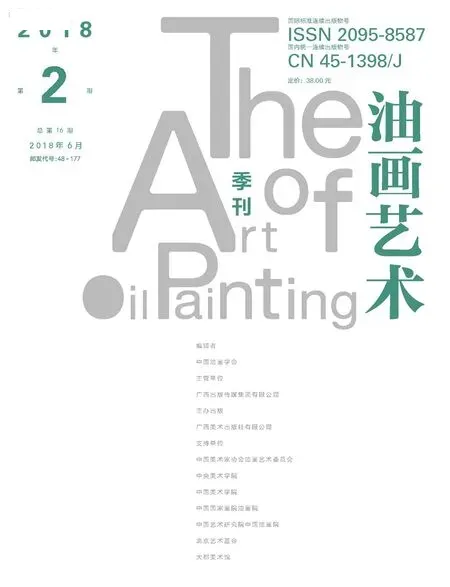三种背影,三个世界
——弗里德里希画中的背影图像分析
2018-09-03刘怿
刘怿
前言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德国艺术精神的象征。当学界长期讨论着弗里德里希的“悲剧风景”、宗教风景,还有民族主义反抗者身份的时候,一个颇为显著的绘画特征却被归到了附属位置,就是画中反复出现的“背影”图像。

图1 弗里德里希 《 海边修士》 油彩画布 110cm×171.5cm 1809年 柏林国立美术馆藏
背影人物在德语中叫“Rückenfigur”(背部人物),英语中将其称为“rear-view figure”(后视人物)。在以往材料中,人们常常提及这种现象,但也只限于只言片语。
国内对其画中背影大致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孤寂的崇高感,传达了画家“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之心” 。第二种则认为,画家将自己投射到背影身上,是为了体现人的渺小,“源于对自然崇拜的无限扩大” 。
英语学界更明确的将这界定为一种匠心独运。有的只将其视为一种原创的浪漫主义图示,是一种被长期忽略的重要贡献。有的则将其视作“第二层观察者”,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寂静的平衡,既不影响风景的主要地位,又暗示了外界对他的观看。
其实,除了以上角度,背影本身就包含了两个方向的指示:一个是背影面向的自然景观,也就是观者的对面,是画内的广阔世界;另一个,是与背影处在相同立场的人本身。这两方面的交互和对立关系便是贯穿其画作的最主要逻辑。
一. 三种背影——形式分析
弗里德里希现存的作品(包括他早年的练习稿、写生草稿以及成型的油画)共三百多幅,其中,风景画贯穿了他的绘画生涯始终。
1.广阔天地间的小人物(1807—1817年)
1807年,弗里德里希33岁时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油画风景创作,就是从这时开始,他的画中出现了第一种背影:辽远壮观的风景画中点缀着非常小的人影。1809年的《海边修士》[图1、2]就是个中代表。
此画以横向构图将画面分为陆、海、空三部分。陆地和海面成为一体,共占画面的四分之一,表现出天空和海陆之间的显著对比。这令本应处于远景的天空呈现扑面而来的压倒性气势,已不限于传统风景画依循的透视规则,而是更具浪漫主义的冲突感。
修士形象占比很小,但被设置在显眼的地方。他处在长边的三分之一处,为画面增添了灵气,又不影响整体的平稳。同时,这个小人构成了画中唯一的纵向单位,视觉上极小,却正好贯穿海陆,就像用针线将两个色块缝在一起时形成的线脚。这种精致的构图方法视觉效果突出,也很容易传达出人的渺小和自然的神圣伟大。这也正是众多研究者对这个人物的一致解读。
人物打扮成修士模样,面向大海和地平线,双手交握于胸前,呈微微颔首祈祷之态。有人关注到画家作画时的自我定位,“弗里德里希在这里把自己画成一位圣方济会修士,面对气象宏伟的大自然进行沉思和体验。” 画中的小人物就像他的替身,承载着个人情感。

图2 《海边修士局部》

图3 弗里德里希 《海边的月出》 油彩画布 135cm×170cm 1821年 冬宫博物馆
2.中等大小的多人背影(1817—1840年)
1817年,弗里德里希认识了他的妻子,从此,他的画里出现了对人物背影的重点描绘,并形成了两种模式。
其一是将人物稍稍放大,并增加人数,如《海边的月出》(图3)。作为有月亮的海景画,这幅作品集中概括了弗里德里希现阶段的创作构思。
海岸线设置在接近画面二分之一处。其海陆空的划分方法与《海边修士》非常类似,只不过陆地和海洋被大大加强,天空则被压缩,同时出现了“月亮”这个光源,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感。
近景的礁石和上方遮挡月色的云层边缘,较《海边修士》阶段的横向风景布局,增强了灵活性和韵律感。同时,对礁石、雾海的描绘也更加写实,增添了一种柔和的人文主义气质。
这幅画中有两组人物。第一组人物并排坐于近景的礁石上(图4),第二组则并肩站在近乎画面中心焦点位置的海岸线附近(图5)。这两组人物的姿态都曾频繁出现在弗里德里希的其他作品中,形成了模式。
而这一系列模式中,还有几点值得讨论。其一是人物两人一组的组合方式。这种双人并列的形式弗里德里希之前就画过。1819年《雪中的修道院废墟》(图6)中,引人注目的教堂废墟和四周林立的橡树之间,有一队走向废墟大门的僧侣,都是不起眼的漆黑小剪影(图7)。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两两一对紧挨着彼此。在这样的语境中,这种组合就无形中包含了他对人和人之关系的理解,或许与宗教语境中“兄弟”的概念有关。
其二是男女的区别。两名女性位于近景,为坐姿,两名男子站在稍远的海岸边,呈站姿。这显示出,男人和女人在弗里德里希的观念中似乎存在不同的精神意义。Werner Hofmann曾表达了对《吕根岛的白垩崖》(图8)一作中女性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女性形象完全独立于右边两个男人的世界观,将注意力指向了远景和近景中间的深渊,也就是关注着界限。Charles Sala也有类似的“中介说”,他提到弗里德里希在1810—1811年作的《雷森格比哥之晨》(图9)当中,山巅十字架的位置有两个很小的人物。一个女人在山顶一手抓住十字架,一手拉住一个想要爬上山顶的男人。在这里,她就充当了人(想要爬上山的男子)和神(十字架)之间的纽带。

图4 《海边的月初局部》

图5 《海边的月初局部》
第三点是人物始终立于边缘的站立位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弗里德里希的海景画大多描绘了礁石海岸,这令海水与海岸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因此,弗里德里希一般采取两种方法来处理人物:其一是将男子形象放在最深入海面的几块礁石上,礁石的大小通常只够一人站立;其二是以女子为主体,令她们坐在海滩中部最大的一块礁石上。但在这幅画中,两组“边界”人物同时出现了,如此一来,“人与自然的边界”在这幅画里也模糊了起来。
3.顶天立地的单人背影(1818—约1825年)
同一时期,弗里德里希的画中还演变出了另一种单人大型背影。这种作品非常少见,但每一幅都令人印象深刻,如1818年《雾海上的漫游者》图10。
这幅作品展现出人物的雄伟气质,在当时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了不同人的赞誉,更被当做一种民族气节的展示。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幅画还被用于宣传政治精神。这种效果一方面归功于人物的放大和雄伟的姿态,另一方面归功于自然景色的移位——自然从高高在上转移到了平视角度,甚至被踩在脚下。近景的岩石呈现出山峰的形状,远景的平川则与一般放在近景的草地或海岸边缘形状相似。这样的风景构图将陆地和天空的位置调换,表现出空旷辽阔、一马平川的感觉。
人物完全占据画面中心,风景也汇聚到背影人物的身上,而不似第一类作品那样吸引眼球。人物背影的放大和居中令人物姿态和服饰细节更容易被看清,人物也产生了一种意气风发之感,虽然这种情况实属偶然。
不过,仔细观察风景部分又会发现,他对风景的处理手法一点也没有简化,反而更加复杂和细腻,始终与人的气势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二、三个世界——精神蕴含
这三类背影图像的发展不但具有图示上的规律,还体现了弗里德里希三方面的体验和观念:第一类图像重点描绘自然景色,反映了他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第二类图像描绘了多人背影,当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了社会性,显示出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更复杂、更世俗的思考;第三类图像则是大幅背影“肖像”,表现了他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反思。
1.对神圣自然的敬畏
“自然”在风景画中本是风景的代名词,指的就是一草一木、人眼所见。但当它进入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中,含义就改变了。
1774年9月5日,弗里德里希出生于德国北方边界附近的格雷夫斯瓦德港市(Greifswald)。他的家庭信奉新教,他也受此影响,常常在画中表露出宗教虔诚。众所周知,新教在教义上已经不似改革前的严苛,它“因信称义”的主要理念更多的与人的心灵产生关系。同时,德国还存在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便是“泛神论”与新教的结合。
这个泛神论是德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就像我国从古至今都存在的鬼神思想一样。海涅在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说:“欧洲各民族的信仰,北部要比南部更多的具有泛神论的倾向,民族信仰的神秘和象征,关系到一种自然崇拜,人们崇拜着任何一种元素中不可思议的本质......基督教把这种看法颠倒过来,用一个充满魔鬼的自然代替了那个充满神灵的自然。”这种“阴暗的北方精神”在民族诗歌和口头传说中保存了下来,也形成了德国独特的审美性格。甚至德国的新教也是植根于这种泛神论,相信弗里德里希的家庭也会难以避免的受到它的影响。
正是这种信仰,令其画中的“自然”成为了“神圣”的载体。当弗里德里希说“任何自然现象都能成为艺术;在高贵的人眼中,上帝无处不在” 时,他不仅仅是在表达“心灵之眼” 的创作理念,也透露出心中对神圣自然的虔诚。

图6 弗里德里希 《雪中的修道院废墟》 油彩画布 121cm×170cm 1819年 被损毁

图7 《雪中的修道院废墟》 局部
2.对世俗关系的探索
第二阶段的背影作品增添了更多人文气息,这与他新一阶段的人生经历有关。
有身份的人物背影出现在弗里德里希事业稳定、成家立业的阶段。1816年12月4日,他被提名为德累斯顿美术学院院士,从此不必再为卖画担忧。1818年1月21日,他与小他19岁的卡罗琳·绷麦(Caroline Bommer)成婚。第二年秋天,他的女儿艾玛诞生了。从这阶段起,他的作品开始出现一些主要人物,色调也开始偏暖。
常有一些关于画中人物身份的指认,往往与弗里德里希作画当时的生活、交往有关。这说明,他不再只身一人陷于孤寂的信仰中,而是变得柔和丰富,进入了温馨的日常生活。但也有理论认为这些形象其实只含有象征意义,指代的其实是宗教意义上的“芸芸众生”。
关于人物身份,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1820年,著名的拿撒勒派历史画家彼得·冯·科内利乌斯(Peter von Cornelius)到弗里德里希德累斯顿的画室看望他之后,弗里德里希便在他稍后的作品《注视着月亮的两个男人》中将他画了出来,并附以这样的评论:‘他们因反动活动结缘。’弗里德里希用审查员的眼光定义这幅画,也是在讽刺当时的社会监管者的疑神疑鬼。” 这个事例一方面说明,画中的人物拥有确切身份,另一方面,也将他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定位展露无遗。
男性背影往往身着深色的斗篷或中长袍,头上戴着贝雷帽,这些都是德国传统服饰,而对掌权的外来入侵者而言,这是“反动”的标志。因此,此类背影象征的人物似乎就映射出弗里德里希本人的政治立场。
此外,人物背影的大小总是相等,似乎是在有意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同样大小的背影带给人一种平等、相类的联想,也反映了他潜意识中对自己和他人关系的认识。
平等的观念可能源自画家年少时的经历。在弗里德里希13岁的时候,他和兄弟们到冰封的波罗的海溜冰,从冰面的洞口掉入了水中,他的兄弟克里斯多夫(Johann Christoffer)为救他而死。20世纪美国精神分析理论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理论表明,1—18岁是一个人的“青春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的自我同一性”,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清楚自己的社会角色......” 弗里德里希在13岁——人格养成的初期,有了一次与死亡面对面的经历,很可能令他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初步认识,他站在幸存者的角度,就会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人和人在生命本质上的等价。正因如此,弗里德里希在绘画中从未有过对社会等级、阶层之类的丝毫暗示,而是更多的关注人和神圣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才是最有力量的,是永恒的、真理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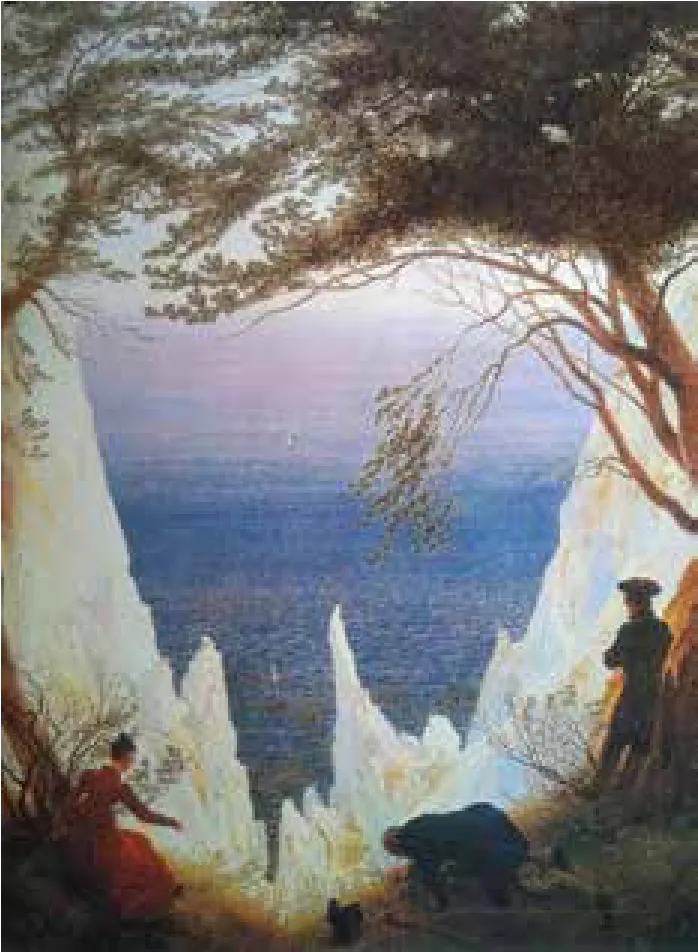
图8 弗里德里希 《吕根岛的白垩崖》油彩画布 90.5cm×71cm 1818—1820年奥斯卡·莱因哈特基金会美术馆藏

图9 弗里德里希 《雷森格比哥之晨》 油彩画布 108cm×170cm 1810-1811年 柏林国立美术馆藏
3.对“我之为我”的表达
第三种背影在氛围上与前两种都不同,人物占据主要的地位,令作品都有些脱离了风景画的规则。
面对这种大型背影,观者很容易被吸引,进而思考“他究竟在想什么”,从而形成一种共情。同样的,对画家来说,当他创造这个主要形象时,也将自己的心情投射到这个形象的身上。由于这个人物没有正脸,就避免了观者将情感转移到某个特定人物上,而是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人类个体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物背影不是任何人,而是画家的精神。
法国巴努的《背影》一书专门对艺术中的“背影”进行了分析:“背影之姿有着三种不同的原因:一为对世事的厌恶,二为遁入自我的世界,三为对彼世的渴望......”
将这三种原因与弗里德里希对应发现,第三种解读——对彼世的渴望,从宗教虔诚的角度来说,很可能一度准确反映出了他的心理状态。不过这种向往不是盲目的宗教虔诚,而是包含了一种理性客观的理解。
弗里德里希的艺术被划作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当时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念相合。
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重视个人精神,关注“自我”。费希特的“自我”理论在当时非常有名,他认为“自我在自我之中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 当中提到,外界的“非我”是由“自我”设定,“自我”也是间接由“自我”设定。这就产生了一对概念——“实践自我”和“理论自我”,与弗里德里希背影的表达逻辑非常类似。
这两个概念是“自我”生效过程中出现的两部分,“自我”只有在与“非我”的互动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力量,如果将这种确证的过程分解开,就像“照镜子”的过程一样。“非我”是一面镜子,“实践自我”是发出动作者,向“非我”作出指示,而“理论自我”是得到确证者,是“非我”倒映回来,印证的那个自我。因此,“理论自我”才是“我”本身,“实践自我”则是为了找到“理论自我”而发出动作的行动部分。
将这对概念代入弗里德里希的画中发现,他的作品中正巧出现了这样两个“我”,画外的“我”和画中的“我”。画外的是画家本人,也可能是任何一位观者,他面向画内发出一个作画或观看的动作,就像“实践自我”那样。画家在画中描绘的是自然,作为一个外物,成为“非我”。接下来,当自然反馈回画家一个本质时,画家选择将这个他想要确证、想要找寻的“本质自我”画在画里,与自然摆在一起,但与画家面对同样的方向,暗示着一种统一。这样,一切就在这艺术过程中形成了闭环。
画中有个“我”,他是“我”的精神,和我站在同样的立场,他就是“自我”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精神本身。这样,画家的画作就成了真正的“心灵的创作”。
费希特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巨大,但弗里德里希究竟在何种层面上知晓或明白他的理论还不得而知。不过从结果上看,他们的理念的确实现了奇妙的吻合。

图10 弗里德里希 《雾海上的漫游者》油彩画布 94.8cm×74.8cm 1818年 汉堡艺术馆藏
结语
弗里德里希的三类背影反映出他对神圣自然的崇敬与向往,反映出他对社会和他人的认识,还反映出他对自我心理和哲学观念层面上的思考。这些认识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不断演化,展现出其自我意识的改变。
而当弗里德里希把背影置于自然中时,自然的神圣地位始终未变。人物站在边缘,与自然保持距离,这是不可僭越的底线。这底线的两边是有限的人和无限的神圣境界。一个始终如一的背影便是对此立场最坚定的传达。
[ 注释 ]
1. 徐沛君:《德国绘画的民族性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1年。
2. 赵世杰:《极地之境——弗里德里希绘画中个人情感对国家意志的服从》,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艺术学院,2016年。
3. 化铉:《弗里德里希绘画中的宗教意象与象征表现》,《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0-83页。
4. Werner Hofmann∶Caspar David Friedrich,London∶Thames & Hudson Ltd,2000,P17.
5. 原文:...that every natural phenomenon can become art and that the noble human being finds God in everything.
6.“ 心灵之眼(spiritual eye)”的概念,主张充分发挥心灵的能动作用,延续了康德哲学的先验唯心论。在这当中,人的主观意识得到了极大重视,甚至可以说是被赋予了本源性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纯粹的人的主观意识的创造——艺术创造,本质上就必然是心灵的创造。后来的浪漫主义艺术家都以实际行动追求着这种心灵的创造。
7. Werner Hofmann∶Caspar David Friedrich,London∶Thames & Hudson Ltd,2000,P88.
8. 张海音主编《医学心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第50页。
9. 费希特著:《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2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