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颜色
2018-08-30陈大雷
文/陈大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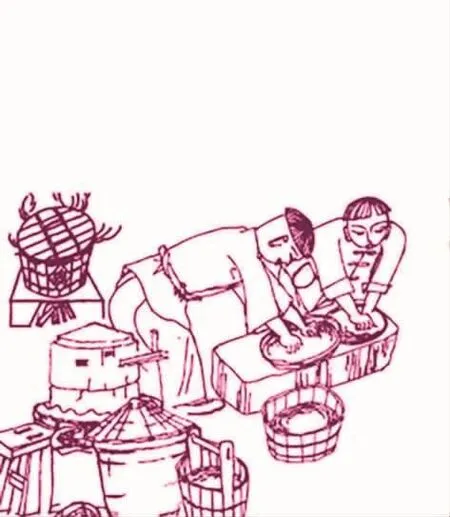
每每想到端午,总会有很多场景印象,在时空中叠印、翻转、跳动着,从心里争先恐后地拥挤着,喷涌着,但每每到了心口就留在那里,梗咽着,只剩下丝丝缕缕的五彩斑斓,像端午的五彩绳,一路萦绕到脑海里。
最早对端午节的记忆是兴高采烈的五彩斑斓。
那是在我五岁前还没有搬家的老房子,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我很困,眼睛酸涩地往一起粘着,但是小孩子对热闹那种天然的向往让我挺着不忍睡去。我枕着手臂趴在炕席上,视线沿着炕席的平面延伸出去,远远地看到妈妈软软地坐在凳子上,一面包着粽子,一面教两个姐姐缝荷包。我几乎能闻到妈妈身上那好闻的香气,闻到粽子的香甜,让我在安心中舒适得更困了。妈妈和姐姐们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清,一派时断时续的嗡嗡声。我的视线在酸涩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短,最后的印象定格在我眼前炕席上做好的几个荷包和我手腕上的五彩线上。荷包是用妈妈给我们缝补衣服剩下的碎布拼出来的,红的、黑的、粉的、紫的,还有花点的,有正方形的,长方形的,还有很多三角形的,斑驳鲜艳的一小堆,感觉也是兴高采烈的一小群,我手腕上的五彩线都是妈妈自己搓出来的,还拴着一把小笤帚,笤帚把用红线缠着。妈妈说这个可以扫掉我们的病,看着我胖乎乎的手腕上这小笤帚我想,挺厉害的。
接下来回忆出端午的颜色是青蓝色。
我长大了,大概是上小学的年龄吧,每次在端午节那天总是很早很早就被爸爸叫起床,带我出去上山。打开房门,天还没太亮,影影绰绰的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夜色和晨雾的清凉,但是看不到雾。拉开挺凉的门栓,走到大街上,就能看到雾了,街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群一伙地一起走在青蓝色的雾里,都没有表情的疾步走着。爸爸弯下腰,用他挺大的手给我扣上衣襟最上面的那粒小小的扣子,然后牵起我的手,一起汇入疾步快走的人流中。在人流中,身前身后都是不说话疾步快走的人,前后看不出很远,只看着前面人摆动着的脊背。总是记得在大桥上,看着笼罩在青蓝色晨雾中的河面,和远处那青蓝色没有透亮的天。记忆中始终没有声音,都是青蓝色的天和雾。从山上采好艾蒿回来后,爸爸一准儿会带我到河边,用艾蒿蘸着河水洗脸。艾蒿的香气和河水混成一团的清凉,感觉这才混沌的睡意里清醒过来,据说这也是为了去病。
再后来是急匆匆的绿色和褐色。
再大一些,依旧是爸爸天不亮就喊我起床,我很配合地一骨碌爬起来,到爸爸一直领我去的山上采回大把的艾蒿,系上前一天买来的五彩葫芦,再急匆匆骑自行车给哥哥、姐姐挂在家门的上方。等回到家,桌上总是摆好了大堆的粽子和鸡蛋,桌对面就是爸爸妈妈的笑脸。心急地剥开褐色荷叶包着的粽子,里面是糯糯软软的糯米,尖儿上是一颗紫红鲜亮的大枣。当然,旁边一定有一碟白糖,这是粽子的绝配,也是多年的标配了。同样标配的就是一盆满满的鸡蛋,挑一个最硬的,把其他鸡蛋一一击败,然后心满意足地剥鸡蛋壳儿,分给每一个人,把最硬的那个鸡蛋大王揣进兜里,在上学的路上继续与同学们的鸡蛋征战。
工作以后,还会在每一个端午天没太亮的固定时间去采艾蒿回来,只是哥哥姐姐家都自己去采了,不再需要我去插艾蒿,所以只回到爸爸妈妈家,急匆匆插上,急匆匆吃饭,然后急匆匆上班。虽然流程都是一样的,桌上的粽子、鸡蛋和白糖依旧,就像爸爸妈妈的笑脸一样从没缺席,但是回忆里所有的颜色都暗淡下来,没了那种鲜亮。
今年的端午是无色的。
在妈妈走了11年以后,两个月前,爸爸和妈妈去“汇合”了,这是从小到大第一个在自己家单独过的端午,没人喊我起床,没有粽子,没有白糖,也没有爸爸,尽管今年的父亲节和端午节紧挨着。
一个人依旧习惯地在那个天没太亮的固定时间里走出家门。路上、山里、河边,都是一家家甚至三代人手拉手的身影,嬉笑着,呼唤着,女人甜软的昵音,男人深沉的膛音,孩子清脆的童音,揉在一起热闹得很。人们拿着采回来的艾蒿去河边洗脸,河水也哗哗得很快活。我看得心活,也想打起精神来凑个热闹采采艾蒿蹲下来洗个脸,可是心窝忽然有点儿痛,堵着的那种,让我伸不出手,也不想再弯腰。
回来的路上才发现,今年的端午回忆是有声音的,但是没有颜色。
回到家,煮了一大盆鸡蛋,平平淡淡地和儿子一起吃鸡蛋,当然,先和儿子用鸡蛋对战了一场,最终也当然地让儿子赢了。
我也是父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