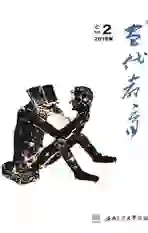浅谈朱自清散文的“三融特点”
2018-08-20张正娥
张正娥
在文学领域,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作者都注重在作品中倾注自己的真实情感。散文也不例外,它也是一种长于抒情的文学体裁。正如无周文的《画出抒情的波澜》一文中所说:“好的散文是以情动人,摄人心魄的。因此,抒情美,是散文艺术美的因素之一。”朱自清的文章之美,也是与他的抒情艺术分不开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铨赋》里指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就是说,情有所感,必有所寄;意有所触,必有所托。浓郁的情感必熔铸于人、事、物中,否则,情无所托,势必所为无病的呻吟和空洞的干嚎。朱自清散文作品的抒情之所以能沁人心脾,是因为他将抒情与事、景、理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的一番特色。
(1)情事交融,即把抒情与叙事相融合。在叙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使他的文章具有一定含蓄的美。
朱自清的叙事抒情散文,往往偏重于叙写生活琐事、儿女情长。如1936年出版的散文集《你我》中有回忆儿时婚姻的《择偶记》、有悼念前妻的《给网妇》、以及《看花》《楂柘寺 戒坛寺》《南京》,还有收在《背景》集中的《儿女》《怀魏握青君》等,内容侧重写儿女情长、友朋之谊,而且写的都是个人圈子里的身边琐事。
虽然都是些描写个人身边琐事的文章,但在读这些作品时,会被这些隐藏在生活琐事中的情感所打動,会感到有股震撼人心的抒情力量。这是因为,朱自清在叙事中抒发的是内心的真实情感,以真情来打动读者,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有很多文艺理论家都很重视真情的力量。例如,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朱自清的这些叙事抒情作品,不仅叙写真事,而且抒发真情,所以写得情意绵绵,娓娓动人《给亡妇》就是一篇至情之作。一九二九年,朱自清先生的前妻钟兼女士病逝于扬州家中,先生写这篇文章来悼念亡妻。文章采用第二人称“你”直呼亡妇,抒写了他对亡妇长远忆念的心曲,倾诉了他对亡妇的最珍贵的感情,在一片凄婉的倾诉中,让人看到一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妇女被生活中种种艰难折磨至死的劳累的一生。作者列叙亡妇生前的琐事,赞美她为妻为母的完美人格。然而,作者并没有回避夫妇间必然会有的一些小龃龉,并没有始终把夫妇感情表现得十分融洽;相反,他写了夫妇关系中某些小矛盾的存在到和处的过程,以此来表现相互间的深情,这样反而使人感到更真实。作者的悼念之情,被表达得朴素自然,没有半句雕琢粉饰之句,一切均是平实而诚挚的诉说,真是一字一泪,读着令人不能自己。
作者在叙事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将抒情与叙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文章事真情浓,是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分不开的。朱自清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重要成员,文学研究会那种“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主张认真地对待人生,深入地观察事物,切实地感受眼前的生活。“丢去玄言,专崇实际”,不要因为“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倡“写实”的文学。他在《文艺的真实性》一文中说:“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这些说明他的散文创作是自觉地在现实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而且特别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因此,在那些偏重于叙写个人生活琐事的散文中,他运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在散文中抒写自己的真切感受。正如他谈选材时所说的那样:“作者将他情意化了,比人更深一层,便另有一番声色。”通过娓娓的叙事,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情意化”地抒发自己的真实感,以此获得另一番抒情的“声色”。
《背景》,是朱自清满誉文坛的代表作,叙写“我”和父亲为祖母去世而奔丧回家,“我”要到北京读书,恰好和父亲同行至南京。“我”渡江到浦口,准备上车北去。父亲是再三嘱咐一个熟识的茶房送“我”,后又怕茶房办事不妥贴,又亲自送“我”上车。临行时,父亲在“变卖典质”“家中光景很是惨淡”的情景下,又特地为“我”买几个橘子来。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和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路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那么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向上缩;她肥胖的身子向右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经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
作品以父亲的“背影”作为艺术抒情的泉口,出远而近,铺陈叙事,字字句句融注了惦念父亲的感情和无以孝敬的痛惜之情,字真意切,荡胸涤肠,袒露出感情的真挚。作者谈这篇散文的写作动因时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来信里那句话,即‘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中的末一句。当时读了父亲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作者将自己的真挚情感与叙事结合起来,而是简单的凑合,而是“情”与“事”的交融,是通过一系列的典型生活细节,抒写自己的表情。因此,在他的笔下,生活的细节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感人的抒情细节,父亲买桔子的蹒跚背影(《背影》);亡妇“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给亡妇》);痛打阿九之后妻的一场哭诉(《儿女》);叶圣陶不与人争辩那句“这个弄不大清楚了”的和易宽容的笑语(《我所见的叶圣陶》)等,这些细节不加粉饰,不着意渲染,就有很强的抒情魅力。
抒情的生命在于真实。作者抒发的感情愈真实,就愈能见其真挚的美。但是这些真挚的感情也要借助一定的抒情方式,才能更好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能产生共鸣,以更好地体味这真挚的感情。朱自清偏重借事抒情的散文,感情委婉、细腻、缠遥、真切。一方面,是他取材于身边真实的事,而且抒发的是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了抒情方式的含蓄蕴藉。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感情好像蒙上一层轻钞,是那么淡淡的,然而又是那么深深地侵袭着读者的心。用他自己作品里的话来形容,就“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塘月色》)。虽然并不奔放热烈,但有“细雨湿衣看不见”的那种味道。当感情到了强烈的时候,他仍然采用很节制的办法来表现它,令人在平淡舒缓之中,慢慢地领略出隽永的意味。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里,他就说过:“原是随随便便地书来,不露咬牙切齿的样子,便是更加亲切,不知不觉将人招了入内。”这些话,正体现了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艺术特色。例如前面提到的《给亡妇》《背影》等,都是通过娓娓的叙事来流露真情,让人慢慢地领会其中的意味。
归根结底,在朱自清的叙事抒情作品中他运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取材于身边真实的生活琐事,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并注意用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把这些情感传达给读者,使其文章具有含蓄的美,即在叙事实之中,让感情通过事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并给自己的经验、印象及知识去理解和补充,使人意味无穷。这种感情不露声色地自然流露,使其文章具有了含蓄的美。
(2)情景交融,即把抒情与景物描写结合,做到景中藏情、情浓景真,从而追求一种绘画的美。
在朱自清的散文中,偏重于借景抒情的作品占较大的比重,如《荷塘月色》《浆声灯影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组篇〉《看花》《南京》《覃柘寺戒坛寺》《蒙自杂记》,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朱自清善于用重彩画笔描绘各种风景画、风情画。因此,人们常说朱自清写景的散文有“工笔画”那样的意境。这就是说朱自清善于沟通精雕细刻、细针密线的描绘,把景物细腻传神地表现出来,使人读后有特别真切的感受,好像亲历其地亲见其景一样。
关于这点,朱自清自己在《“山野掇拾”》一文中曾有过说明。他说作家应“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又说作家观察生活,“于每事每物,必要剥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绳之辨,总之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还说作家要于人们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平常身历之境,也会有惊异之感。“这些说明朱自清在写景散文中,很注意对景物的描写,不仅要逼真、细腻,而且要新颖,重视形似”。在古代,作家们就强调形似。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有这样一段话:“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这里指出的“形”是晋、南北朝的作家们追求的目标。朱自清传承“窥……钻……”。强调形似,在写景抒情散文中,采用了工笔细描的方法,淋漓尽致志地把景物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荷塘月色》就是一篇“工笔画”特点最显著的一篇写景抒情散文。在文中,作者在表现月色下的荷塘和塘上的月色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时候,还进一步作了更精细的分解剖析。把这两个组成部分再分解剖析成许多更小的部分,然后逐一细写,并且从景物观赏者的视觉(“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嗅觉(“微风吹过处,送来缕缕清香”)、听觉(“仿佛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以及景物的静态、动态等角度,写现它们的种种性状,从而把景物表现得格外细腻。
朱自清写的景物,在追求逼真、细腻的过程中,又使这些景物是脱俗的、新颖的。例如,瀑布、河水、明月、杨柳、春花、夏荷等,都是前人再三再四写过的,但是到了他的手里,由于他注意在人们“忽略的地方”和觉得“平常”的地方进行了深细而独到的观察,并作“加倍地描写”,因而使人觉得满新隽永,不雷同不落套。《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的是作者游南京秦淮河所见的景色,其中的水色、天光、月态、灯彩、人影、船形、树姿、琴声、歌声等都是人们常见而又易于忽略的事物,但作者善于把它们都错杂起来作“加倍”的描写,因此写得特别细腻,精密确切地写出了当时秦淮河上那一种洒月交辉、画舫纵横、笙歌彻夜的景象。
在读朱自清散文时,我们不只是看到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幅描写得逼真、细腻的景物,而且我们也从这些景物中感受到了作者绵密深厚的情致。清·宋大樽的《茗香诗论》中说:“有形无神者无论已,形神离合之故云何?陶贞自有言:凡质象所细,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人;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这段话强调了“形”与“神”相结合,才能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否则,“形”“神”若离,则对现实是歪曲的反映。“形”与“神”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缺一不可。而朱自清的写景散文重形式,实是为了“传神”,即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具、情景交融,使读者在读他的写景散文时,既能亲临其景,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那浓浓的情意。例如在《荷塘月色》这篇写景抒情散文里,朱自清先诉说自己不宁的心境,然后描写一个宁静的与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潔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这种借景抒情的名篇还有很多,如《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南京》《春》等,都抒发了作者不同的内心感受。
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一样,朱自清重视以形传神的写景抒情散文,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例如,他在《绿》中是这样描绘梅雨潭的:“……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妄想呀。
她松松的皱结衣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曾经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淡了,我也曾见过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神秘的‘绿壁,从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
梅雨潭的绿水,本不足为奇,但在朱自清的笔下,这绿水是一块绿色翡翠、绿色的玉,而且有着生命的可爱的女儿那种处女般的风韵,迷醉到使人要伸出双手抱她,掬她入口。作者通过比较、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构成了梅雨潭特有的优美绮丽、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境界,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真可谓是情浓景真,意境融融。
朱自清在《山野掇拾》里评孙福熙的散文时说:“文中有画”,“作者便是以文字作画”;并进一步要求:“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歌中还有哲学。”他的写景散文又何尝不是呢?他的诸多著名的写景名篇中,都用优美的文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图景,并借以寄托内心的情感。为了做到情浓景真、以形传神,作者采用了工笔的方法进行描写,把景物描写得逼真细腻,因而他的散文具有一种绘画的美。
朱自清抒情的特色其三是情理相融,即将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追求一种“理趣”的美。
所谓“理趣”,就是诗的意境与议论结合产生的一种抒情美。朱自清有些抒情散文议论因素较多,或者竟可以说是抒情性的议论,因为这些议论是用带强烈的感情色彩语言说出来的,而且是和形象描写、比喻等手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这样的作品非常感人,和一般说理文的议论不同。朱自清在赞扬鲁迅的染感时说:“这是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还有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继续了韩柳杂说的‘理趣美,又偏受鲁迅杂文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叙事中有论理的美,在论理中有抒情的美。”他早期的杂感,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写了一个被兄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卖出的小女孩,表现了自己对那个小女孩的同情,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作者笔下有强烈的感情,但这不在于多几句感叹的口号,而在于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象,通过抒情的议论,对这被卖的小女孩未来的悲惨命运作了一层又一层触目惊心的推想与剖析。他痛苦地指出:“女儿本身姓‘碰,由她去碰罢了!但可知的运命决不加惠于她!”那么命运将加给她什么呢?作者议论说:首先是卖给人家“做丫头”,拶榨她的劳力,接着是“卖给人家做小妾”,或“被卖在妓院里”,做有钱人发泄曾欲的工具,“用藤条打”,“用针刺”,“督责她承欢卖笑”,给她吃“残羹冷饭”,逼她“打熬着不得睡觉”“终于有了一身毒疮!”……通过以上种种推理性的议论,表现了旧时代千千万万穷苦女孩子的命运和“生命市场”上的形形色色。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生命太贱了!生命太贱了!”對被摧残的生命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又向社会提出了严正的责问:“这是谁之罪呢?”把感情引导到对社会问题更深刻的思考方面去。此外,还有《航船中的文明》《旅行杂记》《执政府大屠杀记》等,缘事而论,将叙事和议论结合起来,把矛头指向旧的社会制度、社会风习和反动的军阀政府,幽默诙谐中藏有批判的锋芒。他后期的杂感如《这一天》《文艺节引以为纪念》《论不满现状》《新中国在望中》等,满腔的诗情常常是通过热情的呼唤和痛快的议论表现出来的。
《这一天》是朱自清参加“七·七”抗战两周年的纪念之后写的,文章写道:“从两周年这一天起,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故抗战,我们也能迅速地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失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作者为新中国的诞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引颈展望、仰啸高歌。对祖国深沉的爱恋,对光明的热烈憧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之恨,都是通过融情入理的议论来书写的,以情驭里,情理俱美。这种抒情的“理趣“美,是作者”理智的结晶,更是作者反帝国主义的热情喷薄和升华的结晶。
总之,朱自清的抒情是与叙事、景物描写文化交织起来的,因作品立意和题材的不同,而显示出多姿的抒情美、含蓄美、绘画美、“理趣“美。偏重于叙事的抒情作品则见委婉真切,偏重于描写景物篇章则见细致绮丽,偏重于议论的杂感则相有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