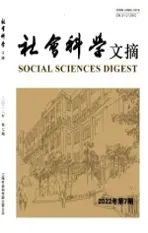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
2018-08-15
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道德的纯粹和技巧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风格上通常能创造一种新的审美范型。杜甫诗歌以对“老”的称说和追求,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真正成就了一种诗歌美学。
“老”是传统诗学中很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据裴斐统计也是杜诗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字,共用过374次。自杜甫以后,经宋代诗歌批评广泛运用,终于在明人杨慎手中得到理论总结,后来成为清代流行的诗美概念,美学意涵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成熟、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上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四个方面。杜甫因对“老”的标举及相应的成就而被视为实践这种美学品格的成功典范,吸引后代批评家由这一角度审视其作品,由“老”的正负两面价值对其晚年创作做出不同评价。
“老”与杜甫的诗歌批评
杜甫喜欢在诗中述说自己的写作经验,也喜欢评价古人或友人的创作,且评论话语非常多样。稍微列举一下杜诗中涉及诗歌写作的诗句,数量之多让人惊讶。尤其是《贻阮隐居》“清诗近道要”,《长吟》“赋诗新句稳”,《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等句,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的美学趣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老”相关的诗学话语。
天宝十载(751年),杜甫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称赞郑诗“思瓢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涉及构思、声律、结构及完成度四个方面的评价。五年后他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中直接用“老”来称赞薛华写作的歌辞:“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处“老”所称道的“风格”并不同于当今文学理论所说的风格,而近于指称作品的整体风貌。参照“何刘”两句看,让人感觉“老”与其说意味着一种风格倾向,还不如说与完成度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老”显然是“老成”的省言,这从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可以得到印证——在早年的《春日忆李白》中,杜甫用“清新庾开府”来评价庾信,到晚年写作《戏为六绝句》时,却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意谓庾信的写作在晚年达到成熟的境地。庾信是杜甫最为钦敬的前辈诗人,诗中提到庾信共八次,就《咏怀古迹》“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来看,晚年提到庾信地方,都与自己的遭遇相关。涉及“对不幸的历史时代的整体性回顾”和“对这种时代里个人生命的落空的深切哀感”。不过相比这精神史的隔空对话,后人更为注意的是杜甫对庾信诗歌老境之美的关注和标举。
由生命体验到美学趣味
“老”原是古代汉语中很古老的形容词,见于殷周甲骨卜辞已知56个形容词之中。本义是年老,它之所以能由衰老之老衍生出后来若干正价的审美义项,是因为与“成”组成一个复合词“老成”,老而有成德改变了老而衰亡的负面涵义,使老与意味着成熟和完成的正面涵义联系起来,为日后许多正价义项的衍生奠定了基础。
“老”进入诗文评的过程尚不清楚,唐初孙过庭《书谱》已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著名说法,传为李白所书的《题上阳台》又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之语,可见它是唐人常使用的批评术语。“凌云健笔意纵横”句具体指出了庾信晚年作品所显示的雄健风格和挥洒自如的笔力,这两点已触及“老”作为美学概念的核心意涵,意味着成熟和圆满,成为炉火纯青的同义词。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老”的美学意蕴加以开掘和深化,但主要是在宋代文学的语境中展开,未深究杜甫诗歌创作和批评所起的奠基作用,以致未能从源头上厘清“老”的诗歌美学的由来。
以“老”为生命晚境的原始涵义,使“老”的审美知觉一开始就与文学写作的阶段性联系在一起。古典文论向来将文运比拟为自然运化,诗歌写作的历程在人们心目中也与生命周期一样,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意谓着“老”首先与对生命晚境的一种肯定性评价相关。杜甫对生命衰老的意识,除了常人共有的对自身的哀叹、对社会的悲观外,还表现出一种观照自然界和外物特有的积极情怀与乐观的审美态度。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使他对人生晚境的描写,不同于萨义德(E.W.Said)所阐释的“晚期风格”,而接近于罗兰·巴特(R.Barthes)曾描述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意谓“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杜甫晚年的写作发生日趋率意和放任的变化,他的生命体验以及相应的美学反思在短时期内得到集中的表达,由此给他的写作烙上最深刻的印迹。这种变化无法在诗学层面上解释清楚,必须放到美学的层面上加以思考。
杜甫写作的“老”境
清代诗人张谦宜曾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这意味着“老”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境界,乃是自然养成的,来不得模拟和追求。杜甫写作的“老”境很大程度上与他自己对“老”的体验相联系。
杜甫对“老”的感觉似乎开始得较早。在乾元元年(758年)春所作《曲江二首》中,对生命极限的意识表明衰老的感觉已占据他生命体验的中心。但他对衰老真正深刻的体验还是在漂泊三年后的同谷时期开始清晰起来的。垂老无成的迟暮感、孤独无伴的寂寥感、前程未卜的悽惶感,灰心任命的绝望感乃至“将老斯游最”的窃幸,无不表明他正经历一个心理上的更年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偶尔自称的“杜陵野老”,变成老夫、老农、老渔等,频繁出现在诗中,集中地显示出理想、自信和豪迈之气黯然销歇后自我意识的变化,使杜甫真正进入那个“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的衰迈老诗人的角色。
秦州之行正是杜甫对政治前途感到绝望、离开政治中心的开始。随着战事结束后蜀中形势的翻覆、朝中故人的凋丧,归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从而意识到文学不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它也是对贫寒人生的一种特殊回报。当然,随着对诗歌的浸润愈深,杜甫也愈加深切地感觉到,以文章名世其实并不比建立事功更容易,这或许是更为艰难的一条路。无论是不是这种警觉促使他对诗歌写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事实表明从秦蜀行程开始,他的创作便进入了一个异常旺盛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蜕变的时期。仅夔州两年间,杜甫就写作了四百多首诗,占了全集的三分之一,足见秦蜀之行后是他不同寻常的一个创作阶段,也就是杜诗的老境。
“老”境的两个层面
“老”境首先意味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居成都时期,有一组以树木为题材的咏物之作(《病柏》《枯椶》《病桔》《枯楠》),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奇异之处在于都是枯病之身。其中包含的对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省思,涉及王朝没落、君主失德、民生凋敝和个人前途黯淡诸多重大主题。我认为这组咏树之作呈现了杜甫晚年思想上的若干重要变化,从中不难体会杜甫心理上正经历的从国计民生到个人命运的全面的幻灭感。
与这种精神层面的深刻化相反,杜甫的写作状态却一改往日的谨慎与自律,似乎进入一种率意自适的写作状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有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漫与”二字被后人视为关涉杜甫晚年写作态度的关键词。随着成都草堂落成,居处暂定而精神放松,一种随意的写作状态也同时到来,它们一方面拓展了作品的取材范围,更为深入日常生活,表现为无事无物不可入诗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突破诗型的固定格式,时时构作创体。杜甫晚年的诸多成就固然源于此,诸多创变甚至诸多缺陷也莫不源于此。
“老”的发现与表现
杜甫不仅是诗歌美学中“老”境的发现者,同时也是身体力行的创造者。他晚年写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持续不断的反省相伴。而对庾信文学老成之美的发现和表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自我彰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凌云健笔意纵横”的重心已由“健笔”向“意纵横”的方向转移。
瘦硬劲健是“老”最醒目的审美意涵。他人或许要到晚境才能企及这种境界,但杜甫在中年即已达成,他晚境的创作则走向了自然浑成的方向。多用虚字造成口语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与语言上的这种朴实自然相应的是诗体操作上的任性率意,所谓“意纵横”是也。杜甫晚年的写作强烈地表现出“老”所意味的自由适意的写作态度,率意但绝不是草率,因为它是另一种成熟的表现和证明。
杜甫评价庾信的“老更成”本义是成熟,即完成度高。他本人晚年有《长吟》曰:“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稳”也是意味着技巧成熟的概念。这是杜甫晚年最为人推重的特点。尤其是五七言律诗的工稳浑成,达到了唐诗艺术的顶峰。杜甫晚年自述诗学心得,有“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夫子自道,论者谓多见于属对之工,其实声律运用之妙,尤臻炉火纯青的境地。清代诗评家指出的杜甫七律出句尾字上去入交替使用,自是用心细密;而多做吴体与喜用拗句,也不能不说是出手纯熟。拗体最终成为杜甫七律的重要特征,为后人揣摩、效法,足见杜甫对拗体的探索已达成熟而足以垂范的境地。杜甫晚年的写作,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老”所含容的美学境界,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成熟、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上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等方面。后人眼中的杜甫及学杜所着眼之处,也不外乎就是这些特点。
“老”眼观杜诗
杜甫的“老”因为出自本人的议论,启发后人从这一角度去品味其自身创作的美学意蕴。自从宋代“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杜诗就被与“老”相关的批评话语所笼罩。首先是黄庭坚从完成度的意义上评价杜诗晚境极绚烂而归于平淡、天然浑成的境界,明代陆时雍又从内容上肯定“老杜发秦川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清初申涵光评《江村》,就杜诗涉及家庭生活琐事而指出杜甫晚年之由奇归真、善于体味日常生活的平淡之美。翁方纲《石洲诗话》专门辨析“漫与”与率意的问题,敏锐地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揭示了杜诗晚年的一个变化。
这些批评家论杜诗都没有使用“老”的概念,用“老”作为批评术语来评价杜诗,似始于宋、元之际。方回《瀛奎律髓》喜以“老”论诗,刘辰翁评杜诗也对杜诗“老”的审美倾向有所抉发,他对杜诗“老成”的理解,相比意势纵横而言,更偏重于艺术技巧的纯熟、结体的浑成以及韵律的圆转,有时还可以特指声律,这是颇为独特的用法。
到清代,诗论家论及杜甫诗作的艺术特点,逐渐省略“成”字而单言“老”,甚至不限于晚年之作。清初“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灿以“老朴坚厚”概括杜诗的风格倾向,论五古又说“诗以坚老古朴如杜甫、元结者为上,清逸婉秀学王孟者次之,高迈蕴藉学苏李者又次之”,这里与老并举的朴、坚、厚、古四字包含了“老”所有的审美要素。关中诗人李因笃评《别常征君》《忆弟二首》《江上》《赠别何邕》,纪昀称赞《曲江对饮》“淡语而自然老健”,都注目于杜诗晚境所造之平淡。清初桐城诗人方奕箴批《雨过苏端》“作诗时岂字字照应,是绪真法老,便合天然”,王士禄评《少年行》“直书所见,不求语工,但觉格老”,纪昀评《中夜》“一气写出,不雕不琢,而自然老辣”,则注目于杜诗晚境的自然适意。李因笃评《无家别》“直起直结,篇法自老”,王士禄评《酬韦韶州见寄》“起老”,方东树《昭味詹言》称“谢鲍杜韩造语,皆极奇险深曲,却皆出以稳老,不伤巧”,则又是评杜甫诗歌结构的工稳和语言的妥帖浑成。要之,杜诗“老”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及变化,这是前人一致公认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些变化。
正如前引吴可《藏海诗话》所说,“老”的美学品格首先与创作的一定阶段相对应,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与年至耄耋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直接相关,所以“老”也因作者身心的老迈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枯寂拙钝、浅率无味和粗鄙颓唐的结果。历来对杜甫的批评,除了不工七绝和诗歌语言粗糙多疵外,主要就集中在老境颓唐一点上。朱熹首先指出杜甫以前精细,“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八哀诗》从宋代起就广受批评,恰好印证了他的论断。王渔洋曾屡数这组作品的拖沓、冗曼之处,以为“纯是暮气,岂少陵顿挫本色”。所谓暮气,正是老境的颓唐之气,是“老”容易由随性适意的写作态度中滋生的负面作风。
也有一些批评家并不纠缠于写作态度,而只是从能力的角度指出杜诗晚境的衰颓现象。黄生曾分别体裁来评价杜诗的得失,认为:“杜五古力追汉魏,可谓毫发无憾、波澜老成矣。至七古间有颓然自放、工拙互呈者。”沈德潜更直接断言:“夔州以后,比之扫残毫颖,时带颓秃。”赵翼认为黄庭坚说杜甫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是惑于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说,而妄以为其诗愈老愈工,其实“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纪昀评《瀛奎律髓》,常在“老”的意义上批评杜诗这方面的缺陷。面对前人这种分歧见解,嘉、道间诗论家延君寿曾加以折衷道:“沈归愚谓工部秦州以后五言古诗,多颓唐之作,或亦有之。然精意所到,益觉老手可爱。……黄山谷善于学秦州以后诗,真能工于避熟就生,归愚先生非之,非是。”这实际上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语言的放任随意不只会导致口语化的浅白和粗率,同时也会带来不经意的失当和尖新。杜甫晚年“漫与”式的写作确实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后果,既有率然的浅白,也有出于随意的生新,全看后人如何看待如何取舍。
当“老”日益成为一种风格范型和艺术境界为诗家认可后,不仅杜甫本人,凡后人学杜而得其髓者,也自然地被从“老”的角度加以欣赏和品味。这就提醒我们,在杜甫的接受史研究中,不仅要从诗体、风格、修辞各层面把握杜诗的典范性,还需要从“老”的角度把握其美学层面上的统一性,超越伦理学、文体学、风格学和修辞学的层面去认识杜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贡献及其典范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