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特区建设思想争鸣
2018-08-05邓伟志
邓伟志
现在不是特区的城市也像特区,可是1979年决定在中国设四个特区的时候,对特区言人人殊,褒贬不一。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是睁大眼睛看争论双方的言论和表情。谁都知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怎样才能把生产力搞上去是一道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既然都看见老路子走得慢,就提醒人们考虑另辟蹊径。另辟的蹊径肯定不同于老路,有争论是难免的。
深圳特区给我上了第一课
1980年深圳特区正式成立不久,我就去了深圳。记得那时蛇口还是荒山,蛇口人正在用炸药轰山,尚未建高楼。蛇口招商局负责人袁庚信心百倍地向我们介绍他们将如何引进人才、如何引进外资的大胆设想。他不要拨款,只要政策。接着,我们又请从上海去蛇口经商的黄宗英,在深圳办广播电视台的祝希娟介绍情况。因为都是上海人,彼此比较了解,谈起来更加敞开,连秘密也给我们透露了一部分。黄宗英讲她为什么来深圳,主要是觉得能放开手脚,能大显身手。祝希娟主要讲她准备办哪些在内地很难办成的、富有特色的、会受欢迎的频道。这算是给我上的特区第一课,既丰富了感性认识,又增强了理性认识。
蛇口大胆引进人才,就是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社会流动”。黄宗英、祝希娟到深圳创业,是社会流动中的一种“水平流动”。流水不腐,社会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会促进社会净化,增强社会活力。回上海后,我立即把袁庚讲的户籍改革告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妻子在南京教书,他没有办法把妻子调到上海来。他曾在我面前发牢骚,说:像他这个条件,(连续)讨几个老婆都很容易,调一个老婆比登天还难。那次他听了我的介绍,情绪高涨,兴奋地说:“再调不来,我们夫妻俩一起去深圳。”
1983年,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又去了深圳。那时深圳国贸大厦正在建,已经建了六七层,说要建53层。我听了吓一跳,上海的国际饭店24层,在我们眼里就算很高了。国贸大厦要比国际饭店高一倍多,实在是了不起。我虽然没见过摩天大楼,但1978年春天我在北京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时,听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讲:152米以上的高楼可以称得上摩天大楼,深圳国贸大厦要建160米,那不就是摩天大楼吗?多让人羡慕呀!
更让我感叹的是深圳朋友告诉我:深圳人干劲冲天,国贸大厦是“三天建一层”。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啊!我暗暗地想:这就是深圳速度!这就是特区速度!
“三天建一层”只是个例子。实际上,深圳的GDP、深圳的财政收入都在突飞猛进。在后来我撰写的《深圳应当是理论研究的窗口》一文中,仍然从“‘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说起,从深圳已经成为公认的“四个窗口”说起,认为“深圳还应该是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窗口”,建议深圳继续“在‘特字上做文章”,“在理论上‘特起来”,“在理论研究的政策上、内容上、学风上和理论研究的方式、手段上都能特起来”。不久,这篇文章被深圳市委宣传部收入他们汇编的《百位学者对深圳的思考》一书。
在珠海特区与端木正交谈
在要不要设特区的问题上有争论,在特区设立之后对如何建特区的问题上继续有争论:“只引进技术不能引进经济”是一说,“只引进经济不能引进文化”又是一说。争论更激烈的是“观念绝对不能引进”。
就在这时,珠海特区政府于1985年底邀请国内学者开了次研讨会。记得千家驹先生参会了。他跟我讲了他在青少年时期与吴晗交往的几个小故事。会议期间,我与中山大学法律系系主任端木正教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住一个房间。当时尚不能随便看港澳电视,可是在特区珠海可以看。我们一起看香港一位讲师、两位副教授评论柬埔寨局势的镜头。看着看着端木教授流露出伤心的表情。我以为他生病了,便问他怎么了。他坦诚地说:“我看了他们三位年轻人的评论,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接着又说:“不论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开放的做法是正确的。”端木正的这番感慨对我也是点拨。是的,他的话很有道理。评论任何事情,都要事前对正反两面的说法有个透彻的了解,发言才能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妄加评论是不着边际的忽悠。讲套话是拾牙慧,味同嚼蜡。
在讨论会上,我直截了当地说:“把人家引进来,怎能只让人家带口袋,不让人家带脑袋呢?”“要看到,东西方文化之间有冲突也有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全盘西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化不了的。”“我们登了外国的广告,就说是西化,那么美国人把我们的五星红旗带上航天飞机,是不是‘东化呢?在美国有那么多中国血统的人当市长、校长、警察局长,是不是卖国主义呢?”会议主持人吩咐我把发言整理成文。于是我以《把经济特区变成社会特区》为标题,发表在《珠海特区调研》1986年第2期上。过些日子,珠海一位副市长对我说:“文章受到读者和省领导的好评。”
厦门特区的范围为什么这样小
1982年厦门大学开学术研讨会,规模蛮大,记得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老先生也来了。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了厦门特区。参观时,大家觉得厦门特区范围太小,尤其是在深圳考察过的人都说厦门特区太小。可是,陪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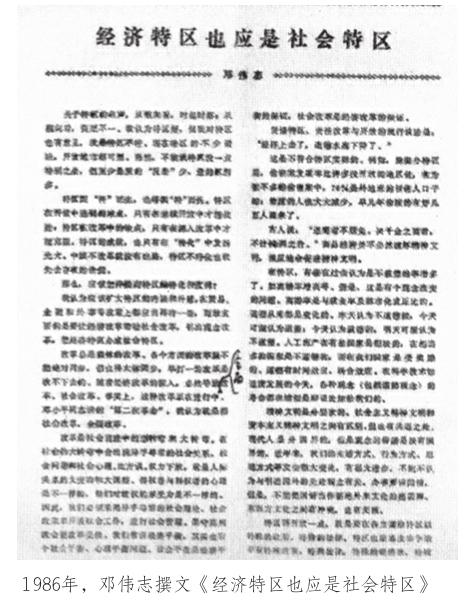
晚上,我去看望一位老朋友。1960年或1961年,厦大校长王亚南带他在上海编书时,这位朋友与我同住集体宿舍,两人床铺只有一米之遥。一别20年,如今他在中国唯一的台湾研究所——厦大台湾研究所工作。老朋友相见,没有客套,说话直来直去。他说:“听他们讲,省委项南想大搞,可是保守派坚决反对,给特区扣大帽子。中央的理论权威胡老(老朋友当是直呼其名的,此处从略)骂特区是‘殖民地。上下都有人卡项南的脖子……”说了以后又叮嘱我不要讲是他说的。我全然明白了。
因此,《厦门日报》记者在会上采访我时,我有意把话题拉到敏感问题上,试探他的观点。真是“海内存知己”,记者完全同意项南的思想。我请他把我支持项南的看法发内参。他说有难度。他劝我为《厦门日报》写文章,从侧面为特区打气。于是我先后在《厦门日报》上发了《“特别值得注意”》(《厦门日报》1983年4月15日),针对当时的争论,指出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自信说成自满,也不要因为个别人才有自满的缺点而拒人才于特区大门之外。发了《“阿堵”勿却》,讲“逐鹿者不顾兔”的道理,批评“愈穷愈革命”的片面性。发了《山崩于前》(《厦门日报》1986年2月7日),提倡“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大声疾呼“即使是山崩于前也不能動摇中国人民推行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决心”。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两位理论家、思想家到广州作报告: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胡老,他先到;再一位是于光远,他后到。于光远作报告时座无虚席,来晚一步的人不得不站着听;胡老作报告座有虚席,不得不把本来没资格来听报告的普通干部拉来充数。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原因是胡老在特区搞了几年后,还隐隐约约地讲特区“有损主权”;于老则旗帜鲜明地认为特区的做法是在很好地“行使主权”。于老的观点,以及于老作报告的场景,传到胡老那里以后,可能对胡老有刺激。胡老离穗返京前给于老写了首长诗,大加赞扬于老报告听众人山人海。我当时在于老身边。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看了这首诗以后,笑逐颜开。他连连说了几个“好!好!好!”,赞扬胡老有进步。他对于老说:“他(指胡老)从骂(特区)‘殖民地到讲‘有损主权是进步,从‘有损主权再到歌颂你讲得好,是又进一步。他没讲你的观点如何正确,应该说,包含这层意思。”
任老与于老接下去深谈时,我便主动去了隔壁房间。我深知他们二人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继续切磋。他们探求真理的精神,保障他们之间能够做到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这般互相推动的领导关系可以从他们晚年坐轮椅的日子里所拍的两张照片上看出来:一张是任仲夷坐在轮椅上,由于光远在后面推轮椅;再一张是于光远坐在轮椅上,由任仲夷在后面推轮椅。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最需的是思维共振,互相推动。
受两场报告能够互动的启发,我为《广州日报》写了篇《关于“对话”的要领》,提倡对话,批评“讲老话、套话,尽管不是假话,但是无补于事”。
南风终有一天会北伐
抗日战争八年就取得胜利,特区之争八年还没有结束。
被北京称为“青年思想教育权威”的三位先生,在全国巡回演讲,每到一处无不受欢迎。不料1988年初他们在到蛇口演讲时,在怎么看“自主选择职业”“淘金”“满街是进口车”等问题上发生了观点碰撞。教育者流露出蛇口青年走“邪路”的看法,立即受到青年质疑。广东有几家报纸作了报道,用当时媒体的语言,叫做“震动全国,波及世界”。《人民日报》辟专栏讨论。在一个月当中,《人民日报》收到世界各地的信稿1531件,其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三位的观点。继《人民日报》之后,一直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
我把这次讨论称作理念上的“北伐”,提笔写了篇《“南风”终有一天会“北伐”》(《社会科学报》1988年9月15日)。我说:“几年前,一直批‘南风,我不赞成。我估计在观念上终有一天会来个‘北伐。这次‘蛇口风波就是北伐的征兆。过去南下干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什么时候能让懂商品经济的南方干部北上呢?我期待着。”接着,我又在《深圳晚报》《深圳特区报》两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颂扬南风。
“北伐”胜利的标志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他肯定了特区,批评了不改革的人。不过,从作为喉舌的报纸版面上,仍然能看出深圳、珠海对论述、赞颂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灿若繁星,而有的省市的报纸论述、赞颂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寥若晨星,还有的报纸因为多发了学习南方谈话的文章,反而被他们的上司批评为“不听招呼”。当时,《深圳特区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发了八篇以后印了合订本,送给了我一本。我捧在手里好像握着杀出血路尖兵的手。
公道自在人心。1997年项南逝世时,自行赶来八宝山向项南遗体告别的人数之多据说是罕见的,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有向项南鞠躬的机会。花圈之多,摆了几十米。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上海人最喜爱的学者型市长汪道涵送的花圈摆在大厅外第二个,进不了大厅。
2018年1月15日我看到深圳人遵照十九大精神,豪迈地提出九个“坚定不移”、三个“一以贯之”,我喜上眉梢。深圳人讲:“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努力在新时代走在前列,在新征程勇当尖兵,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奋力向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迈进!”看后,我深深佩服他们这种“尖兵”“率先”“引领”的宏大气魄,同时也引发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自特区设立以后,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也有划时代的进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力是建设的火车头,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带来观念的变革。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在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课题。有哪些过去没有的行业将要上马,有哪些传统的行业将要下马,亟待人们回答。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了预见,下马的不仅会痛痛快快下马,而且会因祸得福,走出新路;上马的不仅会自觉迎新,而且会有所创新。天下事一早百早,只有早作研究,早作安排,才能成为时代的“尖兵”,才能实现“率先”“引领”。对此我也在摸索中,这里只能说几点不足为训的管见。
(一)正确处理引进外资与向外投资的关系。弱时请人家进来,强时自己走出去。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目的都应当是为了国家富强。请进来不是请垃圾进来,走出去不是去干有损于国家的小动作。要相信,有去有回。
(二)正确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民企,集体、企业等是互补互动的关系。国企要做大,更要做好;民企能大则大,不能大也要小中见大,以小促大。民企是民兵。40年来民企遍地开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陈毅就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今天国家的繁荣也是民企推出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企的“初心”,多为民企搭桥铺路。忘记民企也可以认为就是忘本。
(三)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要正视今天出现的“见利忘义”现象。忘义是国耻。但是忘义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市场經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商讲商德,不会忘义。不要把当今的忘义归罪于市场经济。见利忘义是过度市场化的产物,是不赞成市场经济的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产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商主义原则带来的弊端。上行下效,忘义是不经商的权贵人物的腐败变质带动出来的祸害。
(四)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邓小平在提出办特区的同时,提出“政治改革”,后来被缩小为“政治体制改革”,再往后连“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少提起。这就造成了政企不分,出现“经济上去了,社会风气下来了”的不文明。政企不分也就为“大老虎”出来伤人大开方便之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十九大报告提到203次“人民”。十九大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一定要、也一定会 坚持不懈地践行“人民至上”,多为社会治理着想,多从壮大社会组织上下功夫,推行社会自治,进一步“把社会还给社会”。
广东省在特区推动下,始终坚持“改革走前头,开放立潮头”,连续多年创全国第一。在进出口总额上超过上海,居全国榜首。在广东的好多第一中,我最欣赏的是“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广东在世界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中走在了最前列,意味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正在大踏步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