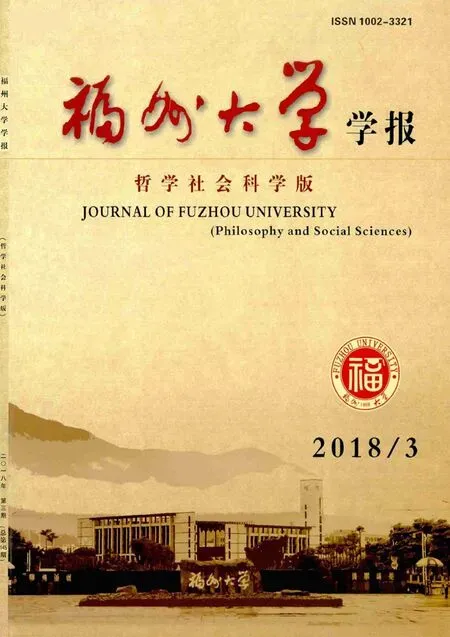台湾诗话鼻祖王松《台阳诗话》的诗史意识
2018-07-30廖一瑾
廖一瑾
(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台北 11114)
一、王松生平——从“四香楼”主人到“沧海遗民”
王松(1866—1930),又名王国载,字友竹、寄生。祖籍福建晋江。王松之祖父来台以儒术授徒。王松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即与开台进士郑用锡的北郭园诸君子往来,崭露头角。当时的竹堑(新竹)是淡水厅治所在地,北台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文荟萃。王松为前清生员,曾受聘于通志局,编写采访册。[1]编采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或许启发了他日后撰述《台阳诗话》的念头,也为他提供了数据。又从《台阳诗话》谈论的人物,百分之五十是新竹人来看,亦不难看出通志局的采访工作,让他不但熟稔新竹地区的“文事”,甚而亦将“事功”也纳入诗话。他谨于修身,名其居曰“四香楼”[2],取汤显祖“四香戒”之意,“四香”即“不乱财,手香也;不淫色,体香;不诳讼,口香;不嫉害,心香。”修身立诚的态度,使他获得好人缘,以及敬重。
乙未(1895)割台,王松携眷回福建祖籍避难,曾赋《海上望台湾》:“如此江山坐付人,陋他肉食善谋身,乘桴何用频回首,懒学长江论过秦。”[3]不料在海上遇盗,财物遭剽掠一空。1896年台湾局势稍稳后返台,易旧居“四香楼”之匾为“如此江山楼”,并自号“沧海遗民”,以志沧桑之痛。富绅郑绍基推重其学养,聘为记室,大小事均咨询之。[4]有《沧海遗民剩稿》《台阳诗话》等著作,列入《台湾历史文献丛刊》。连雅堂《王处士友竹先生五旬寿序》论其为人生平云:
连氏于新竹贤达荟萃的北郭园与王松论交,相知相惜,所言颇是中肯。
二、《台阳诗话》的诗史特征
1905年,王松自费在台湾新报出版《台阳诗话》,书有1898年新竹巨室郑如兰、1899年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序,足见其定稿于1898年,截至付梓出版,续有增补,书中载录人物约224人,其中146人或为台籍、或因游宦、造访来台。新竹人士占50%比例。抒发文学论见者少,以记载台湾风物民情为主轴,留下宝贵的资料。
(一)首篇以郑成功开台事迹为台湾诗史定调
《台阳诗话》第一篇收录蔡德辉歌咏郑成功(1624—1662)之盛德大业七律,并加以赞扬,有藉诗歌为台湾的诗史定调,似效孔子以《周南·关雎》为国风首章,以正人伦之始的意味:
延平王朱成功为开台第一伟人,明祚赖以维持者三十余年;其盛得大业,为中外所钦。世之文人学子,恒喜讴歌是事。余爱蔡醒甫(德辉)所著龙江诗话自载谒延平王庙七律四首云:“沙汕纷纷列舳舻,当年海上拓雄图。鲸鱼入梦生何异?龙种偕来类不孤。人似武侯筹北伐,地同洛邑建东都。知他矢志延明祚,绝岛偏安亦丈夫!”“红旗赤帜树高城,弱冠将军独请缨。宠赉有加天赐姓,征收无处海屯兵。都缘耿耿心长在,岂为区区发数茎?忠孝由来难两尽,邮书往返不胜情!”“森严刁斗拥熊罴,赏罚分明未足奇。只望一身存胜代,敢将两岛抗全师。”“图开赤嵌形堪踞,业复朱家势莫支。智力难争天命在,多君风调俨须眉。”“才尤刚决节尤坚,和议连番总不然。百计筹谋惟报国,一时流寓况名贤。便教藩服能成事,其奈孱躯不永年!史册流芳终有分,漫将遗恨播诗篇。”[6]
诗话第二则亦收郑成功事迹,话说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1820—1879)巡台时,重修台南延平郡王郑成功庙,特署楹联之事:
沈幼丹(葆桢)星使驻节台都,重修王庙,署楹帖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庙在台南府城。[7]
此一楹联至今为台南延平郡王祠镇祠之宝。郑成功于1624年诞生于日本九州岛长崎县平户市,母亲田川氏,父亲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第三则记录日本诗人馆森鸿游南安,祭郑墓诗,以明郑成功的丰功伟业受人尊敬,并驳斥德国人李庶博士只把郑成功认定为“贸易大王”:
日本名士馆森子(鸿)尝游南安,访成功之子孙,以清酒二瓶、黄柑一篮诣覆船山祭其墓。有诗三首,录其一云:“国破君亡何忍言,泪枯闽地旧乾坤。春风一剑三千里,来吊孤臣未死魂。”噫!何令人景仰一至如此!而德国李庶博士所著台湾岛史竟目为海贼朝廷,称成功曰贸易大王,其识见亦诚可鄙也夫![8]
王松在日本乙未据台后,不数年即撰述《台阳诗话》,特列郑成功事迹为首篇,并以“开台第一伟人”尊称之,其救亡图存的苦心孤诣,了然可知。
(二)诗话台湾掌故
台湾居民为多种族群的汇集。康熙年间已在番社设学,推行汉化教育。1892年台湾为干旱所苦,地方县令祭天祈雨,果然天降甘霖。是时王松的一位原住民(当时称为番族)朋友卫壁奎,乃番籍生中之翘楚,作诗歌咏县令祈雨之灵验。王松载其诗也说明番族的来源:
台湾番族,原从南洋“巫来由”诸岛传来,故其言与风俗,多与之同。期间分为三种,摆安、知本、阿眉是也。摆安族最强,余皆柔顺,统称曰“生番”;归化者为“熟番”。散处于本岛东部,穴居野处,渔猎为生,颇有上古之遗风存焉。熟番归化后,有指日为姓者,有由官长赐其姓。出与粤人杂居,无相扰。康熙三十四年,始设立熟番社学以教之,俾解文字,易服装,与汉人同。嗣亦许其应试入学,别为番籍生。有卫华卿茂才(壁奎),番籍中之翘楚也,与余相遇于试院,一见欢若平生,握手论文,颇有特识。丁亥大旱,邑侯方公,竭诚祈祷,雨即沛然。茂才上诗四首,有句云:“使君自具为霖手,难得天人一气通”,为方公所赏。子朝芳,亦入邑庠。[9]
又例如台湾之汉人多来自闽、粤。遇地方有事常借重粤籍义民帮忙。王松读查鼎表扬粤籍义士诗,颇为慨叹:
台湾滨海,居民多闽族,内山则皆粤产也。质直好义,耐苦勤耕。地方有事,当道咸赖焉。其报效亦独力,故着有“义民”之称。查小白明经(鼎)尝题旌义祠五古一篇云:“耰锄服田畴,干戈卫社稷。凌厉气无前,先驱争杀贼。制挺挞坚兵,所遇皆颠踣。少壮不策勋,悠悠徒视息。节重一身轻,浩然天地塞。名并诸功臣,精忠同报国。恨未补天南,恩遥承阙北。冰霜碧血凝,金石丹心勒,松楸泣杜鹃,凭吊增凄恻。”读此为慨叹久之。[10]
其余诸如台岛之山川、产物、风土民情、财经文化,乃至日本明治时代的台湾汉学,皆有所叙说。
(三)保存文献资料
王松的诗话收录了为数甚多的文献资料,分列表1、表2、表3、表4[11]:

表1 《台阳诗话》收录诗话类文献

表2 《台阳诗话》收录诗词文集类文献

表3 《台阳诗话》收录其他著作类文献

表4 《台阳诗话》载录人物[12]
续表4

编号时期诗人人数3道光周 彦、曹 谨、郭襄锦、徐宗干、陈维英、查小白、高鹏飞、王廷干、林则徐、刘星槎、张维垣、黄镶云、郑用锡、翁林福、黄景寅、姜奠邦、王小泉174咸丰许超英、曾薾云、施琼芳、林占梅、吴子光、林薇臣、苏虎七、林汝梅、吴士敬、秋日觐、黄玉柱、陆翰芬、叶春波、彭培桂、刘雪和、郑如兰165同治沈葆桢、陈肇兴、林文察、谢管樵、梨召棠、何孺人、严金清、郑维藩、张谦六、陈沛霖、林 豪、彭延选、刘明灯136光绪蔡德辉、方樾庭、高汉墀、方家澍、陈子潜、陈浚芝、吴逢清、陈文騄、黄如许、郑澄波、郑以典、郑 钱、唐景崧、刘铭传、陈 喜、李文泰、杨俊臣、叶意深、林京卿、林尔嘉、梁子嘉、黄鸿汀、萧母陈太君、陈星郎、施士洁、王国瑞、黄宗鼎、黄彦鸿、蔡仁寿、李鸿章、丘逢甲、林氅云、林骆存、刘永福、陈玉程、刘梅溪、王咏裳、徐锡祉、林允卿、李雅宣、李雅音、王君右、陈任之、沈国盘、吴伦明、林庚秋、陈锡奎、陈庆云、蔡莲舫、王学潜、蔡敏贞、姜赞堂、卫华卿、郑以庠、张幼亦、陈季同、李珍前、陈锡兹、王英奇、龙峒山人、洪瑞卿、王成三、陈沂震、僧显万、僧奉忠、杜淑雅、林达夫、汪式金、蔡佩香、蔡彦清、彭种蓝、杨吉臣、吕汝玉、吕汝修、吕锡圭757日据初期王 松、李石樵、陈淑臣、王石鹏、郑鹏云、郑家珍、许剑渔、施梅樵、陈槐庭、林朝栋、陈基六、戴还浦、罗秀惠、蔡国琳、陈焕耀、谢颂臣、杨希修、陈镇坤、林资修、林资铨、黄茂清、蔡启运、陈沧玉、洪月樵、郭镜澄、林次湘、蔡汝修、蔡惠如、郭镜蓉、王庆忠、王庆超、黄潜渊、叶文游、吴葆荣、张采香、波 越、郑学瀛、郑树南、郑灿南、吴子瑜、吴子衡、林仁桥、儿 玉、纫山衣洲、白井新太郎、佐佐木忠藏、卫朝芳、后藤新平、永井完久、波越重之、叶际昌、叶际禧、李恢业、李逸樵、黄谷如、陈叔宝、曾吉甫、辛柏亭、周子佩、谢介石、沧浪濯缨客、今西上人、庄鹤如、谢汝铨、查奉璋、王瑶京、迷新子、黄云昭、里见义正、樱井儿山、吴德功、张麟书、横堀铁研、副岛苍海、水野大路、樋村龟次郎、土香居国、郑长庚、郭涵光798日据时期海外人士邱菽园、林畏卢、刘 威、袁翔甫、王晓沧、潘兰史、马绍兰、谢安臣、小野湖山99活动时间不详者马耿甫、徐莘田、姜宸英、果杏岑、许雪门、施钰、童蒙吉、郑超英、李沂、胡克昭10
据林美秀统计,224人中,本土人士146人,新竹地区74人,居半数以上,因而认为王松《台阳诗话》“近似新竹诗话”。此似印证了笔者提出王松青年时期参与“通志采访”工作,影响了他所采录的比重。无论如何,他保存文献功不可没。
(四)思想开明,接纳新事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风东渐,王松对此新猷,津津乐道,诗话述及道光年间广东译事萌芽,新知唤起国民新思想:
自海禁开而译事萌芽。道光间,广东有译博物新书五种。其以新理想绍介于学界者,当以此为嚆矢。厥后有侯官严几道先生所译之天演论、原富等书,亦足以唤起国民之思想。[13]
中国因战争而洋务日增,日本因明治维新较早接受西方新知,台湾在日据初期,西方的新名词、新事物也成了诗人歌咏的题材:
近十年间,士之负笈航海、游学于东西洋者,日不乏人。译书层出,竞先遗饷;而又以东京为输出新智识之孔道。其当转输之大任者,则宜首推横滨新民报社。余见其论说所用新名词,如“结果”“起点”“程度”“目的”“间接”“直接”等字眼,皆取和文而用为汉文也。风气所推,各处报馆又从而仿行之、激扬之;奇词异语,遂放出今日文学上之大光明,而成为廿世纪变迁之大势,洋洋乎沛然莫之能御矣。竟有以新理想发为诗歌者,如楚北迷新子之新游仙八首云:“乘兴清游兴倍长,骖鸾驾鹤总寻常。神仙亦爱翻花样,拟坐轻球谒玉皇。”“一曲清歌人不见,是谁高唱遏行云?霓裳自入留声器,仙乐风飘处处闻。”“凤脯麟脂积满盘,萄葡美酒醉人难。忙呼小玉铺台面,安置刀叉吃大餐。”“银河隔断信难通,牛女年年恨不穷。昨日碧翁新下诏,两边许设德律风。”“休言一步一莲花,洛女凌波貌绝佳。着得一双弓样袜,踏来水面自由车。”“广寒宫殿桂花香,仙子如云列几行。闻得嫦峨新奉敕,清虚府改女操场。”“瑶池阿母绮窗开,窗外殷殷响似雷。侍女一声齐报道,穆王今坐汽车来。”“二十六宫敞画屏,御阶仙仗拥娉婷。几多玉女朝天阙,不佩明珰佩宝星。”[14]
新名词如“直接”“间接”“结果”“程度”等外来语,对当时有新的“大光明”的影响。此外王松对明治时代来到台湾的日本汉诗诗人亦多方采录。足见王松对新知的悦纳。
三、结语
诗话者,话他人诗也。一般诗话往往是作者凭其学养、观点,引诗而话之;包含诗评、诗论、诗格、诗法、品藻、本事等。而王松《台阳诗话》却有别于此,不以自身书斋、居所或名号为书名,而采用“台阳”(台湾的美称)。在那艰困飘摇的时代,努力为他眼见的缤纷诗句,建造一个可以广大庇护之所,纵是吉光片羽也加以珍惜。正如王松《自序》所言:“留示后人”[15],使人想起诗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惜才、怜才心境。连横推崇“其裨益于台湾文献者不少”[16],安溪林辂存《牡丹吟社林鹤年之子》更誉《台阳诗话》好比“在枪林炮雨中抢救斯文”[17]。《台阳诗话》搜集资料的广度,印证了其保存文献的诗史意识。
丘逢甲《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诗:“如此江山竟付人,干戈留得苦吟身。乱云残岛开诗境,落日荒原泣鬼磷!埋碧可怜黄帝裔,杀青谁作素王臣!请将风雅传忠义,班管重归故国春。”[18]认为此书苦心孤诣,感动鬼神,期许藉由诗教而永传忠义、期待彩笔重回故国的春天而任其挥洒之日。依此说来,《台阳诗话》不但有保存文献之功,更兼得传承儒家忠义文化之劳。
注释:
[1] 王松在通志局采访,事见早年诗作《岁暮书怀》:“门户中衰觉命悭,逆来顺受亦安然。琴因养性非关趣,诗为娱情不在传。斑管转工修野史(时在志局采访),锦囊并贮看山钱。可怜无限缠绵意,岁月磋跎又一年!”王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收入《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43页。
[2] 王松居所由“四香楼”,改为“如此江山楼”之缘由,见王松《沧海遗民剩稿·自序》:“……乱定后,因省丘墓,由厦渡台。所幸青山无恙,又喜四香楼故居巍然犹存,天之厚我者多矣。斯楼旧名,盖守汤若士先生四香戒也。旧额既失,因更名为如此江山楼;托剑南句以寄慨焉。呜呼!今再啸卧于此间,岂仅‘举目河山’之感已哉!诗友酒徒,风流云散;音书断绝,情何以堪!现所来往者,唯二、三亲旧耳。”王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1页。
[3] 王 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16页。
[4] 廖一瑾:《台湾诗史》,收入《台湾近百年研究丛刊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5][7][8][9][10][13][14][16][18] 王 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57,1,2,54,59,72,72,57,65页。
[6] 王 松:《台阳诗话》,《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 第1页。
[11] 表1参考龚显宗:《台湾文学研究·台阳诗话初探》,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整理。表2亦参照之,笔者另加:俞樾《俞曲园集》一书。表3同参,笔者另加:严几道译《天演论》一书。
[12] 参考林美秀:《王松〈台阳诗话〉的文本特质与书写意涵》,《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学报》第31期,2001年12月,第333-334页。
[15] 王 松《台阳诗话·自序》:“此寥寥者,皆韶年耳目所及,迄今半逐遗忘。兵燹余生,学步邯郸,苦无师友切磋,金针莫度;本为巾箱吟赏之具,亦如燕公记事之珠。况古今诗话,汗牛充栋,已足备知人论世之采择,奚用此为?漫存若干条,有赞叹而无扌为诃,只可留示后人,未敢就正有道。”王 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1页。
[17] 林辂存《台阳诗话·跋》:“王子之才、之行,天下知之者甚伙,姑勿赘。至若今所读诗话、吟草,其神妙处亦尽于诸名人序中,余更何赞一词。但余亦有所耿耿不忘者:盖集中序列姓氏,强半为余挚交;所载山川风物,亦强半为余亲历。呜呼!地割矣,斯文坠矣。大陆已沉,群黎无告,而吾子更能出入枪林炮雨中自葆其道,又得以所葆之道而遗诸余,余何幸而与于此!”王 松:《沧海遗民稿·四香楼少作附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