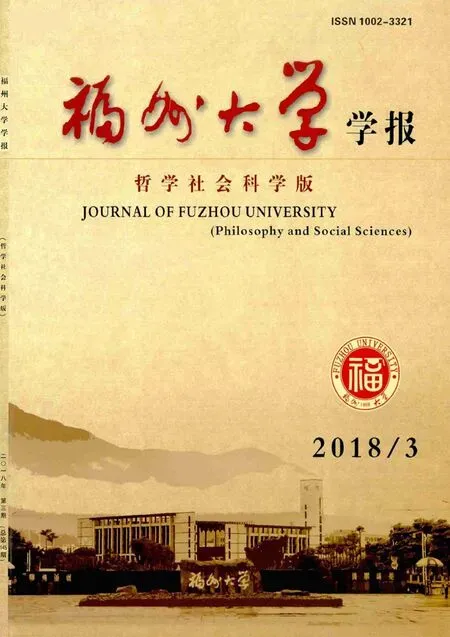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论
2018-07-30张沁兰赖正维
张沁兰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明清时期的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因其“地界万涛,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后转谓之琉球”[1]。明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太祖派遣行人杨载出使琉球,致送国书,通知即位建元。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2]。自此,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
由于福建与琉球隔海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福建在中琉长达五百余年的友好关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窗口与桥梁作用。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3]。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口岸。地缘关系使得闽人在中琉交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闽人与册封琉球使团
由于每位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4]。据已知见的史料记载,明清两代共派遣册封琉球使臣46名,册封琉球国王25次(包括册封琉球山南王2次)。历次册封琉球使臣在京领命后,都必须到福建筹备建造册封舟、招募兵丁及其他随封人员,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才能启程。闽人在册封使团与琉球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前册封,以造舟为重事”[5],而要完成此重任,工匠的选择至关重大。通常,造船工匠来自福建各地,但技艺各有长短。“其在河口者,经造封船,颇存尺寸,出坞浮水,俱有成规。然笃于守旧,而不能斟酌时宜,又苟且用料,而不必求其当,此其失也。漳、泉之匠,善择木料,虽舵牙、橹棍之类,必务强壮厚实。然粗枝大叶,自信必胜,而不能委曲细腻以求精,此其失也”[6]。通过扬长避短,“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7],各尽其长,才能造出合格的封舟。
中琉船路极为险阻,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因而在早期出使琉球的册封舟上,使臣甚至“舟设桴翼,造水带至载棺,而亟银牌于棺首,书云某使臣棺,令见者收而瘗之”[8]。有的使团人员甚至还“随带耕种工具”,以防“飘流别岛不能复回”。同时还必须“虑员役损失,后事俱备”[9]。册封舟能否安全到达琉球并平安返回,生死攸关。而海上行舟,闽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众多册封使及其随员撰写的使事记述中多次提到。如明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使陈侃在关于航海用人中谈及:“漳州以海为生,童而习之,至老不休,风涛之惊,见惯浑闲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长乐、如镇东、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各有能、有不能,唯用人者择之。果得其人,犹可以少省一、二,此贵精、不贵多之意也。”[10]明万历七年(1579)册封使谢杰亦曰:“大都海为危道,乡导各有其人。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由闽以北熟其道者,梅花、定海人,由闽以南熟其道者,镇东、南安人。”[11]
在明清两朝正副册封使46人中,福建籍的册封使臣就达8人,即:明代的陈傅、潘荣、官荣、谢杰,清代的林麟焻、齐鲲、林鸿年和赵新。他们都不辱使命,为加强和增进中琉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按明清规定,册封琉球使除率领官方规定的职司员役外,还可以随带部分由自己选择的从客,包括文人、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书画家、琴师等各方面的专家及能工巧匠,其中不乏闽人。例如,万历七年(1579)萧崇业任册封使时,使团成员中,“取于福州者,自医画、书办、门皂、行匠以凡六十余人”[12]。因此,册封使团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闽人文化代表团。由于册封使团返程须“候北风而后可归,非可以人力胜者”[13],因而册封使团在琉球除按规定完成册封等各种典礼后,还有足够的时间与琉球各界人士进行多方面的文化沟通。其交流内容遍及书法、艺术、医学以及手工技艺和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海宝使团在琉球那霸时,琉球“国王遣那霸官毛光弼于从客福州陈利州处学琴,三、四月习数曲,并请留琴一具,从之”[14]。当使团离开那霸返国之际,毛光弼特作诗一首,题为《从天使幕从客陈君学琴成声报谢》云:“古乐入天末,七弦转南薰;广陵遗调在,拂轸一思君。”[15]闽籍册封使还为琉球带去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清道光十八年(1838),册封使林鸿年在那霸游览瑞泉时,题了“源远流长”和“飞泉漱石”八个字,[16]赠与琉球尚育国王。琉球国王把它刻在石碑上,现今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悠久的见证。
贸易交流也是册封使团在琉球主要活动之一,闽人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明清册封使记载,使团航海人员中常常会出现许多冒充海员者。如嘉靖十三年(1543)册封正使陈侃写道:“从予驾舟者,闽县河口之民约十之八,因夷人驻泊于其地,相与情稔,欲往为贸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术。”[17]康熙五十八年(1719 )册封副使徐葆光也谈到:“是时海禁方严,中国货物外邦争欲购致,琉球相近诸岛,如萨摩州、土噶喇、七岛等处皆闻风来集,其货易售。闽人沿说至今,故充役者众。”[18]明清禁海使沿海民众丧失了出海贸易谋生手段,迫使他们冒充海员,混入册封使团去琉球贸易。因为按明清政府之规定,出使人员“许每人带货一百斤前往贸易”[19],这对贩海为生的闽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万历七年(1579)册封琉球副使谢杰在其《日东交市记》中也记载:“洪武间,许过海五百人,行李各百斤,与夷贸易,实以利啖之,亦以五万斤实所载也:著为絜令。故甲午之使,因之得万金。总计五百人,人各二十金上下,多者至三、四十金,少者亦得十金、八金,于时莫不洋洋得意。”[20]据史料记载,使琉球人员所携带物品往往大大超出明清每人限带百斤的规定,这些货物包括布匹、药材、茶叶、瓷器、食品、工艺品等等,并且贸易额巨大。嘉庆五年(1800)册封琉球尚温国王时,因为担心携带货物过多而延长贸易时间造成久滞琉球,因而重申严格遵守每人百斤规定。当时的册封副使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将其贸易货物与前册封使团比较,曰:“抚军以两舟货价并船户甘结移至,细阅两船货价不及四万,较前度少三分之二。”[21]可见,此前册封琉球使团在琉贸易的货价总额在10万左右,数量不菲。闽人活动大大推动了中琉间贸易的发展。
二、闽人与琉球来华使团
福建市舶司于北宋元祜三年(1087)设于泉州。明初,泉州首先成为中琉间直通口岸。为接待琉球使臣,明廷在泉州车桥村曾建立“来远驿”。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置福州,此后福州遂成为与琉球直通的唯一口岸。明朝还在福州河口地方建立进贡厂和柔远驿,进贡厂用于贮存琉球贡品,柔远驿则用于琉球使臣居住。
明代及清初,琉球进贡使团人数多为150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后,清廷准许增至200人,但“正副使从人十有五名入京,余留边听赏”[22],因此,使团绝大多数人员须停留在福州,从事贸易活动之后归国。除进贡外,琉球遣往中国的使臣,另有接贡使、庆贺进香使、谢恩使、报丧使、请封使、接封使及护送难民的使臣等等。据日本学者赤岭城纪所著《大航海时代的琉球》之统计,明清琉球使团来华842艘船,其中明代493艘,清代349艘。[23]如此众多使臣往返、停留福州,闽人与琉球使臣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
琉球使臣抵闽后,即被安置于柔远驿休息。按规定:贡使每员日给米三升,蔬薪银五分一厘;跟伴、水梢每名日给米一升、盐菜银一分。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24]琉球使团在福州期间,福建官员对他们热情款待。琉球使臣入京以前,须将正贡中的硫磺缴交给督抚诸官员收存,并且拜会福州的主要官吏,如将军、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向他们赠送琉球的土产,以加深彼此的联系。琉球使臣在闽期间,深入各阶层,同各界人士往来频繁,这些都对琉球的文学、工艺、医学、社会习俗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琉球的凉伞及五方旗就是由福州传入的。康熙五年(1666),郑思善、毛荣清率领的琉球进贡使团入京返闽后,“见诸侯之龙纹凉伞,潜然问其凉伞之缘由,毛荣清即与郑思善相共商议而令良匠夫作凉伞及五方之旗,乃发公银四十两买得,带回琉球后即奉呈国王。”从此琉球国“每逢大朝之时”,必“以为排饰”。[25]
由于琉球国远处东南,地多荒僻,产物无几,凡食物器用多需内地供给。明清政府规定:“凡进贡船只,准带土产货物银两,在闽贸易”,并且“其出入关税悉行宽免”。因此,与柔远驿相隔不远的球商会馆成为琉球人在闽贸易的重要场所。福建产的瓷器、茶叶、丝织品、棉织品都是琉球商人喜爱的商品。琉球对中药材的需求也十分看好。据史料记载,球商会馆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根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陈:“乾隆八年(1743)贡船来闽,海船亦止报银五千,而查其返棹货册,约计不下十万两。”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初五,琉球贡船至闽,进口册中琉方报称两只贡船“共带银一万两置买货物”,但实际“所带银两竟十倍于所报之数”。[26]福建官府对琉球贸易事宜大力协助,“遴委贤员验明入馆,召募妥实商人公平交易,官为存案。倘有勒捎稽延,照律治罪,监看之员如敢徇隐立即查参”[27]。当时福州还出现专门承办琉球商务的商人,被称为球商,据称有卞、李、郑、林、杨、赵、马、丁、宋、刘十姓十家球商。
闽人与琉球间频繁的贸易首先极大促进了琉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琉球商人利用海禁时期中国政府对之的特殊关照,将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商品,以贡品为名带到中国,绝大多数在福州球商会馆进行交易,再把所购得的中国商品运到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出售,如此循环,一本万利。如宣德二年(1427)九月十七日琉球国发往暹罗的咨文就有如下记载:“琉球国中山王为进贡事,为照本国稀少贡物,今遣正使实达鲁等,坐驾胜字号海船一只,装载磁器等物,前到贵国出产地面收买胡椒、苏木等货,回国应用。”[28]册封使陈侃也曾记载:琉球贡物中,“唯马及硫磺、螺壳、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地产。至于苏木、胡椒等物,皆经岁易自暹罗、日本者;所谓櫂子扇,即倭扇也”[29]。琉球贡使携带回国物品大致为瓷器、药材、纺织品、文化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这些物品的输入,明显促进了琉球社会的进步及文化的繁荣。其次,闽人与琉球贸易也极大弥补了明清海禁时期福建与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经济往来不足,促进了福建商品市场的繁荣,大大提升了福州港的地位。据统计,明洪熙年至嘉靖末年(1425—1566)的百年内,琉球入明朝贡抵福州港达173次。福州港由此成为成为这一时期最有活力的港口之一。[30]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中也描述道:“迄于清代,河口仍为琉球商人集居之地,故老相传,当贡船来闽时,其地的繁华殷盛,曾为全城之冠。”[31]
根据明清政府规定,琉球使臣进京,沿途各地方官必须负责各自境内使臣的行程,包括车马、食宿,并派专人护送与交接,而福建地方官则须委员伴送全程,即负责陪同琉球使臣抵京及返闽。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下旨,规定外藩使务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到京,参加元旦庆典,若未能依限到京,伴送官还将受到严厉查处。[32]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资料统计,从清乾隆八年(1743)至同治十三年(1875),福建巡抚共委派官员护送琉球使臣入京达54次,护送官111人次。[33]其中,嘉庆十三年(1808)之前,护送官以同知为多,人数为1名。嘉庆十六年(1811),福建护送官、福州府理事同知那绂不幸在京病故,清廷急令福建速派官员进京顶替那绂工作。由于此次突发事件导致护送工作不便,清帝下旨:“嗣后遇有外藩使臣入贡,著各该督抚均于文武员弁内拣派明干者两三员伴送来京,以昭慎重。”[34]因此,嘉庆十六年(1811)后的31次护送琉球使进京,除嘉庆十九年(1814)和咸丰七年(1857)之外,福建伴送官全部选派两名文职官员及一名武职官员。文官多为知府、通判、同知,武官多为副将、参将和游击。福建地方官员在护送琉球使臣进京的过程中大都能尽心尽职,不辱使命,更有因旅途劳累、不幸以身殉职。如嘉庆十六年(1811)伴送官、福州府理事同知那绂在抵京后病故。又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伴送官、延建郡道张汝骧在途病故。[35]他们为中琉两国的友好交往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由于旅途疲劳、水土不及疾病传染,琉球人病故现象时有发生。为此,福建地方官指定东门外的金鸡山、南门外的吉祥山和仓山区的白泉庵一带作为琉球人葬区。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三日,琉球馆接贡存留通事王兆棠曾禀称,琉球“所有口接贡船,并护送内地难民各项来闽官伴水梢,以及飘风难夷,凡在闽病故,向在辖下南关外□□山、张坑山、白泉庵、吉祥山,东关外金鸡山等处契买山地,葬埋标识。溯自前明迄今,计有百十圹”[36]。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刘蕙孙、徐恭生教授等人曾于1963对福州仓山区白泉庵、鳌头凤岭、陈坑山、张坑山一带的琉球墓进行考察,共发现68块墓(碑)。徐教授等人将琉球墓(碑)全部抄录下来。不幸的是,由于十年文革的动荡及城市建设的需要,有些琉球墓遭到破坏。1980年徐恭生教授再次对该地区进行重新考察,又有了一些新发现,从而使这一地区发现琉球墓(碑)的总数由原来的68块上升到83块。[37]
据考察,琉球人墓的形状与福州民间墓形大致相同,有宝顶、碑牌、供案、墓埕,其外围称山墙(或称圹山),左右有扶臂,下面两边为如意摆手。远看宛如一张“太师椅”。碑牌前有一小块长方形供案,可放香烛祭品,供后人祭祀之用。[38]福州这一墓形传入琉球后,被称为“龟甲墓”。琉球人的丧葬风俗深受中国影响。康熙五十八(1793)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时,即发现琉球“通国平民死,葬皆用棺椁……棺制,比中国棺略小,板厚不过一寸,长四尺五寸。墓皆穴山为之。既窆,垒以石”[39]。
对在闽逝世的琉球使臣,福建地方官员有严格的处理程序。首先“取到球官球医同通事各甘结”,证明其确已死亡后,迅速上报。清廷对在华身故的琉球使臣一贯采取厚恤政策,“内阁撰拟祭文,福建布政司备祭品,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一次,如欲将骨骸带回本国,听其带回,如欲留闽,令置地营葬,立石封识”[40]。并且,厚恤条件逐年增加。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三日,琉球进贡正议大夫蔡灼在闽柔远驿病故,“经部议覆准,遣官致祭一次,又给棺价银二十两,于宴赏银两动给报销”[41],永著为例。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二十日,琉球进贡副使正议大夫梁学孔,事竣离京返闽,不幸病故于福州。此次“照例给与棺价银贰拾两,恤银叁百两”,“交付该家属承领。”[42]此后,恤银叁百两亦成定例。对在华病故的琉球使臣,清朝皇帝时常赐以谕祭御碑,“建于墓左,永为荣光”[43]。 1990年在福州发现的王怀楚之墓碑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由清皇帝为琉球在华病故使臣钦赐蔡葬的墓碑。[44]王怀楚,字明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紫金大夫,随王舅毛国珍率谢恩使团入京奉表,献方物,谢袭封恩。[45]王怀楚因途中积劳成疾,不幸病故福州。康熙帝特颁旨钦赐祭葬,碑文为:“钦赐祭葬琉球国紫金大夫怀楚王公葬康熙丙寅岁孟夏吉旦立”[46]。
明清时期诸多琉球人士为了中琉两国的交往长眠于中国,这些在华琉球人墓(碑)既是中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中琉间密切的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闽人与琉球学子
明清时期,琉球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琉球留学生中,除部分入北京国子监学习的“官生”外,更多的则云集福州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各种专业知识及生产技术的自费生或半官费、半自费学生。他们被称为“勤学”。琉球“勤学”深入民间,拜师学艺,学习范围遍及各行各业。他们在福州努力学习,学成后归国报效,为琉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促进中琉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两国民众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福州师傅能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一些世袭行业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琉球学生。以下是根据《球阳》及《久米村系家谱》整理的明清时期琉球人到福州学习各种生产和工艺技术的情况表,见表1。[47]
从表1情况看,明清时期赴福州学习各种生产和工艺技术的琉球“勤学”人数达46人次,学习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生产技术及手工技艺各个层面。

表1 明清赴华琉球勤学生表
中国的儒家思想及文化对琉球具有深刻的影响。琉球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程顺则(1663—1734),字庞文,号念庵,15岁举秀才,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勤学事随谢恩紫金大夫王明佐赴闽,留居四载,师从朱子学家陈元辅。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奉命为接贡存留通事赴闽留驿三载,再次师从陈元辅研究朱子学和诗文。此间他在福州“捐资二十五金,购得十七史全部,共计一千五百九十二卷,归献孔子庙”。[48]归国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程顾则在久米村孔庙之侧建立了明伦堂,从事琉球汉学教育,传播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天文、历法、地理与农业生产及海上交通关系密切,琉球迫切需要在福州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史籍上最早记载琉球人在福州学造历法的是金锵。明成化元年(1465),金锵作为通事随琉球进贡使团来闽,拜师求艺,归国后成为琉球国第一个编制历法的天文学家。[49]此外,康熙六年(1667),琉球还遣久米村人杨春枝、周国俊拜师学习历法和地理。[50]康熙十七年(1678),琉球遣蔡肇功来闽,“从薛一白而学历法”,在闽四载学成归国,造大清时宪历颁行国中,此为琉球使用大清时宪历之始。[51]在天文地理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数琉球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久米村人蔡温。蔡温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担任进贡存留通事赴闽,在闽任职期间,他拜闽人刘日霁先生为师,“精学地理,悉受其秘书及大罗经一面”。回国后任琉球历史上第一位国师,后任法司官兼任国师。他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亲自主持了羽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他还“奉命始教农田经界之法”等,“令匠人始造测影定漏器物”,进行测量,为琉球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山林防护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52]
在传播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手工技艺方面,闽人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琉球人总官野国将薯苗从福州带回琉球栽培,从此,番薯广植于琉球。[53]康熙二年(1663),为学习制作白糖和冰糖,琉球人陆得先奉命随庆贺使团赴闽,即到南鼓山寻觅良师,“悉承其教而传授熬白糖、冰糖及朱涂黑赤梨地乃制造金银箔等之法而归国,就将其漆器及金银箔之法教授于贝摺势头,且白糖之法教授于浦添郡民焉”[54],自此,白糖、冰糖、漆器、金银箔等制作方法在琉球推广开来。此外,琉球还从福州学会了铸钱法。康熙五十三年(1714),琉球那霸蓄懿德赴闽,奉命学习铸钱之法,归国后为铸钱主“铸出鸠目钱十一万贯”[55]。这些无疑都大大促进了琉球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医学与民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此琉球亦注重派遣学生到福州学医。康熙二十七年(1688),琉球人魏士哲师从福州黄友会医师学习补唇医术。黄会友为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有祖传补唇奇方,周旋四方,疗治缺唇,然此药方一世一传,虽亲友不敢传之”,魏士哲师从黄会友后,“悉受其传方,又得秘书一卷”。黄先生还亲自辅导魏士哲为一位十三岁缺唇儿童治疗,“不数日痊愈无痕”。归国后,魏士哲在治好许多缺唇儿童的基础上,成功为国王世孙尚益疗治缺唇,三昼夜痊愈无痕。他不仅医术好,并且医道亦高,“为国家教彼两人,从此补唇之医法国中广焉”[56]。琉球国王对魏士哲深为赞赏,康熙四十九年(1710)官拜紫金大夫。
闽人的书画艺术也深受琉球学子的青睐。康熙二十二年(1683),琉球王府派遣璩自谦、查康信两人到福州学画,拜谢天游、孙亿为师,历时五年之久。[57]康熙四十三年(1704),琉球又派吴师虔来闽拜孙亿为师学习三年,吴师虔回国后成为琉球国王府的画师。[58]此外,琉球歌舞戏剧也深受闽人影响,许多乐师都曾到过福州拜师学艺。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琉球御书院乐师陈其湘在福州学习音乐和戏剧,历时六年,归国后“奉命为教授御书院乐生,以中华歌并琵琶三弦等事”[59],为琉球文化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闽人三十六姓与琉球社会
在明政府与琉球建立正式藩属关系二十年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鉴于琉球国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特“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60],充分显示了明政府对琉球的特殊优待,此举亦受到了琉球国的热烈欢迎。琉球国王大喜,“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俗称久米村)”[61]。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中“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为朝贡之司;习海者为通事,为指南之备”[62],其“子孙世袭通使之职,习中国之语言、文字”[63]。闽人三十六姓居住地久米村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及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中心。在此后的岁月,众多闽人三十六姓后代被派遣回中国学习。《球阳》就曾记载:“洪武以来,唐营之人或入闽或赴京,读书学礼,不定回限,通于诸书,达于众礼,待精熟日而后归国。”[64]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华奋发学习,学成后归国报效,深受重用。
闽人三十六姓及后裔是将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到琉球的重要使者,他们为琉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促进中琉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往发挥了以下独特的作用:
第一,闽人三十六姓对琉球造船航海业的发展及海上贸易中介国地位的形成功不可没。明代琉球虽为岛国,却“缚竹为筏,不驾舟楫”[65]。落后的造船航海业阻绝了琉球国与外界的往来,导致“东瀛之岛,如暹罗、苏门[答腊]、满喇加、高句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66]。闽人三十六姓抵达琉球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由于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67]这些习操舟、善航海之民抵达琉球后,必然大大推动了琉球造船航海业的发展。继明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后,万历年间(1537—1620),琉球又向明廷请求增补闽人三十六姓。其表文曰:“世久代更,人湮裔尽,仅余六姓,仍染侏亻离椎髻之习,天朝文字音语尽行盲昧,外岛海洋针路常至舛迷,文移多至驳问,舟楫多致漂没,甚至贡期缺误,仪物差讹。”[68]这亦充分体现闽人三十六姓对琉球海上交通及中琉朝贡活动的重要作用。
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琉球王国借助闽人三十六姓大力发展其航运业,并且利用海禁时期东南亚、日本对中国商品的渴望,依仗其具有朝贡贸易的优势,实行中介贸易。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琉球国贸易船只往来于暹罗、佛大泥、安南、苏门答刺、旧港、爪哇、巡达、朝鲜、日本等国与地区间。频繁的中介贸易不仅沟通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并且为琉球国带来了滚滚财源,从而造就了琉球历史上的“百年盛世”,亦即“大航海时代”。而从事中介贸易的主力军正是闽人三十六姓为主体的福建移民。据赤岭诚纪《大船海时代的琉球》统计,大航海时代的百年间,琉球遣往东南亚一带的贸易船只,船上通事及火长二职,几乎全由久米村人担任。以明正德四年(1509)至隆庆四年(1570)的六十一年为例,琉球遣往东南亚一带36艘贸易船只,久米村人担任通事者达74人次,担任火长34人次(其中有两艘船只没有记载火长姓名,故无法统计)。[69]
第二,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大大加强了琉球王国与明清之间的朝贡贸易关系。琉球遣使中国,名义种种,如进贡、接贡、庆贺进香、谢恩、报丧、请封及接封等等。进贡使每两年进一次常贡;接贡使接回中国皇帝的敕书、赏赐和进京的琉球使臣;庆贺进香使庆贺中国皇帝登基,并向大行皇帝进香;谢恩使代表琉球国王谢中国皇帝特殊赏赐之恩;报丧使告前王之丧;请封使奏请中国派遣使臣祭祀故王并册封新王;接封使来福州迎接赴琉球册封的中国使臣。不管琉球以何种形式遣使来华,目的无非有两个方面:其一,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其二,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促进本国经济上的发展。虽然明清琉球派遣来华的入贡使团官员及员役人数不断发生变化,但久米村人却一直居于重要位置。
据琉球《历代宝案》资料统计,康熙朝(1662—1722)琉球遣华使臣频繁,共遣使团来华至少58次。其中,派专船进贡27次、接贡20次、庆贺进香1次、谢袭封恩3次;此外,还随进贡船或接贡船等遣使报丧3次、请封2次、接封2次。其中,久米村人担任的官职有:紫金大夫3人次,正议大夫33人次,朝京都通事31人次,都通事71人次,存留通事49人次,在船通事28人,火长76人次。[70]
第三,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对琉球国文化的繁荣及社会的发展亦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的戏剧作品,正是通过闽人三十六姓传入琉球。明万历年间(1573—1620),册封使萧崇业、谢杰赴琉球期间,曾观看戏剧演出,回国后记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宫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之。长史恒跽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买胭脂》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亦嫌不使见。惟姜诗、王祥、荆钗之属,则所常演。夷询知,咸啧啧羡华人之节孝云。”[71]这些中国流行的传统剧目,或歌颂尽忠尽孝的封建伦理道德,或歌颂反抗富贵强暴、争取幸福美好的生活,给琉球社会打上深深的中国传统及文化影响的烙印。不仅如此,由于闽人三十六姓的移居,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亦带到琉球。明天顺年间(1457—1464),册封琉球使臣潘荣在应邀游览了万松山、潮月轩、送客桥等八景名胜后,对其设计建造者琉球程均大夫等人大为赞叹:“程大夫,中华人也,用夏变夷,均之职也。果能以诸夏之道而施之蛮貊,渐染之、熏陶之……”[72]正是由于带有先进文化及手工技艺的移民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琉球的辛勤耕坛及传播,琉球国从此“始节音乐,制礼法,不异中国,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73],“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74]。
五、闽人与琉球漂风难民的救助
由于琉球为海岛国家,与外界往来全靠海道维持,在航海工具尚处落后的时代,海难事故自然不断。每当冬、春两季盛行的东北信风刮起时,琉球各岛间或中琉航道间穿行的贡船、商船和渔船便很容易被大风吹刮到闽台沿海。据统计,仅乾、嘉、道三朝(1736—1850),遭风船就多达283艘,难民5000人,其中琉球船只漂风至闽省沿海和台湾岛沿岸占了漂流到华总数的37%左右。飘风至台湾本岛和附近洋面的共计62次,主要地点有鸡笼[基隆]、淡水、宜兰、噶玛兰、彰化、凤山、三貂角等地。飘风至闽省其他地方共计70次,飘至地有福州府的闽安镇、连江、长乐、平潭、福鼎、霞浦、湄洲、惠安、金门、漳浦、厦门等。[75]
明清两朝都十分关注琉球漂风难民的救助及抚恤事宜。明廷规定,每当遇有琉球难船漂风到境,一旦验实,官给豢劳费,驿道送至福建本省,逐名安插柔远驿舍,照口支给,虑饥给养,念寒授衣,保证难民无忧冻馁,完原到国。清承明制。康熙二十三年(1684),礼部奉旨再次重申了对待漂风难民及各国解送人员之规定:“海禁己开,久[各]省民人海上贸易行走者甚多,应移文滨海外国王等,各饬该管地方,凡有船只漂至者,令收养解送。查前此朝鲜国解送漂海人口来者,官赏银叁拾两,小通事赏银捌两,从[人]赏银各肆两,于户部移取赏赐,礼部恩宴一次。嗣后外国如有解到漂失船只人口,照此例赏赐恩宴,遣还其彼处,[收]养漂失船只人口之人,应令该国王奖励赏赐。”[76]中国、琉球乃至东南亚诸国,都十分关注飘风难民的救助、安置及遣返工作。乾隆二年(1737),针对东南沿海各省时常有琉球漂风难船漂至,乾隆帝特颁谕旨:“……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漂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飘泊之人船,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入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77]乾隆帝的这道谕旨不仅要求各地官吏对飘风难民“加意抚恤”,还提出可以“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并且“永著为例”,因而基本确立了对飘风难民的抚恤制度。此后,经过逐步完善,清代最终形成了一整套较为规范的抚恤制度。
由于福州是中方指定中琉间往来的唯一港口,因此福州柔远驿成为琉球及东南亚诸国飘风难民的重要安置地和转送点。难民船只如飘到福州以外的福建各地或外省,照例由各地方当局负责将难民护送到福州柔远驿,再遣送归国。清代规定,难民从到闽之日安置柔远驿始,如系贡船遇风,正、副使每员日给廪给银二钱;官员每员日给蔬薪银五分一厘,口粮米三升;跟伴水梢每名日给盐菜银一分,口粮米一升。起程返国之日,按名另给一月行粮。乾隆朝(1736—1795)时,上谕加意抚恤琉球难民,于是闽省在上述待遇外,另每名发给蓝布四匹,棉花四斤,茶叶一斤,灰面、烟各一斤。[78]对于贡船遭风遇难,清廷抚恤更为优厚。对于琉球沉失的贡品,本着“远道申虔,即与赍呈赏收无异,谕令不必另备进”[79]。乾隆五十八年(1793),同意江苏巡抚奇丰额上奏:“外夷船只因风飘至内地,所有应行估变物件,地方官必当格外体恤,于照值变价外略与便宜,方为柔怀远人之道。”[80]因此,对于琉球难民遭风打捞货物及损坏无法修复船只的变卖,各地官府均特别优惠。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规定贡船损坏赏给工料银一千两,并且永著为例。[81]此外,对于琉球难民的飘来和遣归,福建布政使司都有详细咨文通知琉球国王。难船返航时,布政使司发给执照放行,难民随带的货物进出关时海关循例予以免税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明清历代对中琉关系之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漂风难民相互救助过程中,闽人与琉球民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救助琉球漂风难民的过程中,闽台民众表现出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无偿赠衣馈食,并且时常不怕危险,千方百计给予救赎。如乾隆十一年(1750)正月十五日,琉球麻姑山人多良间亲云上等40人往中山王府送年贡返回,遇风浪漂至台湾彰化县金包里地方,被当地民众下水救起,“即捐给口粮车辆护送至[官]府”。由于难民随身衣服、被褥等俱已漂失,当地官员“酌动公项各制给铺盖一副并各捐俸厚加赏赍,分配商船四只,委员护送赴省”,安顿柔远驿。[82]又如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十一日,琉球那霸府人林廷芳等9人所驾差船陡遇飓风,“漂至台湾琅乔海口,船只冲礁击破,该难夷等凫水上岸,误入生番乡内,均被生番拘留,幸经附近汛弁谕,由土民杨天宝等备银赎回,将伊等送到凤山县衙门,转送台防厅安顿,并蒙给有衣食,由台护送来省”。[83]这里所谓生番即指僻居深山的土著居民,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外来人员抱有敌意,甚至发生误会加以杀害。
与此同时,琉球官府及民众对中国难民的救助亦是尽心尽力。乾隆十六年(1751),一艘琉球难船飘收厦门附近铜山营,由铜山营兵船送到厦门,当时有“厦门行铺金德隆等六人,因乾隆十四年(1749)各有保结船只被风飘至琉球,感中山王抚恤送回。今遇伊国难番到厦,共备猪、羊、鸡、鸭、酒、米致送酬答”[84]。咸丰二年(1852)三月二十一日,美国“罗伯特·包恩”(Rober Bowne)号船从厦门贩运华工410名前往美国旧金山,这些华工分别来自闽省的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等地。途中华工不堪忍受凌辱而举行暴动。四月七日,“包恩”号在琉球国八重山石垣岛崎岐洋面触礁,华工弃船上岸,受到琉球国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救助。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九日,琉球国王世子特遣都通事郑嘉政、王家锦等,“派驾楷船、马舰二只……配载所留华人,一只百四人,一只六十八人,解送闽省”[85]。滞留在琉球的125名华工历经苦难,多亏琉球王府和民众的大力相助,终于于咸丰三年(1853)十月十四日回到了故乡。
清光绪五年(1879),由于日本对琉球的吞并,中国与琉球两国绵延五百余年的友好往来及交流被迫中止,闽人与琉球历史上的特殊情缘也因此暂时中断。自1972年以来,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福建与冲绳友好往来关系的重续带来了新的契机。继1981年5月20日,福州市与冲绳县那霸市正式结成友好城市后,1988年9月23日,泉州市与冲绳县浦添市结成友好城市。1992年,为了纪念福建人移居冲绳600年,冲绳闽人后裔在闽人的居住地建造了久米村发祥地的纪念碑,那是从福州制作的一艘海船石雕,船帮两侧刻着闽人三十六姓的姓氏。同年冲绳人民还在那霸市建造了一个“福州园”,园中建有福州三山、闽江万寿桥和白塔、乌塔等,园中所有的材料都是来自福州。1995年11月20日,厦门市与冲绳县宜野湾市结为友好城市。闽人与琉球的友好交往又开始了新的、更加绚丽多彩的一页。
注释:
[1]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第八十卷,明刻本,第12页。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十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
[2] 张廷玉:《明史》第三二三卷,列传二一一,外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1页。
[3] 胡宗宪:《筹海图编》第十二卷,经略二,开互市,明天启年刻本,第109—11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8—399页。
[4] 高歧辑:《福建市舶提举司志》,1939年铅印本,第36页。
[5][14][15][18][39]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2年,第1,235,270,8,221页。
[6][12] 萧崇业:《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98,99-100页。
[7] 谢 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74页。
[8] 李廷时:《乞罢使琉球疏》,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卷46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040页。
[9] 张学礼:《使琉球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9页。
[10][13][17][29] 陈 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2,17,22,12页。
[11] 谢 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75页。
[16] 新屋敷幸繁:《新讲冲绳一千年史》,日本东京:雄山阁,昭和46年,第237页。
[19] 夏子阳:《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81页。
企业的精神激励机制,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网络系统。在强化企业的精神激励机制时,下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举措都是迫切需要且行之有效的:
[20] 谢 杰:《日东交市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83页。
[21] 李鼎元:《使琉球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155页。
[2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四〇一卷,第1页,“礼部朝贡从人”,嘉庆戊寅修。
[23] 赤岭城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日本那霸:冲绳タィムス社,第13-14页。
[24][27][32][34][40][41][42][77][80][81][82][8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3,20, 715-716,495,9,10,1368-1369,2-3,248,248-249,15,1084-1085页。
[25][50][53][54][55][57][58][64] 球阳研究会:《球阳》,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日本东京:角川书店,昭和57年,第223, 226,206,221-222,259,592,280,300页。
[26] 以上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9页。
[28] 台湾大学编集:《历代宝案》,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第2册,第1277页。
[31][36] 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5,240页。
[33] 赖正维:《清代中琉关系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42—49页。
[35] 赖正维:《清代福建委派官员护送琉球使赴京考》,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3—610页。
[37] 徐恭生:《福州仓山区琉球墓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8] 徐恭生:《中国·琉球交流史》,日本那霸:日本冲绳南西出版社,1991年,第56—57页。
[43][49][52][56][61] 那霸市史编集室编:《久米村系家谱》,《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集第6卷,日本那霸:那霸市役所,1980年,上册,第311,55,365-377,26,295页。
[44][46] 郑国珍:《福州发现琉球国使者墓碑》,《福州晚报》1990年5月9日,第3版。
[45] 伊波普猷等编:《中山世谱》,《琉球史料丛书》4,日本东京:井上书房刊行,昭和47年,第125页。
[47] 球阳研究会:《球阳》,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日本东京:角川书店,昭和57年。那霸市史编集室编:《久米村系家谱》,《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集第6卷,日本那霸:那霸市役所,1980年,上、下册。
[48][51][59] 以上均见那霸市史编集室主编:《久米村系家谱》,《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集第6卷,日本那霸:那霸市役所,1980年,下册,第545-559,932,470页。
[60] 龙文彬:《明会要》第七十七卷,外藩一,琉球,中华书局,1956年,第1503页。
[62] 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239页。
[63] 张学礼:《中山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11页。
[65] 萧崇业:《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112页。
[66] 周 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201页。
[67] 茅元仪:《武备志》,第二一四卷,海防六,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9117页。
[68][76] 台湾大学编集:《历代宝案》,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第1册,第140,226页。
[69] 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日本那霸:冲绳タィムス社,第46-51页。
[70] 台湾大学编集:《历代宝案》,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第2册,第899页—第3册,1878页。
[71] 谢 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79页。
[72][74] 潘 荣:《中山八景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136—137,137页。
[73] 伊波普猷等编:《中山世谱》,《琉球史料丛书》4,日本东京:井上书房刊行,昭和47年,第44页。
[75] 王耀华、谢必震主编:《闽台海上交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78] 台湾大学编集:《历代宝案》,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第9册,第4938页。
[79] 《清仁宗实录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18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63年,第43页。
[84] 台湾大学编集:《历代宝案》,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第5册,第2634页。
[85] 伊波普猷等编:《中山世谱》,《琉球史料丛书》4,日本东京:井上书房刊行,昭和47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