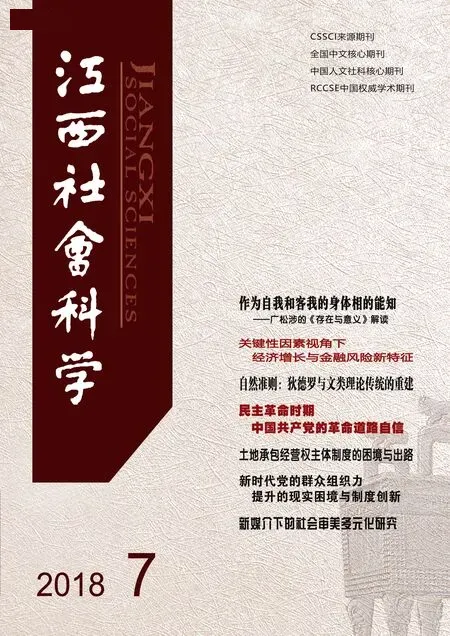地缘、趣缘、学缘、血缘:湘军要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2018-07-26黄民文
■黄民文
晚清王朝内忧外患,命运多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剿灭发捻、抗击外辱、捍卫疆土、筹办洋务、变法维新等过程中,湘军集团成员之间互相提携、互相帮衬、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从而形成近代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湘军。目前学术界对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研究,有部分文章与书籍有所涉及①,但对其进行专题研究者尚少,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以求抛砖引玉。
一、湘军要员之间的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是指“由于长期居住在一起、共同生产和生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1](P156)。地缘关系的种类可以分为同乡关系、邻居关系等。由于同一地方出生、生活的人“受到同样的风俗、习惯、文化的影响往往具有同样的地方性特点”,彼此之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所以同地出生之人往往具有强烈的同乡观念。[2](P39)在交通闭塞的中国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便是地缘关系。
所谓湘军,“主要指晚清50年由湘军统帅指挥,由湘籍士兵为主体组成的部队”[3](P486)。湘军集团就是中国近代这一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军事政治集团。在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中,虽然非湘籍人士不少,如李鸿章、沈葆桢、阎敬铭、马新贻、鲍超等,但湘军集团的绝大多数是湖南人。据王盾《湘军史》所载,前期湘军中共有督抚20人,其中曾国藩、左宗棠、刘蓉等14人为湖南人,占总人数的70%,外省籍只有李鸿章、沈葆桢等6人,占总人数的30%。[4](P11)至于普通兵员,由于湘军将领们认为“同乡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临阵不会败不相救”,所以湘军在招募时,根本“不招无根之勇”,“凡欲招募或增募,必欲回湖南原籍招募,利用同乡亲友关系,相互吸引,编为一营”。[5](P108)正由于此,从前期的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至后期的魏光涛、宋庆、刘松山等所统领的湘军,湘籍成员始终占绝大多数。正如王闿运所言:湘军不仅将领以“湘人为最多”,军中自营官以至下士,也“大抵皆湘人”。[6](P315)
湘军集团成员不仅省域色彩浓厚,而且在湘之内其区域地缘色彩也十分明显。湘军将领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湖南各地,而是集中在部分府县。从同治、光绪两朝湖南籍湘军集团督抚统计情况来看(见表1),两朝湖南籍湘军督抚共30人,其中总督12人,湘乡4人,新宁2人,湘阴、长沙、浏阳、隆回、茶陵、衡阳各1人;18名巡抚中,湘乡5人,新宁2人,益阳2人,新化、衡南、益阳、宁乡、常宁、桂阳、凤凰、湘阴、衡山各1人。可见湖南籍湘军督抚主要分布在湘乡、新宁、益阳、浏阳等地,其中湘乡为最,新宁次之。此外,如果更细微观察,还不难发现,上述30人中,9人在湘乡,1人在新化,1人在宁乡,1人在衡山,1人在衡阳,1人在衡南,2人在益阳,共计16人集中在曾国藩所在的湘乡县及其相邻府县。很明显,湘乡为湘军将帅的集聚中心。②

表1 同治光绪两朝湖南籍湘军督抚统计表
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所以在湖南境内同样会呈现出强烈的区域地缘色彩,原因有二:其一,湘军建立之初,军队主要来源于江忠源、罗泽南、王錱的三支团练队伍。[7](P49)前一支队伍分布在新宁,而后两支队伍分布在湘乡。而且湘军后续招募过程中,将领们也往往回自己家乡招募。譬如,曾国荃在招募时,“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8]将从兵出,毋庸置疑,湘军督抚将帅也就多出自新宁、湘乡两地。其二,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传统中,由于“地缘关系的封闭型很强”,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地区观念、乡土观念、老乡观念”。[9](P34)这些观念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曾国藩、江忠源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疑会对其队伍中的同乡故里予以帮助、提携。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曾、江的继任者也同样会如此。故而便形成近代以湘乡、新宁两地人物为核心的湘军集团。但由于新宁的领头人江忠源英年早逝,其职位、功绩及其与晚清中央政府的人脉关系均不如曾国藩,故其所提携和影响的乡人也便比曾国藩少。又由于前一代人功德与地位影响后一代人的成长进步,故江忠源、曾国藩之后的第三代、第四代督抚将帅中新宁籍人员也比湘乡籍人员少。
二、湘军要员之间的趣缘关系
趣缘关系是指志趣相投之人结成的人际关系。共同的兴趣、爱好、理想、志向、价值观念等是他们结成友谊的基础。这种关系比较单纯。由于志趣相同或相近使他们之间相互认同,相互欣赏,甚至相互支持,因此这种关系的牢固性有时甚至超越其他关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的性格、爱好不尽相同,但湘军集团主要成员在身份、理想、价值观念等方面十分相似,所以他们的趣缘关系也比较相近。
首先,他们大多为士子一类,趣味相投。据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首脑及骨干成员共475人,其中,文职人员211人,具有文童以上学历者208人,高学历者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10](P83)至于督抚以上者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等则多为举人以上。正由于他们都为士子,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能惺惺相惜。譬如曾国藩与刘蓉,两人初次见面便“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③数年后,曾国藩从浏阳过往长沙时,又逢刘蓉、郭嵩焘在长沙会试:“(三人)相见欢甚!纵谈古今,昕夕无间。留月余,始各别去。”[11](P635)后来曾、刘两人还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常“彻夜长谈”,不在一起则不断通信,谈古论今。[12](P145)又如左宗棠与胡林翼,两人于道光十三年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相识后:“一见定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11](P11)他们即使性格相异,也往往相互十分敬重。如曾国藩与江忠源,两人性格迥异,曾国藩老成持重,江忠源“任侠自喜”。但自江忠源在北京参加考试拜见曾国藩后,曾国藩甚顾惜其才[11](P639),对江多有帮扶,江忠源也对曾国藩投桃报李,在曾国藩奉旨筹办团练后,对其鼎力相助。至于其他,如李续宾与王錱的长兄王勋也以“‘道义性情相孚’,自十二岁订交,多年一直往来不辍,互证所学”[13](P90);刘典与罗泽南也曾“一起在城南书院切磋学问”[14](P162),“互研性理”,十分“交厚”[4](P391)。
其次,他们大都崇奉理学,理念相近。湘军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仅多为读书人,而且他们所崇尚的学术也多倾向于理学。如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刘蓉、郭嵩焘、胡林翼等莫不如此。曾国藩31岁开始随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以朱子之书为日课”,32岁后更加致力于程朱理学,常与理学名家倭仁、吴廷栋、陈源衮、何桂珍、宝仁和、邵懿辰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至其筹办湘军时则以理学治军,选拔将领讲求“忠义血性”。[15](P7)罗泽南则“比曾国藩更像理学家”,他“不仅按照理学家的方式修身、讲学,且有理学著述《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西铭讲义》等刊行于世”。[16](P392)罗泽南经年讲学,其诸弟子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也多受其影响,而崇尚理学。左宗棠5岁入私塾,6岁开始接触《论语》《孟子》,20岁就读于城南书院,师从湖湘名儒贺熙龄,贺对其极为“伟重”,常“授以汉宋儒先之书”,“诱以义理经世之学”。[17](P138-139)其26岁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便取“朱熹《小学》8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18](P220)。其出仕之后,更在为官之地大量刊刻理学著作,希望“以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19](P191)。刘蓉“早岁溺于记诵词章之习”,但“泛览累年,茫然无所得”。[20](P94)后长期游学于岳麓书院。刘蓉入岳麓书院后便浸润于理学,认为:“夫程朱卒不可议,议程朱者非妄则诞。”[21](P128-129)郭嵩焘年少时亦从事辞章之学,后受密友刘蓉等人的影响也致力于理学,赴京会试拜访理学大师唐鉴后,知理学应在“日用行习之间,辩之明而守之严”,便“躬亲实践”于理学。郭嵩焘对理学义理见解独到,著有“性理精义札记”“《大学》《中庸》章句质疑”等作。[22](P8-9)胡林翼出身于理学世家,其父系晚清理学名家胡达源,其岳父系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代表人物陶澍。胡林翼7岁时,陶澍便视其为“伟器”,而以女“字之”,自后更大力栽培。受胡达源、陶澍影响,胡林翼自幼以理学为宗,日后成为晚清时期与倭仁、曾国藩齐名的理学核心人物。[23](P112)
再次,他们多讲求经世致用,重视洋务,思想趋同。晚清湘军集团成员多倾向理学,以理学经世。理学经世是湖湘理学的传统,发源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再传弟子胡安国、胡宏父子,传承于明清哲学家王夫之,近代以来由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人所开启。湘军集团理学士人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其中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曾国藩堪称晚清理学经世第一人,其修身“以朱子之书为日课”[24](P19),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为行事准则;其募兵以“朴实”为上,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其选将惟“将德”首论,要求将领必“有忠义之气”[25](P212-213);其研究学问重视“经济”实学,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其更认为“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并将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作为自己经济之学的必读之书[26](P94-96);其一生镇压太平天国、清剿捻军、筹办洋务也大凡皆以理学为指导。胡林翼也可谓理学经世的典型,他“鄙视和反对理学庸儒泥古不化、不切实际的空谈和迂腐”,以“居敬穷理”除暴安良,以“讲明义理”为教战之方,主张整理财政,严禁贪污中饱,倡导用人首重气节,选才不拘一格,务求人尽其用。[27](P21-26)除曾、胡二人外,湘军集团其他成员也多讲求理学经世。正由于湘军集团主要成员多本理学而经世,故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以义理经世的理学群体。[25](P212)
由于讲求经世致用,湘军集团主要成员的夷夏观念不同于同样崇尚理学的倭仁等保守派。倭仁等人坚持华尊夷卑,反对师事西方。湘军集团成员则继承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精神,在看到西方的长处后力主学习西方,发展洋务。譬如,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看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后,便倡导“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期“永远之利”,从而创建中国近代第一个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又奏请清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由此诞生。左宗棠身为闽浙总督,看到中国的海防与航运都受制于洋人后,便奏请清廷“精炼兵勇”,“仿造轮船”,继而主持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船舶制造厂——福州船政局,并创办船政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郭嵩焘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之后,洋人“与中国交接往来”,已成“为一定之局”,为通晓洋务、少生衅端,而忍辱负重、出使英法。[28](P370)
三、湘军要员之间的学缘关系
学缘关系是在学习或学术研究与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涵盖师生、同窗、学友等关系。这种关系比较纯洁,彼此之间往往容易结成真诚的友谊。在中国,由于尊师爱友的文化传统,往往还会以此形成一个相对牢固的人际关系圈。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另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便是学缘关系。④
在湘军集团的学缘圈子中,首先是罗泽南的师友关系网。罗泽南系双峰石牛乡(旧湘乡中里)人,“19岁开始以授徒为生”,“先后任乡间塾师讲学20多年,所授学生,多为湘军悍将,或学者名儒”。[29](P72)其弟子中从二品以上湘军将领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6人;追随其南征北战以至战死的将领有钟近衡、钟近濂、罗良干、罗信东、罗镇南、谢邦翰6人;此外还有王开仍、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翁筼登、潘鸿焘、左枢、罗信南等“不尽从征战”,但“颇有时名”者多人。[30](P52-54)此外,曾国藩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也都曾从学于罗泽南。[31]正由于罗泽南与众多湘军将领是师友关系,且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以罗泽南及其弟子所筹的乡勇团练为基础,因此有人将曾国藩称为湘军之父,而将罗泽南称为湘军之母。除了学生之外,罗泽南还与一些湖湘近代名儒保持了良好的学友关系。罗泽南在城南书院从学时,宁乡刘典、浏阳谢景乾曾与之“讲习讨论,互相砥砺”。在长沙时,罗泽南还与郭嵩焘兄弟“来往问学”,且“相得甚欢”。罗泽南42岁时,云贵总督贺长龄、太常寺卿唐鉴居家,罗泽南也都曾“往语学问”,且十分融洽。贺长龄临终前甚至“遗命其子延为师”。有小诸葛之称的湘军幕僚刘蓉,与罗泽南则亦师亦友。在刘蓉与罗泽南交往中,罗泽南“与语《大学》明新之道”,刘蓉至为叹服,互订“莫逆”之交。此后十余年间刘、罗常“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30](P6)
其次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的师友关系网。曾国藩在湘军集团中的师友关系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师生学友,另一类是幕僚部属。在学友中,曾国藩与刘蓉、罗泽南三人为涟滨书院同窗,且曾同处一室,“换帖称兄道弟”,“结为好友”。[32](P189)曾国藩与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等都曾在岳麓书院深造,互为岳麓书院师兄弟。[33](P68-69)在师生中,曾国藩是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业师。李瀚章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国藩门下”,1853年入曾国藩湘军,曾国藩“十分器重李瀚章”,李瀚章也将曾国藩“倚为靠山”。[34](P129)李鸿章在甲辰年入都会试时“受业”于曾国藩,后亦“投身湘军幕府”,曾国藩以“伟器”称李鸿章,李以“神圣”敬曾。[35](P1)至于幕僚部属,曾国藩虽然并没有与他们有真正学业上的授受经历,但曾国藩对他们多有栽培,故而也形成一种师生关系。如庞际云、陈士杰、洪汝奎、李榕等曾氏幕僚,只是在考取功名时曾国藩担任过他们的考官或阅卷大臣而已,但都被视为曾国藩门生。还有更多幕僚甚至连这种关系都没有,但由于曾国藩一直对他们“精心培养,视若子弟”,而他们对曾国藩也“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36](P265-271)故彼此亦有师生之谊。刘长佑、彭玉麟等曾氏部属同样如此。他们与曾国藩也无直接的学业授受关系,但在交往过程中,曾国藩对他们多有指点提携,故而自视为门生。譬如,刘长佑在得曾国藩提携后始终称曾国藩为老师。[37](P221)彭玉麟也在得曾国藩举荐后长期自视为曾国藩门生。
除罗泽南、曾国藩以外,其他湘军将帅之间也有不少人存在师友关系。譬如李续宾与杨昌浚均师从罗泽南,互为师兄弟。李续宾的儿子李光久从7岁至14岁受业于杨昌浚。[38](P3)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受学于曾国藩幕僚王闿运,为王闿运弟子。[39](P356)陶澍与左宗棠为忘年交,陶澍逝世后左宗棠亲自教导陶澍的儿子陶桄,为陶桄业师。[40](P3)左宗棠早年在长沙开馆授徒,周开锡曾“与之受教”[41](P160)。左宗棠、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等又都“曾受教于贺熙龄”[42](P16),故他们也可以视为师出同门。刘坤一则“自幼师从江忠源”[43](P135),为江最得意的门生。戈鉴早年“从老师储玖躬与太平军作战,受其训”[44](P122),后以战功加布政使。至于其他中下级的军官中也有不少互为师生、同窗。因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在组建湘军时曾“充分发动士大夫、士绅”尤其是岳麓、城南书院等各府州县书院生员、童生投入湘军,使之“成为基层营哨官或营务幕僚”。所以湘军中许多中下层人员亦具有师生、同窗之缘。[4](P4)
四、湘军要员之间的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以婚姻和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⑤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往往以血亲或者姻亲相联结。
在这种血亲关系中,曾国藩家族最为凸显。曾家在湘军集团中成员众多、地位显赫,除湘军统帅曾国藩本人外,还有其兄弟两江总督曾国荃、追赠按察使曾国葆、湘军统领曾国华,其儿子兵部侍郎驻外大臣曾纪泽、兵部武选司郎中曾纪鸿,其孙子福建兴泉永兵备道曾广铨、御前散秩大臣曾广銮、广西知府曾广钧、湖北按察使(署)曾广镕、候补道曾广钟。曾国藩兄弟家庭中军政要员也为数不少。曾国藩四弟曾国潢的儿子中有中宪大夫曾纪梁、奉政大夫曾纪湘,孙子中有江苏候补道曾广祚。曾国藩五弟曾国葆的儿子中有广东惠潮嘉兵备道曾纪渠,孙子中有枣阳知县曾广敷、中书科中书曾广镛,曾孙中有安徽补用知府曾昭楙。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的儿子中有湖北榷运总局局长曾纪寿,孙子中有陆军部主事曾广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儿子中有兵部员外郎职方司行走曾纪瑞、户部员外郎云南司兼广东司行走曾纪官,孙子中有都察院左都御史曾广汉、刑部奉天司行走曾广河、安徽候补道曾广江,曾孙中有法部会计司郎中曾昭言、邮传部员外郎路政司行走曾昭篯。[45](P234-249)总之,曾国藩家族上上下下近30人在清廷任军政要职,为湘军集团中的第一大家族。
除曾国藩外,其他湘军将帅的亲属后辈也有不少人为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譬如,左宗棠家族中有左宗棠儿子兵部主事左孝勋、举人左孝威、江苏按察使左孝同。[46](P74)郭嵩焘家族中有郭嵩焘弟弟内阁中书郭昆焘、贵州补用道员郭伦焘及郭昆焘之子浙江知府郭庆藩。[46](P402)江忠源家族有江忠源兄弟广西提督江忠义、参将江忠信、福将江忠济及江忠源儿子兵部郎中江孝棠。刘长佑家族中有其族叔两江总督刘坤一,其同辈四品京堂刘纪能、千总刘长伟,其子侄凉州同知刘思询、二品荫生特用通判刘思诣、广东佛岗同知刘思谦、兵部郎中刘思训、四川候补知府刘思祥等。[47](P281-286)李续宾家族有其兄弟安徽巡抚李续宜、武昌镇总兵李续焘、总兵李续远、知府李续艺,其子侄浙江按察使李光久、贵州补用道李光燎、直隶知州李兆焯等。[48](P268-270)刘岳昭家族中有其同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和刘岳晙、江西候补知府刘岳昕、太傅寺卿刘岳旸等。[48](P273)
湘军集团中之所以有许多人为父子、兄弟、祖孙等,一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江忠源、刘长佑、李续宾、刘岳昭等人在发迹的过程中带动自己的亲族同进同退,一起建功立业,封官加爵。如曾国藩带动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刘岳昭带领自家子弟刘岳旸、刘岳昀等一起参加湘军,故而得以共同提升。二是由于这些人注重对自家子弟的培养,在自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时,也督促自家子弟修身养德。譬如曾国藩,单后人整理的家训书籍就有多种。三是由于封建时代官爵的世袭,使得这些人的后辈能继承爵位,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罗泽南的儿子罗兆作、李续宾的儿子李光久等无不以此取得爵位。
湘军集团中不仅有众多父子兄弟,而且有许多儿女亲家。通过这些姻亲关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结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权势网络。这些姻亲关系中最为显著的同样是曾国藩家族。曾家后辈数代中不少人与湘军要员子女结为夫妻。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原配云贵总督贺长龄之女,继配陕西巡抚刘蓉之女。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娶两淮盐运使郭沛霖之女郭筠,次女曾纪耀嫁池州知府陈源衮儿子陈远济,三女曾纪琛嫁湘军猛将罗泽南之子罗允吉,四女曾纪纯嫁广东巡抚郭嵩焘之子郭依永,小女曾纪芬嫁广东知府聂亦峰之子聂缉椝。曾国藩孙子曾广镕娶宁夏知府黄自元之女,曾广铨娶曾国藩幕僚按察使李元度之女,孙女曾广璇嫁李鸿章侄子李经馥,曾孙曾昭权娶李续宜重孙女李懿康,玄孙女嫁李续宜重孙李进崧,重孙曾昭健娶陶澍玄孙女陶希庆。除位高权重的曾国藩以外,曾国藩兄弟及其后人也有不少与湘军权贵结为儿女亲家。如曾国华曾孙女曾昭楣嫁两广总督谭钟麟孙子谭季甫(谭延闿之子)。曾国潢长子曾纪梁娶湘军将领魏承樾之女,次子曾纪湘娶湘军将领易良干女儿。曾国荃孙女曾广璈嫁左宗棠孙子左念贻,孙子曾广江娶陕西按察使唐树楠之女,曾孙曾昭言娶两江总督魏光涛之女。曾国华之子曾纪寿娶李续宾之女,孙子曾广钦娶曾国藩幕僚刘瑞芬之女,孙女曾广镛嫁湘军猛将李续宾之子。[49](P232)
较为显著还有左宗棠家族,虽然左家的姻亲关系没有曾家那样权贵色彩明显,但左宗棠子孙的婚姻也大抵讲究门当户对。据载,左宗棠的子女中左孝威娶山东道监察御史贺熙龄之女,左孝同娶湘军猛将王錱之女,左孝勋娶道员夏廷樾之女,左孝瑜嫁两江总督陶澍之子陶桄,左孝琳嫁候补道黎福昌。左宗棠的孙辈中左念恂娶两江总督魏光焘侄女,左念慈娶湖北巡抚李续宜孙女,左念康娶闽浙总督杨昌浚侄孙女,左念惠娶曾国华外孙女,左念谦娶按察使陶桄之女陶敬仪,左念贻娶曾国荃孙女曾广璈,左念蘸娶李鸿章侄孙女李国裕,左念恒娶新疆巡抚饶应琪之女饶君枚,左又宜嫁江苏提学使夏敬观(剑丞),左静宜嫁邮电部维新派官员龙绂慈(达夫),左念宜嫁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之子聂其昌。左宗棠的第四代也延续这种湘军将领之间的姻亲关系,左宗棠曾孙子左景昌娶的是李续宜曾孙女,左宗棠曾孙女左伯瑾嫁的是陶桄的曾孙。⑥
除曾、左二人外,其他湘军集团成员子孙后辈互为姻亲者也不胜枚举。如郭嵩焘家族后辈中,郭嵩焘三子郭立辉娶按察使李元度之女,五女适左宗棠侄子左浑,六女适李鸿章侄子李经方。郭昆焘(郭嵩焘弟)次女嫁户部郎中舒焘之子舒习勤,三女嫁安徽巡抚江忠源之子江芾生。⑦陶澍家族⑧后辈中,陶澍之女陶瑱姿适监察御史贺熙龄之子贺毂,陶瑗姿适湖北巡抚胡林翼,孙子陶益谦娶左宗棠侄孙女左颖荪,孙女陶和贞适胡林翼之子胡子勋。[50](P351-361)聂缉椝家族中,聂缉椝之子聂其炜娶广东提督刘松山孙女,聂其贤娶浙江杭嘉湖道陈乃瀚品之女,聂其煽娶四川盐茶道黄承暄之女,聂其煐娶刑部郎中李瀚章之女。[50](P351-361)此外,王錱与杨昌浚、康景晖,胡林翼与左宗棠、罗泽南,李续宾与钟近衡,江忠源与刘长佑……都有姻亲关系。⑨总之,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门当户对、互相交好,姻亲关系十分复杂。
五、结 语
综上可见,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纷繁复杂。他们大都来自三湘四水,有天然的同乡之缘;他们大都崇尚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他们之间多有师生之谊、血缘之亲,有紧密的情谊关系。这些牢固、深厚的人际关系构成湘军集团主要成员聚合共生的重要前提。譬如,罗泽南、王錱筹办团练时其骨干成员多来自于自己的学生,依靠的是师生之情;李续宾、李续宜招募团练队伍时,被招人员多来自于其故土的李氏家族,依靠的是血缘之亲;江忠源在新宁筹建楚勇时,参与者多为同族与同乡,倚重的是血缘与地缘之因。再如,刘蓉、郭嵩焘力劝曾国藩“墨袆从戎”,出道筹办湘军,是源于彼此之间缘趣相投,情义相合。[33](P140-141)罗泽南、王錱、江忠源、刘蓉、郭嵩焘、李续宾、彭玉麟、李鸿章等都追随曾国藩出生入死,除了曾国藩的人格魅力以外,更重要的还是源于他们之间的同乡之谊、师生之情、血缘之亲等人际关系因素。
这些紧密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之间相互帮衬与提携。曾国藩奉旨筹办团练之初无兵无粮,罗泽南将自己的千余湘勇交与其训练指挥,江忠源率领自己的楚勇听从其差遣调度,郭嵩焘想方设法为其筹办粮饷,刘蓉、彭玉麟不取薪酬为其筹划操劳。在罗泽南、王錱、江忠源等人支持曾国藩的同时,曾国藩也对他们大力提携。以罗泽南为例。曾国藩对胡广总督吴文镕说:罗泽南“实学识过人,可与谋军事者也,视张润农、王漠山皆迥出其上”[51](P224)。他对湖南巡抚骆秉章说:“罗山酝酿甚深,德望为敝邑所推服。来示评骘,极为谛当。”[51](P328)他对咸丰皇帝说:“管带湘勇委员罗泽南,行军整暇,沉毅有谋……请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请赏戴花翎。”[52](P56)至于其他湘军将领,如刘蓉、杨昌浚、李续宾、李续宜等也无不得其推举而擢升。曾国藩甚至对追随其出生入死的普通兵勇大力提拔。从湘勇出师起,到同治年间,“曾国藩所部湘军达12万人,其中保举的当不下万人”[32](P151)。正由于他们之间互相支持和提携,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一个关系紧密的军事政治集团。
这个军事政治集团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地位举足轻重。湘军鼎盛时期,人员数十万,五十多年中,其“督、抚、提、镇遍天下,防区逾十八行省,军功保举参、游以上逾六千人,其中提、镇即达一千五百人”[4](P13)。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集团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罗泽南、刘蓉、李续宾、杨昌浚、胡林翼、刘长佑、杨岳斌、彭玉麟、劳崇光、骆秉章、江忠源、刘坤一、刘岳昭、刘锦棠、蒋益澧、魏光焘、谭继洵、王之春等晚清重臣⑩,他们占当时晚清督抚数量的近六分之一[11]。而且他们任职之久、地位之重非其他督抚可以比照。
正由于这个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在岌岌可危的晚清王朝中,从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到筹办洋务巩固大清基业,从发展海防保障海疆安全到收复西北维护西部疆土,从政治改革变法图强到出使西洋维护国权,无处不显现他们效忠清朝、效忠国家的身影。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存在,大清帝国早就被内乱外敌所颠覆,国家的领土也早就被西方列强所侵占。另一方面,在挽救清王朝的危机中,清帝国不得不赋予他们更多的政治、军事、人事与财政权力,从而使地方督抚中汉族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这不仅打破了晚清王朝的满汉之防,更动摇了满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当清末新政要收回这些督抚的权力时,他们走向了对立面,在武昌首义后有的甚至宣布独立,进而加速清王朝的灭亡。然而其影响并不仅止于此,民国以后,各地军阀甚至以晚清督抚惯有的权力体制为基础各自为政,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总之,湘军集团左右了中国近代的发展,而这个集团形成的基础是他们之间紧密的地缘、血缘、趣缘、学缘关系,因此人们在研究近代湘军、甚至近代中国历史时,绝不能忽视这些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
注释:
①对湘军集团人际关系涉及较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东安的《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成晓军的《曾国藩家族》、王盾的《湘军史》、胡卫平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等。
②这里的湘乡指曾国藩生存年代的旧湘乡县,包含今双峰、娄底市区、涟源及湘乡一部分。
③对曾国藩与刘蓉初次见面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道光十二年两人于涟滨学院初次见面,一说为道光十四年两人于朱氏家舍初次见面。具体见谭云良的《曾国藩与湘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这里根据年谱记载而论,见熊治祁《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页)。
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际关系主要有血缘、地缘、趣缘、业缘关系几种,业缘关系中主要包括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学友关系、主宾关系等。由于湘军集团成员的同事关系——即都属于湘军一员,在《湘军志》《湘军史》等书籍中多有论及,故本文主要从学缘关系——即师生、学友关系角度来进行梳理其业缘关系。
⑤姻亲是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包括配偶的血亲如岳父、夫之妹、亲家等,及配偶的血亲的配偶如妯娌、连襟等。血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是以具有共同祖先为特征的亲属,包括直系血亲如父母、子女等,及旁系血亲如兄弟、叔伯、侄子、外甥等。
⑥参见李连利《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华中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左焕奎《左宗棠略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参见《湖南省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谱牒)》。
⑧陶澍虽然不是湘军集团一员,但其子陶桄为左宗棠女婿,其女婿胡林翼为湘军重要成员,故其后人亦为湘军集团成员。
⑨王錱四女许杨昌浚之子杨鸿度,王錱长女许康景晖之子,李续宾子李光久聘钟近衡之女,胡林翼的妹妹嫁左宗棠的侄子;胡林翼季妹嫁罗泽南之子,江忠源侄女嫁刘长佑之子。
⑩王盾的《湘军史》统计了前、中、后三个时期湘军集团主要成员。湘军前期有:总督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杨岳斌、毛鸿宾(湘军幕僚、非湘籍)、劳崇光(湘籍、非湘军出身)、郑敦谨(湘籍、非湘军出身)、骆秉章(与湘军关系密切、非湘籍),巡抚曾国荃、唐训方、刘坤一、江忠源、李续宜、江忠义、田兴恕、刘蓉、郭嵩焘、胡林翼、沈葆桢(湘军非湘籍)、阎敬铭(湘军非湘籍)、李鸿章(湘军非湘籍)、马新贻(湘军非湘籍)、李孟群(湘军非湘籍)、恽世临(与湘军关系密切、非湘籍)、张亮基(与湘军关系密切、非湘籍),提督李朝斌、黄翼升、李成谋、鲍超(湘军非湘籍)、江长贵(湘军非湘籍),兵部尚书彭玉鳞。湘军中期升任总督者有曾国荃、刘坤一、刘岳昭,升任巡抚者有刘振堂、刘典、蒋益澧,另有藩臬15人、提督24人、总兵54人。湘军后期升任总督者有魏光煮、杨昌浚、李兴锐、谭钟麟,升任巡抚者有陈士杰、周开锡、谭继询、游智开、王之春,另升任藩臬16人、道员39人、提督12人、总兵41人。
[11]根据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所载(见该书第60页),同光两朝共有总督、巡抚266人。而据王盾《湘军史》载湘军集团督抚占了40余人,故湘军集团成员所占当时督抚的比例约为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