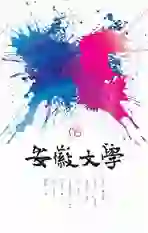采菊
2018-07-20吴艺
吴艺
一
小区公园里那几株红枫叶子开始红了起来,满腹心思,感染得踏枝的黄眉、柳莺暂歇了歌唱,歪着脑袋一动不动,似乎它在想着如何应对萧瑟之秋的袭来。公园一角,那几十株相拥的合欢林慢慢泛黄,从春夏的青枝绿叶般单纯经由岁月的推移来至暮秋的宁静与熟稔,此时的枝柯之间似乎一下就有了不离不弃的情谊,亦如朝阳亦似晚霞;如同树名,无不寓意彰显。铺满河堤的酢浆草,比之前瘦了许多,粉红色的花已凋落得所剩无几,与它周围的黄壳竹形同天涯旅人……
感受着这些植物世界所呈现的秋暮之气,内心难以平静如水,念着过去那些本应该美好温暖的烟尘生活不可重新来过,想着久远的自己心向往之的皈依之所终不至于如飘逝的尘埃。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比知情识趣更让情怀郁结的人留恋与追寻的呢?
这样的季节,菊花应该盛开了吧?万物萧索的沉郁,寒霜覆盖草叶的凄惶,夜晚辗转思归的人……在这样博大浩渺的时空里所有的主观都是无能为力的,看着眼前琐事如水流走其实什么都做不了,就像握不住手掌里的流沙。当一缕菊香的季节来临,需要它的绽放奉送冰洁情怀,人淡如菊的处世态度,为染疴的思绪与无状的光阴疗伤。人海里行舟,喧嚣的浪涛溅沫于身随时都可能把你湮灭,你还能到哪里遁世?与菊花相伴,内心的世界就会落下纷纷的雪花,覆盖杂乱的足迹。人生其实都是旅途,要么地理上,要么心灵上;用足迹丈量的那叫沿途的风景,用心灵感悟到的是人生的苍凉。浑浑噩噩與随波逐流的人群有几人能彻悟——你一出生就迈向衰老的路上,都是路过此生而已。淡泊物质与功名,追求精神世界的充盈显得稀缺但令人向往。
对此,需要一种有形的寄托。在古典的世界里,面对的是物质匮乏、生产资料短缺的年月,但充满着农耕的诗意。虽然住着茅草屋,柴扉虚掩,篱下丛菊,月下独饮,物质的欲望微乎其微,心里却是干净和愉快的。寄情于山水,远离庙堂遁世江湖,与所谓的功名、利禄做个了结。而不是只会在失意的时候才想起《好了歌》,再怎么凄凄惶惶也难回到过去。
二
不过,自从选择羁旅异乡,来到太湖南岸的这座小城为稻粱谋之后,我已很久没有见到菊花了,特别是几万丛五颜六色的菊花争相盛开吐蕊,视觉之惑近乎晕眩。
那还是在老家,江南的富庶之地,不仅有鱼米之乡馈赠的殷实的日子,更有年年的菊花盛开。那时,几乎每年从国庆节开始,在市中心的赭山公园就要举办一个大型的菊花展,各个品种的菊花汇集在这里,每个颜色的都有。它们被放置在搭建的主题不一的舞台上,这些冷艳华美的菊花像戏曲中的角色,用静止的色彩完成祝祖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寓意。
那时我应该还在读初中吧,一个懵懂而又忧伤的少年,喜欢离群索居,经常会跑到赭山的深处,隐身在各种植物的包围中,在这样干净没有纷争的世界里久久不想回家。菊展的喧闹,像是侵占了我的领地。那时,我还不知道所谓的魏晋名士,还有采菊东篱的陶渊明等,要不也能发几句感慨,理解这些赋予了新意却违背了本意的菊。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上溯以往,我其实最向往的是魏晋的放达、盛唐的瑰丽以及宋元的山水,我偏执地认为,只有这三个历史时期除了血腥的政治外还有生活的诗意和文人的任性不羁可以共存,彰显着个性,本真着自我。
就拿魏晋来说,那时时局不稳,政权的更迭、权力的转移犹如“走马灯”令人眩晕,而士人阶层却嗜酒成风,毫无节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要在纷乱的时局中韬光养晦,便以嗜酒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超脱。我倒认为这是名士们追求旷达放任,并以饮酒作为表现形式而已,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生态,毕竟还有许多的名士在朝为官,也都安然无恙。
他们无非饮酒、服药、清谈,隐遁在政治以外的桃花源里享受着农耕馈赠的诗意,令后人们向往不已。孔群每当田里收成不佳时,他关心的不是口粮不够的问题,而是担心不够酿酒用的;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厨房里贮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其实最让人击节称赞和扼腕唏嘘的当属嵇康,他因连坐获刑要斩于东市,他却惦记着古琴谱《广陵散》要失传,后悔没有把曲谱传授于人,并要来古琴现场抚弦,这幅断头台上慷慨悲歌的场景成为古典文人精神世界的高峰,却也那么的悲凉……这些众生相如同恒河数沙遗留下的金粒,一直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闪光。
瑰丽的盛唐,在灿若晨星的文人士族中,似乎只有李白最个性鲜明地完成了“嬉笑怒骂”的人生。他笑傲王侯,蔑视世俗,指斥人生,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让国舅为其磨墨、力士为其脱靴的任性之举,无不酣畅淋漓,令人击节称赞。在那样伟大的历史时期,其实有更多的文人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绊,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李白似的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口无遮拦,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李泽厚先生为此总结说:“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所处时代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的。”
至于宋元山水,绝不能仅仅认为是“望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客观存在,这更多的是文人们隐遁山水自然的主观表达,一种精神上的至高无上,犹如陶渊明眼里的菊花世界。宋元山水表现出充分的任性,恍若想象中的“魔界”,如王诜《渔村小雪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即使作者为画标明了地址也难按图索骥到真实的面貌。或许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千世界,变化万千,一滴水、一粒沙、一枚叶、一只鸟,其实都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如果把“宋元山水”看成一个符号,那它释义应该是:脱离世俗羁绊的充满想象力的奇幻表达,是时间也无法抵达的高处。
三
其实我所喜欢与向往的这样三个历史时期,更多是我内心那丛清香幽渺的菊花的文化意义使然。
这清雅淡然的菊,自从有了陶渊明,就被上升至文人精神世界的一处皈依之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或许是渊明退隐庐山脚下劳动之余休憩时的一个瞬间,而这就被定格为传统文人士大夫们仕途失意时所向往的一种生活的再现。纵观历史,仕途无非两字——失意;而仕途中人,又多是诗词歌赋以及文章高手,失意之时,要么寄情文字,要么避世过“菊花”一般的日子。
而超脱人世的陶渊明是宋代苏轼发掘出来的形象。在只有出仕才能实现男人们以及家族荣耀的漫长年代里,这是唯一的晋升与存世之途,渊明也不例外。在他入仕之初做祭酒这样的小官时,曾写有《劝农》谆谆教导所邑乡人勤于农桑;而《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鲁迅说,“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起初的渊明所谓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只是一种外在现象。不过,那时真正的文人入仕者大凡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精神操守,一旦感知到非主观溃决之时,会采取一种政治性的退避,过一段隐居生活;但只有渊明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在他为官八十余日写下的《归去来兮辞》即表明心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是怎样去意已决,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
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中践行的那样,“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彻底与轩冕荣华、功名利禄决裂,并在田园躬耕中营造诗意,实现内在的人格完美,这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的质朴的眷恋中找寻到了精神的出口——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
而推崇陶渊明的苏轼又何尝不是因仕途失意才体悟到“菊花”的价值呢?这犹如是文人们丢失的魂!
四
现如今,在这样的深秋,我是多么渴望遇到能点亮心灵的丛丛菊花。客居苕上,旅人的身份是逃脱不掉的,就像黥在我内心的印迹,时时刻刻提醒——我是没有故乡的人。
但我心灵与精神的故乡从没迷失过。特别是近几年,我几乎把所有的闲暇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沉浸在这个丰赡而多彩的世界里,会发觉有形的物质是那样的短促与虚幻,重新思考的人生意义越发清晰可辨。
有时会想,老家的菊花展已经停办多年,或许会随着岁月的久远淡出我的记忆,但少年时代的青涩因为有了菊香的熏染,会是成为诱惑让我迈进精神与心灵故乡的迷香吗?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