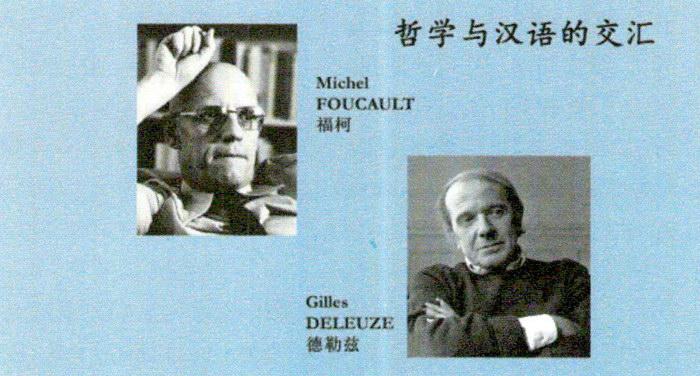“月球语言”
2018-07-17白乐桑
白乐桑
“您为什么学习中文?”这是我四十年来经常被问及的问题,直到近些年我才发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我学习中文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人们问我,您为什么学习中文。”
四十年前,中国打开大门欢迎第一批外国学生,那是1973年11月18号,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星期天,下午四点,从巴黎奥利机场起飞,到达罗马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然后抵达开罗,又停了一个小时,在开罗机场喝了杯薄荷茶,机场上摆放了几架伪装过的小型战斗机。接着是潮湿空气中经过的卡拉奇、仰光,最后才到达目的地——北京。
经过22小时的漫长旅程,在降落前的几秒钟里,终于透过玄窗向中国瞥去了第一眼。夜色深沉,没有前灯的自行车影子在道路上模模糊糊地移动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张贴在机场主楼显眼的地方。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记录着这一天的飞机起降情况——这就是我的第一眼中国印迹。
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中国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之后还上百次地在中国旅行。这些在中国的印迹是我个人的历史,也使我的感觉、情感、感受和想法一点点发生变化,时光流逝,那些听到的声音,记住的词语越来越带有真实的意义。
如果一滴水珠真的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也许可以使我们跨越文化异质的表层,跨过平常感觉到的并不真实的现实,隐约看到另一种语言和书写系统留下的印迹,它告诉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后来长期从事教学法和教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我一直对个人因素,特別是个人的心理因素非常重视。所以,当自己在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有了不小的名气的时候。我也不得不开始对自己从小进行反思,特别是思考在我一生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你觉得汉语四声调难学吗?我走上汉语之路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从个人角度说,我儿时有哪些因素能促使我后来选择了汉语?这些因素对我选择汉语和学好汉语甚至起一些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用法文说,我就是出生在“黑脚”(pieds-noirs)家庭,是一个“黑脚”,对不同的文化有着好奇的和探索的天性。
法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哲学家、评论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1957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加缪是法国人。但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Mondovi)。他父亲在大战中阵亡之后又移居到阿尔及尔。1933-1936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学习哲学。
加缪就是一个“黑脚”,意思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一般来讲,对于“黑脚”的来历有这样一种解释:法军19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登陆的时候,士兵穿的是皮鞋。而当地的阿拉伯人是光脚走路。据说就是根据这个小小的细节,从法国本土过去的法国人被称为“黑脚”,意思是穿皮鞋的。
按这一习惯说法,当有法国人问我说你是在哪儿长大的,我说我是“黑脚”,他们也就明白了。噢,原来你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我觉得这不仅是简单地是一个称谓问题。根据我的分析和理解,这里面蕴含着比较深刻的意义。“黑脚”意味着:你是法国人,可又不是在法国本土长大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国的边缘人。所谓边缘人,指的就是置身在海外,虽然是离法国很近,尤其是跟法国南方文化特别接近(比如我,母语是法语,接受的文化也是法国的)。总之,“黑脚”虽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但与当地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海外省。
我出生在一个“黑脚”家庭。我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很早就来到了阿尔及利亚。我爷爷奶奶都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再往前说,我的祖先可能是来自西班牙领属摩洛哥,因为它北部有一小部分是属于西班牙的。在那个时候,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都集中在摩洛哥的这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还能记得我爷爷奶奶有时出于情感的原因,还会说出几句西班牙语,尽管他那时候已经是全讲法语了。我小时候接受的全部是法国语言文化。
我爸爸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过不少职业,主要是做会计工作,但同时也在学校里兼课,教授现代希伯来语。我们家庭是很小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也就是普通的百姓。但有一点,我父亲特别爱好唱歌,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特别爱好,而且他的嗓音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呢,也是为了回答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中文的声调那么难学,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起我父亲。他除了做小会计以外,最主要的业余工作就是做合唱团的指挥。他不仅喜欢唱歌,而且喜欢做合唱团指挥。所以,我从小一直看着他就是指挥。当然,他是业余的指挥。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可是。我现在坚信明白一个道理很重要。
小时候(第一排,左四),“黑脚”同学们……
加缪
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因为要照顾五个孩子和做家务。我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我父母社会阶层不高,但也不算低,属于中等。他们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一直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让我们买书。所以,我们小时候读的文学方面的书特别多,尤其是哥哥和我。
我最近几年多次主持了有多位汉语老师参加的培训班。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汉语老师应该最像什么人呢?有的中国志愿者回答说,应该最像一个大夫,纠正学生们的发音。我说,大夫不行,因为如果老师是大夫的话,那学生成了病人。我觉得这种比喻不太好。有的说。老师应该最像一个园丁。我说,那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比喻,也不恰当。如果老师是园丁,那学生是什么,是花吗?是蔬菜吗?我认为,一个老师,一个外语老师,最应当像一个乐团指挥、合唱团指挥或者导演。我认为,这是最得体的、最好的比喻。这对我后来的汉语教学潜在的影响很大。
此外还有什么?我刚才说了。我爸爸还兼职教授学生现代希伯来语,也就是说教外语。家庭的这种氛围对我后来的选择也有影响。我既是法国人,又不是一个正统的法国人。我现在分析,这些因素可能决定了二十年以后我就开始主修一种莫名其妙的、最遥远的语言文字,那就是汉语。或许只有看到了我小时候的环境或者个人细胞,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并且学好了汉语。我敢肯定地说,如果我在汉语四声方面没有太大的困难,那是因为我跟其他孩子相比在语音环境,也就是调子环境方面要丰富多了,丰富好几倍或者几十倍。我从一生下来,父亲给我唱歌特别特别多,就是到现在我對音乐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而且爱好古典音乐。所以,声调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个人的特征,我肯定是受爸爸的影响,因为我见过他教课,知道他的教学方法等。另外,他是乐队的指挥,而且爱好唱歌。这些都提升和丰富了我耳朵的听力和对声调的敏感度。当然,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当时肯定也没有意识到。
1950年,我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奥兰省(Oran)第二大城市西迪贝勒阿巴斯(Si,di Bel Abbes)。在学习方面。我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语幼儿园、法语小学就读,后来还上了初中。
1962年。就在初一快念完了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我跟随绝大多数的“黑脚”赶紧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到了法国本土。当时的局势还是比较恐怖的,因为有支持法国统治的,也有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两派之间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既不是这一派,也不是那一派,夹在中间最难受。在这方面,加缪写得特别好。他说过。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期间,最吃亏的就是“黑脚”。“黑脚”是法国人,但不是法国大地主,因为法国大地主是那些刚刚从法国本土过来的人,一般拥有很多很多的土地。“黑脚”却不是,多为小资产者,从事会计、老师等职业,或者做生意。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比本地阿拉伯人的高,但又无法跟那些刚从法国本土过来的大地主比。加缪说,最吃亏的就是“黑脚”这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大款,不是富翁,可所有财产都留在那里了。
那一年,我刚刚12岁,离开从小住过的房子,赶紧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开始几个月,我们家到的是阿尔萨斯地区。阿尔萨斯地区是法国最冷的地方。而西迪贝勒阿巴斯一直天气非常好,就像尼斯那样冬天不冷夏天很晒。所以。由于气候很不一样,我们家先后换了两三个城市。最后定居在离巴黎150公里的兰斯(Reims),它也是香槟酒地区的省会,有一座特别漂亮的教堂。由于走了不少城市。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感情方面的休克。也是一种文化方面的休克。
从文化上说,我是属于法国南方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法国也是有区分的。南方是橄榄油文化,北方是黄油文化。我到现在不太喜欢用黄油做菜,是典型的法国南方像普罗旺斯、马赛那一带的人。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即南方的知识分子很平民化。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文学家“黑脚”加缪经常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球迷。你知道,在当时也包括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中很少有球迷。他们觉得这是太俗的。可是,加缪因为是平民出身,又是黑脚,所以说自己是球迷。我也一样,从小就是球迷。为什么?因为“黑脚”有这种平民化的传统和爱好。我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少数对足球感兴趣的人之一,这是有文化原因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支持我生活的那个城市的球队,它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冠军。现在,我支持的是巴黎圣日耳曼队。
法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萨特(Sartre)。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巴黎知识分子,是比较高层次的。他喜欢在咖啡馆高谈阔论什么的,而很少接触平民或者是接触足球。
加缪和他就大不一样。加缪的母亲是文盲,虽然来自西班牙,但不是犹太人。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在发言中说过一句使大家很感动的话:我今天获得诺贝尔奖感到很荣幸,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母亲永远读不懂我的作品,因为她是个文盲。
回到法国本土之后。我继续读完初中和高中,1968年通过了高考。然而,当时的法国正闹五月风暴。我当时18岁,正好是高中毕业班。所以,我的高考证书很有意思,它颁发的年月本来应该写的是1968年6月,因为每年都是6月颁发。由于当时很乱。我们的高考证书是7月25号才颁发的。我读高中的时候,法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改革就是高中毕业班新增加一门哲学课,是真正的哲学课。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在高中毕业班时读了一年的哲学。虽然还有其他科目。但是。我跟不少同学一样对哲学的印象特别深,兴趣特别浓厚。我们上的哲学课有形式逻辑,有认识论。有所谓的伦理,有科学史,有康德,有黑格尔,什么都有。所以,我的印象很深。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多一点,当时已经在巴黎大学主修哲学了。后来,他当上了教哲学的老师。我通过高考以后,于1968年秋天也进入巴黎第八大学,跟我哥哥一样主修哲学。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超越个人的选择,是超越表面一些现象的选择。
当时,我对哲学感兴趣是毫无疑问的,可哪儿能知道一年以后我会主修汉语呢?最近,我经过研究发现,在我们汉学界,在汉语教学领域,同时主修哲学和汉语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而,我当时哪能知道这些呢?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先是主修哲学,我上的那个哲学系是当时全法最先进的。为什么?因为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五月风暴之后由国家设立的。这是一所在各方面都比较先进的大学。尤其是在学科方面。比如说,它当时是全法唯一有电影系的,还是全法也许全欧洲唯一建立精神分析学系的一个大学。它就是巴黎第八大学。另外,正因学科比较全,它也设了一个中文系,为了表明这个大学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当时法国已经有了几个中文系。
虽然入学的第一年就知道有一个中文系,可是,我主修的是哲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汉语之路。我一般不相信偶然性,可在这一点上我承认可能是偶然的。当时,我们大学是一所实验大学。就在我快结束哲学系一年级学业的时候,校方发了一个通知,说从下一年开始,所有的学生必须同时主修两个专业。我们是在开会时听到这个通知的,当时我就举手,问这第二个专业选择外语行不行。这个问题是我自然地即席提出来的,而不是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校方马上回答说,当然可以。学校不是有好几个外语系吗,英语系、西班牙语系、中文系,什么系你都可以去。但是,他们说你也可以去学社会学系,或者经济学系。我说不不不,我去学外语。还是我那句话,我当时不知道我提出学外语是不是合乎我的一些可能是内在的动因。我当时还不知道。可是,这的确是自然的,不光是兴趣,还可能源于一些自然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哪儿。很可能就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父亲营造的那个歌曲环境。
所以。1969年开学后,我除了上哲学系二年级之外。就直接去了西班牙语系。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呢?我在中学学过西班牙语。它对我来说一直很容易。当然,这还是一个自然的兴趣。我当时并没有太想我祖籍可能是来自西班牙。我只是觉得比较喜欢这种语言,而且离法语比较近,不像英语那样。
于是,我就去注册西班牙语系,开始一年级的课。我现在记不得是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时我就做出了一个完全改变了我一生的选择:放弃了西班牙语系,直接去中文系注册。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说,为什么去学习汉语。当时并不是非常清楚的。清楚的是什么?那就是放棄西班牙语,因为我当时觉得西班牙语与法语太相近。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太普通的选择。我当时没读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书,还不知道自己属于AB两类中的哪一类,如是听觉的还是视觉的,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等等。
根据美国的现代心理学,学生们的专业选择,一类人是基本上向往遥远新鲜的陌生的专业,另一类人是选择熟悉的或相近的专业。根据我最近的总结,我显然属于第一类,也就是无论编写什么著作还是个人的选择,都愿意去发现。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放弃西班牙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太容易。我虽然喜欢这种语言,可它对我和法语来说太相近了,太普通了。我在放弃西班牙语的同时,去中文系敲门。就是在中文系秘书办公室门上的“中文系”三个字吸引了我。对我来说,这三个汉字太有魅力了。是它们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9年,哲学系老师,福柯教授、德勒兹教授
很遗憾,汉字的魅力被中国人自己低估了。我们都知道,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字曾遭遇到中国知识界和政治家的无情批判。就是在目前,我觉得中国学术界经常把汉字当成一种包袱,有一种自卑情结,甚至企图用拼音文字来取代。他们把中国文字看作是烦琐的东西,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许多外国人,至少对我而言,初次接触,汉字绝对是正面的。它们一方面美观,另一方面还很神秘。我提醒大家,在西文特别在法文中“神秘”绝对是一个褒义词。我感觉到,这个词在中文中的意义有时候微妙一些,有时候好像有一点点贬义。但是,我讲汉字神秘绝对是褒义的。神秘的意义就在于吸引人们愿意去发现。到现在你问法国普通的老百姓对中文有什么印象,他们还会说很神秘。中国也一样,尤其是过去的中国,我认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也是神秘的,但这个神秘绝对是褒义的,人们很愿意去了解或发现。但是,对我们来说,英国不神秘,英语也不神秘,因为太相近了。
于是,我就开始敲门。进去之后,秘书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哲学系的,现在学校不是要我们主修第二个专业吗。我想学一点点中文行不行。他比较幽默地回答说:“欢迎,但那个专业的学生少得可怜,只有六个同学,加上你就七个了。他们已经上了两三个星期的汉语课了。”我说:“那好吧。”就这样我开始走上学汉语之路了。我记得一清二楚的是,没多久,其实过了第一个星期,我就被汉字迷住了。
到了1969年10月,我学会了十几二十来个汉字。这时我做的是什么呢?马上去找中文读物。当时偶尔也可以从图书馆里拿到《人民日报》什么的。拿到这些中文报刊后又做什么?这很有意思。我后来发现这不止是我的习惯,而是很多很多汉语学习者的习惯。那就是在学会几个字或者十几个字之后。找来任何一个中文读物,从中查看学过的字在哪儿。比如,学过“天”字、“女”字、“雨”字。你就查一下。花一定的时间,最后能查到,雨,下雨的“雨”就在这儿,“女”字就在这儿。但是,这篇文章什么意思当时你肯定一点都不懂。
这个效果很有意思,花了那么长时间就查到你学过的这几个字,整篇文章的意思百分之百都不懂。你本来应该失望嘛,可效果正相反,你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很有成就感。我后来才知道,这不止是我的习惯。其他汉语学习者跟我一样,学过几个字就想查一下,哪儿有,哪儿能找到,而能认出来找出来就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不像中国人自从20世纪包括到现在一提汉字就说汉字难。中国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正因为汉字,才有200年前的雷慕沙(Remusat);正是因为汉字,才有后来很多主修汉语的人。没有汉字,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接受访谈了。
我这个人本来听觉是非常敏感的,可汉字是视觉的东西,这更激发了我的兴趣,因为汉字是很陌生的,因为汉字的透明度是零。如果看英文,因为与法文很相似,很透明,所以,我能猜到它的意思。可是,如果不认得汉字,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你会说“谢谢”,可你若没有学过汉字,“谢谢”这两个字摆在你的眼前,你都不知道这就是“谢谢”。
正因为透明度几乎是零,我就特别愿意发现汉字后边有什么,汉字后边是什么境界。所以,我觉得我的发现精神、挑战都与汉字的神秘有关。其实,在发现这个汉字神秘之前,我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后来,我当汉语老师的时候。也经常问我的学生:“你们为什么学习汉语?”有的学生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听过什么关于中国的故事。我不属于这一类,我第一次听到一点点关于中国的信息是在高中毕业班的哲学课上,哲学老师偶尔会提到有关中国思想方面的东西。他讲的虽然很少,但引起了我的兴趣。除此之外,我从来没读过任何中国文学,不知道有关中国的任何传说。
所以,我学习汉语的真正动机就是感到它很神秘,想去弄明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学过几十个汉字,马上就拿《人民日报》或者什么中文报纸想看一看,经常坐地铁时错过车站,因为特别想查到我学过的字。这就是目的,没有别的目的。比如,“女”字就在这里,文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也就是学了一个星期的汉语,我就在那些不是学中文的同学和朋友面前显摆了,按我现在的话就是开始传播汉语了。当时我做的也很简单,写一个“天”字给他们看,然后问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汉字吗,他们当然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很自豪地,甚至也不只是自豪地向他们讲解,说这是“天”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汉字和喜欢传播汉字。我后来发现,不止我是这样,很多很多西方人也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古埃及文字的最后解码者就是一个法国人,好像西欧人就对那些古文字兴趣比较浓厚吧。反正我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我经常给我的朋友看一些汉字,我先写出来,然后让他们猜猜。他们当然猜不着,最后,我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当然马上就显示出了兴趣。而我一发现他们对汉字的兴趣是我激发出来的。就更加感到非常自豪。
我再跟你们说说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情况吧。中文系教课的老师中,法国人、中国人都有,中国老师的情况当然比较特殊,因为那时没有中国公派的教师,法中文化交流也中断了。中国在“文革”以前有向法国公派的老师,因为中法建交很早,是在1964年。所以,我说的中国老师有的是长期居住在法国的华人,有一些是兼课的,还有的是台湾人。其他一部分老師是法国人。我们上过的课有文言文,有现代汉语,当然是以现代汉语为主,以简体为主。识繁写简,认识繁体字可是写的是简体字。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学会写繁体字,只是认识。在语言方面有语法课,有汉法、法汉的翻译课,有口语有听力等等。其中,文言文课是一位法国教授上的。现代汉语课大部分是中国人上的,只有一门现代汉语语法是法国人上的。
在老师当中,有一位姓丹尼斯(Denes)的女老师,她可能是所有的老师当中最好的,很年轻,那时只有27岁。最近,我在1964年1965年头两批法国留学生的老照片中终于认出了她。丹尼斯老师是1964年或1965年在北大读过书的法国留学生,从中国回来后就开始教中文了。但是,丹尼斯老师不到30岁就得癌症不幸去世了。她真是最好的一位老师,汉语很棒。在教我们的老师中,还有一位姓奥利弗(Olivier)的瑞士人,汉语虽非母语,可他的汉语好得不得了,虽然那时我从来没来过中国,但凭感觉能辨别出他的语音非常纯正。这个瑞士人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但也在去年拿到的北大1964年和1965年留学生的老照片中认出了他。他也比较年轻。他后来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不能忘记的是,这位瑞士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去中国这个说法,给我印象比较深。另外,我们还上了一些其他中国文化课和中国历史课。前者主要有现代文学,鲁迅什么的,后者主要讲中国古代历史或者现代历史。
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上的第一堂课是一位台湾人上的语言课,他叫赖金南,人挺好的。他在课堂上说,汉语是没有语法的。我们一听都高兴万分,因为我们学的语言都是有语法的。下课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开始交流,认为老师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因为没有语法的语言可能是没有的。可是,当初他就是这么说的。从法文角度看,汉语就是没有语法的。在当时,法国的汉语教学还没有任何真正的教学方法,教学效率也比较低。说实话,教我们的现代汉语老师尤其是语言老师没有真正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也不好。可是,我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还是很浓厚。我们那时学汉语没有任何就业计划,连一点点就业计划都没有,这方面的计划绝对是零。学习汉语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自己想学。
所以,按现在的话,我当时学的是月球语言。月球的意思就是说非常遥远,是不可能去的国家的一种语言。最近有人问我,你有没有计划去台湾?这一问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对我来说,中文就是中国。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去台湾,可能是因为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文化交流,如助学金。我反正就没想过,觉得是没有任何去中国的机会,也没给自己确立任何就业的目标。过了半年、一年、两年,我父母、我的朋友就发现我已对中文着了迷了。我虽然主修哲学和中文两个专业,可对中文的兴趣特别浓,是全身心地投入。所以,他们开始为我担心,为我的就业担心,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当时只能回答:“对,这是个问题。”我没讲,说不定中国会开放。我从没想过,觉得中国就是封闭的。可无论如何,我对汉语还是入了迷。
入迷到什么程度?我当时所有朋友几乎都可做证。我有哲学和中文两个主修专业,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这样和我打招呼:“中国人你好!”他们给我起的一个外号就是“中国人”,法文是Chinois。英文是Chinese man。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主要对他们讲关于中文、关于汉字、关于中国语言等方面的内容,较少讲哲学。所以,他们,也包括我父母开始问我:“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当时,我好像是这样回答的:“我知道学汉语可能没有任何就业价值,但中文的学士学位毕竟是文科,可以拿这个中文学士学位在法国教法文。”但是,这到底可行不可行,我当时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