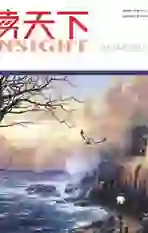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因素
2018-07-16万玲玲
摘 要:近些年来东野圭吾的小说深受大众的喜爱。经过阅读发现其小说当中包含大量的暴力书写,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野圭吾对于暴力的书写并不同于以往。一方面保留了以往的暴力场面,例:酗酒,打架,杀人等情节;另一方面呈现出一种新的暴力——精神暴力。东野圭吾的作品中虽然有大量暴力书写,但十分节制合理,让读者在保持阅读热情的同时不觉血腥残忍。作者通过暴力书写,用这种冷寂的方式让人们得到反省与治愈。
关键词:东野圭吾;暴力美学;“冷”暴力与“热”暴力;节制
一、 暴力美学的渊源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讲“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致便是美到极致。”丑作为否定美极具审美价值,暴力作为人性丑的一部分,自然可作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美只是审美判断并不是人们主观认为的道德与真善,虽然暴力会给人们带来感觉上的不适,但是并不能影响其成为审美对象。暴力美学一词作为一种专业术语首次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影评人的笔下。影评人将暴力上升到美学的角度,追求血腥,暴力镜头和场面道德诗意化,刺激性、崇高性及悲壮性的形式主义趣味,表现出一种纯粹的视觉快感,至此暴力就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美学风格和表现方式。“暴力美学来源于对‘吸引力蒙太奇的继承与发展。1923年,埃森斯坦在《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吸引力蒙太奇”的概念,其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列宁的电影工具论,俄国形式主义,美国的蒙太奇技巧和方法。吸引力蒙太奇的精髓是使用离开现实和脱离叙事情节的画面元素和组接方式创造出有视觉冲击力和表意明确的电影文本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暴力美学从吸引力蒙太奇发展而来的一个技巧论形式美学概念,提供的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原指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其本质是让动作化为美感”。暴力美学一词的出现也正式标志着暴力与美学的正式融合,并开拓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暴力作为人的极端欲望的外在表现,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山海经·海外西经》当中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於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商周列国全传》中比干挖心,西伯侯食子肉,马元食人肉。《水浒传》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莫言《檀香刑》“周聋子被德国兵挑了肚子,花花肠子像鲤鱼一样钻出来,斩首的舅舅的尸体像个酒坛子一样倒下,腰斩的人的辫子像蝎子的尾巴 一样翘起来。”诸如此类暴力场景数不胜数。
二、 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暴力美学
(一) “热”暴力
暴力美学通过打架流血,吸毒,奸淫,杀戮,黑暗角落等极度残忍且极具感官刺激的场面,让人从麻木的状态中产生大的精神波动,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这种冲击刺激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适感与排斥感,艺术家通过这种反向表现方式吸引人们的关注。所谓“热”暴力指极易被人们的视觉捕捉的血腥残忍的暴力场面。往往带有人类原始动物兽性冲动,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通过力量的发泄,造成外在的流血死亡,从而实现“本我”的极端欲望。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热”暴力场景。
1. 死亡场景的叙述。悬疑推理与死亡暴力是紧密相连的,推理小说总是逃不开:杀戮死亡——推理调查——找出真相的故事结构,尽管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方式以及表现顺序,最终跳不出这样的结构。对于“热”暴力的表现,东野圭吾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因死者的死法和故事叙述视角的不同而异。《嫌疑人×的献身》中“富樫的脑袋近在眼前。暴睁的双眼一片死灰,仿佛正睨视着屋顶。脸由于淤血变成紫黑。勒进脖子的电线,在皮肤下留下深色的痕迹。富樫再也不动,口水淌下嘴角,鼻子里也溢出鼻涕”由于并未使用锋利的作案工具所以没有大量的流血,只有尸体狰狞的画面。通过靖子的眼睛所见,所以这一段死亡场景的描述中透露出一种既解脱又害怕的意味,将靖子杀人后的惊恐细致地展现出来。在《白夜行》中对于尸体的描述是通过笹垣警官与其他办案人员讨论案情的方式表现死亡场景。警察作为案件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死者,其态度是冷静、审视的。因此对于死者的描述没有夹带丝毫的情感因素,公式化甚至冷漠的话语,非常符合警察身份。在《放学后》中作者对于死亡的描写则是通过死者临死前的个人体验加以表现的,将死者遭遇死亡,感受死亡的细腻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2. 人物肢体碰触。东野圭吾的小说中暴力美学还表现在人物的强烈肢体碰撞。《嫌疑人×的献身》靖子前夫找靖子复婚,靖子不答应,便尾随靖子到住处勒索钱财,看见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儿回到家,上前调戏,女儿美里不甘,趁富樫背过身穿鞋的时候用花瓶想将其砸晕,却未得逞,富樫头破血流却没能如愿,反过来抓住美里,“美里想逃却被富樫一把抓住肩膀,富樫身子一歪,把她压倒在地。美里缩成一团,快被压扁,富樫整个人骑在她的身上,左手拽着她的头发,右手甩她耳光。‘臭丫头,老子宰了你!富樫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另一边靖子看见女儿快被打死,母爱暴发,抓起旁边电暖桌上的电线走到富樫的背后,用线勒住他的脖子,富樫死命挣扎,最终狰狞地死去。
(二) “冷”暴力
冷暴力是“冷战”一词的衍生品,是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热”暴力在实施手法上往往采取肉搏,带有激烈的肢体冲突;“冷”暴力表现形式多为冷淡、轻视、放任、疏远和漠不关心。在伤害表现上,“热”暴力对于当事人产生的伤害大多集中于肉体上,而对于旁观者产生精神伤害。“冷”暴力往往致使当事人精神和心理受到侵犯和伤害,不会波及旁观者。以往推理小说大多侧重推理调查的过程,但东野圭吾对于谁是凶手并不关心,很多作品甚至在一开始就向读者宣布了凶手与作案手法。东野圭吾十分关注犯罪動机,对于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的挖掘往往构成小说的主体部分。按我国刑法教科书的定义,“所谓犯罪动机就是指刺激,促使罪犯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和思想活动,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实施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由此可见,东野圭吾相比“热”暴力的刻画,更注重“冷”暴力层面的表达。其作品中的“冷”暴力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 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即暴力实施者通过尖酸、刻薄的话语达到对被施者的精神或心理伤害。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语言的暴力双方并不仅局限在犯人与受害者,还包括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受害者与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与周围看客。《嫌疑人×的献身》富樫再次看到继女美里时:“和继女打个招呼怎么了?”“没那么严重。我走了,美里改天见”富樫对着里面说道。他终于走向玄关:“她将来肯定是个美女,真令人期待”“这怎么是胡说?再过三年她就能挣钱了,到时候哪家酒廊都愿意雇她”。富樫让尚未成年的继女去酒廊卖身,这些语言深深地伤害了继女美里的心,也成为富樫丧命的导火索。“我可要提醒你,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该死的是你。”警察在审问石神时,石神辩解:“她略表悔悟了?枉费我替她除掉眼中钉,听说她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关她的事。”这一段话,如果是在靖子不知道案件的后续案情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她内心的伤害。
语言暴力不仅体现在对话双方的身份上,还表现在对话内容与对话双方的相关性上。比如富樫对美里、靖子的威胁对话,对话双方与对话内容直接相关,并造成一方的伤害。此外,对话双方与对话内容中的涉事人没有直接联系,内容可能造成涉事人的伤害,但对于对话双方不会造成精神伤害。主要体现在案件调查者之间的对话。《嫌疑人×的献身》中汤川和草雉推理案情时“大概是石神发现了花岗靖子的罪行,决定帮他消灭证据。他认为光是处理掉尸体还不够,一旦查明尸体的身份,警方必然会找上花岗靖子。到时她和她的女儿,不见得能抗到底,于是他拟定了这个计划,另准备一具他杀尸体,让警方认定他就是富樫慎二。警方肯定会逐步查明被害人是何时何地如何遇害,警方调查的越深入,花岗靖子的嫌疑就越轻,这是当然,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是他杀的,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富樫慎二。你们调查的其实是另一桩杀人案”虽然通过对话并不能让我们察觉出其中的暴力所在,下文中“他想要的,是他杀尸体这块拼图要完成整部拼图不能少那一块”。两位调查者大胆的猜测石神的杀人动机,作者一开始便运用上帝视角揭示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花岗靖子,前文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石神在替花岗靖子顶罪的同时为了掩盖真相而另杀一人,若没有后续,这一段的揣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污蔑。
2. 环境压抑。“冷”暴力作为一种精神虐待,压抑冷淡黑暗的环境氛围,使其伤害程度更深。《嫌疑人×的献身》“厚重的云层覆盖着天空,隅田川倒映下的暗沉苍穹,一片污浊”“小屋的高度,顶多只及背部,有些甚至仅仅及腰。与其说是屋子,恐怕成为箱子更贴切,不过要是只用来睡觉,也就够了。小屋或箱子附近,不约而同地挂着晾晒衣架,显示出这里乃是生活空间。”这段环境描写渲染了氛围,为后续的情节展开埋下伏笔,使得在真相大白的时候,石神杀掉的流浪汉的情节不显突兀。《白夜行》中“已经十月了,天气仍闷热难当,地面也很干燥。每当卡车疾驰而过,扬起的尘土极可能会让人又皱眉又揉眼睛”。压抑的环境造成精神压抑,从而加倍人物的精神伤害。
3. 恶意揣测。鲁迅先生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以恶意揣测他人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生存环境使得人们将之变为一种肆意伤害人的工具,而实施者却全然不知伤人与否。《嫌疑人×的献身》中花岗靖子的同事在向警方录口供时猜测石神是为了靖子而每天绕远来到店里买便当。草雉警官在推测案情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靖子是杀人犯。《白夜行》中雪穗的同学嫉妒雪穗的漂亮与优雅便随意的认定雪穗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扒出之前的贫穷身世。
(三) 东野圭吾对于暴力美学的创新
东野圭吾说:“现在的我,会尽量写出即使不爱推理小说甚至不喜欢阅读的人看了都会觉得有趣的作品。”东野圭吾的大部分推理作品都采用“热”暴力与“冷”暴力结合的方式将故事呈现给读者。暴力美学的代表昆汀·塔伦蒂诺主要通过极其血腥暴力的场面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例如《嗜血狂魔》电影全程向我们展示了枪战、死亡、流血、吸毒等血腥暴力场面。东野圭吾的作品中不乏这样的“热”暴力场面比如《放学后》前岛老师被血淋淋的被杀害场面;《嫌疑人×的献身》富樫慎二的死亡挣扎;《白夜行》中桐原洋介的尸体解剖等。其独特之处便是花费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冷”暴力——作案者的杀人动机,借用这样的方式使得读者释放心中的精神压力。
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暴力因素体现着日本大和民族人民节制的特点,无论是在描写“冷”暴力还是“热”暴力,都未进行过度渲染。死亡场景极其简洁,三言两语带过,有些甚至只给予人们暗示并没有直接的文字展现,《白夜行》中美加被快递员强奸,只通过美加的痛苦感受让读者推断被强奸的事实。《嫌疑人×的献身》中流浪汉的死亡,在故事结尾处真相大白时被简单提起,仅仅为打破石神的心理建设逼迫其认罪。“死亡文化历来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这部分的表达。东野圭吾的作品中的死亡表达是在描述当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困境,是在彰显后现代文明中新生的文化危机给个体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现代社会中新兴的话语权取代了一些传统文明留给社会的习惯与制度,这种代替使人产生异化。”东野圭吾描写死亡不仅仅局限在肉体的死亡,因此对于死亡的场景的描述十分节制,换言之东野圭吾并不想通过死亡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种种不满,他的叙事重点是让人们从精神上得到拯救。
三、 总结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样暴力美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对于自身的审视与挖掘。表面上暴力美学是在追求形式上的感官快感,但是暴力美学正是通过对于人的自身的承认和肯定、反省与检讨让人本身更加清醒的认识自身。东野圭吾通过自身对于暴力的理解完美的将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得到结合,并将暴力情绪加以节制,拿捏有度,使用暴力却不耽于暴力,使得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不致过度伤感,却能得到心灵的治愈。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子倩译.嫌疑人×的献身[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8.
[2]东野圭吾,劉子君译.白夜行[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8.
[3]东野圭吾,刘子倩译.放学后[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8.
[4]钟翔.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死亡书写[D].长沙:湘潭大学,2012.
[5]尹洪,冷欣,程辉.试论暴力美学及其特征[J].体育与艺术,2008.
作者简介:
万玲玲,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