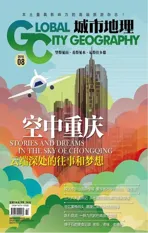台北访张大千故居
2018-07-14文
文+
十一月的台北,骄阳依旧炎炎,空气中渗透湿热的因子。突然而降的雨,淅淅沥沥,带来了些许清凉,焦躁的情绪不翼而飞,惬意舒心之下,顿感自然造化的高深莫测。
摩耶精舍,为艺坛宗师大千先生台北的寓所,紧邻市郊外双溪溪水双分之右侧,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距不远。1976年1月,78岁高龄的大千先生,万里迢迢从海外来到台北定居,选择这片青山簇拥、绿水环绕的坡地,作为自己最后的栖居地。这里曾是一片荒废的鹿苑,选址时,大师发现乱石墙角边,孤立着一棵白梅树,风姿绰约,偏爱梅花的他当即拍板。建筑模式按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精心设计,花时近三年,择林点丛,叠石理水,随冈营墅,才有了今天花木扶疏、精巧玲珑、风格典雅、极富园林之胜的摩耶精舍。
进入庭院,就像身临大师所创造的山水画境之中,处处可以欣赏到奇巧的构思。宅院中央一方天井,两个相连的小池塘,白、橘、黄、黑四色锦鲤戏水池中。盆景中的松、柏、梅、榉,树干姿态雄伟苍劲。特别是入口玄关处被称作迎客松的黑松盆景,枝态泻如飞瀑,以四十五度角下坠,又似向正在进门的访客鞠躬欢迎,情致憨厚。四盆铁柏,蟠曲矫劲,据说树龄都已在200年以上。沟渠旁,几棵挺拔的梅树,虽无初春蓬勃娇艳的花朵,却枝繁叶茂,形姿古朴。
正屋,以木材架构。沿中庭通道,可进入客厅、画室及餐厅。客厅布置素雅,一帧与毕加索合影的旧照,引人注目。但让我惊奇的是,客厅中每一扇落地玻璃窗上,都贴有形状各异的放大膜,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都能清楚地看到院内错落有致的美妙风景,像把一幅幅山水画活灵活现地呈在访客的眼前。临近客厅的画室,气派极大:大师挥毫作画的坐身蜡像,栩栩如生。
会客室里,摆满大师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奇木异石,藏品之丰,无与伦比。餐厅的墙壁上,悬挂着大师亲笔题写的“宾宴食帖”,干贝鸭掌、红油豚腣、菜茗腊肉、干烧鳇翅、葱烧乌参等菜名,让访问者垂涎三尺。
由前院沿中庭,可到后园和屋顶花园,奇花异草比比皆是。小小天地,就是一座微型植物园。为表孝思,大师在后园广植萱草,慈孝之心,昭然可见。后园最显眼的一盆阳明山绒毛野杜鹃,树龄七十多年,盆边刻着大师亲笔题字“摩耶精舍供养鹤林连理”。大师还钟爱荷花,特别欣赏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所以园中自然少不了荷。他以八斗水缸精心栽植荷花,然后移入池塘。花开季节,无论晨昏,看着接天碧叶,红蕖冉香,不亦乐乎。
精舍最绝妙的风景,在圆木高擎、棕榈遮顶的翼然亭。从影娥池到翼然亭,不过几十米,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江南园林的精华,尽囊其间。静坐亭中,聆听外双溪淙淙水声犹如天籁飞入,便可恍然彻悟“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狭窄的长廊,一边是大师至爱的猿猴、珍鸟、鹤鸾,一边是仿制江南的舒适的美人靠,营造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小世界。
走出精舍,紧闭的大门把半个世纪的传奇深锁宅院。我脚步迟缓,颇难相舍。雨还在下。烟雨中回望台静农先生题写的“摩耶精舍”匾额,一代宗师的艺术、爱情、人生,一切似乎都那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