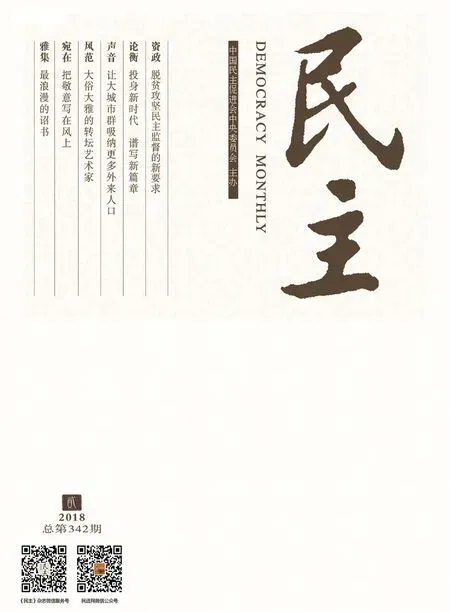小浪底北岸
2018-07-14葛道吉
□葛道吉
春上,我再次来到黄河,仍是小浪底北岸栉比的山梁。
那山梁好长,从遥远的王屋山蜿蜒下来,直插黄河。山梁与山梁的间距不像拢头发的梳子那般规整,有的狭窄,有的宽敞。就有4个乡镇10万民众在沟沟叉叉的土地上耕种。这里满眼的苍茫,村庄是很难一眼就看得见的,全隐在1000余平方公里的山坳沟壑里。
道道山梁像极了巨龙探水。浩瀚的水域淹没了很多散落的村庄遗址与梯田,让历史上光秃秃的山梁变得林木蓊郁。水改变了生态,改变了这里祖祖辈辈人的生活方式。
“老远看到车就知道你来了。”老人在路旁迎接。我赶忙打招呼:“老陈大伯可好,大娘也在吧!”“在!忙着给你炉红薯。”大娘总记着我爱吃红薯。去年冬季,我进到老人居住的土窑洞,看到刚出炉的热红薯,忍不住一气吃了两个,不住地说着好吃好吃。大伯大娘只是笑。我已是大伯大娘这个窑院的常客了。在小浪底体验生活,看到很多山梁、岛屿都成了风景区,都成了开发好了的休闲山庄、游乐场所。唯独这个交通不便的偏僻角落没有开发,就因为老陈大伯死守着这个衔着水的山梁。他说这是一疙瘩好土,养人!就格外吸引了我的兴趣,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去年秋季,我无意间发现了老人深埋心底的一个秘密。那是山头最为美艳壮丽的时刻,各种果树红黄盈枝,有李、杏、山楂、石榴、蟠桃、柿子以及玉米、大豆、花生、红薯等。果实飘香引来了无数的蜂、蝶、喜鹊及其他飞鸟。老人说:“鸟们吃不了几个果,都等一年了。”我想亲眼目睹老人收获的场景留几张照片,就和老人约定采摘的时间。谁知,老人还有一个极其隆重的程序。那夜,我随身带着帐篷睡在隔壁另一孔破旧的窑洞里,环境的静谧逗起我写作的兴致,早晨就贪睡延误了时间。出门伸一下腰身,突然发现老人面对一炷香,正襟下跪在窑院前边不远的一块台地上。香在面前长方的石槽里缭绕着青烟,老人深深叩下头,前额贴着黄土。我悄悄走了过去,生怕惊扰老人。三次叩头,老人叫了声:“爹!娘!姐!哥!”高声说:“今年又丰收了!”
老人面对古老而崭新的黄河,一番话在水面上打漂,有波浪涌来,声音一扬一扬送去远方:“……咱们家满山的秋作物和瓜果,你们都回来看看,随便吃,随便摘,再不要为没吃没穿发愁了。咱西岭村移民到轵城镇后,全部住楼房,孙儿孙女都在市里工作,也买了房,买了车。爹,娘,早些年咱们做梦都不敢想,自从小浪底大坝建成,咱们这沿河村庄都搬迁了,都过上好日子了。我要叫你们亲眼看着,西洼到山梁那100亩地是咱们家承包的。我身体很好,孩子们整天嚷着叫我去市里住,说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哪有咱这老窑得劲!我一天不见水就不踏实。我就在这儿住,叫你们年年不愁吃,不愁穿……”
老人很动情,嘴角抽了抽,就滚下了老泪。我忍不住叫了声老陈大伯,老人没防备,身体震了一下,说:“今天孩子们都要来卸果,你就拍照吧!”我赶忙拉大伯起来,说:“您老这把年纪了,不能伤感,身体要紧。”“没事,十年前我75岁,孩子们谁也不让我承包,今年85还没觉着老。”“这地方世外桃源,长寿!”我刚说完,大娘已站在身后了:“春节孩子们非叫回市里过年,过不到破五就嚷着要来。这地方不知道有啥好!”大娘其实也是很踏实的。又说:“饭成了……”
老陈大伯抬眼看看日头,急急说:“走,回吃饭!”
没多大功夫,山腰上来了3辆车。老陈大伯两个儿子都已儿孙满堂,重孙重孙女像小鸟一样扑进老爷老奶怀里,四世同堂,幸福无边。
儿孙们纷纷拿出准备好的各种编织袋,有的摘杏子,有的摘石榴,还有背着锄头直接到一边刨红薯、刨花生。我捕捉到了丰收的喜悦,捕捉到了重孙、重孙女欢快的脚步与小鸟一样嘹亮的叫声,着实为这样的场景兴奋。这时,突然不见了老陈大伯。仔细看,那块高地上放了把椅子,老陈大伯正在椅子上坐着。看到儿孙们一袋一袋往车里装,心里的踏实和满足全荡漾在脸上,笑容里写满深沉的自豪。
车开走了,窑洞里丢下了各种老年人的营养食品。大娘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不让买非要买,放坏了也没人吃。”当然,他们明明知道那是孩子们诚诚的心意。
太阳斜到了西山头,老陈大伯又坐到那把椅子上,面向黄河水愣神。我感觉是个机会,就在老陈大伯身边一块石头上坐了,小心着问:“爹娘都已过世,大伯怎么如此伤感呢?”
老人像触动了一下,看我一眼,我很小心而真诚。老人急忙把眼光投向水面,银白里有阳光,水很亮,波浪像地垄一样一棱一棱放光。
那是将近80年前的事了。老陈大伯慢慢把浑浊的眼神从水里收回来,给我讲了他的家与黄河水的恩恩怨怨。当时老陈大伯7岁,姊妹5个,上有两个姐一个哥,下有一个弟弟。大姐18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哥哥十五六岁,已能帮老爹干活。二姐13岁。
1937年的初冬季节,印象最深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挨饿,整天赤脚丫子没鞋穿。那日掌了灯,河岸河水与岸畔小路全部被夜色包围。姐姐陪嫁的那口红漆木箱,是爹对河南岸一个生意人的承诺得到的报酬。一共10根木头,生意人能在日本兵的枪口下神不知鬼不觉把木料从山上运下来,但无法运过河去。船只全部被控制!就找到了河北岸公认水性好的人,并且以一口红漆木箱作为筹码。爹给娘说,“只剩两根了,回来就把闺女的事给办了。”趁没有月亮,河上好走。爹照样让哥哥跟着,好有个照应。
爹身背一只葫芦,那是渡河人的胆。一只胳膊挽一根木料,爹在水里往前推。没想到的是,那日气温急剧下降,穿棉衣也顶不住河槽的贼风。还算顺利,对方接收后二人击掌完事。爹在拐回的途中没了力气,胳膊腿划一下就很困难。不应该啊?原来,是被河水冻僵了!
爹下水前让我哥在北岸照应,在早该拐回来的时间里,我哥突然看到河中央模糊有个黑点,心里说回来了。就隐隐听到有微弱声音说:“我不行了……”是在水里漂,没有击水声。我哥不由分说就下了河,怎能眼看着爹遭此不幸?
哥哥根本没想到自己的水性不是太好,使尽了本能的极限,把僵硬的爹往岸边拖,突然感觉河水的力量如此强大,自己太渺小了。我要救爹!在无数次坚定信心,给自己生命鼓劲的时刻,也记不清自己灌进去多少致命的黄水……若干年后,下游10里的地方是关阳码头,码头上有老人回忆黄河的事情。说曾在夜里听到河里有人呼救,并说是西岭村的,虽少气无力,但还有生命。日本人控制着码头,村里年轻人全跑得无影无踪。要不然,那呼救声怎么能就这样顺水东去……
第二天拂晓,窑洞里仍然漆黑一片,有微微的晖亮挤进门缝。娘毫不犹豫披衣起床,不能再等山雀的打鸣。这山沟里,这黄河边,早起的信号就是天麻麻亮时的鸟叫。娘踏着熟悉的山路径直下河,上、下跑了十多里路,河水的混黄没有任何反应。娘回来了,看到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没说一句话。那天,娘像变戏法一样在窑洞里变出了耀眼的玉米面,狠狠地煮了一锅面饼,我和弟弟破天荒吃了肚儿圆。第二天,大姐随着那口鲜红的木箱,被一个男人接走了。临走时,大姐说:“等爹回来吧。”娘说:“走吧,你爹和你弟到河南还需些时日。”
转眼到了春上,干瘪的土地长出了可以救命的绿草。二姐扮着男装在河滩挖野菜,却被山头上日本岗哨的子弹打中了脑袋,二姐一头扎下没再起来。娘眼泪的河流就要赛过黄河,我从没见过一个刚强女人的悲伤,那样强大而震撼,坐在二姐的身边整整哭了一天,悲声震动了黄河,更震动了山上的日兵。他们投下来一些盒盒罐罐的食品,娘不由分说,全扔进了黄河。我们就地挖了坑,娘为二姐拢了拢头发,用一领破席掩埋了。
黄河北岸是日军控制,南岸是国军把守,把两岸百姓对峙得生灵涂炭。我和弟弟饿得骨瘦如柴,娘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在陌生人手里接过3个馒头,就把弟弟给了人。
我成了娘心中唯一的希望。一连几年,我跟在娘的屁股后山里山外讨饭,为了能够让我活下去,娘吃了多少苦、受过多少辱……
老陈大伯已泣不成声了。我实在不忍老人如此动情,立马有了负罪之感。忙起来安抚老人说:“好了大伯,咱不说了,这些年的变化老娘会高兴的。”
“我有一点安慰是,老娘走得很安详。我用当地最隆重的礼仪为老娘下了葬。”大伯顿了顿又说:“现在遗憾的是,老娘仍在水里……”
“这样很好!”我突然说:“您没有把老娘迁走是对的。你想想,小浪底是国家工程,它让我们多少人改变了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老娘老爹包括哥和姐能在水下团聚,对咱们家庭来说,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老陈大伯突然抬起了头,使劲儿看住我的脸:“他们团聚了?”眼里射出惊喜的光芒。我使劲儿点了点头。我俩如释重负,互相用欣喜的目光对视着。我清楚地看到,老陈大伯嘴角扬了扬,脸上放出了会心的笑,刚刚被眼泪打湿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