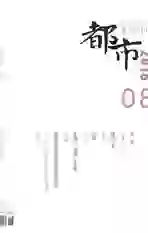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女性浪漫主义的萌芽
2018-07-13傅书华
傅书华
在小说边缘化的今天,在成名作家创作开始板结化且对他们新作的评论也趋于板结化的今天,新生的作家却如野草般旺盛地生长,也许会形成中国新时代文学园地中的别一景观。
虽然,为他们召开的研讨会也接二连三,赞扬不断,但僵化的研讨会模式及相应的作家作品论却早已令人厌倦。如果用“典型现象”的方法,因此于其中找出目下创作格局中新的创作生长点及其优劣,或许会对此有所改观?也更有利于新生作家的生长?我对苏二花小说的评论因此而发生。所谓典型现象,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就是王瑶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研究方法:“对于‘一个人(一个作家)可以有两种考察方式,‘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如果把‘一个人看作是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统一体,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典型现象”。
苏二花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现象”,是因为她的小说,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女性浪漫主义的萌芽。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浪漫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及中國现存的文学格局中,都很缺失。传统中国,一向以现实的生存、以群体伦理作为价值本位,个体生命难得张扬,其站在彼岸世界的价值立场上,超越此岸现实生存许可的想象更难以获得认可,因之,以此为价值本位的西方经典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土壤贫瘠,更难以形成传统、形成潮流。“子不语怪力乱神”,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现实生存许可至高无上的文化思想根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品的,其实都很可存疑。譬如屈原的《离骚》或者《西游记》,尽管有着奇特或瑰丽的表面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但在《离骚》那因忠被谤的悲愤中,在《西游记》那在实现神圣目标在成仁路上对个体生命欲望的收编与规训中,哪有个体生命之魂的存在呢?你如果非要将这些作品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作品,那也只能称之为中国化的浪漫主义作品。倒是商业经济初步兴起的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个人”高扬的五四时代青年郭沫若的诗作等等,可称为浪漫主义的杰作,但却凤毛麟角难成潮流,或者虽成潮流而又骤然跌落。然,当中国真正大规模地以商品经济变革了中国社会土壤的结构性,并且实际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千家万户的个体性的日常生存时,而商品经济是以个体利益为根基的,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存在,伴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生命的觉醒与浮出历史地表,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浪漫主义就有了成为民族精神发展广阔空间的可能。在这其中,女性因其性别的个体生命感性这一根本属性的敏感,在这一价值向度上,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就使得苏二花的小说,虽尚属萌芽,却也因此具有了时代的前沿性先锋性,并有了作为“典型现象”言说的价值。
苏二花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从目下看,主要表现在对外在个体生命形态自由及旺盛生命力的追求、对现实社会生存法则的彼岸性拒绝的内在价值形态的描写、华丽的语言美与瑰丽的想象这样三个方面。
对个体生命形态自由及旺盛生命力的追求
粗粗地浅浅地初次读《四大爷的照片》,你会有一种深深地感伤与不一样地感动:在外当兵后来转业到省城钢铁公司又上了大学的四大爷,因为自身对生命的热烈与在外新的生活的召唤,欲与在农村家乡结婚的妻子离婚———虽然这在农村家乡的妻子,在婚前婚后对他一往情深,虽然这在农村家乡的妻子,生性善良软弱勤劳俭朴,为他在农村的家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但四大爷仍然执著地坚持离婚,甚至为此不惜身负骂名得罪全家全村老少,甚至为此不惜利刃割腕以死相争,但终因全家人的阻拦,终因四大娘身患绝症需要治疗休养,不得不放弃离婚之念,不得不放弃心上的同学姑娘,不得不与四大娘相守一生。及至告别人世,他惟一的苦恼是被束缚得喘不上气来的“闷”,他惟一的愿望,是希望不要把他葬在祖坟里以挣脱这束缚,是希望把他的骨灰撒在风中自由地飞。但就是这最终的遗愿,他也未能实现———他最后还是按传统习俗被葬于祖坟中。小说在讲完这辛酸悲伤的故事后,在最后一段写道:“如果非要说他的一生是悲剧的,那他的悲剧该是谁造成的?他是要和这种悲剧做斗争的,但当他举起雷霆万钧的拳头时,却根本找不到对手。这个悲剧的过程太过冗长,直到把他开始之初的悲壮与激愤逐渐消磨到平静,直到最终连目标都混淆起来。”这似乎也是作者在文末点出这小说的主旨来。你如果调动你对以往类似题材作品的认知经验,你会觉得,单单从故事与情节上作既定理性的分析,这小说其实没有讲出什么新的故事来,这仍然是一个现代爱情与传统道德二律背反的故事,虽然它把这一“老而又老”的故事讲得更为缠绵动人,但毕竟没有给我们小说的传统叙事增添什么新的元素。但你如果不带既定理念地再细细地读一读,如果你认真地细究你读后那不一样的感动其为何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小说是内在地蕴含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形态与小说叙事形态的,那就是对个体生命形态自由及旺盛生命力的追求与浪漫的想往,这些新的情感形态与叙事形态,是通过小说主人公那小女孩的视角与言说完成的。
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主人公———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与口气讲述大山里自然风景的绚烂多姿与小女孩生命形态的自由自在:“如果你不是生长在农村,你就不会知道农村的春天是怎样的一种美好,你也更无法体会一个赤裸着双脚奔跑在蓝天青山绿树碧水之间的孩童,有着怎样的恣意与欢畅”。接着,作者就通过种种自然景物与女孩的行动,来具体体现这种美好与恣意、欢畅,其核心则是“风姿绰约”的“山桃花”才是外表“强大、庄重”的大山内在生命的真正所在。正是循着这一线索,作者在其后顺理成章地写了四大爷的照片对主人公小女孩的魅力所在:那照片不同于其它人照片的规范与统一,而是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动姿与鲜活;作者也才能顺理成章地写了四大爷本人对主人公小女孩的魅力所在:无论是小女孩对四大爷的痴心期盼,还是四大爷举着小女孩在空中旋转给小女孩的自由感,亦或是四大爷手掌那“男人的味道”,等等等等。可以说,四大爷就是小说主人公小女孩心中的神,是她心中对生命对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但这不是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成长,而是对个体生命自由形态及旺盛生命力的追求。这追求,在小说其后的叙述中,就化为四大爷照片背后那壮观的钢铁厂,化为四大爷女同学那诱人的照片,也化为四大爷那逃离家乡“落寞与孤愤”的身影,化为“树与草”“油绿———浅绿———黄绿———浅黄———深黄———金黄”的变换。如是,小说的最后一句才会与小说的开头回应说:“但我确信他是真实地消逝在自由的风里了,待到明年春天,他就会吹开山腰间那株艳艳的山桃花。会的,一定会”。
不是“四大爷的照片”及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故事与主题,不是那外在的显赫的大山的象征,而是在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女孩子对“四大爷的照片”的讲述中所流淌着的对个体生命形态自由及旺盛生命力的情怀,而是那“风姿绰约”的“山桃花”的隐喻,才是这小说真正的价值之所在,也是这小说给当今小说园地所增添的新景观。
因了中国当今社会都市商品经济所催生的个体生命形态自由的不健全及作者对这一生命形态感受的不力,作者们很容易驾轻就熟地从叙述传统乡村生活中来回应时代对个体生命形态的呼唤,这就是苏二花的《社火》。这小说的故事及情节没有更多创新之处:写从农村家乡出走多年的兄妹俩,大哥奋斗多年,虽然在城里终于立足,但却患了胃癌濒临死亡,妹妹即小说主人公在城里与一个有妇之夫相爱八年,但终于被其太太纠集众人剥光衣服暴打街头,且又被网络人肉搜索尽人皆知,却又怀了那人的孩子。或因都市自然生态被毒化而身患绝症,或因都市伦理生态被毒化而身心俱损,两个伤痕累累的“出走者”在春节前回到家乡,或想就此了结生命,或想打掉胎儿另谋生路。但在家乡未被污染的自然生态———龙泉及未被污染的伦理生态———乡情亲情的抚慰与滋养下,在强大的生命仪式———社火的浸染中,二人终于重新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振奋了生命的精神。这小说,你很容易落入到在都市乡村、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冲突的视阈中给以审视的窠臼,因而虽然会对小说给以称赞,但却未能发现这小说真正的价值。这篇小说,其故事、情节的叙事不是重点只是背景,流淌在其字里行间的情感的流动,氤氲在自然及乡间风情画面里的描写与抒情,在这流动与描写抒情中所蕴含的对旺盛生命力及损害生命之力的渲染,才是这小说真正的着力之处,也是这小说艺术力量之所在,并由此构成了这小说的浪漫特征。
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二花的另一篇小说《爸妈的田地》这小说写的是在省城或县城工作并已各自成家的儿女几个,因了日常利益的矛盾,或借钱或帮儿女找工作或亲情慰藉不到位等等,从而相互心存芥蒂,亲情日渐淡薄。但在共同于退休后返回乡下种田的爸妈的田地的劳作及收获中,儿女几人重温了亲情,天伦之乐融融。这小说从爸妈与儿女辈分上,从爸妈退休后执意从城里返回乡下种田上,从爸妈用各种理由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定期回乡下种田及收获上,从一家人的农耕生活上,都给读者以用传统家庭式农耕生活给现代都市商品经济之痛疗伤的意味,但如果仅仅以这种理念来破解这小说的意蕴,那这小说其实也并无多少新的创见。与《四大爷的照片》《社火》相似,这小说所叙之事甚至其中传神细节,都是作为所抒之情的依托的,是小说从开头流淌到小说结束时的女主人公超越所叙现实之事的抒情,才是这小说的基本格调,也因此构成了这小说浪漫的色彩。只是无论是《爸妈的田地》还是《社火》作者总是以怀旧以传统以乡村作为载体,来构成对今天对现代对都市的超越,你也就不得不感叹,这传统文化力量的强大,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作家,习惯于同质性地驾轻就熟于旧路,不得不感叹,这新时代中国女性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是否有枝繁叶茂的可能。
对现实社会生存法则的彼岸性拒绝的价值形态
但我也终于欣喜地看到,在苏二花的小说中,有着一种更为突出更为纯粹的浪漫主义新质,这让我对新时代中国女性浪漫主义的萌芽的成长又充满了信心,这种新质就是在其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社会生存法则的彼岸性拒绝的价值形态。
中国的传统社会,现实世俗生存法则与价值法则同一,罕有西式站在彼岸神性世界对此岸世俗世界的批判,就是说,彼岸神性世界的价值形态是此岸世俗世界理想中的价值形态,是在此岸世俗世界中注定不能实现的,但却不能因其不能实现就否认了其合理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不能在世俗世界中实现,才构成了对世俗世界的批判与价值性召唤,而这,也正是西式浪漫主义文学的价值根邸之一。伴随着新时代中国商品经济所生成的全民性的个体生命的浮出水面,站在理想世界的价值立场上,超越现实生存缺陷,也正在成为新时代个体生命的精神立场之一。苏二花的小说,则对此作了初步的反映,这也正是其小说浪漫属性的根本性体现。
最为突出的小说是她的《疤痕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及现实世俗生存法则,都把以力反抗以力制人作为男性力量之美的体现,但《疤痕净》却全然不是这样,而是对此做了根本性的颠覆。这小说写少年王伟的父亲王燎从小奉行的就是男子汉应该用拳头解决一切,谁拳头硬谁就有男子气概,为此,他在当地打架出了名,其标志就是他脸上的刀疤。王燎的父亲则奉行在这种拳头文化中,如果吃了亏,就要用各种手段报复对方,让对方受到加倍的惩罚。但王燎的儿子王伟却不是这样,他主张以忍让来等待对方的觉醒。所以,在同学殴打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还手,事后,也不动用社会压力来报复惩罚对方。这让王燎觉得王伟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但王伟却用跳楼自尽以警醒父亲的方式,来证明什么是男子汉的气概。以暴力对抗暴力,在惩罚对方暴力之时,否认对方暴力的合法性合理性存在,却又在自己用暴力惩罚对方暴力时,使自己的暴力获得了合法性合理性认可,从而在价值形态上,不再否认而是在法理上认可暴力的存在。但王伟却因了认识到父辈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恶果,因而采用了以忍让、宽容、爱来消解暴力,并在根本上全面拒绝暴力的合法性合理性。小说以王伟送给其父王燎的疤痕净最终消除了王燎脸上的疤痕,来喻示着应该以忍让、宽容、爱来消解与治愈暴力与仇恨给世界给人类带来的伤痕。在现实世俗生活中,以暴力对抗暴力,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合理性,用忍让、宽容或者用爱来消解暴力,在现实世俗生活中,则往往并不具备可行性,但这并不能否认,我们站在彼岸神性的价值立场上,对此岸现实世俗世界的暴力行为及其他所有行为,做出价值性的否认与批判,而且,也只有做出这种价值性而非事实性的否认与批判,我们才能在这样的价值召唤价值批判中,更为清楚准确地看到此岸现实世俗世界中的种种缺陷,而不是在这些缺陷的现实合理性存在中,模糊了对其缺陷属性的认识,从而让这些缺陷得以以正确的面目,绵绵不绝。这种模糊所造成的恶果,无论在中国的历史还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比比皆是。刘小枫在多年前批评茅盾等人对冰心的批判时说过:“让那些伟男子感到难堪,甚至因难堪而感到愤怒的是,弱女子竟然有比他们更苦涩的信念,有在任何悲惨和丑恶的处境中都不愿抛弃的神圣情怀……一位弱女子竟然拼命要求告那被中国历史判为不可能的然而却是神圣的东西,要拼命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法则抗争,拒不承认它的绝对力量的精神意向”这样的一种神性价值立场,在中国一向受到漠视、误解,几不为人所知,苏二花的这篇小说及其他小说,则草蛇灰线般地对此给以了延续,并觸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深刻而又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主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苏二花的另一篇小说《氢气球》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但其催人泪下的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写出了人生的某种无奈境况———这种无奈境况来自于现实生存法则的强大;却在于写出了来自于从彼岸价值世界标准出发的对此岸现实生存法则的批判。这小说的主人公是儿童小斌。小斌从小聪明美丽过人,但却得了小儿佝偻病。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舅舅甚至小斌的妹妹,都曾以种种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对小斌的极为关爱喜爱疼爱,但又为各自迫切的生存压力所限,忙着各自的事情,不可能永远时时地关爱着小斌,并必不可免地在小斌需要理解与关注的时候,忽视了他冷落了他。应该说,从现实生存法则来说,小斌所有亲人对他的忽视与冷落,都有着各自的现实存在的理由,无可指责。但从彼岸价值世界的标准来说,小斌所有的亲人,在小斌最后离世的悲剧中,却又都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正是这种站在彼岸神性世界对此岸现实世俗世界合乎现实法理的缺陷的观照与批判,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浪漫主义属性。
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二花的另一篇小说《猫爱》这小说主要写主人公王曼在小猫最初受难时对小猫的疼爱及其后与小猫的亲密相处互为依存,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及在这流逝中各自需求的变化,王曼与小猫终于成为了相互折磨的仇敌。小说后半部分写杨总对离婚后的王曼动人的百般呵护,这呵护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但你只要想想王曼对小猫最初的呵护也是真诚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你对王曼与杨总的现在与未来,就会有着如同王曼与小猫关系先爱后恨的一模一样的预判。这预判在小说一开头,写离婚时王曼对前夫先爱后恨的情感历程中,也曾经得到过证实。要而言之,情感的美好与高峰,总是存在于瞬间之中,或者说,是在瞬间得到充分集中突出的实现。这种瞬间状态,在社会现实中,不可能成为永恒状态,这就是现实生存法则。但从彼岸神性价值法则的标准出发,人又是希望这瞬间状态成为永恒。如果你在现实世俗世界中,希望实现彼岸神性世界的价值标准,力求把这瞬间状态实现为永恒状态,那么,则因了不合现实世俗世界的生存法则,在现实世俗世界中,注定会成为悲剧。但人又不应该为此就放弃彼岸神性世界对此岸现实世俗世界缺陷的观照与批判,而这,也正是女性天性,或者说,是女性性别意义的真正体现。苏二花的小说,也是如此。
华丽的语言美与瑰丽的想象
重揭示现实生存的中国文学传统,表现在文学语言上,就是对文学语言朴素美的追求,并认为朴素美是高于华丽美的,苏东坡的“绚烂之极乃归于平淡”的语言朴素论一直为写作界所推崇,就是实证。其实,浪漫主义文学以瑰丽的想象来对现实世界的情感超越,必然地需要着绚烂华丽的语言美,不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而是绚烂华丽与朴素简约是分别不同并列而立的两种形态的语言美,犹如文学世界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肩而立,只是我们常常把现实主义看得高于浪漫主义罢了。
华丽的语言美与瑰丽的想象,也必然地成为作为女性浪漫主义文学萌芽的苏二花小说的创作特点,我在这里仅举示例,让读者以一斑而窥全豹。
可以作为示例的,是《社火》中关于社火的描写文字:“有着万人之众的禳瘟会,人人都挥舞了手臂跳起了舞蹈。人一重,灯一重,烟一重,鬼一重;唢呐一重,旺火一重,古老的榆树又一重;油灯一重、炮架一重、戏台一重、僧人的袈裟还一重;天一重、地一重、星光一重风一重;九曲阵一重、地狱图一重、十殿阎君是一重,万人舞蹈腾起的尘土是一重。在今夜,人鬼不分、人神不分、人物也不分;在今夜,生不分、死不分、明暗分不清;在今夜,哀伤与欢快不分、悲戚与欣喜不分、少壮与耄耋不分、天堂和地狱不分;在此时,人影憧憧、鬼影憧憧、月影憧憧、树影更憧憧;在此时,手在舞、腿在舞、腰在舞、衣袂在舞、头发在舞、整个身心全都在舞;在此时,男在舞、女在舞、老在舞、小在舞、整个龙泉都在舞……我也有我自己的舞蹈。你看我髣髴如轻云闭月、飘摇若流风回雪;你看我如鲲鱼遨游,其大不知几千里,似鹏鸟怒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你看我轻罗小扇、蛾眉懒画,红笺小字、独上兰舟;你看我彗星袭月、白虹贯日、烹羊宰牛、斗酒十千。我长臂一舒,就能凌云壮志直插云霄;我纤腰一扭,也能情义缱绻百转千回;我长发一甩,就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我脚步一挪,也是登高临远风疾猿啸。我为什么舞得如此酣畅淋漓遍体通透,是因为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只能是这样的问题。我微笑着。用双手捧住了我微微隆起的肚子,你听,一个胎儿强有力的心脏在跳动,隆隆,隆隆,隆隆。”只有這样绚烂华美的文字,才能渲染出生命形态的热烈与狂劲,也只有这样绚烂华美的文字,才能表现出女主人公生命意识的复苏与高涨。
再譬如,《四大爷的照片》中写七岁的女孩子在山中的生活:“一只色彩明快的黄蜂很执拗地追随着我,因为我的手里正握着一束盛大开放的蒲公英花。蒲公英的花是黄色的,是那种很热烈的黄,明亮且执着。它每一个层层叠叠的花朵上,都储蓄着一个微型的太阳,当我手里握着一大簇太阳的时候,黄蜂就无限仰慕地追随而至了。黄蜂的大肚子上,也有黄色的环,是那种华丽的黄,镀了金子一般闪着光。这两种黄交相映衬着,极大的满足着我柔嫩质朴的感知与认识”。色彩的灿烂与女孩子生命的灿烂是交相辉映的,也为后面的叙事奠定了基调。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苏二花的小说,其故事其情节,只是一个背景,真正成为其情感载体意义载体的,是这些由华美语言表现出来的热烈场面与浓浓的抒情,没有了这些语言,热烈的场面与浓浓的抒情也就无从表现,她的小说,也就因此失去了根本性的支撑。
在苏二花所创作的小说中,还有着相当数量的现实主义小说,或者是借鉴现代主义手法所写的小说,如《海拔八百米》《鱼尾文》《秘密》《鸿运当头》等等,在我看来,这些小说均不及我前面所例举的小说,虽然因其揭示社会现实矛盾的尖锐,或者是情节的一波三折,或者是象征寓意的多义性,而多为评论者所称赞,但在我看来,这些小说,终不能与写类似题材的男性作家相比。如前所述,即使我在本文中所例举的小说,评论者也多用现代传统都市乡村的既定视角,从故事与情节入手,来探究这些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因之,在我看来,苏二花对自己小说中浪漫主义的特点,可能并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这一方面表现在,她创作了相当数量的非浪漫主义小说上,一方面表现在前述我例举小说的故事情节的设计上———我总觉得,苏二花在这些故事情节的设计上,更多地是从其理念预设出发,其理念预设又多受时下文学界主导倾向的支配与影响,而其小说中浪漫主义的元素与特色,则是其艺术直觉的产物,表现在其语言叙述与场面描写上,而恰恰是这一部分,构成了其小说尚未受到评论者应有的重视。苏二花这些作为新时代中国女性浪漫主义小说萌芽创作的形态与特点及其在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无论是未受到中国文坛应有重视的孤独的蒋韵,还是如同赵树理那样在接受过程中被误读的葛水平,抑或是被漠视的小岸,以及在山西许多的女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每每念及此,我都不由得为中国浪漫主义氛围的稀薄所感叹,也对新时代中国女性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是否能够大树成林,充满了困惑,只是常常有感于此,遂不吝浅薄,拙笔成文,就教于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