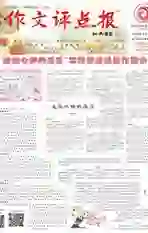西栅的梆声
2018-07-12迟子建
迟子建
乌镇是一枝莲,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是它张开的花瓣。东栅因为天光和烟火气盛,这片花瓣在我眼里是银粉色的。西栅呢,它被不绝的流水环绕着,那层层叠叠的楼台水阁,迷宫似的灰街长巷,也就有了舟楫的气象,似乎你轻轻一推,它们就会起航。
来乌镇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白鹭、云朵、晨雾。与它们比起来,依赖车船出行的人,是多么被动啊。白鹭来,乘着清风,扇动着丝绸一样的翅膀,倏忽间就翩然而至了;云朵呢,如果它们思念身下这片枕河入梦的人家了,从天宇的某个角落出发,且歌且舞,飘飘洒洒,也是说到就到了。比起白鹭和云朵,晨雾不是远客,它们就栖息在乌镇纵横交织的水泽深处。
我在乌镇,住在西栅。西栅由十二座小岛组成,所以进出西栅,须乘坐渡船。到乌镇时已是晚上九点,江南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好像乌镇这个素服女子忙活了一天,正在做安寝前的沐浴。从西栅的码头登船,去通安客栈,大约一刻钟。西栅的渡船是我喜欢的那种,带篷的木船,梭形,人工摇橹,至多坐六人,既不像大船那样笨拙少情调,又不像只能容一两个人坐的小舟,在水波上活跃得像条鱼一样,让人心生不安。不大不小的渡船,如同恰到好处的鞋子,最适合游人的脚。船家是个女子,乌镇人对她们有个亲切的称谓:船娘。而我觉得,女子的性情,最适合在西栅摆渡。因为这儿不是荒凉的海域,需要顶天立地的男人披荆斩棘;西栅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是个听桨声的地方,由性情多温婉的女子做“掌门人”,再妥帖不过了。
天色已昏,九点一刻,我独自出了门,看夜下的西栅。
石板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西栅静起来,而另一种光明,却升起来。点缀着夜晚的灯光,以乳黄为主,但也有幽蓝的光带,裹着石桥,使桥有了闪电的气象。那一盏盏古朴的风灯,在苍灰的屋檐下,随着晚风轻轻摇荡,像恋人温柔的眼。我走进一条深巷,周围竟一个人都不见,那一座座阒然无声的深宅大院,使我怀疑里面居住的不是人,而是神灵。我有些害怕,连忙回到离出发点不远的放生桥那儿,桥下有一个小酒吧,还有零星的顾客。刚停下脚步,就见柳树丛中闪出一只猫来,雪白雪白的,它好像赶赴什么约会,飞也似的越过石桥,去另一岸了。猫离去了,一个清扫员出现了。她一手拎着撮子,一手提着扫帚,打扫石巷。我看了看撮子,里面最多的是落叶。
我跨上桥,刚好看见有一只载客的船从远处荡来。我听见客人在问:“岸上是什么树呀?”船娘答:“香樟树。”之后再无人语,有的只是水声。我看着这只船渐渐接近石桥,然后鱼似的从桥下跃过,不见了踪影。正当我要走下石桥的时候,一阵梆声石破天惊地响起,这是打更的人在报时了。打更的人穿行在哪一条巷子,我并不知晓。但这寂寥而空灵的梆声,与教堂的钟声一样,让我身心顿时为之一爽。是啊,这禅意深厚的梆声让我明白,所有的盛典和荣耀,不过是一季的盛花,会转瞬间化为流水。那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包括我自己,不过是这世界的过客而已。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在脱离了灯火璀璨、人语喧嚣的环境后,惧怕一个人走夜路。这复古的梆声,让西栅的夜白了。
【赏析】
本文用童话般的笔触对乌镇的美丽自然和人性进行了一次温情凝望。在作者看来,乌镇是轻盈的,诗意的,甚至带有一丝如梦似幻的神秘。只有摆渡的船娘,零星的顾客,才带着水乡的烟火气息,让人觉得踏实和羡慕。流水的无情,禅意深厚的梆声,让她冷静和清醒,让她产生一种生命易逝、繁华易逝的感伤。这种感伤源于对生命更深刻的思考,源于對生命价值的自觉审视和叩问,使散文在细密的抒情之外又呈现出了思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