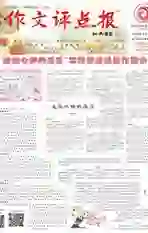魔季
2018-07-12张晓风
我沿着坡往山上走,春草已经长得很浓了。唉,春天老是这样的,一开头,总惯于把自己藏在峭寒和细雨的后面。等真正一揭了纱,却又谦逊地为我们延来了长夏。
山谷已经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绒绒的芦花海也都退潮了。相思樹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儿的小草是黄绿的。还有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藤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山。我慢慢走着,绿在我里,我在绿里。
那边,清澈的山涧流着,许多浅紫、嫩黄的花瓣上下飘浮,像什么呢?我似乎曾经想画过这样一张画——只是,我为什么如此想画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心底也正流着这样一带涧水呢?
我们已把窗外的世界遗忘得太久了,我们总喜欢过着四面混凝土的生活。我们久已不能想象那些溪畔草地上执竿的牧羊人,以及他们仅避风雨的帐篷。我们同样也久已不能想象那些在垄亩间荷锄的庄稼人,以及他们只足容膝的茅屋。我们不知道脚心触到青草时的恬适,我们不晓得鼻腔遇到花香时的兴奋。真的,我们是怎么会疾驰得那么厉害的!
忽然,走来一个小女孩。如果不是我曾看过她,在这样薄雾未散尽、阳光诡谲闪烁的时分,我真要把她当作一个小精灵呢!她慢慢地走着,好一个小山居者,连步履也都出奇舒缓了。她有一种天生的属于山野的纯朴气质,使我不自已地,想逗她说几句话。
“你怎么不上学呢,凯凯?”
“老师说,今天不上学。”她慢条斯理地说,“老师说,今天是春天,不用上学。”
啊,春天!噢!我想她说的该是春假,但这又是多么美的语误啊!春天我们该到另一所学校去念书的。去念一册册的山,一行行的水。去速记风的演讲,又数骤云的变化。春天春天,春天来的时候我们真该学一学鸟儿,站在最高的枝柯上,抖开翅膀来,晒晒我们潮湿已久的羽毛。
那小小的红衣山居者好奇地望着我,稍微带着一些打趣的神情。
我想跟她说些话,却又不知道该讲些什么。终于没有说——我想所有我能教她的,大概春天都已经教过她了。
慢慢地,她俯下身去,探手入溪。花瓣便从她的指间闲散地流开去,她的颊边忽然漾开一种奇异的微笑,简单的、欢欣的,却又是不可捉摸的笑。我又忍不住叫了她一声——我实在怀疑她是笔记小说里的青衣小童。我轻轻地摸着她头上的蝴蝶结。
“凯凯。”
“嗯?”
“你在干什么?”
“我?”她踌躇了一下,茫然地说,“我没干什么呀!”
多色的花瓣仍然在多声的涧水中淌过,在她肥肥白白的小手旁边乱旋。忽然,她把手一握,小拳头里握着几片花瓣。她高兴地站起身来,将花瓣往小红裙里一兜,便哼着不成腔的调儿走开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了一下,她是谁呢?是小凯凯吗?还是春花的精灵呢?抑或,是多年前那个我自己的重现?在江南的那个环山的小城里,不也住过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吗?在春天的时候她不是也爱坐在矮矮的断墙上,望着远远的蓝天而沉思吗?她不是也爱去采花吗?爬在树上,弄得满头满脸都是乱扑扑的桃花瓣儿。等回到家,又总被母亲从衣领里抖出一大把柔柔嫩嫩的粉红。啊,那个孩子呢?那个躺在小溪边打滚,直揉得小裙子上全是草汁的孩子呢?她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啊,春天多叫人迷惘啊!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谁负责管理这最初的一季呢?他想来应该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了,当他的神笔一挥,整个地球便美妙地缩小了,缩成了一束花球,缩成了一方小小的音乐匣子。他把光与色给了世界,把爱与笑给了人类。啊,春天,这样的魔季!
【感悟借鉴】
张晓风用轻柔的笔触、优美的语言,诠释春天里的美与乐。春有魔力,春的感召力、象征力和生命力在本文中渐次呈现。遵循作者的写作思路,实写了两个画面,一个是大自然的画面,具体描写了绿色的谷和清澈涧水里的花瓣儿;一个是人在自然中的画面,即作者与凯凯在春意盎然中相遇的画面。紧随每个实写的画面后,各有一个自然段“犹抱琵琶半遮面”式地虚写:前一个触景生情,引发对牧羊人、庄稼人闲适生活的回想;后一个由此及彼,由凯凯联想起童年的自己在江南的春天徜徉。作者或以“我们久已不能想象……”的句式,或以多个问句形成连贯之势,呈现虚实交替的过程,彰显作者联想、回味的过程,表达作者对春的喜爱、对童年的追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淡淡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