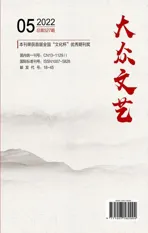影视批评的社会学方法新论
2018-07-12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150000
赵 乔 (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150000)
一、打破“反映论”
没有一种文艺批评方法能够像社会学方法这样,在我们当代的学理语境中长盛不衰。传统的社会学影视批评打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旗号,却仅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眼光来审视影视,从而致力于将影视看作是意识形态代言工具,过度强化影视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种批评的缺陷乃在于无法形成对影视艺术的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结合。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是80年代末期,影视表现风格日趋多元化,影视的审美属性成为影视批评的新热点,而影视批评中也越来越融入符号学、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等等视角与方法,社会学方法却日渐式微。90年代末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社会学方法又重获影视批评的青睐,种族、性别、青少年亚文化、空间等等社会学范畴在影视批评中迸发出惊人的理论力量,迅速与审美批评并驾齐驱,直至现在依然方兴未艾,然而此时的社会学方法就只是一种解读影视作品的方法,鲜有批评者能够认识到其作为一种观察影视的根本性思维与决定性视野的重要意义。
影视批评中社会学方法的价值在于剖析和阐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深刻地认识现实理解社会。在当代社会学方法的使用史中,无论是传统的阶级分析还是更多元的社会主体分析,都是在“反映论”的视野下解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这几乎成了社会学方法的底色。但实际上,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极其复杂,绝不是单纯而直接的“反映”。首先,影视作为典型的大众文化,积极参与对现实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正是文化建构的后果;第二,影视对现实的反映往往是曲折的,影视中的现实甚至是经过伪装而扭曲的“现实”,影视之于现实仿佛碎片之于星丛整体,必须缝缀起碎片方能显现整片星空,简单地说,只有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俯瞰才能解构影视的文化编码。社会学方法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这种历史视野。本文借社会学中“功能论”、“冲突论”和“互动论”三种阐释社会的经典理论,试图打造一种新的社会学影视批评模式,从多重视阈探寻影视与现实的关系。
比较而言,通过传统的反映论视角与方法感知的现实只是现实感,而通过功能论、冲突论和互动论多维视角与方法体认的现实则是现实寓言。所谓的“现实感”指的是影视中所呈现的真实的生活场景、热门的社会现象、普遍的生活遭遇,而“现实寓言”指的是影视中无限接近真实社会境况的现实表征,无意识地暴露社会深层、结构性问题。
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表意文本之中还含有一个潜文本,作者通过写作传达某种意义,而阐释者则通过批评构造出潜文本。潜文本所携带的意义是作者自己所意识不到或没有明确传达的。而阐释者则有可能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和方式,将一个个别的文本辩证地嵌入到整体的社会历史中去,将个别文本转换成社会总体的寓言。可以说,新的综合性的社会学方法,建立在对文本与社会“互文”的体认基础之上。影视的互文性,不仅局限于不同影视的互相指涉、共享主题、雷同桥段;也不囿于影视与文学或其他媒介之间的转换;最重要的是影视作为表意文本与整个社会历史之间的互文,串起多部影视,将这些影视与社会现实勾连在一起进行诊断,就有可能去发现某个特定时代的症候。
在本文中选取的影视案例主要为两季《欢乐颂》(2017,2016)、《小别离》(2016)、《小丈夫》(2016)、《虎妈猫爸》(2015)、《大丈夫》(2014),均是近三年受消费市场认可和追捧的热门剧集,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均被研究者视为社会学的影视化表达。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吃瓜群众”,热衷于比对这些影片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吻合,比如将由热门IP小说改编的《欢乐颂》与现实生活进行比对,大城市生存的居大不易、三十岁剩女的悲哀、恋人买房署名问题等等,看主角的经历是否让观众感同身受地“扎心”,这样的思路无疑是反映论的。笔者却注意到,这些电视剧在更隐秘的层面形成互文,构成现实寓言,将这几部电视剧勾连在一起,恰恰呈现了一个日益形成并坚固的中产化社会图景,以及潜伏在表面的欣欣向荣之下的危机困厄。所以笔者希冀借助对这几部电视剧的互文解读来说明前文中所提倡的新的影视批评社会学方法,开拓社会学方法的内涵。
二、功能论视角:影视与现实的疏离
下面分别对“功能论”、“冲突论”、“互动论”三种视角进行阐发进而示范影视批评中社会学方法的新形态。
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论,意在说明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而且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共同维持着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这一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那么各个部分会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功能论”影视批评,即强调影视作为一种幻想形式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也就是大众文化的造梦功能,这里所说的“社会稳定”更多的是意味着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以及对社会不良情绪的排遣化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焦虑与挫败感的纾解。
在“功能论”视角审视下的现实主义影视剧显现出与当下社会现实的疏离。首先,追求纯粹的爱情。《欢乐颂》中安迪与包奕凡、曲筱绡与赵启平之间的爱情都是高度理想化的,甚至是轰轰烈烈的;邱莹莹与应勤的复合也是以应勤最终摆脱“处女情结”困扰、唯独执着于爱情的前提下;关雎尔对谢童由不得半点将就,只要选择了就义无反顾;只有樊胜美与王柏川的爱情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所以在二人开放式的结局中,樊胜美主动提出了分手,并且表示即使两个人还可以重新开始,也应该是以各自独立的姿态。这和流行的青春偶像剧以及近些年极受电影市场欢迎的青春片有相同的套路。这些青春类型片无一不执着于回忆青春,让青春在记忆中重新焕发光彩;无一不纠结于年少的爱情,甚至将爱情当作神圣的信仰,仿佛因为曾经发生过那样刻骨铭心的爱情,人生才具有意义。在此,“功能论”的视角和方法引导我们发现,想象轰轰烈烈的爱情,是因为爱情已经变成了能够抵抗当下庸常生活的唯一可能,绝对纯粹是为了克服这个功利市侩主义盛行、日渐物化、冰冷残酷的社会给人的内心蒙上的焦虑和阴影。第二,弥合阶层的差异。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却产生令人羡慕的伟大友情,每个人对友情都无比珍视。在“欢乐颂”里共处的五个女孩之间的情谊是本剧的最大看点,任谁遇到了难处,经常是五个人聚在一起想办法,进行陪伴宽解。甚至还有曲筱绡在樊胜美老家,借助包奕凡的人脉,替樊胜美出头与其无赖哥哥进行谈判从而解决了樊胜美的麻烦,然而这一切却又不让樊胜美知道、无需她领情,这样的情节架构凸显了曲筱绡仗义机智的江湖气概,更凸显了“欢乐颂”姐妹之间的真情,曲筱绡的颐指气使、诡计多端、惹是生非都不再令人生厌,因为曲筱绡是在关键时刻可以伸手拉姐妹一把的人,她是如此的重情重义。在这一点上,《欢乐颂》和《小时代》系列电影呈现出很大的相似性,所以有评论者称《欢乐颂》是后者的剧版。毫无来由的姐妹情深填补了阶级差异的鸿沟,掩饰了财富不均、社会地位悬殊的真实社会境况。第三,预设圆满的结局。无论现实多么糟心、过程多么艰辛、矛盾多么尖锐,但是最终还是一团和气的美好,仿佛所有电视剧剧都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当我们为矛盾的解决长舒一口气,沉浸在冰释前嫌的欣喜中,忍不住为雪中送炭点赞时,实际上正是陷入了“光明的尾巴”所制造的叙述幻觉之中,圆满的结局给了我们希望和满足。在“光明的尾巴”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是处理无解社会问题的惯例手法。
三、冲突论视角:影视与现实的辩证交织
社会学理论中的冲突论,与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功能论不同,它关注的是社会动荡与变革,大到永恒的阶级冲突,小到种族差异、性别歧视,广如整个社会的转型与断裂,深如阶级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比如中产阶级与“新穷人”的不断壮大。冲突论认为,这个社会无论多么繁荣发展却仍然潜伏着导致变革的不安定因素。“冲突论”影视批评,撕掉了影视柔情的美学面纱,将其作为社会冲突寓言的内核剖出,意在通过影视去捕捉社会危机。
通过“冲突论”视角就能够洞察现实主义影视剧努力掩饰、想象性解决的现实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看,现实主义影视剧与现实辩证交织,在走向现实寓言的过程中逐渐抵达真正的现实、历史的真实。首先,塑造阶层形象的意识。放眼近几年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聚焦的现实矛盾不一样,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尽管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纷纷出场,但勾连起来却共同呈现了一个中产化社会的图景,在不断地表达与型构中,一个阶层的形象愈加完整和清晰。表面上是呈现一个丰富复杂流动的社会,翻过来却是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这恰恰是一种深层认知的建构,而非对现实的单纯反映。电视剧作为典型的大众文化,在促使我们以某种方式感知现实的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与学术知识生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建构认知的方式,一是视角的选择,在《欢乐颂》中,看似每个人都带有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标签,然而这个隐藏的贴标签的人正是中产者,因为在阶层的区分与体认中含有强烈的情感态度与引导倾向,对于比自己更高的阶层是仰视、无法企及的无奈,对于比自己落魄的阶层则是俯视、恨其不争的同情;一是对中产阶层构成的溯源,《虎妈猫爸》所谓的“虎妈猫爸”不仅是教育理念的形象分野,同时也是阶层内部差异的形象表征——来自农村靠读书改变命运与从小生长在优越家庭环境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组成家庭,他们之间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正是一个阶层同一化的过程。第二,想象全景社会的欲望。在这个单子化、原子化的社会,大多数人都囿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圈地自存、受制于各种规则条框不敢逾越,无法了解自己于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没有能力超越个人视野去思考别人的处境,这样一种状况使阶层壁垒日益坚固,吊诡的是一方面形成了群体性冷漠与无知,另一方面却养育了大众对八卦与隐私的窥探欲求、滋生了大众对社会总体与全貌的求知欲望。现实主义影视剧在某种意义上正迎合与满足了大众的欲望,同时,在积极建构社会全貌的过程中也显现着这种欲望。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认知建构必然是主观而非客观现实。于是我们看到在《欢乐颂》中差异化的社会阶层代言人,二十二楼的每个人从身份地位、性格爱好到言语品味都是依特定阶层量身锻造,填满了大众对不同阶层的所有好奇。而在围绕中学生留学问题展开悲喜的《小别离》里,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三个家庭又成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镜像,当因为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而给方圆和文杰这个中产家庭带来地震和旋风般影响时,较之更高阶层的轻松应对和更低阶层的无奈放弃,实在令人唏嘘。当这些画面同时在大众眼前铺展开,实际上正是提供观察与了解其他阶层的一个切入口。可以说,尽量展示全景的社会、差异化的阶层状况已经成为现实主义电视剧叙事的共同结构原则,然而愈是疯狂地想象社会总体与建构他者,愈是暴露出自身偏于一隅的视野局限。第三,重构伦理价值的冲动。社会变迁与转型导致了社会的失范与无序,传统伦理价值虽然根深蒂固,但是不断地与现实发生龃龉而遭受质疑,陷入伦理困厄的大众亟需新的伦理价值指引。当下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也积极参与了伦理价值的重构,这些电视剧试图呈现一种“中国式关系”——在维护传统价值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寻找突破,并且为其合理性正名。“欢乐颂”二十二楼、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五个女孩,这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空间与人际的隐喻。《欢乐颂》用了很大的功夫来讲述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二十二楼的五个女孩两两都有交集,但是通过细节刻画,电视剧不断地提示观众她们的亲密程度、交往界限、相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难理解这背后有阶层设定的缘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视剧在谨慎地探寻陌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其中暗含的正是重构伦理价值的强烈冲动。《大丈夫》和《小丈夫》在这方面的意图暴露更加明显,有年龄差距的婚姻是典型的非“门当户对”,所以总是引起争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面临更多问题,这两个电视剧努力地告诉人们有年龄差距的婚姻是应该被认可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但尴尬的是,化解的途径经常是悬置或者无视矛盾,电视剧在定义新的伦理价值和规范时的无助和犹疑反过来又刺激着建构的冲动。可以说,对现实主义影视剧塑造阶层形象的意识、想象全景社会的欲望、重构伦理价值的冲动的体认帮助我们发现真实的社会图景。
四、互动论视角:影视对现实的迎合
社会学理论中的互动论,又与着眼于宏观社会状况的功能论、冲突论不同,互动论从微观切入,拆解具体的互动交往过程,辨析个体诉求与反射回应,互动论认为,无数的互动联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互动论”影视批评,着重考察影视与现实互相延伸的状况,发掘影视中隐含的受众立场与文化召唤方式。
“互动论”视角所见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之于现实,既非“功能论”所见的疏离,也非“冲突论”所见的辩证交织,而是迎合,“互动论”视角所勾勒出的影视与现实积极互动的状况,正凸显了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亟待受众参与和认同的文化生产逻辑。从显性的层面看,通过精准的受众定位,对电视剧人物形象独特风格和个性魅力的强化,激发观众对形象“同款”的强烈消费欲求,此外电视剧中已经非常普遍的故事情节中加载广告植入,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从而使影视有效地连接现实生活中的大众群体。从隐性的层面看则更为复杂,因为受众立场在现实主义影视剧中往往是预设的,所以在叙事中流露出的情感评价与价值判断就会显得“接地气”,易于获得大众的共鸣。而如何争取到更多的大众?这就要在电视剧里面差异化群体中寻找更多的共性,于是我们看到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生存状态和品味乐趣竟然有极多相似的地方,不妨说,“反区隔”成为了这类电视剧独特的文化召唤方式。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这本书中,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了不同的趣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天然的趣味,趣味与阶级相关联,阶级是区分趣味的根本,所谓的“反区隔”正是解除趣味与阶级或者说阶层的关联。还是以《欢乐颂》为例说明,首先,根本停不下来的工作。五个女孩都是事业女性,富有的安迪去包奕凡的家里都要带上电脑抽空工作;同样富有的曲筱绡过年的时候受到奶奶冷落,干脆到国外争取项目资源;底层的邱莹莹不上班的主动去各个公司推销咖啡;樊胜美和关雎尔周末到小区附近的咖啡厅继续工作……无论属于什么阶层,拼搏奋斗都是常态。第二,吃无差别。《欢乐颂》对于吃饭的情节总是呈现得非常细致,安迪这个社会精英女性,在享受美食方面和邱莹莹并没有什么差别,绝非一味五星饭店高档场所,家里的火锅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还会带着包奕凡去小快餐店吃包子。第三,趣味等同于个人爱好。听音乐会、看话剧、读书这些不是某个阶层专有的精神生活和需求,也不必然是高雅格调,对于安迪、关雎尔这就是个人爱好,曲筱绡不擅长这些反倒增添了她的可爱。在电视剧里有个情节,赵启平和他的母亲一见面就互相拿出写有生僻字的纸条比较谁认得的字比较多,曲筱绡在一旁无所适从,在这里,文化爱好不仅仅不高雅,甚至已经有点恶趣味了。“反区隔”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平庸化的社会,这是电视剧迎合现实的后果,有趣的是,将“冲突论”与“互动论”的视角结合起来看,这种“反区隔”正是一个日益中产化的社会的文化建构方式,取消趣味的阶级属性,却又处处显示出普及化的趋同化的趣味。
把社会学方法作为一种观察影视的根本性思维与决定性视野,从多重视阈把握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寻找运用社会学方法解读影视作品的新策略,是本文的题中之义;调动赖特·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综合多种社会学视角,串联起多部互文的影视作品,将其作为社会寓言的内核剖出,才是社会学方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