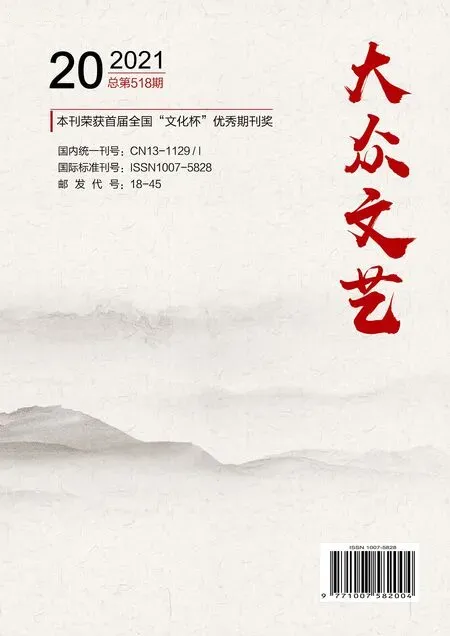埃贡·席勒绘画作品中的母性形象研究
2018-07-12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310000
(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310000)
母亲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母爱也是人类来到世界上感受到的第一种情感。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母性的依赖和崇拜是一种“原始情节”,沉淀于人类文化意识深处。对于孩子来说母亲是其存于世间身体和情感的依靠,同时母亲也是孩子对世界进行摹仿和认知的首个对象。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其独立的人格逐渐要求摆脱母亲的束缚,孩子与母亲的对抗日益凸显,此时的母亲不得不接受与孩子分离的无奈。在埃贡·席勒的众多表现母性的绘画作品中这种母与子之间的依赖于挣脱间的矛盾关系就体现的极为明显。
一、席勒与母亲的关系
埃贡·席勒的母亲玛丽·绍库普生长在一个信仰捷克天主教的传统波西米亚家庭,她是席勒生命中的第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唯一一位陪伴席勒一生的女性。玛丽·席勒是一位典型的世纪末欧洲中产阶级女性,在父权统治和社会传统思想的双重压制下,她在丈夫与孩子间努力扮演着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她,自结婚之日起疾病、死亡、忧愁、苦痛便成为她生命中的关键词。
由于丈夫的早逝而陷入经济困顿的窘境,加之自身疾病的困扰已经让玛丽·席勒精疲力竭,与儿子埃贡·席勒之间脆弱的母子关系更让她心力憔悴。同时,她将自己对生命的恐惧用抱怨的形式毫无保留的展现在年幼的席勒面前。心理学家罗洛·梅曾指出:“父母的恐惧不只会‘影响’孩子的恐惧,孩子更会因为双亲之故,学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事物。儿童的焦虑发展,主要是来自他与父母的关系”1,因此玛丽·席勒的恐惧和抱怨便使得席勒在压抑的环境下也变得敏感而焦虑。得不到母亲关爱的席勒,同样以抱怨的方式对他的赞助人诉说自己对母亲的怨恨:“我不能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我母亲为什么会用这种与我期望中所真正需要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我!如果仅仅是别人就算了!但是,她是我自己的母亲!难以言喻的悲哀!而且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可能发生。这违背了自然的本性。……我与我的母亲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我与她血脉相通,但在精神上我们完全不同,这并非不幸,真正的不幸是很多时候她对待我时的举动如同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这让我很受伤。”2埃贡·席勒对母亲玛丽·席勒有着复杂的情绪,他爱着他的母亲,但是他的爱没有得到回应,更没有得到满足,于是起初这份对母亲的爱转化成对母亲强烈的怨恨甚至仇视。在他描绘母亲以及母与子题材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几乎都一幅面目狰狞、用心险恶的模样。
席勒创作于1906年的作品《玛利亚与孩子》中他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邪恶的母亲与孩子在一起的场景。画中的母亲是圣母玛利亚,她在画面的中后方,观者看不清她的面容,只能看见一双睁大的眼睛,眼神中流露着凶狠的目光,在她怀里的是一个有着卷曲头发的儿童——耶稣基督。基督通体雪白,眼神中充满了害怕。与历史中流传下来的宁静祥和,闪耀着母性光辉的圣母子图相异的是,席勒笔下的圣母一只手摸着怀中耶稣,另一只手却似乎想要去捂住正在呼救的耶稣的嘴,作品中看不到母爱的存在,却给人一种紧张恐怖之感。整幅作品是红色的色调,特别是圣母的头发和衣服完全隐没在暗红的背景中,只有耶稣基督使用了白色,成为画面的亮部。席勒没有遵循透视的原理,而是将圣母子二人处理成具有装饰性的平面,并且只突出圣母子圆睁的双眼和不成比例的巨大的手,这使得作品的气氛更显诡异。玛利亚既是圣母的名字同时也是席勒母亲的名字,席勒正是利用这样的“巧合”隐喻自己对母亲的不满和愤怒。
二、孕育中的母性形象
母亲是人类生命的缔造者,这是生理本能赋予女性的职责与命运。一个女性孕育生命的过程充满着艰辛,她承载着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及整个人类对生命的渴望。人类时时刻刻在面对未知的恐惧和死亡的威胁时,是母性的光辉照亮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壮大之路,母亲是生命和慈爱的象征,因此母亲在众多艺术作品中被艺术家们塑造成神圣、伟大、美丽、温婉的形象。然而在埃贡·席勒的作品中,怀孕的母亲却都是一副将死或已经死去的模样,她们正在被死神召唤,或者干脆成为了死神的代言,腹中的生命在周遭死亡的威胁下危在旦夕。生与死的矛盾在画面里形成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张力,不安、焦虑和肃杀的气氛呈现出席勒对人类死亡本能的认识与思考。
埃贡·席勒之所以会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表现怀孕母亲的形象与他童年时期受到的心理创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席勒的父亲阿道夫·席勒在婚前感染了梅毒并且将梅毒传染给了席勒的母亲玛丽·席勒,梅毒病毒不断感染玛丽腹中的胎儿,导致玛丽接连的小产或产下死胎。因为梅毒,死亡一直笼罩在席勒的家庭中,除了未出生就已经离开人世的婴儿,在三岁的时候他便亲身经历了十岁姐姐的早夭,之后他的父亲又因为晚期梅毒的爆发疯癫而亡。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席勒对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恐惧,母亲的多次死产,让他不得不将新生与死亡联系在一起。1910年初,席勒在维也纳大学妇产科朋友埃尔温·冯·格拉夫的允许下,以前来进行产检的孕妇为模特,创作了多幅“妇产科水彩画”3。在这些水彩画中,席勒运用红色、橘色、蓝色、紫色等表现性的色彩描绘模特的皮肤,使孕妇们看上去仿佛得了大病一般,显现出强烈的主观意味。例如作品《穿红色袜子的站立女裸体》中描绘了一个红色头发穿着红色袜子的裸体孕妇,席勒用黑色的线条勾勒了她身体的线条,因怀孕而胀起的肚子显得沉重不堪,席勒用绿色、黑色、黄色和橙色表现孕妇的皮肤,反常且阴暗的色彩使孕妇看上去呈现出一种病态,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死亡的气息。
19世纪末,产妇在孩子出生时死亡是一件并不罕见的事情,因此怀孕生子对于女性来说充满危险和恐惧,新生命降生的时刻同时可能会葬送母亲的生命。在“妇产科水彩画”系列作品中,席勒还仅仅是用带有表现性的手法暗示了死亡的存在,但在此之后创作的作品《死亡的母亲I》则直接表现了母亲的死亡。此作品中席勒描绘了一个已经死亡的怀孕母亲。画中的母亲披散着头发向右无力的歪着头,她眼睛紧闭,棱角分明的脸上是土褐色干枯的皮肤。她歪向右边的头与伸出的左手形成了一个近似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代表了画中母亲隆起的肚子。与传统表现孕妇的绘画极为不同的是,席勒在画中明确画出了孕妇腹中的胎儿。孩子所在的圆形空间不仅是画面中最亮的地方,也是整幅作品的中心,他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等待着自己的降生。孩子的头靠向左边,正好位于母亲的脸颊下方,仿佛是想与母亲更加亲近。他半睁着眼睛右眼上长着浓密的睫毛暗示着不断生长的迹象。与母亲蜡黄皮肤和枯瘦的脸庞相比,席勒在表现胎儿时使用了象征着生命的红色与橙色表现了胎儿的嘴唇、脸颊和双手。整幅作品中母亲和胎儿都被无尽的黑色包裹着,他们仿佛被置于宇宙的混沌之中。席勒用连续的大笔触一圈圈的画出了分割胎儿和母亲的空间,新生的力量被暗示着死亡的层层黑暗包围着,最终陷入死亡的涡旋里。
对于席勒来说,他用母亲的形象,特别是孕妇的形象直接表现死亡的景象除了表自己对母亲经历的同情、对自己童年时心理阴影的抚慰,更展现了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无助,流露出自己的悲悯情怀。
三、宗教隐喻下的母性形象
埃贡·席勒在他所创作的女性题材绘画作品中直面人类死亡的景象,此时他使用了带有宗教隐喻的圣母形象来阐释死亡的神秘,以及诉说在面对死亡时人类所显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惧。
众所周知,宗教是人们在面对死亡畏惧时精神的庇护地,并且给予了人类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基督教信仰至席勒生活的年代已经在欧洲延续了上千年,然而世纪末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人们早已不再将“上帝的全能”奉为精神信仰的圭臬,之后尼采振聋发聩的一声“上帝死了!”,更是彻底打破了人们的信仰体系。然而旧有的信仰已经崩塌,新的信念尚待建立,人类又无法用科学技术对终极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焦虑、恐惧、惶惑成为整个社会气氛的写照。面对此情此景的席勒将人类的死亡与宗教的死亡相类比,用圣母玛利亚的死亡揭示自己对人类生命生死轮回的理解。
圣母玛利亚是基督教中耶稣基督的生母,在西方艺术史中圣母玛利亚被无数大师塑造为一个集贞洁、美丽、温柔、生命活力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形象,圣母玛利亚是人类母爱、生命、希望的象征。然而在席勒的寓意性作品里,他颠覆了传统的象征意义,将圣母玛利亚描绘成将死或者已经死去的形象,此时的圣母虽然依旧抱着婴孩,但她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成为死亡的代表。创作于1912年的作品《母亲与孩子II》中席勒便以母与子的主题描绘了圣母的死亡。作品的尺幅并不大,但席勒使用了圣像画的构图模式,将母亲和孩子绘于画面的对角线位置上,饱满的构图使画面的气氛显得庄严肃穆。画中的母亲微侧着清瘦的脸,紧闭着双眼和嘴唇,灰色的脸上颧骨下陷而且没有血色,她的头发与背景的黑色融为一体只有一条蓝色的带状条纹将其头发与背景稍微分离开来,这条蓝色的条带既像母亲身着的衣服的帽檐,又像圣母头后象征拥有神性的光圈。母亲伸出干枯的右手紧紧搂住孩子的肩膀,她怀中的孩子则面对着观众,睁大着蓝色的眼睛,微张着嘴,露出无比恐惧的神情。孩子黄色的头发像太阳的光圈,又像跳动着的火苗一般向四周竖起。他伸出左手,五指张开,好似在向外求救又好似想要挣脱母亲的怀抱。整个画面除了母亲、孩子的脸和手处于光亮之中,剩下的背景部分是一片黑暗,席勒的用笔快速又狂放,不均匀的色彩痕迹表现出黑暗世界里的动荡与杂乱。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紧闭着眼睛的母亲仿佛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她闭上的眼睛切断了所有关于生的希望,暗示着自己已经落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随着一战的爆发,人类开始经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战争爆发初期,包括奥地利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带着对战争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对英雄主义的狂热奔赴前线,当时众多欧洲民众并不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一个怎样可怕的地狱场面。然而席勒在民族主义疯狂煽动的情绪下保持着冷静,这不是因为“他觉得战争让他从艺术创作中分心,而是因为他敏锐的感觉到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敌人”4。席勒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直觉感受到来自战争和死亡的威胁,面对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无情践踏,时隔两年之后的1915年,席勒再一次以宗教隐喻下的母与子为主题创作了《母亲和两个孩子II》和《母亲和两个孩子Ⅲ》。如果说之前母与子作品中母亲和圣母的死亡更多的代表了席勒对自己童年经历死亡噩梦的诉说,那么此时死亡的圣母玛利亚则代表了席勒对整个时代、对正在遭受死亡折磨的人类的无可奈何和无限同情。
综上所述,可见席勒用隐喻的方式探索着人性中死亡本能的神秘和强大,他一次次通过描绘母亲死亡的图景,描画生与死看似矛盾的同在景象是想要向人们强调生命中死亡的必然,坦然承认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扭曲。但同时席勒也在画中呼唤生命的力量,当死亡逼近时,生命的希望之光尽管微弱,却依旧闪耀。
注释:
1.[美]罗洛·梅.朱侃如译.焦虑的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4.
2.Roessler, Arthur, Erinnerungen an Egon Shiele, Vienna,1948. 62.
3.Kallir,Jane. Egon Schiele’s Women,Prestel Verlag, 2012.87.4.Kallir, Jane. Egon Schiele’s Women, Prestel Verlag,201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