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爹记
2018-07-10郭焕平
1
星期天下午,我在开教师例会,讲了三句话,手机响了。我看都没看一眼,把手机挂了。手机又响了,我又挂了。手机再次响起来,我瞄了一眼,六叔打来的,还是挂了。六叔爱喝酒,是那种离了酒不能活命的人,隔三差五来学校喝一顿,一喝就醉,一醉就麻,一麻就闹,讨嫌死了。手机第四次响了,我连忙说在开会,等一会儿打过来。我正要挂电话,听六叔说爹三轮车翻了,胳膊砸断了。六叔见我没挂机,接着说爹是在田家沟那条路上出的事,现在他把爹送到柳坪镇卫生院来了,叫我快到医院去。
我赶快结束讲话,直奔卫生院。在大厅遇见了王医生。我问王医生刚送来叫德中的病人住哪间屋。王医生说在北面从东往西数第二间屋。我进屋见张医生在爹腿子上缠纱布,爹闭着眼睛。我喊了一声爹,爹应了一声,声音又低又沉,像蚊子嗡嗡叫。张医生说病人体弱,喊一声够了,莫和病人说话。张医生介绍了诊断结果:爹腿上破了一个洞,流了好多血。左胳膊不能动弹,肿了,片子拍了,骨折,打石膏带固定住就行。正说着,护士送报告进来了。张医生瞅了一眼报告说,血的指标是5.5,低于 6个指标必须输血。张医生叫我到县人民医院买一袋400毫升B型血来,越早越好。我听到B型血,心里咯噔了一下。娘去年在县人民医院切子宫肌瘤,输的是O型血。我自己是A型血,爹应该是A型血才对。我问张医生,买B型血,没搞错吧?可要查仔细啊!我还想说什么,突然想到后面话不能说出来了,那说出来丢死人了。张医生说不可能错,这错了会出人命的。
通过分析血型,得出我不是爹亲生的结论。我是个私生子,这个怀疑了几十年的问题,今天有了结果。其实,几十年来,关于我的身世之谜,传闻从未间断过。奶奶对我讲,在我三岁那年一个冬天下午,爹与娘又吵架了。吵架原因,无怪乎是我长得不像爹。爹双眼皮,我是单眼皮。我眉毛上有颗痣,爹没有。我屁股墩子上有块黑色胎记,爹屁股墩子白白净净。爹在一气之下,将我扔进了屋后水塘里,若不是娘跳进水塘救起我,我早冻死了。四岁那年,爹将我送给了远安县一吴姓人家。这吴伯老婆十几年没有生娃子。他们捡到我,不亚于捡到了一块宝,好吃好穿好玩的,要啥买啥。说来奇怪,我到吴伯家第二年,吴伯老婆生了一个胖小子。娘听说这件事,怕人家有了自己孩子,我会失宠,娘把我接回了家。我回来后,爹和娘常常吵架,大都为了我。一不小心,我做了错事,爹会请我吃“包面”。“包面”指的是饺子。爹握紧拳头,用指头的骨结,狠狠钉我脑袋,紧接着,我脑袋会起几个大包,这大包形似“饺子”。从这时起,高坎奶奶对我说,我不是爹亲生的,是娘偷人怀上的。小伙伴常在背后喊我“野种”。要知道,在当年,名声比黄金贵得多。我哪里容得下这个屈辱,冲上去和小伙伴们拼命,要撕他们的嘴。往往是我一个人对付一群人,结局是我被打得头破血流。娘看见我这一副模样,立马跑进厨房,一只手提菜刀,一只手拎剁骨头刀,挨家挨户去骂她们。娘边跺脚边骂,哪个龟孙喊我娃是“野种”,我手里家伙就饶不了谁,那是一副一起死亡、共同毁灭的架势。娘从早晨骂到中午,从下午骂到晚上,从晚上骂到天亮。娘骂得他们白天不得安宁,晚上睡不成觉。坎上坎下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看见娘这个架势,只好采取不理会态度。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和小伙伴们玩了。我独自呆在家中,很少外出。有时上山放牛,我会戴一顶鸭舌帽,把脸遮严,遇到村民,从不搭腔。我是他们眼中的“另类”。我孤僻。我寂寞。我过着属于我一个人的生活。
2
血是二妹在县人民医院买的,用去三百八十块钱。住院费是我垫的,预交了两千块,头一天就花光了。医生催要再交两千块。我给大妹和二妹打电话,让她们两个商量,怎么交,交多少,我不管。之所以要这样做,缘于这个家庭结构復杂。1992年4月,我十三岁,读六年级。娘发誓再也不受爹欺负了,与爹离了婚,彻底离开了这个家。娘带着我,嫁到了高崖村姓唐人家。高崖村也属于柳坪镇管辖。娘的第二任丈夫,我的继父叫来顺。娘叫我莫喊爹,喊伯。来顺伯在村里开了一个瓷土场,生意还过得去。1998年夏季,暴雨下了两天两夜,瓷土场发生大面积滑坡,矿渣掩埋了三台东风大卡,七个民工,还有老板来顺伯。家变为一贫如洗。娘成为寡妇,终生未再嫁。
爹与娘离婚半年后,爹又续了二房,在家办了一个养猪场。爹二房先后生了两个姑娘,我喊大妹和二妹。两个姑娘成人后,二妹嫁在县城,大妹招在家里。在我们李湖塆村,男的到女方倒插门叫招女婿。大妹说是招在家里,也没在家住过一天,成年在广州打工,极少回家,连续五年过年也不回来。小妹近些,偶尔回来几次。2008年夏季,村里遭遇自然灾害,天底儿破了,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大雨,爹六十多头猪冲下了大河,不知道去哪儿了。猪圈冲散架了,损失二十多万块。爹眼泪流干后,来问娘,我是不是他亲生的。娘一口咬定,说我绝对是他亲生的,若是撒谎了活不过腊月三十。当年还不知道能做亲子鉴定,所以口头说的为准。这番言论,爹已经问过娘无数遍,娘也用同样一句话回答过爹无数次。爹说,好,儿是我亲骨肉,我养了十三年,供儿读到六年级,你说带走就带走了。一年按四千块钱算,一次付我五万二千块抚养费。娘说一分都不给。爹说到法庭去告娘,五万二千块,蚊子咬个豁儿都不行。两人吵了一大架,差点动了手。我找来花奶奶。花奶奶在我们家解决了五天,把大妹和小妹招回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姊妹三个每个月给爹一百块生活费。住院药费三人平分。爹提出不办养猪场了,想办个菌种厂,可惜没本钱。我说,我们每人先预付三十个月生活费,三千块钱,行吗?爹说可以,差的钱他自己想办法借,等赚到钱了,再分批还给我们。那时,我一直认为,我就是爹亲生的。
我要去找亲爹,感受一下父爱。我一定要找到爹,尽点孝心。就算是死了,我也要找到他的坟,磕几个头,烧几张纸。是个男人,必须的。
谁是我亲爹,娘清楚。去问娘,那就要揭开娘的伤疤,在上面撒盐。娘身体虚弱,前年得过肾结石,开过刀。去年查出子宫肌瘤,动过手术。娘一直都有冠心病,经受不了打击。更重要的是,娘曾经疯了好几十年。
经过慎重思考,感觉这事问娘风险大。担心娘不理我,又怕娘受了刺激,病复发了,那后果不敢想象。不问娘,这事就不靠谱。我大脑浮现出一个人,这个人是前面提到的花奶奶。花奶奶与花没有关系,她住的地方叫花天池。最初大人叫我们喊花天池奶奶,喊了一段时间,嫌字多,拗口,直接喊花奶奶。据说,花奶奶年轻时候做过康泽秘书。这事真假没有考证过,不过康泽在历史书上读到过,人家当过国民党中常委、特务头子、计俘绥靖区总司令。1948年7月16日,康泽在襄阳被活捉,随后襄阳城解放。花奶奶跑得快,一口气跑到我们花天池躲了起来。花奶奶肚子里装的全是墨水,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全知道,天上飞的还知道一半。花奶奶当过几十年妇女主任,会说事,会做思想工作。两口子吵架的,闹离婚的,女人要跑的,男人在外头搞了相好的,只要找到花奶奶,打发个三五百块钱,不光把事给你解决好,还能保证百分百满意。
花天池是个小地名,属我们李湖塆村管辖,是个鬼不生蛋的地方。上一座山,下两座山,再翻一座山,到了。来花奶奶家,她翘着二郎腿,坐在道场坎上看书,面前横着一根木棍。一只老母鸡在她脚下啄食。她扬起棍子,吆喝了一声,老母鸡咕咕咕跑了。花奶奶这声吆喝,依然响亮,依然有劲。听声音,你哪里猜得到人家已经八十九岁了。
哎呦呦,今天莫不是刮得东南西北风啊,怎么把我们崔校长刮来了啥?
花奶奶呀,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开始我有点说不出口,一直吞吞吐吐。在花奶奶催促下,我说明了来意,也给花奶奶提了要求,不管她用什么方,抓什么药,不能让娘晓得我在打听亲爹是谁,也不能让德中爹知道。同时,花奶奶必须为我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我爹是哪个。花奶奶拍着胸脯说,没事,保证给您办好,不出半点差错。我把红包掏出来,里面装了六百块钱,顺手塞进花奶奶裤兜,起身出屋。花奶奶拽住我袖子说免了,莫搞这一套。我把她手一松,出了屋。我问啥时候有答复。她说好事不在忙中取,一个星期。我上车时,花奶奶补了一句,我可是你娘媒人,你娘就是我从襄阳城说来的,她最听我话。
3
一个星期后,逢周末,我去花奶奶家问结果。见到花奶奶我就问,娘对你说名字了吗?花奶奶连声说,快坐下,喝杯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听我从头给你说起。
1979年3月,惊蛰过后第三天,花奶奶领来了一个漂亮姑娘,说是给爹说媳娃子,我们李湖塆把老婆叫做媳娃子。姑娘见爹一表人才,爹还是国家脱产干部,我们村小校长,县级优秀教师。姑娘没走,当天留了下来。姑娘是娘。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爹刚起床,被两个警察押走了。后头捎话回来,说爹猥亵女生,作风不正,耍流氓。爹先关了紧闭,后来判了三年刑。
爹坐牢去了。娘没有粮票了,没有油票了。娘出生在襄阳城,不会做农活,生活相当贫困。这时,娘同班同学赵福星同志,从市里下派到我们乡里,任供销社主任。赵福星可怜娘,经常给娘送些粮票和油票来。娘也经常给赵福星送些土豆黄瓜之类的菜去,两人一来二往,渐渐产生了感情。娘为了感激赵福星,有了出轨行为。花奶奶说,赵福星是我亲爹。我问花奶奶,赵福星三个字是娘亲口对您说的吗?花奶奶拍着胸脯说,当然是娘亲口说的。我提出了疑问,娘1979年三月嫁过来,两个月后爹去坐牢,那就到了五月。我是十二月份出生的,娘只怀了我七个月。花奶奶说,七个月出生正常,属于早产,只要不是六个月莫怀疑。对于这个赵福星,我偶尔听说过,从没见过。那时我是个毛孩儿,人家在乡里干了三年就回市里去了。我问花奶奶知道赵福星在哪里住吗?花奶奶进屋找了张纸出来,上面写有赵福星地址。花奶奶说赵福星是她襄阳城一个姐妹的表哥,地址是准的,不得錯。
花奶奶转身喝了一口茶,接着又把铜水烟袋在桌子腿上磕了几下,换了一袋烟丝,猛抽了几口,继续讲。
爹在监狱表现好,屡次立功,两年零三个月后,爹提前释放。爹出狱后,开始上访。爹说他是清白的,是被当时副校长国成陷害的。爹找到了当年告他的小英和兰花。小英和兰花说真的对不起爹,爹是清白的。当时国成拿来两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写,只要叫她俩儿签上名字都行了。爹让小英和兰花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让学校部分老师和他教过的部分学生,给他写了一堆证明材料,交到县检察院。县检察院重新办理此案,历经多年调查取证,2005年做出终审判决,认为爹犯罪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爹得以清白做人。这几年,爹还想要点退休费,找了若干年,上面没有给出明确结果。花奶奶后面讲的这些内容,没有我清楚。因为爹的申诉过程我全程参与,不过她没讲错,只是漏了一些细节。
4
我没有冒昧去找赵福星老人,怕人家把我当骗子,又怕人家拒绝见我。我来到襄阳城,先找到花奶奶那位姐妹,请她把赵福星女儿约出来,在一家餐馆见面。我们说明来意后,那位女儿吃惊,眉头紧锁,愣着不说话。我想,她是怀疑我生活贫穷,来找亲爹,是不是要钱。我说,我是我们镇上中心小学校长。我把任职文件给她看了一眼。她仔细瞅了几分钟,没有疑问。我说我一个月有三千多块工资,我爱人是我们镇上副镇长。我连忙将爱人任职文件递给她看,她仔细瞅了几分钟,认为章子不假。我爱人一个月也有三千多块工资。生活谈不上多么富裕,但是过得也不差。我把从老家带的土特产递给她,有香菇,木耳,土鸡蛋,全是纯绿色食品。我从公文包拿出一块表,说这是给您爸见面礼,一点心意,请笑纳。那位女儿说土特产收下了,手表不要,等到见到她爸后,让我亲自交给她爸。最后提到主题,说我们不会找您爸要一分钱,我就是想见我亲爹,感受一下父爱,尽点孝心就够了。一番闲聊后,得知那女儿小我两岁,叫我喊她妹妹。打消顾虑后,我问爸是单眼皮吗?她说是。我问爸眉毛上有颗痣吗?她说有。我问爸是A型血吗?她说是。我心里嘀咕,赵福星是我亲爹,八九不离十了。我还打算问爸屁股墩子上是否有块黑色胎记,话刚到嘴边,我连忙又吞了进去。人家是女孩子,问这话不雅观。再就是,问了人家也会说没看到过。哪有女儿偷看老爸屁股的啊。妹妹瞅了瞅我,看我也是单眼皮,左眉毛中间也长了颗痣。妹妹说回家后,她给爸先做思想工作,再说明情况,看爸是个什么意见,从电话里把情况告诉我们。我说谢谢啦!妹妹说,都快成一家人了,不必客气。
第二天下午,我在旅馆里睡午觉刚起床。手机响了,妹妹打来的,说爸愿意见我。我问到哪里见。妹妹说爸年龄大了,腿子不方便,叫我们到她家里去。我坐的士,按照妹妹提供的地址,来到了“在水一方”小区。妹妹在小区门口等我。我左手提核桃乳,右手拎八宝粥。妹妹见我吃力,接过八宝粥说,昨天带了那么多好吃的,爸蛮喜欢的,今天又买这些东西,太浪费了,太客气了。我说都成一家人了,孝敬爸一点儿小礼,应该。
爸开门。看到爸第一眼,我看到了他单眼皮,还特意看了爸眉毛那颗痣。我发现,那颗痣长在爸右眼。心里嘀咕,有点变化,也属正常。我盯着爸脸,仔细看了一番,感觉和我说不上多像,也说不上有多么不像,反正不是很明显。我喊了一声爸,爸说别叫我爸,叫我伯。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手表,要给爸戴上。爸拿起手表,看了一下牌子,说飞亚达表,要好几千块,拿回去,我家里多得是。爸将手表塞进了我公文包。听妹妹说爸当了几十年粮食局长,估计不会稀罕一块表。
金雪过得还好吗?
金雪是娘名字。我说将就点吧,反正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
哦。过得好,我放心了。
不过娘身体虚弱,前年得过肾结石,开过刀。去年查出子宫肌瘤,动过手术。娘一直都有冠心病,一年四季不离药。
嗯……赵伯出了一口长气。
赵伯叫妹妹出去溜达一圈,他要跟我单独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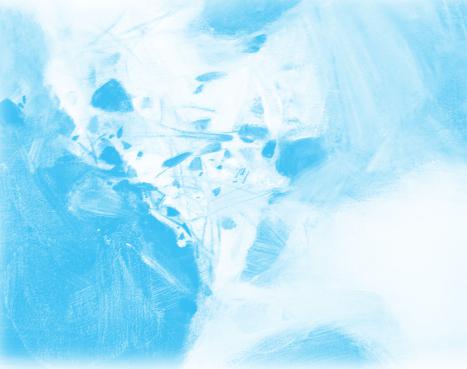
赵伯说他离开我们乡里时,我两岁,会说话,会走路。他知道我住在哪里,不过,这么多年一直不来看我,也不管我,不是故意躲避,有原因。他和娘清白,他和娘没有出轨行为,娘也不是那样人。听到这里,我核对了单眼皮、痣、血型等问题,问他这些东西怎么如此巧合。赵伯说的确是巧合。我问赵伯屁股墩子上有一块黑色胎记么,赵伯说没有。赵伯说不信把裤子脱了给我看。我说赵伯不会撒谎,我相信赵伯的话。我还是认为赵伯是我亲爹。赵伯说绝对不是。我有些固执。我提议,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请赵伯配合我一下,到市中心医院做个亲子鉴定。我从包里掏出手表说,赵伯,把表收下了,当年我爹坐牢,是您救济我娘粮票、油票,不然,我会饿死在娘肚子里。您就算不是我爹,您是我救命恩人,一定要收下。赵伯不肯收下,把表往我包里塞。赵伯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做亲子鉴定,怕是熟人看到了,会笑掉下巴壳子,得考虑考虑。我将表扔在沙发上,转身走了。等赵伯追出门,我已经下了楼。
5
回到旅馆,思来想去,拿不定注意。是马上回家,还是在这里等一天,不知道赵伯要考虑几天。来一趟,不容易。算了,再住一天。还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手机响了,赵伯来电。他在电话中说同意配合我做亲子鉴定。赵伯这天特意戴了一顶礼帽,戴了一副墨镜,把脸遮得严实,我差点没认到。
我和赵伯来到市中心医院,交了两千六百块费用。走完了所有程序,医生说第二天上午拿结果。我把赵伯送回家,准备起身回旅馆。赵伯说不要走,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说什么秘密。他说我知道你亲爹是谁。我惊讶,说不会吧,结果还没出来呢。赵伯说我八十三岁人了,离土不远了,撒谎了活不过月底。我问,我亲爹是谁?赵伯说,莫急,等我喝口茶了慢慢给你讲。
赵伯和娘是初中、高中六年同学。娘出生在襄阳城北京街。姥姥经商,家境殷实,上头有两个舅舅。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统一制度。当年11月,赵伯和娘参加了高考。赵伯差八分没考上大学,娘差五分没考上大学。第二年春天,姥姥动用多方关系,把娘安排在胜利街小学当代课教师。一年后,1979年2月的一天,胜利街几位老师,在教导主任带领下,把校长朱油堵在了娘寝室里,以朱油耍流氓为由,将他送到了派出所。校长朱油开除了公职,娘也灰溜溜离开了学校。娘没脸见人,藏在屋里个把月不出门。3月,娘离开襄阳,出嫁了。赵伯补了一句,说朱油是他侄儿子小姨爹,常在他侄儿子家聚餐时相遇。听完赵伯讲述,我额头上直冒冷汗,脊椎骨凉沁沁的。我问了一句,朱油是我亲爹吗?赵伯说,朱油亲口对我说的,绝对是。赵伯找出纸和笔,上面写了朱油地址和电话。
从赵伯家出来,我径直去了旅馆。没心思吃饭,也没心思去找朱油。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拿了鉴定结果,没错,赵伯的确不是我亲爹。
6
在去见朱油之前,我让赵伯给他通了电话,先将我向他介绍一下。电话打过去没过几分钟,我手机响了。
喂,您好!哪位?
我是朱油。你是金雪儿子吗?
我是金雪儿子。
你在哪里?
我在美丽印象大酒店。
我马上过来找你。
您老了,不方便,我去找您。
就这样定了,你到酒店大门口等我,我坐的士,三分钟到。
见到朱伯,我第一眼瞅的就是他眼皮。可惜,他是双眼皮。再瞅他眉毛,眉毛中间,上下前后,没有痣,到是有两颗蚊子屎。心里嘀咕,他不像是我亲爹。看身高,身高和我差不多,1米70不到。看皮肤颜色,都是黝黑色。
金雪还好么?
我将回答赵伯话一模一样重复了一遍。
哦。朱伯舒了一口气。
金雪可把我害惨了。朱伯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我赶快转移话题,问朱伯什么血型,朱伯说A型血。这个还对得上,要是B型血直接拉倒吧。我问朱伯屁股墩子上有黑色胎记吗?朱伯说,有到是有,不过不在屁股上,在腰窝子里。说着,朱伯已经把衣服掀老高,只見腰窝子处有一块黑色胎记,比我那块要大两倍。
我在犹豫,不知下句话该说什么。
朱伯说你来找亲爹的吧。
我愣着不出声。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朱伯说我哥们已经给我介绍你了。这时我才想起去之前打过一个电话。
这次我没主动介绍我在干什么,月收入多少。也没介绍爱人在干什么,月收入多少。
朱伯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一农村小学教书。朱伯说当老师好,我年轻时就是一名老师,还当过校长,我们曾经同过行。朱伯又问我爱人在干什么,我说在政府上班,普通办事员。朱伯说好工作,国家公务员。我说哪里哪里,一般一般。
朱伯叹了一口气,突然又来了一句,金雪真是把我害惨了。朱伯说他和娘出事后,老婆成了别人老婆,孩子也成了别人孩子。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声搞坏了,谈了好几个对象,没有一个愿意跟他结婚。朱伯还说,要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知道。要问光棍是怎样炼成的,只有朱油知道。我想笑,强忍着,憋在心里,不敢笑出声。暗自佩服朱伯,真幽默。朱伯说他办了所培训学校,让我去看看。我说出来几天了,家里还有事等着回去处理,下次再过去看。朱伯说一年能赚十来万块钱,生活水平不差。就是没买房子,襄阳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前几年感谢政策好,分了一套廉租房,将就点能住。说完后,朱伯又来了一句,你娘把我害惨了。
听到这句话,已经是第三遍了。我纳闷,朱伯当年已经有家室,且又比娘大十几岁,娘当年是个小姑娘,难道是娘主动勾引他不成?
我在深思。朱伯问我,你不是来找亲爹吗?我不吭声。我说,朱伯能讲讲我娘的事情吗?朱伯说讲是可以讲,不过有个要求。我问啥要求,直说。朱伯说多年来,我一直怀疑你是我儿子,可一直找不到你。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去做个亲子鉴定,要是没钱的话,费用我出。自见到朱伯第一眼,我感觉朱伯不像我亲爹,所以从未考虑做亲子鉴定一事。既然他说到这个份上,我说可以。他问什么时候去做。我说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学校有事催得紧,明天想赶回去,现在就去做。朱伯说好,走。
7
到了市中心医院,朱伯跟在我身后不说话,也没见他主动掏钱,费用两千六百块是我出的。拿到收据,我后悔了。说实话,这笔费用,我是不情愿出的,我本不想做鉴定。我想不通,朱伯为啥要主动提出做鉴定。老程序走完,叫第二天下午去拿结果。
出医院大门,我心里不是滋味,跟醉酒想吐的感觉一样。朱伯说叫我到他廉租房去坐坐,我说免了。我邀请朱伯到旅馆里去玩,开的是标间,有张床空着。进旅馆后,我给朱伯泡了杯茶。朱伯喝了一口,躺在床上。没等我提醒,他又来了一句,金雪真是把我害惨了,接着讲起了他和娘的故事。
1970年秋,朱伯到胜利街小学教书,1976年4月当校长。1978年正月十六,娘来到这所学校当代课教师。娘活泼开朗,热爱学生,工作积极,尽职尽责,头一年被评为区里优秀教师。
1979年春开学第一周,那天是星期四,朱伯去教室查岗,发现三年级一班没老师上课,学生在自习。该班语文老师是娘。朱伯径直来到娘寝室。那是一间只有五个平方米小屋,仅够放一张小床。朱伯敲了一下门,没人反应,又敲了一下门,发觉门没有插紧,漏了一丝缝。朱伯从门缝里看见娘躺在床上哭。朱伯推门进屋。娘见校长进来,哭得越怕厉害。朱伯安慰了娘几句,给娘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娘说她没心思上课,然后敞开心扉,给朱伯讲起了她的烦心事。
娘有个初恋情人叫浩男。娘住北京街东头,浩男住西头。两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两家关系原本很亲密,但是在1971年的一个夜晚,浩男父亲,在一群红卫兵挟持下,抄了娘的家。姥爷忍受不了这番羞辱,趁姥姥外出买菜的空,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姥姥自此,将浩男一家视为仇人。原本每天一起上学的两个孩子,在家长呵斥下,各走各的。但是,大人间的仇恨,并没有让两个孩子心生隔阂。私下依然相互关心着对方,倾慕着对方。他俩一起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高中毕业,两人都没考上大学。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爱已经是天注定,两人越怕离不开了。姥姥知道了娘的恋情,抵死不同意这门亲事。两个年轻人执意要走到一起。无奈之下,姥姥把店铺转给了别人,还要卖掉北京街房子,带娘上武汉去投靠小姨。
朱伯问娘是不是也要走。娘说浩男不准她走。浩男说娘要是走了,他就不活了,去跳襄江。襄江是襄阳母亲河,像一条绸带横贯东西。浩男还说,姥姥要真去了武汉,他就立马和娘成婚。
朱伯说为了这群孩子们,叫娘不要走。朱伯叫娘把炊具搬到学校来,住他一室一厅小单元。朱伯到家里住,他家隔学校只有200米远。
朱伯进娘寝室,半个小时才出来,这一幕被甜甜老师看到。甜甜回家给当教导主任老公原野说了。原野说注意观察,有了动静立马告知。
姥姥卖掉房子,走了。浩男死死抱住娘双腿,不准娘走。娘没走,娘来学校上课,住进朱伯寝室。姥姥走后第三天,娘和浩男在学校礼堂里,举行了简单婚礼。
第三周星期三,班长秋天来找朱伯,说娘没去上课。朱伯去寝室找娘,娘在寝室哭。朱伯把娘训斥了一顿,问娘为啥不上课。娘说浩男走了。朱伯问浩男去了哪里?娘说浩男去了前线,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朱伯说那怕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浩男为国做贡献,好样的。朱伯还说浩男命大,打完胜仗,就会回来。朱伯叫娘向浩男学习,赶紧去上课,不要误人子弟。
朱伯进娘寝室二十多分钟才出来,被上早自习的原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第四周星期五早自习,秋天又来向朱伯报告,说娘没去上课。朱伯火冒三丈,来到娘寝室,敲门,娘不开。朱伯怒了,一脚将门踹开。娘跪在饭桌前大哭,桌上放着浩男遗像。娘将火纸,废书本,一张张扔进火盆。火苗旺,火光四射,房内烟雾缭绕,眼睛迷糊,快要睁不开。娘见朱伯进来,随手拿出一封信,向朱伯扔来。朱伯看了一眼信,信上写的是浩男在夺取高平战役时,不幸牺牲。朱伯看信同时,娘近乎发疯的状态,将衣服一件件脱掉,扔进火盆。等朱伯看完信,娘脱得只剩内衣。娘突然起身,猛向窗户边扑去,喊着不活了,要去见浩男。窗外的襄江,波涛汹涌,似一只饿狼,匍匐在襄阳城腹。朱伯害怕娘从窗户跳下去,连忙从后边抱住娘的腰。这时候,教导主任原野和几名老师已经守在門上,眼睁睁目睹了这一抱。不管朱伯怎么解释,老师们说他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不是屎也是屎。娘只穿了内衣内裤,那明摆着是对娘不轨,不是在耍流氓,那还能干些啥?朱伯讲到这里时,眼睛红红的,几滴泪水,从眼角滚了下来。
等朱伯情绪稍微平静后,我说到吃晚饭时间了,出去吃大虾,我请。
吃完饭回来,我问朱伯,浩男真的在攻克高平时牺牲了吗?朱伯说,浩男没有牺牲,那信是浩男父亲找人写的。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浩男父亲是我外甥子姑爹,我外甥子说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完过后,浩男回来了。浩男回来叫我外甥子找过你娘。我外甥子对他说你娘已经结婚了。浩男在武汉军分区上班,住武汉军分区干休所。你想找他,给我外甥打个电话,就能搞到准确地址。朱伯掏出手机,准备找他外甥。我说,别慌,现在不找,过几天再说。
8
第二天还没起床,手机响了。县教育局安全科打的,叫我上午八点半赶到局三楼会议室开会。突然开会,估计哪所学校出了安全问题,马虎不得。我给朱伯丢了三百块钱,说这次来什么礼物都没买,让他想吃啥买啥。出门时,想起一件事,我拐回来,叫朱伯下午去拿鉴定结果。朱伯说拿到结果就给我打电话,我说谢谢了。朱伯说不客气。我说请朱伯到我家里去做客,朱伯说地址都不写一个,到哪里去找你呀。我掏出笔,给朱伯写了地址才告辞。
会上午10点结束,吃午饭时我回到学校。一路上,浩男这个名字一直在我大脑里萦绕。仅仅只是萦绕,没有激起去找他的念头。到了下午,朱伯没来电告诉我鉴定结果,我也懒得问他。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朱伯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谈谈。我说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说。朱伯说他拿到鉴定结果了,说我是他亲儿子。我说不可能。他说医学检验结果,不会有错。他叫我给他搞三万块钱,算是赡养费,一次了断,以后保证不再要了。我挂了手机,不再接他电话。他发短信,说我不给钱,他去告我,人民法院见。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邻居王珂打来电话,说不好了,我爹也晓得我不是他亲生的,要告娘,叫娘赔偿他精神损失费。我连忙跑回家,走到道场坎上,看见朱油也在那里。事情是朱油搞砸场的。朱油找我没要到钱,来找娘要钱了。朱油说我是他亲儿子,娘说不可能。朱油拿出亲子鉴定结论,娘说手都没牵过,咋可能生个亲儿子,我儿亲爹是浩男,你知道么。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背水路过门前五婶听见了。五婶本来和娘都有矛盾,这一听,哪里了得,赶紧跑去给爹说了。
我走到朱伯跟前,叫朱伯把亲子鉴定书拿出来我看。朱伯拿出结论,我也拿出结论。我的结论和朱伯结论恰好相反。我手中结论是上周跑到市中心医院拿的。这次上襄阳,了解到朱油并没有办什么培训学校。他是一个好吃懒做,成天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朱伯是办假证那些人给他做的假结论。朱伯见事情败露,灰溜溜跑得不见踪影了。
看到爹时,爹气还没消,眉毛只竖。我说,爹,您虽不是我亲爹,但您比我亲爹还亲。您也不要找娘要精神损失费了。我养活您一辈子,生活费一分不少您,医药费我还是平摊。
王珂站起来,边拍巴掌边说,说得好。说话算话,谁不算话谁是四条腿爬爬。
我说说到做到,谁不做到谁是四条腿爬爬。
爹笑了。
我樂了。
娘病了。
娘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四年。
我的亲爹是不是浩男,我不想弄清楚,也从未找过,就让他成为一个谜,至到海枯石烂。
【作者简介】郭焕平,男,1976年生于湖北南漳李湖塆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北省南漳县教育局督导办公室副主任。短篇小说散见《北方文学》《四川文学》《时代文学》《山东文学》《陕西文学》《中国作家文学》《短篇小说》等杂志。小小说散见《微型小说月报》《2016中国年度作品选》《短小说》《领导科学》《小小说大世界》《精短小说》《华文小小说》《参花》等杂志,《经济日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 《农村新报》等报刊。出版有诗集《红蜻蜓》,小小说集《情事美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