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书房
2018-07-06黄荣才
黄荣才
林语堂曾经在《我的愿望》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八个愿望,其中第一个愿望就是和书房有关:“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詈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与野叟曝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这个愿望自然就让人想起了林语堂的书房“有不为斋。”“有不为斋”是林语堂书房的终点,但不是林语堂书房的开始,林语堂的书房是浓浓淡淡的一条线,这条线的头在一个叫平和坂仔的地方,也就是林语堂深情称赞的:“我的家乡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
林语堂最初的书房应该就是现在平和林语堂故居那个占地120平方米的“同”字型小屋,但不是在小屋后半部分他出生的小阁楼,而是在前半部分,当时他一家吃饭、聊天,包括林语堂听父亲讲故事、读书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不是正式的书房,但却是林语堂接触文化,梦想起航的地方。当年,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在假期早上八点之后就摇铃召集儿女,在这里给他们上课,讲的是四书五经、《幼学琼林》等等,林语堂也是在这里,读到了西溪教堂牧师范礼文博士带来的《通问报》,这份报纸是上海的林乐知牧师编的。正是通过这份报纸,林语堂首次接触了西方文明,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也是从这扇窗口,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在童年的林语堂心中种下了“要当个作家,要写一本让全世界知道我的书”的梦想种子。
林语堂在平和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接受了启蒙教育之后,1905年,在林语堂十岁的时候,离开平和到厦门鼓浪屿读书,养元小学、寻源中学,1912年林语堂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其后的清华大学任教、国外留学、北京大学任教、厦门大学任教等等人生履痕,没有什么有关林语堂书房的痕迹,或许因为没有独立的书房,这些痕迹基本看不到了。只有在厦门鼓浪屿漳州路44号,有座廖家老宅,这是林语堂夫人廖翠凤的娘家,在那座朝南的建筑里,被称之为“立人斋”的地方,有过林语堂新娘房和书房的说法。这里是林语堂短暂停留的地方,毕竟191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后就携妻出国留学,这个地方林语堂停留时间最长的就是1926年回厦门任教的那大半年时光。
林语堂正儿八经的书房是在1927年到上海从事写作之后,尤其他在编写了开明英文教材,有了大笔收入,被称之为“版税大王”,在上海的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买了一处花园式房子。这房子很大,林语堂的女儿回忆说,在这处地方,单单院子里的白杨树就有四十多棵,可以想象空间的充足,有处书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何况,这时候,写作已经成為林语堂生活的主要内容,书房也就成为林语堂主要的工作和活动场所,写作,以及和文友之间交流畅谈,就成为书房重要的内容。即使在1936年林语堂全家出国,一直到1966年定居台北,书房,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林语堂生命中重要的空间,伴随人生。
林语堂不喜欢书房太过于整齐,也不喜欢把书房里的书按照图书馆的方式分门别类,尽管,林语堂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到图书馆看书。他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林语堂觉得自己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享受各种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因为哈佛大学有卫德诺图书馆,只要不上课,林语堂就到图书馆去,去当他那挑选坚果的猴子。但到了拥有自己的书房,书籍就应该可以随意放置,自己的书房和图书馆是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林语堂认为,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在自己的书房里,书架应该别成小天地,随意搭配的书籍会把书架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之感。他厌烦那些把书籍当成摆设,一套一套的归类摆放,甚至连书籍的书皮都没有扯下来,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这样就把原来高尚的阅读变成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买书原来是高尚的娱乐也变成暴发户炫耀显摆的工具。林语堂在编《人间世》的时候,收到一个叫姚颖的作者一篇《我的书报安置法》的文章,姚颖在文章中写到反对书籍分类,林语堂非常兴奋,把姚颖引为知己,并且把这篇文章译成英文,他在自己编辑《人间世》《论语》的时候,发表了姚颖多篇文章,并且在远赴美国之后,还为姚颖的散文杂文集《京话》作序。
林语堂在书房工作的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打扰。唯有廖翠凤可以进去送送茶水,但也是轻手轻脚,担心影响林语堂的工作。偶尔女儿到他的书房,林语堂会把孩子抱起来,耐心回答女儿的提问,甚至是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给女儿,满足她“也要写作”的撒娇行为,这是林语堂对女儿的喜爱和宽容,是爱心流淌的时候,但这种时候也不是经常,更多的时候,林语堂的老婆和孩子们都知道林语堂写作不容打扰。当林语堂在美国写作《京华烟云》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林语堂提前告知当天会完成。到了快傍晚的时候,廖翠凤和孩子们等在书房的门口,林语堂推门而出,宣告大功告成。大家一起鼓掌,孩子甚至唱歌祝贺,林语堂宣布要去理发,提议全家到外面吃饭庆祝,孩子们一片欢呼。这是多么温馨热烈的场面,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在书房门推开的那一瞬间达到了一个高峰。
林语堂喜欢边抽烟边写作,他戏称他知道自己的文章里哪一页尼古丁的味道最浓。在林语堂的心目中,“吸烟者不必皆文人,而文人理应吸烟,此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足以天地万古长存也。”这样的高度让林语堂不仅仅觉得吸烟理所当然,甚至是非烟不可,因为从“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演绎出学问是闲谈出来的,而“既是夕谈,大约便有吸烟”。这时候吸烟就有某种高贵的味道,“吸烟之所以为贵,在其能代表一种自由谈学的风味。”于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大学之所以毛病甚多,就是“谈学时不吸烟,吸烟时不谈学”。林语堂觉得吸烟能够让人心旷神怡,思维畅通,自然就妙语连珠了。他甚至渴望在他去世之后,有友人能够在其碑文上刻“此人文章烟气甚重”,就心满意足。他把自己曾经戒烟三个星期认为自己是“误入歧途”,做了一件“荒唐的事。”
在林语堂书桌的右端有个烧焦的痕迹,那是林语堂放烟的地方,也就是他吸烟的时候,或者要忙着什么,或者是习惯动作,有时候就把还燃着的烟放在那地方,短暂停留后才拿起来再吸,林语堂吸烟很少停止,可以说一支接一支,久了,自然就留下痕迹,林语堂干脆在旁边刻上“惜阴池”,自己估量着用上七八年的时间,能够把“惜阴池”这两英寸厚的桌面烧透。当他戒烟的时候,这“惜阴池”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让林语堂颇为惆怅,重新吸烟之后,在那地方重新放上烟,林语堂“心上非常快活”。后来因为搬家,书桌卖了,否则也是一道风景。
吸烟问题不仅仅让林语堂心路备受悲欢起伏和把其与教育、学术挂钩起来,甚至还影响了林语堂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林语堂和廖翠凤这对伴侣把婚姻演绎得非常精美,其中种种原因和诀窍,有一个是廖翠凤不仅仅允许林语堂在家里吸烟,还允许林语堂在床上吸烟,让林语堂每天醒来之后,可以美美地先吞云吐雾一番,这让林语堂很为感激。其实,不仅仅是吸烟,林语堂还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因此,他的卧室某种程度上是书房的延伸。
林语堂认为“我的喜欢躺在椅中的习惯,和我的拟想将一种亲热自由潇洒的文体导入中国杂志界的企图之间,确有一种联系存在着”。因此林语堂可以堂皇地为了舒服宁愿把椅子的脚锯短一些,在没有锯短倚脚的时候,变通的方式就是“把写字台的屉斗拉一只出来搁脚”。可以想象林语堂把屉斗拉出来之后,一只脚搁置其中,把自己放松地放在椅子上,文思泉涌,自然,少不了他那只烟斗。
椅脚越锯越低,“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平躺在床上”。坐姿的改变已经从椅子到了床上,在林语堂看来,安卧眠床是有着许多欢乐的,不过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躺在床上,而是“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睡在斜度约在三十度的大軟枕头上,两臂或一臂垫在头的后面”。这样的姿势能够给心灵来一个大扫除。在林语堂看来,“一个人的头脑,只有在他的足趾自由时,方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在头脑自由时,他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因此林语堂喜欢在床上阅读。如果读得兴趣浓厚,他就继续读下去,如果兴趣降低,就把书当作枕头而睡,因此有了一张林语堂非常惬意地躺在床上看书的照片,而林语堂的家里,自然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这也就是林语堂所谓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
对于林语堂书房,也许现在大家最为熟悉的是台北林语堂故居的“有不为斋”,这是个林语堂书房从抽象到具象的地方。我曾经两次到台北林语堂故居参观,对于这个林语堂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地方,我充满景仰。台北林语堂故居位于台北仰德大道二段141号,也就是在阳明山的山腰上,绿树掩映中,可以看见这处白墙蓝瓦两层楼的建筑。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是林语堂亲自设计的,是他生前最后十年定居台湾的住所,这个庭院方圆达千余平方米、楼房共计330多平方米。林语堂设计时撷取了东方情调与西方韵味———乍看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细看之下却发现,二楼顶着那一弯长廊的竟是四根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吻合了他东西交融的文化心理。在中庭一角,有鱼池、假山,遍植翠竹、枫树、藤箩。鱼池边有一石椅。林语堂生前喜欢坐在池端的石椅上,“持竿观鱼”他曾用得意之笔描述“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林语堂的书房,叫“有不为斋”,墙壁上,“有不为斋”的题词高悬,书房里陈列着他的近60种著作和4000多种藏书。书房角落里安置着一张写字台,桌面上放着笔、稿纸、放大镜、书籍和茶壶、茶杯。书房一角的展示柜里有一台当年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这台中文打字机是林语堂倾家荡产,耗费了大量心血在1947年发明的,他不仅花光了12万美元的积蓄,还一度举债过日子。林语堂说这是他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明快中文打字机采用林语堂独创的上下字形检字法,使中文打字变得快捷易学,每个汉字只需敲打3键,每分钟最快能打50字,直行书写,能拼印出九万个中国字,而且不须训练即能操作,十分轻巧简便。展示柜还摆放着林语堂当年自来牙刷、自动门锁、自动发桥牌机的设计图、专利书及相关记录。书房里还有几只林语堂用过的烟斗,托着烟斗,满脸笑容,几乎成为林语堂的标签。林语堂喜欢口衔烟斗,或者用微热的烟斗擦鼻头。书房的中间,是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呈碗状,本面为银色,缸口外沿塑有一“勺”状物,酷似一只烟斗,这是林语堂自己发明的,勺状的地方就是用来搁置烟斗的。这种烟灰缸,在平和林语堂故居也有一个,这是林语堂生命最初的十年是在平和,渴望走出去;最后十年是在台湾,渴望回来这个循环的一个小小注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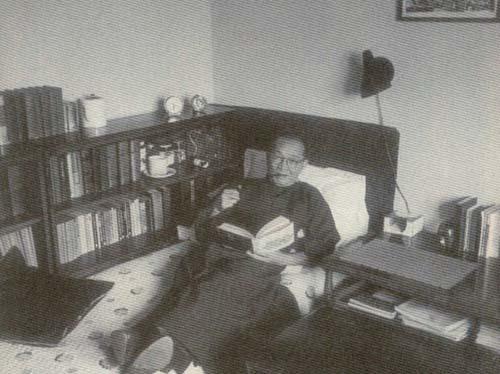
对于为什么把书房叫“有不为斋”,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不为斋解》,对此做了解释。在文章中,林语堂坦承这个斋名有点道学气,属于言志类的书斋名。林语堂是个有着基督教背景,深受儒家“有为”思想的影响,也欣赏道家“无为”的情怀的人,他自言自己的人生是一捆矛盾。他的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往往也有“不为”的事,他不流于世俗,选择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直接触动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有不为斋”是因为康有为的名字,林语堂认为:既是“有为”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不为”。引自孟子的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尽管许多东西证明物极必反。
林语堂认为自己书房的名字有点长,但比起另一个著名的斋名“仰观千七百二十七鹤斋”来,还不及它的一半。后面这长长的斋名应该是清朝赵之谦的书房名,因为1929年绍兴墨润堂影印了一套书,这套书是《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一共有七十七卷,是清朝赵之谦编的。
被朋友发问为什么叫“有不为斋”,让林语堂盘点了一回内心,林语堂说“我恍惚似已觉得,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他列举了数十种“不为”的事,让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的内心操守底线,也印证了林语堂有所为,更有所不为的思想境界。
在这间书房,林语堂编写了《当代汉英词典》,创作了盘点人生的《八十自叙》,撰写了弥漫浓郁乡情的《我的家乡》。从书房走出去,是个阳台,这个阳台是林语堂喜欢停留的地方,他在这里抽烟,遥望天母灯光,若有所思,若无所思,感受闲适的愉悦,勾起怀念家乡的惆怅。
书房,也就以具体或者模糊的形象,在林语堂的生命轨迹,刻画下深深浅浅的印痕,从林语堂生命开始的地方到安息的地方,成为一道风景,让我们在怀念大师的时候,感受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