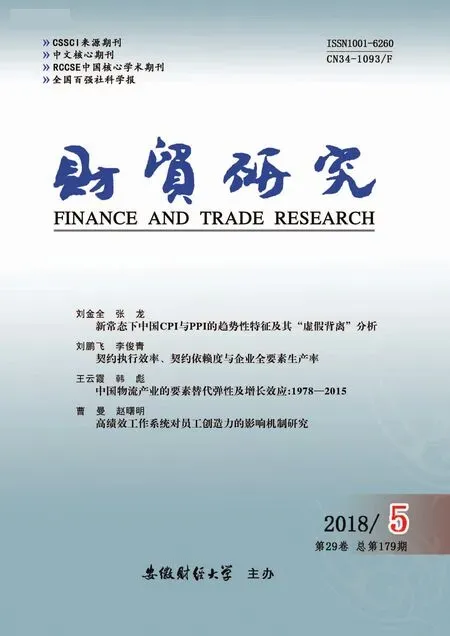契约执行效率、契约依赖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2018-07-03刘鹏飞李俊青
刘鹏飞 李俊青
(1.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72; 2.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31;3.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背景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已经成为官方共识。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衡量指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Solow,1956;Klette,1996;Romer,1990;Hall et al.,1999)。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和状态核实等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诺思,2014;Acemoglu et al.,2007)。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事前的专用性投资难以明确纳入契约或由第三方证实,在事后的谈判过程中投资方面临“敲竹杠”的风险,从而导致投资的无效率(Williamson,1985;Grossman et al.,1986;Hart et al.,1988)。作为制度的一个方面,良好的契约执行效率有助于实现契约内容,降低企业投资的无效率性,促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的生产效率(Acemoglu et al.,2005;Acemoglu et al.,2007;Nunn,2007)。由于所使用的特定生产技术不同或所处的特定环境不同,不同行业中的企业会具有不同的契约依赖性,契约执行效率提高将对契约依赖性较强的企业生产率提高作用更加明显。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契约执行效率改善的积极作用也会存在差异。
由于中国法律体系不完善,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条件具有很大差异,因而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契约执行效率状况。同时,不同地区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和契约依赖性,从而为我们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水平以及不同契约依赖性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一般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所以本文重点考察以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契约执行效率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详见:世界银行集团,“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08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衡量地方司法系统强制执行合同效率的指标,绘制得到图1。图1中,时间为计算自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至判决执行后收回欠款的天数,成本为完成诉讼程序花费的诉讼费、执行成本、律师费用等成本占诉讼标的额的比例。从图1可以看出,各地区在强制执行合同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东南沿海地区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合同平均花费时间为230天,而东北地区则为363天;东南沿海地区花费的成本平均为诉讼标的额的11.5%,中原地区则为29.9%。

图1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合同的时间和成本的地区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整理。
由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衡量契约执行效率的指标仅有2006年的数据,而本文数据为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因此借鉴党印等(2014)、罗煜等(2016)的方法,用樊纲等(2011b)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分项中的“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子项来衡量,该指标来源于企业对当地执法环境的评价,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当地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效率。本文着重考察该指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从图2中可以发现,契约执行效率最高的上海为7.79,而契约执行效率最差的贵州仅为1.04,这也直观反映了各地区契约执行效率的差距;各省区的TFP水平与其契约执行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分析,即: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敲竹杠”风险较低,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专用性投资,强化了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进而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反,契约执行效率较低的地区,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限制专用性投资和生产专业化并不利于技术进步,这也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

图2各省区的契约执行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和说明: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和樊纲等(2011b)研究计算整理而成;使用OP法计算企业的TFP,以增加值为权重计算各省区平均的TFP水平;契约执行效率为各省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子指标的平均值。
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企业契约依赖性也不同(Nunn,2007)。以Nunn(2007)计算的契约依赖度指标进行考察发现,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塑料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中的企业契约依赖度最高;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的企业契约依赖度最低。契约依赖性越强的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产品的专用性投资程度越高,中间投入产品的复杂性往往较高,涉及较多的异质性特征,并且投入要素之间的互补性也越强。专用性的投入要素容易遇到“敲竹杠”风险,从而减少要素投入,同时要素之间较高的互补性也会大幅降低其他要素的投入,从而严重限制企业的生产,有效抑制企业效率提高,因此,对于这类企业,契约执行效率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然而对于契约依赖性较低的企业,契约执行效率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根据不同契约依赖度的中位数,可以将企业分为高契约依赖度企业和低契约依赖度企业,以分别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这两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的差异。从图3可以看出,各省区契约依赖度较高企业的平均TFP与契约执行效率的拟合线的斜率更高,而契约依赖度较低企业的平均TFP与契约执行效率的拟合线的斜率则较低,表明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契约依赖度较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更加明显。

图3 各省区契约执行效率与不同契约依赖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和说明: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和樊纲等(2011b)研究计算整理而成;以契约依赖度中位数划分高、低契约依赖度企业,并使用增加值为权重计算平均的TFP;契约执行效率为各省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子指标的平均值。
基于这些经验判断,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研究契约执行效率影响生产率的机理,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在具有不同契约依赖度的异质性企业中考察了这一影响的差异性。
二、文献评述及影响机理分析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不断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诺思(2014)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正式的讲,是对人类相互关系的人为约束”,并认为“一个社会不能有效率、低成本地执行合约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经济停滞和现代落后的最重要原因”(诺思,2014)。众多研究也表明,制度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原因(Scully,1988;诺思,2014;La Porta et al.,1997;Hall et al.,1999;Acemoglu et al.,2001;阿西莫格鲁 等,2015)。许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改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Xu,2011;徐现祥 等,2005;方颖 等,2011;樊纲 等,2011a;Zhu,2012;毛其淋,2013)。North(1991)将经济制度分解为限制政府掠夺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保护企业合约执行的契约执行制度。产权保护制度能够遏制政府之手攫取私人财富,增强经济主体的长期投资动力和提高投资效率,扩大专业化分工,促进新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Coase,1937;Williamson,1985;Hart et al.,1988;Acemoglu et al.,2005;余林徽 等,2013)。
大量研究证实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然而契约执行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例如,Acemoglu et al.(2005)认为,契约执行效率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金融市场发展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余林徽等(2013)也认为,契约执行制度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些研究则发现契约执行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学与经济学相关的文献认为,法治效率对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La Porta et al.,1997;Rajan et al.,1998;张健华 等,2016;罗煜 等,2016)。Nunn(2007)认为,契约执行效率较好的国家对于契约依赖性产业的出口具有优势。Acemoglu et al.(2007)认为,契约的不完全程度减小了对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李坤望等(2010)、蒋冠宏等(2013)分别考察了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地区能否在契约依赖性强的行业形成出口优势、增长优势。综上,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不同行业的增长或出口的重要影响机制是: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并未细致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不同契约依赖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
跨国生产率差异是导致跨国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Klette,1996;Hall et al.,1999;Romer,1990)。而一个经济体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是由微观企业的生产率构成的,目前很多研究也主要集中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有微观企业层面的因素,如管理才能、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信息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等;企业外部的因素,如生产率溢出效应、竞争、管制政策、灵活的要素市场等(Syverson,2011)。最近的一些文献从市场竞争、政策规制与制度等方面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Olley et al.,1996;Melitz,2003;Acemoglu et al.,2007;张杰 等,2011;Brandt et al.,2012;毛其淋,2013;余林徽 等,2013;简泽 等,2014)。本文即沿着这一思路,细致考察了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同契约依赖度的企业影响的差异性。
根据Williamson(1985)、Grossman et al.(1986)、Hart et al.(1988)等关于不完全合约的观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专用性投资,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无法纳入契约或被第三方证实,因此投资一方将面临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其投资收益可能被对方窃取,由于可能预料到出现这种欺诈行为,投资者事前就不会充分进行专用性投资。根据Romer(1990)、Acemoglu et al.(2007)的观点,企业技术进步是使用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大形成的,因此使用更广泛的中间投入品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地区,契约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企业面对“敲竹杠”的风险较低,专用性投资品的成本也会较低,可以缓解专用性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生产过程中不同要素具有互补性,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会相应促进非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从而使得企业产出增加。使用专用性投资的企业利润增加,会促使企业使用更加广泛的中间投入品,即能够引发更多的创新,促进该地区企业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如果企业生产更加依赖于专用性投资品,则该企业具有较高的契约依赖度,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便越明显(Nunn,2007)。相反,较差的契约执行效率环境中,会出现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品不足的情况,进而降低非专用性投资品的使用,减少企业的产品生产,限制企业使用更加广泛的中间投入品,阻碍该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契约依赖度越高的企业,较差的契约执行效率对其生产率的阻碍作用更显著。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1。
研究假说1:契约执行效率提高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密集使用专用性投资的契约依赖度较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要更加显著。
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不同性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性。外资企业的原料来源或市场通常位于国外,由于其经营的国际化,可能受到更多国际环境的影响,因而与本地的契约执行效率关系并不密切(张杰 等,2011),因此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孔东民 等,2014)。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的差异性。由于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事实上政治地位不平等,司法体系、行政体系对于国有企业具有偏好特征,而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效率较低。因而,一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改善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该地区国有企业存在的契约欺诈等行为,而解决该地区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契约欺诈等行为的作用则相对有限。例如,解决国有企业经济纠纷的经济合同法在1981年通过,而规范私人合约的民法通则到1986年才通过。有报道指出,“尽管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总体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政务环境,但在操作层面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李晓磊,“中国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困局”,《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11-27(005)。。这表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并未充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根据2001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投资环境进行的企业调查,89%的国有企业会签订合同,而民营企业的比例是85%;国有企业通过法庭解决商业纠纷的比例是23%,而民营企业是14%;国有企业通过企业间谈判解决与供应商纠纷的比例是74%,而民营企业为82%(Long,2010)。这组数据反映出司法系统能够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纠纷,而不能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的纠纷。面临商业纠纷,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私人关系进行调解,而非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其重要原因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未能得到司法体系的充分保护,其在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长期的合作和联系后形成较为稳定的私人关系,当其面临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欺诈问题时,更加依赖于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解决问题。制度环境改善并未对民营企业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民营企业更加依赖非正式的私人关系来解决契约欺诈问题,因而地区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较为有限。国有企业则与政府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司法系统也依赖于政府的司法官员任命和预算拨款,从而使得国有企业面对更有利的司法环境(马俊英 等,2015;干春晖 等,2015)。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也表明,国有企业签订合同的比例与利用法庭解决争端的比例均高于民营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更容易从契约执行效率改善中获得益处。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更便利地通过法律系统解决“敲竹杠”问题,因而契约执行效率改善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例如,Long(2010)发现,法院效率改善对国有企业进行新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由于制度改善对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支持,导致契约执行效率改善能够更大程度影响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应,造成国有企业代理成本较高(李寿喜,2007;刘瑞明,2013)。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国有企业对于较强专用性投资的管理能力要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要弱,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在一定程度表明国有企业管理专用性投资带来的“敲竹杠”问题能力较弱。随着契约依赖度增加,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可能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比民营企业要大。胡一帆等(2005)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内部控制问题,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改善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非国有企业。孔东民等(2014)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也发现,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制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水平,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形成对外资企业的“追赶效应”。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2。
研究假说2:随着契约依赖度提高,相对于民营企业,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最小,影响并不显著。
经过较长时期的经营,大型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为成熟的生产管理经验,企业运营更为透明和公开化,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小(温军 等,2011)。大型企业具有较为成熟的管理流程和较为标准的生产工序,其生产往往涉及标准化、一般化的中间投入,具有比较广阔的市场来支持其生产,契约依赖度较低。同时,大型企业具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能够凭借自身财力和经验减弱契约不完全对自身的不利影响,因而具有较低的契约执行效率敏感性。相对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等问题更为严重,在融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劣势(杨咸月,2014;梁冰,2005)。小型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标准化程度往往较低,其生产更多地涉及非标准化的中间投入,更加依赖关系性投资,因而小型企业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计算结果,以全部企业销售收入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小型企业平均的契约依赖度数值为0.89,而大型企业则为0.88。小型企业对数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3.30,而大型企业则为4.29。这也一定程度说明了大型企业具有较低的契约依赖性,小型企业不具有雄厚的资本和充足的经验来应对契约不完全形成的“敲竹杠”问题,因而具有较强的契约依赖性。另外,大型企业进行跨区域经营的能力更强(宋渊洋 等,2014),可以进行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可能会使大型企业形成对其他地区契约执行效率的依赖,从而减弱其对当地契约执行效率的依赖性。由于经营能力有限,小型企业更集中在当地进行生产和经营,从而对该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3。
研究假说3:相对于大型企业,随着契约依赖度的提高,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小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更加明显。
三、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回归模型设定
在计量模型方面主要利用Nunn(2007)、李坤望等(2010)、蒋冠宏等(2013)的方法,运用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的交互项来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具体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tfpijkt=α0+α1×zrj×instit+Xβ+firmk+yeart+εijkt
(1)
其中:i、j、k、t分别表示地区、行业、企业、年份;instit表示省际的契约执行效率指标,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分项指标来表示,反映了生产者对该地区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性的评估,因此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该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雷新途等(2012)利用该指标衡量不同区域的履约法律环境,党印等(2014)使用该指标衡量企业面临的法治环境,罗煜等(2016)也使用这项指标衡量执法效率,其认为该指标最能反映当地司法部门的执法水平,因此,我们将这一指标作为度量契约执行效率的核心指标,而李坤望等(2010)、蒋冠宏等(2013)使用《2008中国营商环境指数》中的合同执行成本来衡量契约执行效率,但该指标实际对应2006年的数值,因而缺乏连贯的数据,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使用该指标对2006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考察;zrj表示j行业的契约依赖度指标,因此系数α1成为本文关注的系数;firmk表示企业固定效应;year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
X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合其他文献的做法,我们选取如下的具体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age)。大量的实证文献均发现企业年龄对TFP具有负向影响,即新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余林徽 等,2013;毛其淋 等,2013)。
(2)企业所有制。参考杨汝岱(2015)的方法,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state)、外资企业(foreign)和民营企业(private)。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其生产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较高(聂辉华 等,2011;杨汝岱,2015)。
(3)企业的销售收入(sales)。使用主营业务收入(以各省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的对数值衡量企业的规模,并取自然对数值。企业规模增大,有助于通过学习效应提高生产率(余林徽 等,2013)。
(4)要素密集度(klratio)。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数除以从业人数的平均值表示,使用这一指标控制企业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上的技术选择状况(简泽,2011)。
(5)资产负债率(debt)。使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这可以用来控制企业的负债状况(简泽 等,2012)。
另外还在回归中加入了出口比率(export,出口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补贴比率(subsi,所获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人均GDP(pergdp)、经济开放度(open)、国有工业企业比重(stateratio,国有工业企业占该地区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等指标。由于企业生产率难以影响宏观变量,因而可能存在较弱的内生性问题。由于企业层面的变量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张杰等(2011)、张健华等(2016)的方法,将除年龄、所有制之外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都取滞后一期值,以减弱变量内生性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1)契约依赖度指标(zr)。Nunn(2007)通过计算美国不同行业的中间投入中非市场化交易部分的比重,以此来衡量该行业内企业的契约依赖度。Nunn(2007)将生产要素根据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分为三类:如果要素投入是在交易所交易的(sold on an exchang),则表明要素的交易市场较厚(thick),这种要素不是特定关系型的(relation-specific),要素使用过程中能够避免“敲竹杠”的风险;如果要素不在交易所交易而是以公开出版物中参考价格交易的(reference priced in trade publications),则市场的厚度和特定型关系都处于中间水平;如果中间投入既不在交易所交易也不按照参考价格交易,则表明该要素是关系型的,要素使用过程易受到“敲竹杠”的影响。利用美国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鉴别出每个行业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投入种类和使用比例,采用如下方法可以计算契约依赖度指标(zr):
(2)

(2)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使用传统的OLS方法估计C-D生产函数,并利用残差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可能存在同时性偏差问题(simultaneity biases)和选择偏差问题(selection biases)(Olley et al.,1996)。同时性偏差会使得可变投入的系数有向上的偏误,而选择偏差会使得企业资本的系数有向下的偏误。只有在不可观测的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是时不变的条件下,固定效应估计才能解决同时性问题。Olley et al.(1996)发展了一种半参数方法(即OP方法)来估计生产率,实质上是使用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的时变的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而选择性偏差问题则使用生存概率方法加以解决。Levinsohn et al. (2003)提出了另一种半参数方法(即LP方法),实质上是使用中间投入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以解决同时性偏差问题。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存在比较严重的进入和退出问题,即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所以本文使用OP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使用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稳健性分析的替代指标。
参考鲁晓东等(2012)的做法,选择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变量。使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衡量产出,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指标衡量资本存量,投资指标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数额的本年变动额加上本年折旧计算而得,以企业的从业人员衡量劳动投入。同时,以1998年为基期的省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平减;以1998年为基期的省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和投资进行平减。然后对所有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除稳健性分析第一部分的TFP为LP法计算的企业对数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外,本文的TFP数值均为OP方法计算的企业对数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
(3)数据来源。本文的宏观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即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参考聂辉华等(2011)和毛其淋(2013)等的处理方法,删除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合计、中间投入合计为空值或小于等于0的观测值,以及从业人数小于8、资产合计小于流动资产、资产合计小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的观测值;同时删除1949年以前成立的企业样本以及年龄小于0的样本。由于行业的契约依赖度指标数据限制,我们仅使用两分位代码为13~42的制造业企业数据。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的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在表1的基准回归结果中,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依次加入企业年龄、所有制、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发现,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均保持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对于契约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也印证了前文中的结论。
而通过对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我们则发现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干中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企业年龄对生产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生产率往往越低,而新成立的企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我们以民营企业作为基准组并加入所有制变量,则发现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外资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这也与杨汝岱(2015)的结论类似。另外,资本劳动比率的系数显著为负,似乎有悖直觉,但这与简泽(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过度使用资本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效率。负债率对企业生产率也具有负向影响,负债率高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约束,使得企业生产效率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出口变量的系数为正,“出口学习”、“出口选择”等效应会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张杰 等,2011)。补贴比率的系数不显著,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的系数值均显著为负,经济开放度系数并不稳定,人均GDP的系数则为负值。

表1 契约执行效率、契约依赖度和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注:控制企业、年度固定效应;标准误使用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为调整后的t值。下表同。
(2)根据所有制分样本的估计。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考察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样本中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并维持在0.0132上下;而民营企业的系数大约为0.0026,这显著为正;外资企业的系数则不显著。如前文分析的原因,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外资企业对本地的契约执行效率依赖程度较弱,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其生产率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与民营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契约执行效率对国有企业具有偏好特征,司法、行政等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契约欺诈等问题,而对解决民营企业存在的类似问题作用相对有限。当面临契约不完全造成的“敲竹杠”问题时,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正式法律手段予以解决。而民营企业则没有能够享受到相同的法治待遇,可能更多地利用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的制度来解决纠纷(马俊英 等,2015)。Long(2010)发现,国有企业签订正式合同的比例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商业纠纷的比例均高于民营企业,并且以开发新产品来衡量创新,法院办事效率提高对于国有企业影响比民营企业要更大。综上,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并未从法制效率改善中获得较大的益处,因而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更显著。
同时,由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对应,导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有效的激励方式来高效经营企业(胡一帆 等,2005;李寿喜,2007;刘瑞明,2013)。而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率方面,国有企业的均值为0.5,民营企业为0.07,外资企业则为0.08。这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于不完全合约的“敲竹杠”行为处理能力较差,更加依赖外部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综上,随着契约依赖度增加,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要更加显著。

表2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考察契约依赖度、契约执行效率和生产率的效应

表3 按企业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
(3)按企业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政府鼓励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契约执行效率对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又有何不同呢?本文按企业规模的三分位数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以分别考察契约执行效率对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加入其它控制变量之后,契约执行效率提高对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随着契约依赖度的增强,契约执行效率对小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面对更为标准化、市场化的投入品环境,大型企业受到关系型投资带来的“敲竹杠”风险较小,即使面临“敲竹杠”问题,也有实力降低其不利影响。而小型企业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问题,在融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劣势(杨咸月,2014;梁冰,2005)。随着契约依赖程度的提高,小型企业面临的关系型投资力度加大,更容易受到“敲竹杠”风险的威胁,并且小型企业缺乏处理“敲竹杠”问题的实力和经验,因此小型企业进行更大范围交易和更复杂生产的难度会增加。另外,中国企业跨地区经营伴随着较高的制度成本,而较大规模的企业更有实力和经验,更有跨区域经营的能力(宋渊洋 等,2014),大型企业跨地区经营有助于降低对当地制度的依赖性。而小型企业则集中在当地发展,从而更加依赖于当地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因而,相对于大型企业,随着契约依赖度提高,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小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更大。
(二)稳健性分析
(1)使用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为了克服O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误差,我们使用LP法计算的TFP值代替OP法计算的TFP值重新对基准回归进行估计,最终得到表4所示的结果。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均保持在1%的显著水平为正。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使用LP法计算TFP的估计结果
(2)使用《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衡量契约执行效率。在一些文献中,利用世界银行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调查的《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处理商业纠纷的成本数据来衡量契约执行效率,如李坤望等(2010)、蒋冠宏等(2013)等。《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给出了各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城市处理商业纠纷的天数,该指标可以作为衡量契约执行效率的负向指标。借鉴李坤望等(2010)、蒋冠宏等(2013)文献的方法,我们使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城市数据代表该省区的情况,并用365除以该指标得到类似年周转次数的指标inst2,此时该指标与契约执行效率变为同向关系。由于该指标对应2006年的数据,所以只使用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结果可以发现,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仍然在1%显著水平为正。

表5 使用营商环境指数作为契约执行效率指标的回归结果
注:回归中没有控制年份虚拟变量,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3) 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由于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方面的可能,解释变量可能具有内生性。为了降低遗漏变量问题,我们控制了较多的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如销售收入、所有制、年龄、出口比率、补贴比率等,省级控制变量如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经济开放度、人均GDP),利用个体-年度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从而能够消除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异质性和不随个体变化的年度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加控制变量,并利用个体-年度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些能够进一步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尽管如此,遗漏变量问题可能依然存在,如对企业的生产预期并不能进行计量,而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针对选择契约执行效率的具体衡量指标,我们使用现有研究文献中采用较多的《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合约执行成本数据作为契约执行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使用2006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仍然保持稳健,这一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指标的测量误差问题并没有对回归结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制度如何测量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且不同的研究选择的指标也不同,本文的测量误差问题可能仍然存在。如果存在测量误差,这会使得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的核心变量的系数被低估,而在基准回归中的结果已经保持显著为正了,而克服测量误差应该会使得核心变量的系数增大,从而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研究结论。由于契约执行效率变量是用省级层面的指标衡量的,而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层面的指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一般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以便选择自己的决策,所以省级层面的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而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比较难以影响到该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从而使得反向因果的问题较弱。另外对于企业层面的解释变量,我们都将取滞后一期值进行回归,这也有助于减小反向因果所导致的问题。因此本文的回归模型能够降低联立性问题的影响。即使如此,可能还存在逆向因果问题,比如企业生产率提升可能提高对契约执行效率的要求,从而形成正向的反向因果链条,这种正向的反向因果效应则会使得基准回归的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被高估。

表6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注:*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t值;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为16.83;由于样本可能存在异方差,因此采用K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来检验弱识别问题;如果使用常用的依赖iid假设的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则更加倾向于拒绝弱识别问题。
以上对内生性产生三个来源都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从而有效降低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中的系数出现偏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办法是使用工具变量法。参考徐现祥等(2005)、李坤望等(2010)的方法,我们选择中国三大改造前的民营经济发展作为现在契约执行效率指标的工具变量。具体计算方法是:使用1955年各省区的非国有工业总产值除以最大值进行标准化,从而得到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工具变量(zr_iv)。从表6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回归中内生性检验的卡方统计量较大,表明以市场化指数中的“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子项目衡量的契约执行效率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KP统计量)远大于Stock-Yogo的10%显著水平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识别问题。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zr_iv)的系数显著为正。第二阶段回归中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通过与表1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契约执行效率与契约依赖度交乘项系数显著提高了,说明契约执行效率的内生性可能源于测量误差的影响,这也说明基准回归中可能低估了契约执行效率对不同契约依赖度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对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契约执行效率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对于契约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能够更显著的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依所有制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改善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随着契约依赖度的增加,契约执行效率提高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要大于民营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契约执行效率提高对小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大。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再维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企业的生产技术更新、效率提高和效益改善,而这一转变的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亟待发挥制度红利的作用,需要改善法律环境、完善司法体系、提高执法效率,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契约执行效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亦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实现特定类型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2015.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党印,鲁桐. 2014. 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地区层面的差异[J]. 制度经济学研究(1):54-81.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2011a.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9):4-16.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2011b.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方颖,赵扬. 2011. 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5):138-148.
干春晖,邹俊,王健. 2015.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 中国工业经济(3):44-56.
胡一帆,宋敏,张俊喜. 2005. 竞争、产权、公司治理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关系[J]. 经济研究(9):44-57.
简泽. 2011. 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资源再配置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J]. 管理世界(5):11-23.
简泽,段永瑞. 2012. 企业异质性、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J]. 管理世界(8):15-29.
简泽,张涛,伏玉林. 2014.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8): 120-132.
蒋冠宏,蒋殿春,王晓娆. 2013. 契约执行效率与省区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J]. 世界经济(9):49-68.
孔东民,代昀昊,李阳. 2014. 政策冲击、市场环境与国企生产效率:现状、趋势与发展[J]. 管理世界(8):4-17.
雷新途,李世辉. 2012. 资产专用性、声誉与企业财务契约自我履行:一项实验研究[J]. 会计研究(9):59-66.
李坤望,王永进. 2010.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季刊)(2):1007-1028.
李寿喜. 2007. 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J]. 经济研究(1):102-113.
梁冰. 2005.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及融资状况调查报告[J]. 金融研究(5):120-138.
刘瑞明. 2013. 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一个文献综述[J]. 世界经济(11):136-160.
鲁晓东,连玉君. 2012.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2):541-558.
罗煜,何青,薛畅. 2016. 地区执法水平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J]. 经济研究(7):118-131.
马俊英,史晋川,罗德明. 2015. 出口贸易、所有制部门结构与制度进步[J]. 世界经济(12):108-134.
毛其淋. 2013.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分析[J]. 金融研究(2):156-169.
毛其淋,盛斌. 2013.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J]. 经济研究(4):16-29.
聂辉华,贾瑞雪. 2011. 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J]. 世界经济(7):27-42.
诺思. 201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宋渊洋,黄礼伟. 2014. 为什么中国企业难以国内跨地区经营[J]. 管理世界(12):115-133.
温军,冯根福,刘志勇. 2011. 异质债务、企业规模与R&D投入[J]. 金融研究(1):167-181.
徐现祥,李郇. 2005. 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J]. 经济学(季刊)(4):83-100.
杨汝岱. 2015.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 经济研究(2):61-74.
杨咸月. 2014. 大、中、小企业货币紧缩效应及其差异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0):3-20.
余林徽,陆毅,路江涌. 2013. 解构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1):127-150.
张健华,王鹏,冯根福. 2016. 银行业结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商业银行分省数据和双向距离函数的再检验[J]. 经济研究(11):110-124.
张杰,李克,刘志彪. 2011. 市场化转型与企业生产效率:中国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571-602.
ACEMOGLU D, ANTRAS P, HELPMAN E. 2007.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3):916-943.
ACEMOGLU D, JOHNSON S. 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5):949-995.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1369-1401.
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2):339-351.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4(16):386-405.
GROSSMAN S J, HART O D.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691-719.
HALL R E, JONES C I.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83-116.
HART O, MOORE J. 198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J]. Econometrica, 56(4):755-785.
KLETTE T J. 1996. R&D, scope economies, and plant performance [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3):502-522.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1997.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52(3):1131-1150.
LEVINSOHN J, PETRIN A. 2003.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317-341.
LONG C X. 2010. Does the rights hypothesis apply to China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4):629-650.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71(6):1695-1725.
NORTH D C. 1991.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97-112.
NUNN N. 2007.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569-600.
OLLEY G S, PAKES A. 1996.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J]. Econometrica, 64(6):1263-1297.
RAJAN R G, ZINGALES L. 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J].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88(3):559-586.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S71-S102.
SCULLY G W. 1988.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3):652-662.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65-94.
SYVERSON C. 2011. 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2):326-365.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Free Press.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1076-1151.
ZHU X. 2012.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10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