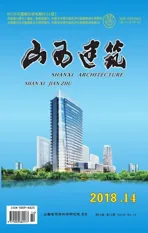建筑叙事学在历史建筑更新中的应用方法分析
2018-07-03金敬梅
丁 聪 金敬梅*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2)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状态,大量产业类建筑、传统的居住类建筑等建筑被历史遗留。而随着人们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提高,历史建筑的更新和再生成为人们的共识。过去在我国历史建筑的更新过程中,常常重视建筑历史符号在形式上的应用而忽略了建筑文化叙事的传承,使建筑的人文精神一再遭到破坏,这种去掉了叙事的历史建筑更新,使得作为故事承载的历史建筑不断被千篇一律的“历史符号”所取代。当人们越来越追求文化归属和精神共鸣,建筑叙事学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出现在大众视野。
叙事学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来源于文学和电影,只不过叙事工具不同,文学作品用文字叙述,电影用画面和声音叙述,建筑同样是一种叙事的工具,用场所作为容器来承载故事。80年代后叙事学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城市、建筑设计的相关理论中来,将场所的空间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整合为城市的地域特色,在人与场所之间建构历时与共时的关联关系[1]。因此,建筑叙事学可以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手法进行分析,应用于历史建筑的更新中来[2]。
1 建筑叙事学应用于历史建筑更新中的现状
国内外将建筑叙事学作为一种手法应用于历史环境更新项目中的实例,从叙事手法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线性叙事、并置叙事和解构叙事[3]。
线性叙事的手法在历史建筑改造项目中常常出现在历史建筑群或有强烈的叙事线索的历史建筑的更新项目之中。如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岛”更新项目,这个由多个博物馆建筑组成的群体在二战期间被造成不同程度的毁坏,在后来的修复改造项目中,建筑师奇普菲尔德并没有在细节上完全复原原有的建筑,也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建筑尺度和体量上再现了战争之前建筑风貌,使得残缺的历史片段得以修补,成为完整的线性叙事[4]。
并置叙事的手法则更为常见,目前国内大部分由旧工厂改造为艺术区的项目都采用了这种手法。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图书楼改造项目。建筑师将新的内层表皮嵌套在旧的民国时期的建筑外壳中,减少不必要的装饰,保护原有的建筑历史痕迹。新的内部空间和原有的建筑结构之间保持着视线和流线的联系,人们在使用新的展览功能时,也能感受到原有建筑的历史文化叙事。从而实现了新的场所功能与旧的建筑历史事件并置对话,从而实现新旧时空的和谐共生[5]。
解构叙事的手法在实际案例中应用较少,且往往结合了前两种手法并用,但是应用这种叙事手法所产生的对历史建筑的整体印象会更加强烈。例如德国累斯顿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的改造项目(见图1)。这座建筑原为德国一座军械库,在历史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改建为撒克逊军械库和博物馆、纳粹的博物馆、苏联博物馆、东德的博物馆,现在重新改建成为统一的德国军事博物馆。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将一个锋利三角楔体刺穿整个建筑,打破原有建筑的对称性,使整座建筑在叙事中的历史片段反复分离与重合,实现空间的解构和时间的消弭。这种解构叙事的手法使人对历史产生跨越时间的深层共鸣,表现了对战争历史的反思与批判[4]。

2 建筑叙事学在历史建筑更新中的应用
以三个历史建筑更新项目为例,分别从线性叙事、并置叙事、解构叙事这三种视角分析建筑叙事学在历史建筑的更新中的应用。
2.1 线性叙事在武汉首义文化区改造项目中的应用
武汉红楼,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武昌起义革命军政府所在地。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被列为湖北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而由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红楼逐渐被拥挤的城市道路包围,成为了一座“孤岛”。由于这样的环境不利于红楼庄重的历史形象的塑造,武汉市政府决定将其与周边的蛇山,首义文化公园,纪念广场、纪念碑、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紫阳湖公园从北至南联系起来,改造交通,形成纵、横两条景观纪念轴,打造成为武汉首义文化区(见图2)。这种线性叙事手法提升了整个革命历史文化区的整体性,使得历史叙事不再脱节。红楼则是作为这一整个叙事序列中一个点而取得了统一的效果。线性叙事手法将不同的叙事空间以一条线索串联,可分为轴线型和非轴线型。而非轴线型根据不同的叙事内容和表达需求又可以分为直线型,折线型,曲线型等。应用线性叙事的建筑更新项目往往更有统一性和延续性。如上文中的首义文化区改造项目中的线性叙事手法使得整个历史线索更为统一,而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岛”更新项目中,线性叙事手法的应用使得断裂的建筑叙事得以延续[6]。

2.2 并置叙事在茶儿胡同8号更新项目中的应用
茶儿胡同8号(如图3所示)是一个坐落于北京大栅栏地区中的典型的“大杂院”,这里曾经有近十几户人家居住于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个家庭都在院子里建造了自己的附加厨房。在以往的建筑改造项目中,这些私人的加建结构遭到了拆除。而在这个项目中,建筑师张珂和他的团队认为这些加建的结构是胡同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并且是胡同历史的见证,因此他们决定保留这些结构,并加以改造和再利用。这些加建结构最后被建筑师改造成为图书空间或者是迷你的艺术空间,延续了胡同的历史并加强了社区之间的联系。建筑师通过将过去大杂院中加建结构和新的四合院建筑空间并置,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这种并置叙事手法适用于新、旧两个时空并存共生的情况,并置时空,使得两个时空互相对话,历史建筑的叙事得以延续,也让历史建筑与人产生新的共鸣[7]。
2.3 解构叙事在“南宋御街”改造中的应用
杭州中山路的“南宋御街”是一条拥有很多时代造就的建筑组成的道路(见图4)。因其有着多条线索共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王澍在做这条古街的改造项目时,并没有将其简单地统一成为一种风格或是“历史符号”,而是在坊巷分界处、在路上构筑坊墙片断,使整条路被十几处坊墙解构成为一个个街/院混合的叙事空间,使整条街具有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叙事结构(见图5)。王澍将整条街上不同时代建筑的叙事时间加以解构,将一个个不同时期造就的空间打散,再重新串联出一种“同时性”的印象[8]。解构叙事常从一个中心出发,用不同的角度传达信息,让人对历史建筑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印象。解构叙事也分为解构时间和解构空间,上文讲述的德国累斯顿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的改造项目便是用“解构空间”的手法进行历史建筑更新,这种手法会将时间的概念弱化,使人在建筑空间中产生跨越时间的情感共鸣;而王澍的南宋御街改造项目中,是采用了“解构时间”的叙事手法,将不同时期建筑的时间线索进行解构,放置在同一网络上,使人对不同时间性质的空间产生“同一性”的印象。解构叙事在历史建筑更新的应用中,相较于前两种叙事手法,不管是“解构时间”,还是“解构空间”,都会使建筑叙事的表达和人的内心感受更加立体化。
3 建筑叙事学在历史建筑更新的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分析

上述案例分别从建筑叙事学中的线性叙事、并置叙事、解构叙事三种叙事手法讲述了建筑叙事学手法应用于历史建筑更新中所塑造的空间特征、叙事特征和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线性叙事手法将不同的叙事空间以时间线索或者事件线索串联,常常应用于叙事线索断裂的历史建筑或历史建筑群,以修复残损的历史建筑空间叙事,使其“再生”,达到文脉延续性的效果;也应用于缺乏时空线索的历史建筑群体,创造新的线索,将一个个如同“孤岛”的历史建筑进行联系,达到整合统一的效果。应用了线性叙事手法更新的历史建筑,相当于修复或者重新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叙事骨架,建筑叙事给人的感觉更具有逻辑性,历史建筑的空间特质更为统一,叙事线索更加清晰。然而这种叙事手法较为单调,仅仅给人一种历史建筑的叙事线索,没有使人得到对历史时空叙事的新的感受和思考。并置叙事手法是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放在同一个叙事面上,使新旧时空相互对话,可能新旧时空在功能和气质上产生了差异,但两者相互肯定,和谐共生;也可能新的空间是旧的空间的传承,使得建筑的历史叙事得到了延续。并置叙事使历史建筑的叙事得到了新的表述,拓展了人们心中历史建筑叙事的宽度,能够给人崭新的时空感受,也能延续时空的历史,记录历史建筑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变化。相较于线性叙事得到了更深一层次的心理体验,对时空的叙事表述更有广度,然而并置叙事手法也有其局限性,过于强调新旧时空的交流和延续使人的思考停留在新与旧的感受之间。解构叙事手法可以将空间进行解构,使历史建筑的时间线索变得模糊,使人在建筑空间中产生跨越时间的情感共鸣;也可以是将凌乱的时间线索进行解构,重构历史建筑或建筑群的叙事空间,使其展现同时性。解构常常伴随着不重组与重组的做法。解构后不重组,使得人对历史建筑时空叙事的感受和体验也产生解构,产生有自身独特性的思考。解构后重组,往往伴有设计者本人的引导性的目的,消解人对原有的历史建筑的时空感受,能够将人的感受引导到设计者所想创造的氛围中来。这种手法跳脱了前两种叙事手法在一个平面上去看待历史建筑更新的做法,转为更为立体的操作,使历史建筑的叙事除了“延续”“再生”外产生新的发展方向,给人带来的内心感受也更加“因人而异”。在将建筑叙事学的三种叙事手法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应用在历史建筑更新中时,应该根据不同的叙事主题、叙事对象和叙事目的进行选择,这三种叙事手法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出现。
4 结语
从建筑叙事学的角度看待历史建筑的更新,可以引发人们对历史建筑时空的思考和感受,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建筑在历史和文化上的传承和创新。事实上,不管是线性叙事、并置叙事还是解构叙事,建筑叙事学在历史建筑更新中的应用都是围绕着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历史建筑如何和人产生共鸣,如何产生人们需要的历史、文化和记忆,这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也是建筑叙事的内涵所在。
参考文献:
[1] 杨纵横.从空间到场所[D].重庆:重庆大学,2013.
[2] 陆邵明.建筑叙事学的缘起[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5):25-31.
[3] 郭红艳.基于叙事法的事件型纪念建筑空间设计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大学,2013.
[4] 吝元杰.历史环境再生之时空叙事的结构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5] 韩文强,丛 晓,吕云涛,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图书楼改造[J].城市环境设计,2014(7):114-115.
[6] 陈 峰.基于事件视角的历史建筑再生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7] 张 轲,张益凡.共生与更新标准营造“微杂院”[J].时代建筑,2016(4):80-87.
[8] 王 澍.中山路:一条路的复兴与一座城的复兴,杭州,中国[J].世界建筑,2012(5):11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