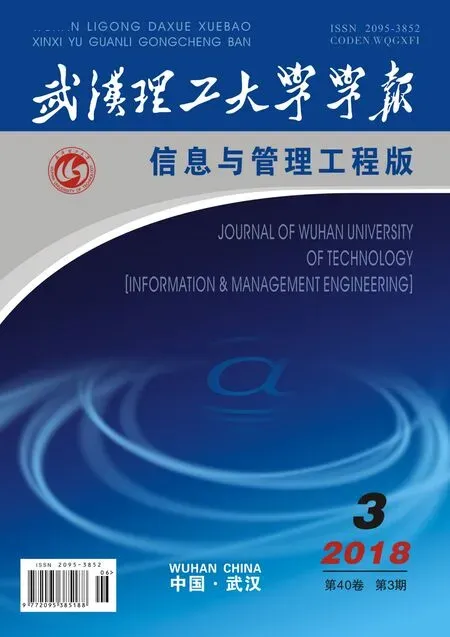家长式领导及信任对员工知识回避的影响
2018-07-03丁志慧
万 翔,丁志慧
(1.武汉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院,湖北 武汉 43007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1世纪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单一领导的知识已经难以应对新时代、新环境、新技术等要求,如何充分吸收外部知识和盘活内部知识成为很多企业关心的重要话题。因此,让员工将隐性知识与其他员工共享,减少员工知识回避行为,是企业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回顾有关知识管理的文献发现,学者们大多关注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研究[1],缺乏对员工知识回避行为的关注。有学者指出领导风格会对员工知识管理行为产生影响[2],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关注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3],缺少对中国文化情境下领导风格的关注,如家长式领导。
已有文献表明,在个体层面上知识管理活动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个体知识管理活动施行的难度,其核心问题是降低个体参与难度;另一方面是知识管理活动个体参与的意愿,其关键是提高个体参与的主动意愿。知识管理活动涉及到自身有价资源的交换,由此信任逐渐成为知识管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因为信任不但能促进合作,而且能促进信息之间的交换。根据社会交换的视角,信任往往是交换的基础或交换过程的产物,组织内上下级的信任可以影响下属的知识管理活动[4]。在交往过程中维持和激发社会关系主要靠信任,因此,有必要研究家长式领导对下属信任的影响和信任在家长式领导与下属知识回避行为中的影响作用。
1 研究理论与假设
姜定宇等提出了家长式领导的二元理论,分为威权领导与仁慈领导两类[5]。前者是指领导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绝对不容其挑战自己的权威,进而达到严密控制下属的目的;后者是指领导以个别、全面及长久关怀的形式关怀下属的个人福利。之后张君等认为家长式领导还存在第三个维度,即德行领导[6]。笔者采用家长式二元领导理论,即威权领导与仁慈领导,这不但符合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恩威并施的行为特征,而且符合笔者的研究视角,即探讨领导对下属的直接影响。在家长式领导风格中,对下属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威权领导与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则是通过领导自身的修养,对下属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1.1 家长式领导与下属知识活动
尽管知识管理非常重要,但涉及到个人利益冲突及意愿等问题,因此知识活动成为组织不确定性的活动。ROGERS将员工的知识活动分为两大类[7]:积极知识活动与消极知识活动。积极知识活动指员工的知识创造与分享,是为了提高组织绩效,不同组织或个体之间分享解决问题的各种信息的过程。消极知识活动分为:①知识回避,指在完成工作过程中不使用自己的知识;②知识挪用,指将任务中获取的知识用于其他方面。作为企业管理者,期望自己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下属形成更多的积极知识活动,从而避免消极知识活动。因此,笔者以员工知识回避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以期为实践中减少员工知识回避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不同的领导风格将会影响员工知识管理活动,但直接将家长式领导风格与知识活动相联系的研究并不多。张永军等研究发现,仁慈领导正向影响组织学习的各个维度,而威权领导则对组织学习大部分维度有阻碍作用[8]。仁慈领导更多体现在对员工的福利、工作环境、年假等工作之外的关心,在我国讲究人情回报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员工则会表现出对领导关心的感激之情。于是在组织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员工,为了报答领导的关心,其需要展示积极性,从而减少自己知识回避行为。强调下属绝对服从、权威不容挑战的威权领导,则会展现“独裁”作风,贬抑下属能力,且对下属不断教诲,有很强的控制能力。由于上级掌握了企业重要的资源和人事权力,下属对上级会表现出一种顺从和敬畏,但这与知识共享氛围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威权领导会促进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呈现出更多消极的知识活动。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a仁慈领导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
H1b威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
1.2 信任的中介作用
MCALLISTER将信任定义为“对他人行为积极预期的一种心理状态,且信任者愿意维持这种状态,接受其带来的可能性风险”[9]。已有的信任研究文献表明,信任关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体交换信息的意愿,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意味着交换信息的意愿越强,这也决定着知识活动选择的不同。信任又可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笔者将分开探讨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情感信任是以情感为基础,是双方对于情感基础的一种信心。具体来说,情感信任是人际间基于对方的品质、善意等要素的判断而形成的一种情感纽带,如互助、真诚及利他等。已有研究表明,情感信任会促使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分享自身的核心信息、观点与知识,进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会促进知识(显性和隐性)的交换,一旦产生信任人们则会自愿进行积极知识活动[10]。
由于家长式领导讲究恩威并施,当领导呈现出“威”行为时,下属的反馈多是敬畏与服从,下属参与知识活动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在威权领导作用下,由于下级对权威的尊重和敬畏,下级对上级的能力寄予高的期望,认为上级能够应付很多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从而对上级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的核心是交换双方的核心独有资源,而威权领导的行为更多是单方面的,缺乏与下属的互动和实质性的资源交换,难以与下属形成情感信任,这表明情感信任在威权领导与下属知识回避之间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仁慈领导表现出对下属的全面关怀行为,领导对下属不仅是情感交流,还充分展现出了领导对下属的信任与关怀,下属对领导这些行为的回馈方式是表现出对领导高水平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更多呈现出仁慈领导与下属间的情感信任。较多学者也证实了仁慈领导的行为是领导与下属间建立情感信任的重要因素。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下属会将情感信任转化为自我积极的知识活动,情感信任水平越高,下属展现出的回馈动机则越强,这也越有利于积极的知识活动,进而减少自身的知识回避行为。根据以上认识,提出以下假设:
H2情感信任在仁慈领导对下属知识回避的影响间起中介作用。
认知信任是指对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是建立在对对方能力、可靠性、责任感及依赖性的基础上。以往研究发现,认知信任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哪种方式更有效、更便利、更可靠,而不是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亲密程度。当领导呈现出威权领导行为时,其强调的是下属对领导的服从,依照领导制定的规则、工作流程及领导的需要开展工作,这样做下属一方面会免于领导的惩罚,另一方面领导与下属间的信任会有所增加。尤其是当领导的指示促使下属的工作业绩更加突出时,下属对上级的能力会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同时上下级之间的信任会进一步加深。根据信任的定义可知,威权领导与下属间表现出来的信任更多是对对方能力、可靠性、责任感等的认知信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在知识管理过程中,为了维护与领导之间的认知信任,下属一方面要坚决执行领导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或意愿进行知识共享活动,进而更多的是选择知识回避。此外,由于认知信任无获取功能的局限性,也就无法促使领导与下属之间彼此资源的交换,因此,领导对下属知识回避行为更多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仁慈领导作用下,下属的回报心理会被加强,SCHOORMAN等证实了领导可靠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仁慈,这会促使下属对领导的高度信任,这种信任的形成更多是领导与下属情感的交流,而不是基于问题导向的认知信任[11]。因此,认知信任在仁慈领导与下属知识回避之间的作用并不明显。根据以上认识,提出以下假设:
H3认知信任在威权领导对下属知识回避的影响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考虑到医院员工密集程度高,知识更新较快,因此选择医院的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合适。2016年5月—8月,笔者组建调研小组在湖北省多家医院展开调研,并通过培训会的形式对各个成员进行培训。为确保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医院领导将对应医院各科室负责人召集起来,详细说明问卷的内容及调研的重要性,调研人员跟随科室负责人展开调研工作。各科室成员填写成员问卷1,题项主要是家长式领导与人际信任相关内容;科室负责人对科室内每位成员的知识回避进行评价。问卷发放共计290份,回收问卷218份,有效问卷188份。此次研究的人口统计变量信息为:在性别比例上,女性占76%,男性占24%;在教育程度上,有硕士学历的占3.6%,大学本科占55.7%,专科占36.5%,中专及以下的占4.2%;从事本岗位工作年限在1年以内的占23.0%,5~9年的占22.2%,10~15年的占26.3%,16~20年的占26.5%,20年以上的占2.0%。
2.2 变量测量
(1)家长式领导。量表取自于文献[12]的家长式量表,分为仁慈领导和威权领导两个维度,均采取李克特5点制计分。仁慈领导和威权领导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sα分别为0.903、0.764,整体量表的Cronbach′sα是0.778。
(2)人际信任。借鉴文献[9]编制的量表,包括两个维度: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均采用李克特5点制计分,要求受试者评估与领导间信任的强弱。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sα分别为0.763、0.864。
(3)知识回避。知识回避取自于文献[7]的量表,采取李克特5点制计分。知识回避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839。
(4)控制变量。依据已有知识活动研究的文献,选择性别、学历和岗位工龄3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与结果分析
3.1 同源误差检验
考虑到所有数据的收集来自于同一行业的个体,可能会出现同源误差的现象,甚至影响到研究结果。因此,依据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将两阶段问卷中6个变量的所有题项汇集起来同时进行因子分析,同源误差大小则通过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来反映。结果表明,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占18.93%(累计解释63.85%),所占比例不大,说明不存在较严重的同源误差问题。
3.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仁慈领导与知识回避(r=-0.372,p<0.01)显著负相关,威权领导与知识回避(r=0.381,p<0.01)显著正相关;仁慈领导与情感信任(r=0.435,p<0.01)显著正相关,威权领导与认知信任(r=0.392,p<0.01)显著正相关;情感信任与知识回避(r=-0.196,p<0.01)显著负相关;认知信任与知识回避(r=0.261,p<0.01)显著正相关。笔者的假设初步得到验证。

表1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N=188,**表示p<0.01
3.3 回归分析
根据BARON等检验中介的三步法可知[13],若控制自变量,同时检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性,如果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同时自变量的效应并没有消失或减弱,即可认为完全中介作用或部分中介作用存在。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M2显示仁慈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回归系数为-0.386,p<0.001),假设H1a进一步得到支持。模型M3显示威权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回归系数为0.412,p<0.001),假设H1b进一步得到支持。模型M10同时将自变量仁慈领导和中介变量情感信任加入到回归方程中,回归结果显示模型M10相对于模型M2而言,仁慈领导对员

表2 家长式领导及人际信任对知识回避行为的层级回归结果
注:N=188;*表示р<0.05;**表示р<0.01;***表示р<0.001
工知识回避行为影响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仁慈领导和情感信任对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因此情感信任在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回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支持。同理,模型M11同时将自变量威权领导和中介变量认知信任加入到回归方程中,回归结果显示模型M11相对于模型M3而言,威权领导对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影响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威权领导和认知信任对员工知识回避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因此,认知信任在威权领导与员工知识回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支持。
4 结论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笔者实证检验了家长式领导对员工知识回避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仁慈领导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②威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回避行为;③情感信任在仁慈领导对员工知识回避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④认知信任在威权领导与员工知识回避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研究中探索了知识回避的前因,丰富了员工知识活动的理论研究。实证检验了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的不同中介效应,也进一步丰富了信任相关的理论研究。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厘清家长式领导对员工知识回避的作用机制,有利于认识到家长式管理的隐性危害。组织领导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领导风格进行调整,避免过多采用威权领导行为。当员工存在知识回避意识时,采用仁慈领导行为可以达到抑制知识回避的效果。尤其在中国情境下,关心员工及其家庭,为下属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困难,是一种有效管理员工知识活动的方式。同时,通过厘清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不同中介作用,有利于提高信任管理的针对性。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背后不同的交换资源,是组织信任有效管理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在组织管理过程中信任氛围的培养,应根据信任的不同机理,合理构建领导与下属的信任关系,从而提高组织信任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厘清员工知识回避的内在机制,有益于培养积极的员工知识活动。除了常规奖励员工积极知识活动外,应鼓励员工参与组织管理,建立有效的领导与下属的沟通机制,促进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从而使员工知识管理的倾向逐渐转为积极的知识共享行为。
参考文献:
[1] 吴磊,周空.家长式领导风格下知识共享行为研究:主管信任的中介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3):149-154.
[2] 王双龙.华人企业的家长式领导对创新行为的作用路径研究[J].科研管理,2015,36(7):105-112.
[3] RHEE Y W, CHOI J N. Knowledge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goal orientations as antecedents and in-group social status as moderating contingenc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7,38(6):813-832.
[4] RUTTEN W, BLAAS-FRANKEN J, MARTIN H. The impact of (low) trust on knowledge sharing[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6,20(2):199-214.
[5] 姜定宇,郑伯埙.华人差序式领导的本质与影响历程[J].本土心理学研究,2014(42):285-357.
[6] 张君,孙健敏.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家长式领导研究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2017(11):24-26.
[7] ROGERS E W. Cooperative knowledge behavior in high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the employment game, cooperative knowledge behavior and firm performanc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00.
[8] 张永军,张鹏程,赵君.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基于传统性的调节效应[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2):169-179.
[9] MCALLISTER D J. Affect and cognition- 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1):24-59.
[10] 陈可嘉,陈鹏,陈洪.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组织视角隐性知识管理仿真[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6,38(4):441-445.
[11] SCHOORMAN F D, MAYER R C, DAVIS J H.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32(2):344-354.
[12] 郑伯埙,周丽芳,黄敏萍.家长式领导的三元模式:中国大陆企业组织的证据[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3(2):344-354.
[13]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6):1173-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