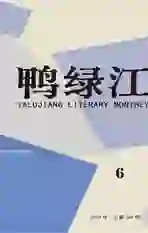我有两座城
2018-06-23陈瑞琳
[美] 陈瑞琳
车子里放着国内乐坛流行过的曲目,男人唱的是《江山美人》,女人唱的是《真的好想你》。直面的冷气吹得眼睛有些发涩,戴着墨镜,也能感觉到得克萨斯的阳光是如此晃眼,车轮徐徐滑动,前面就是休斯敦中国城的百利大道。
二十五年了,眼前的这座城太熟悉,那几个地标式的高楼已经被我看得老态龙钟起来。前些年做记者跑广告,我们这一行叫“扫街”,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去扫。最难为的是收账,尤其是那些脱衣舞厅,老板们都是凌晨才上班,我曾经在夜半的霓虹灯里穿过酒色,才能拿到拖欠的支票。前方的拐弯处就是那幢外面漆成黑色的房子,墙上还留着一排艳女的头像,如今已人去楼空。美国老了,這个国家显然已经透支到力不从心,好像一个过度消费的壮汉,虽说还立着一副宽大的架子,但肌肉下垂已雄风不再。
望着这座年轻又斑驳的城市,既没有云烟的山岭,又没有揉在掌心的雪花,但是它竟然有九十多种活跃的语言,据说住在这里的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在外国出生。每次我遥望着高速两边一幢幢神秘的大楼,总感觉在那些透亮的玻璃窗后,都会隐藏着无数生命的故事。
怎么也忘不掉1993年开春的那一天,休斯敦的太阳却是出奇地亮,亮得整个城市先是灿黄再燃烧变红。异乡女子的我,正孤零零地站在这车水马龙的百利大道上,身上的衬衣浆洗得很白,身后是巴士车站滚热的水泥电线杆,但绝望的寒意却忍不住让我瑟瑟发抖。
那一天,因为走了太多的路,胃里饿得发痛。直到太阳下坠,也没能找到一家愿意雇用我的餐馆。坐在一家越南女人的店里,买了一个三明治,店主随口问我是哪里人,说完“西安”两个字我就后悔,因为她的表情告诉我“西安”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看着三明治里薄薄的肉片,嚼着干渣渣的法式面包,心里一阵发酸,不禁想起了从前最爱吃的关中肉夹馍,还有那个曾经海纳百川的古都长安!
那是1992年的冬天,母亲来古城墙下的校园看我。年轻教师住的筒子楼因为厕所堵塞而发水,恶臭的污水已经漫延到了家门口。母亲踩着砖头进了屋,又踩着砖头在门口的炉子上给我烧菜。夜里我对母亲说:“我要走了,就是想早一天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以在自家烧饭,洗澡,上卫生间!”母亲的眼睛立马红了,心里万般不舍,还是点头拥抱我:“去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怀想那些初到美国的日子,不敢有梦,为了温饱,我曾端着自己包的冻饺子在烈日下叫卖,也曾在黑夜的暴雨中迷路不知所返。流浪之中,一个台湾留学生愿意卖给我一部旧车。见面那天我钱不够,他仔细瞧我,问:“大陆来的吧?”我说“西安!”他一乐:“成交!”我最后送他上了飞机,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高速公路。
有了车轮的我立马创下了“三家餐馆关门大吉”的打工纪录。问题的严重是我总把英语的“莲花白”(cabbage)和“垃圾”(garbage)两个单词调包。客人一问:“春卷里包的什么?”我就回答:“垃圾!”吓得客人每每失色甩手离去。
就在第三家餐馆将要关门的时候,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华侨忘记给我小费却丢给我一份洒满油腻的中文报纸。那是我在美国看见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其激动绝不亚于见到亲爹亲娘。报上有一堆招工广告,炒锅,抓码,算账,看仓库,反正七十二行都不要我这种人。沮丧之际发现了“副刊”上的一句话:“提起笔就是作家!”半夜里我到处寻找纸笔喜极而泣:美妙的方块字哟,是你要来救我吗?
因为漂泊,懂得思念,懂得了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懂得了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他们若不远游,怎会有这样深刻的愁韵?古人尚明白“置身异乡”的丰富体验,谁能说,闯荡新大陆的暂且“苍凉”,不正是生命里最难忘的驿站?异域生活的冲击,移民生涯的甘苦,散文,这个最让我迷恋的文体,在异国的暗夜中带给我重新焕发生命的希望。
2009年,为了领取“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急匆匆的我踏上了回乡的路。高空中,那皇天后土的古塬已经清晰可见,心在悬空,飞机开始下降,直扑脚下的这座曾经生我养我的城市。走过了千山万水,还是这座城每次回来都让我心跳眼热。
细雨中,父亲来接我。车子经过西大街,改建后的宽阔让我完全不认识了。两旁已是百货高楼、豪华酒店,街面上川流的人群时不时地从地下的商场里突然冒出来,唯有那久远的1路电车还是从前的样子,缓缓地停在了南广济街站的街口。往事悠悠再现,就是这个距市中心不足千米的地方,记忆中的母亲总是牵着我的手在这里下车,然后走进路旁的一座深宅小院,那里有母亲的亲人,也有我的亲人。雨水灌进我的泪眼,天上的母亲哟,女儿今夜又看见你了!
三十年成长的岁月,我的脚印几乎能将这西大街上每家铺子的门槛磨平。海外漂泊的日子,多少次梦回长安,大唐帝都,车马萧萧,东南西北十字四条大街,唯有这西大街,好像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栖息之地。小时候父亲教我唐诗,那诗里有许多的句子都是写长安城,现在终于懂了古人的“长相思”,为何非得“在长安”!
夜色已浓,又想起了那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可惜这雨中无月,但长安城的灵魂,感觉就在这夜色里。我开始想象,当年的杜甫每次回长安,肯定都是在暮色中,月儿要升起来了,他老人家终于望见了长安的西门城墙,趁着夜的遮掩,赶紧用袖子抹去了眼角的一行老泪。据说当年的李白也是喜欢住在西城的,那里有老回民的酒家客栈。还有那“长生殿”,猜想唐玄宗肯定是盼着天儿早早黑的,只有到了夜里,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时光。那一千多年前的才子佳人们,肯定也是最喜欢长安的夜,天色黑了,他们才能放开了情怀喝酒,才能看见可心的艺伎弹唱着红颜知己的丝竹之声。神往的大唐夜晚,一定是钟鼓齐鸣,乐舞飘香,远处的边塞则是金戈铁马、兵锋镇守,祖先的帝国,正雄踞在世界的东方。
正遐想着,父亲指给我看马路对面新建的城隍庙。彩绘的楼门,曾是母亲生前的最爱,母亲喜欢缝衣裳,又总希望我穿得与别家孩子不一样,就常常到这里来搜寻那种领口上的花边或者小手绢和小袜子。每次买完针头线脑,母亲就拉着我往西走,到了桥梓口的回民街,先要一碟腊羊肉,再配上几个刚煎好的柿子饼,看我还想吃,就再到贾家叫一笼灌汤包,母亲多是看着我吃,自己却从旁边的铺子里端来一碗红油油的汉中米面皮子,慢慢地陪我。
怀念从前,春天时南进终南山,翠华峰下,踩着王维诗中的清泉石流,体味着古人的“终南捷径”。夏日里东临骊山,华清温泉,凝脂芬芳,回廊楼阁,“长恨”绵绵。跨过兵谏的五间厅,再越山腰捉蒋亭,遥看始皇陵,留笑烽火台。秋天时向西,那里有老子炼丹讲经的楼观台,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看竹林摇曳,望仙雾飘渺,人与自然,气脉如此相合。冬日时再去北,涉水过咸阳,踏上五陵原,登乾陵无字碑,长长的汉唐龙脉一直向远方蜿蜒伸展。
都说古时八水绕长安,杜甫也赞“长安水边多丽人”。探着水迹,东城外有半坡人的遗址,最早的长安人神奇的创造便是那汲水用的尖头陶罐,精美的鱼尾纹让今天的艺术家也惊叹不已。再游去东南,小溪河畔蓦然就发现了戏里唱的王宝钏十八年望夫的寒窑,田野里真的就不见野菜,唯有红鬃烈马的塑像威然立在窑前。灞水折柳,惹来自己一襟眼泪。清凉的古刹碑林,碑刻环绕,青石叹息,幽谧中骇然一惊,原来是大文豪苏东坡豪迈奔放的手迹。
“到家了!”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你还记得南郊外有个唐苑吗?就是当年皇帝狩猎的上林苑啊,现在可是柏树参天,百羊开泰,连园中的小路都是当年的古磨盘铺成的!还有东郊的浐灞开发区,那里已变成江南的水乡,亭台楼阁,湖中鸟岛。对了,还有一个新建的陕西民俗村,那里每个院落,都是从乡下的官邸人家搬来的,每一块砖,连那拴马的石柱都是咱们关中历史的文物!”
回到古城的第一个早晨,因为兴奋,因为时差,天麻麻亮就起来,急切地拉着父亲,要去看小南门里的早市。这些年,小南门的早市,多少次入夢,那混合着各种生命交响的市井声浪,竟完全胜过了铁马冰河,那小小的门洞,几乎就是我在异国他乡最深的盼望。
催着父亲在街边的小凳上坐下,来一碗我最爱的豆腐脑。再顺着街走,油饼、油条、肉夹馍、水煎包,挨个尝过去,因为太早,还没有凉皮,走到最后,父亲的脚步又迈进了老兰家的桌子,跟我说:“你还没喝最香的清真胡辣汤呢!”
恍惚中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小南门,男人多穿着警察蓝的中山便装,女人也多是过年才买一件新衣裳。中国人的日子转眼之间就变了,变得天天可以吃饺子,随时可以穿新衣。望着脚下清澈的护城河水,眼睛里几乎有泪,当初放我远行的母亲在九泉之下已不能再张开双臂,她虽然没能看到今日的长安,但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砖,都散发着母亲那温暖的气息。
走在城墙根下,摸着那些厚重的砖瓦,三十年成长的水乳交融,早已让这座城市融入我的血液,就如童年时爱上的那些食物里的味道而永远无法改变。听说一个老人如果失忆,只要他回到故乡就能想起所有的故事。
车子里又响起《真的好想你》,眼前的景象却是通向山姆休斯敦大道的环城高速。在这虎踞龙蟠的高架桥上,德州大平原上特有的云朵正在空中翻卷,它们时而如海浪在绵延起伏,时而又如群雄逐鹿的草原,那种粗旷豪迈,正好像要激励着每一个异乡人去完成属于自己生命的故事。
生命如船,梦想如帆。从儿时的八百里秦川,到今天的墨西哥海湾,两座城连接的却是同一个人类发展的大时代。地球那边的城是我的父亲,这边的城连着我的孩子。一个是我来的地方,一个是我去的所在。宽阔的太平洋就如同桥梁,将两个半球相连,将人类的血脉相连,也把爱与梦想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