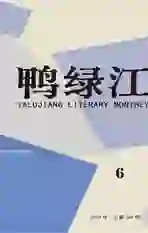城里月光照不到乡村的田野
2018-06-23二湘
[美]二湘
小时候最喜欢去乡下外婆家玩。记忆中外婆的家是一帧泛黄的老相片,古朴而悠远。外婆家的房子原是黄土坯的房子,乌黑黑的瓦檐,黃融融月亮一般土黄的墙。右边是卧房,中间是堂屋和厨房,左边还是卧房。卧房里是一溜连着的三张老式木床,床架上有各种花鸟的漆画,一年四季挂着的是粗布的白而泛黄的蚊帐。夏天的晚上,睡觉之前,总是要四处细细找寻长脚的蚊子,必得把它们消灭殆尽方能安心入睡。黄土房子终日散发着一股薄淡的尿骚味——在房子的最尽头是一个尿桶,给晚上起夜的人用的。尿桶旁边是一个长长的木楼梯通向二层的阁楼。阁楼里有很多老旧的物件,大大的木箱子,脱了漆,叠放在一起。老式的柜子,大而笨重,外面贴着老旧的年画,像是阿里巴巴的藏宝箱。于童年的我,这阁楼似乎终日弥漫着一种陈旧而神秘的气息。
我上小学时,夏天放了暑假常去外婆家玩。我母亲兄弟姊妹多,除了小舅舅念书进了城,几个舅舅都是留在乡下。记得大舅舅一家是住在外婆的黄土坯的房子的后面,紧连着就是二舅舅家。三舅舅是住在外婆家左边的那一溜卧房里。一大家子,住得团团转。舅舅们孩子也多,我很高兴有很多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和我们玩。除了人多,狗儿猫儿的也多,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下面窜,骨头一落地,就给叼了去。一派生机勃勃,人丁兴旺的景象。
到了“双抢”的时候,总是几家凑在一起,一家一家收割稻子。大家用打谷机打谷子,接着插晚稻秧。这一阵是农村里最繁劳的一段时间,对孩子们却是欢乐的节日。因着这几天大家都是凑在一起吃饭,菜蔬也因此特别丰盛,又都是现摘的,新鲜可口。而外婆还会去林场里买了鲜肉,肉片炒朝天椒,又香又辣。双抢结束,农闲的空当,人们会去看电影,露天的电影,双面都可以看。我们走好几里地去看电影,远远的就看到好多的人,密密麻麻的,铺满了一整个晒谷子的禾塘。
再后来,舅舅们就都去了广东做农民工,家里只有舅母们和幼小的孩子们,舅舅们赚了钱,家里头开始建房子,土坯房子拆了,修了两层楼的红砖房。渐渐地大家似乎都不怎么种田了,双抢的盛景越发不见了。奇怪家家好像也都不缺饭吃。再后来,舅母们也都跟着进了城,乡下只剩下了外婆外公和孩子们。红砖房也慢慢破旧了,但是也没有人管。舅舅们都进了城,深圳,广州,或者是长沙,不知道什么样的旮旯角落里。他们或者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是在建筑工地上,又或者是做了哪家公司的保安或者门卫,他们成了城市的一员,却是在最靠近地面的一层,尘土一般,被城市的风从一个角落吹到另一个角落。
而在这尘土之上,城里的房子在如梭的岁月里渐渐长高,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我小时候住在卫生学校的后面,四层高的楼房,每一家都是一样的结构,最简单的田字形结构。田字形的四个格子里各是两间卧房,客厅和厨房。后来公家统一改修,把厨房改成了一间卧房,把厨房移到了阳台。一套房间只有一个卫生间,而且极小,仅容一人。
再后来我上大学时我家搬到了莴家园那边,原先还是比较偏远的地段,很快周围的楼房也多了起来。那里的房子宽敞了一些,有三个卧房,只是还是和原来结构差不太多。再后来我出了国,回到家,家里已经搬到江北了。江北原本是大片的农田,可是修了桥以后很快也热闹起来,现在已然成了繁华地段。家乡的小城就是这样一点点扩展,原来的乡村田野迅速地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在结结实实地变化着,最显著的就是居住环境,城市的高楼越修越高,越修越多。每家每户的房子似乎也是越来越宽敞,装修越来越精致。我记得原先家里都是水泥地。我家在莴家园的房子那时候涂上了时兴的红漆,乡下来的婶婶在门口站着不敢进来,要脱鞋,忙被我妈拦住了。现在的房子里铺的都是木板或者大块的瓷砖,看着特别舒心。一开始房子里都没有热水,慢慢地家家都有了热水器,随时能用上热水。因为隔得远,每回国一次觉得最显眼的便是这居住环境,城市是越来越齐整,越来越舒适了。然而和城市的繁华相对照的就是乡村的衰落。
每次去外婆家,房子却都还是1980年代的红砖房,再不变更。房屋里面老式的描了花鸟图样漆画的木柜,灰黑的厨房和灶台,从未上过漆的老式座椅,依然如故。一切像是沉睡在那个年代,不复醒来。而乡村里似乎只剩了老人和留守的孩子,不,还得加上四处游走的家禽。彩色的花公鸡,麻栗色的老母鸡,似乎给这张黑白老照片上点染了一丝亮色。乡村,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新鲜活泼充满蓬勃活力的绿色乐园,而是变得如此颓败,像是一幅斑驳的旧画,渐渐剥落,露出最原始的底色。
而这其实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连接乡村和城市的交通纽带日益变得便捷。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要坐两个小时的长途班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的土路。从镇上到大山脚下外婆家的村子的一条土路,道路两旁有青幽幽的稻田,有欢快的小溪一路流淌。清澈见底的溪水,和溪水里光滑美丽的鹅卵石让这一路充满了乡村的静谧和纯净,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般美。那样的一条路,也就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再无法忘怀。后来就通了高速,从城市到乡镇的高速,平坦宽阔。镇上的柏油路也一气儿铺到了村口。回外婆家的路变得如此快捷,我似乎再找不回记忆中那条怎么也走不到头的土路了。
又何止是到外婆家的路,交通越来越迅捷,天涯不复是天涯,海角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车程。我2000年回国的时候还不太觉得,那时候在国内买机票还很不方便,只能托国内的朋友帮忙。后来网络发达起来,随便去哪个网站,买机票,用国际信用卡都可以支付。而现在有了微信支付以后,更是简单方便。距离因为时间的缩短而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回国的频率也因此增加。许多1980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十多年也不回国都不罕见,我到美国是90年代末,第一次回国是三年之后,比起那时候的留学生已经算短的了。而如今,许多人都是每年都要回国,一是要孩子回国学中文,二来也是实在便捷。在国内出行也是方便得很,尤其是这几年高铁像一张密密的网,把大好的河山点点片片都连了起来。北京到天津不过二十分钟,北京到长沙不过七个小时。回想当年从北京回老家,先是坐绿皮火车,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长沙到家乡的小城又是六个小时火车。不过短短二十年,世界已然发生了当年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城市和城市之间,国与国之间,家与国之间,已然近在咫尺。
越是如此,我越是无法明白乡村的被遗弃。大片的乡村被时代,被这个地球村甩到了一个沉寂的角落,慢慢生长,慢慢逝去,慢慢地被遗忘。它们似乎是永远停在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沉醉不醒,慢慢褪色。乡村,是我外婆的家,也是我的家,也同样是很多人根脉最初生长的家园。我看到了城市迅猛地蜕变,然而,我无法释怀乡村的停滞。甚至不只是停滞,而是倒退。
记得作家格非在《望春风》的后记里说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述说乡村了。他十七岁离开了家乡,动手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回了两趟老家,却发现老家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瓦砾,过去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过的路都化作了废墟和野草。我上次回国,去外婆家,特别能感同身受那样的悲凉和哀叹。到处都是破败的老房子。那些村落那么安静,人影稀疏,看到的也只是老人和孩子,极少看到年轻人。田野不复是记忆中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记忆中那里有着最鲜活的蔬菜,紫油油的茄子,金灿灿的黄花菜,黄澄澄的梨子,红黑黑的茨菰,剥开了里面是白嫩嫩的肉。记忆中那里还有热闹的老屋,一屋子的人,冬天的时候一起冲糍粑,夏天的时候在禾塘里乘凉摆龙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姐表弟们,他们又都去了哪里?
城里的月光那么好,可是它照不到乡村的田野。乡村的田野太广袤,广袤得无法分享城里一缕皎洁的月光。没有月光的乡村在一点点枯萎,一点点颓败。面对城市化的浪潮,乡村变得无影无踪。只是在我的记忆里,乡村忽远忽近,悠悠荡荡,却永远不会褪色,那是我最亲近的故土,那是我近在咫尺的家园,珍藏着我童年记忆的家园。那条通向大山的土路,那土路旁边清澈的溪流,千万年地流淌,每一刻都在变换着它的姿态和颜色,那是我再也回不去的乡村。
父亲的二胡
我父亲八岁的时候成了孤儿。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起他的身世,但是偶然的他会说几句。譬如我中学历史学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说那时候的情形比这惨烈多了。“你爷爷的两个兄弟就是那时候死的。”又比如我们学乡土历史的时候,他会拿起我们的教科书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没有写社教呢?”
这样子慢慢地我们也把他的家事凑齐全了。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保长,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三。秋收起义那年大儿子刚成了家,新娶了媳妇。那天正好他媳妇回了娘家,他带着大弟去镇上赶集。那么巧就碰到了革命军游行,两个人挤进去看热闹,却被认出是保长的儿子。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两个人绑了,游街以后就杀了。我爷爷本也闹着要去镇上,两个哥哥嫌他小,碍事,没带上,反倒捡了一条命。可惜他也不长命,我父亲出生不久他就得了伤寒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改嫁给张木匠。
这个张木匠据说是个命硬的人。我后来看《白鹿原》,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我就想,这不是张木匠嘛。他第一个老婆被马蜂蜇了第二天就死了,第二个老婆是我爷爷的大哥的遗孀,她新婚的老公被群众杀了后不久她就改嫁给张木匠,结果没几年也病死了。我奶奶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她嫁给张木匠以后,生了三个闺女,我的三个姑姑。兰姑,慧姑,秀姑,她们都长得好看。我就想,大约我的奶奶也是好看的。我奶奶再一次怀孕的时候,有一天爬梯子去阁楼里取东西,不小心摔了一大跤,去了医院打了一针说是保胎的,结果不但孩子没保住,连大人的性命也丢了。那一年,我父亲刚满八岁。他说只记得家里闹哄哄的,三个妹妹都在哭。他没有说他有没有哭,我猜他一定是哭了,只不好意思与我们说。张木匠后来又娶了个城里人的小老婆。那时候解放了,不准三妻四妾,小老婆就被休了,然后改嫁给张木匠。那个小老婆据说人也不坏。但是到底也不是亲娘亲爹,周围还有一堆有一半血缘关系或者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我父亲是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没依没靠的一个人讨生活。
据说我爷爷是颇有些才气的,毕竟是保长的儿子,小时候读过私塾的。我父亲说,爷爷二胡拉得特别好,那时候还在镇上的戏台子上演出过,我家里那把二胡就是爷爷传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是得了些真传,也是方圆十几里地的秀才,不仅二胡拉得好,字也写得好,还会在大衣柜门上画百鸟朝凤和富贵花开。那时候,附近乡邻有了红白喜丧事都爱喊他。一来父亲会编对联,写对联,二来他还会打算盘,可以兼做账房先生。我小时候,别人喊他,他总是甩下手里的活拔腿就跑,母亲在他背后大声地呵斥,他只当没有听见。
父亲最风光的时候大概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时期,他称做社教的那个一两年,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事吧。他那时还是单身,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台下是乌泱乌泱的一大片。群众把他们报告团的人当神一样敬,盛情挽留他们留下来做干部——真有留下来的。可是父亲天性单纯,又被热血澎湃的时代冲晕了头,压根想不到要做什么官,还是兴致勃勃地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一场一场地做报告。然而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很快就不搞什么社教了。父亲回到老家种田,而那些留下来的就做了官——乡长甚至是后来的县长。他有时候说起某某某当年还没他讲得好,现在都做了区长了。母亲就开始嘲笑他,骂他蠢,看不准形势。 他也不恼,任母亲说,就像平常任何事情一样。他就是听着,不生气,也不发火。
我家兄弟三个。我初中就开始住校,很少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哥和我都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小弟也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我弟留在了省城,我和我哥都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还是件颇新鲜的事,县里的报纸找到了我们家采访父亲母亲。他们两个拘谨地坐在禾塘的竹凳子上,父亲一开口眼泪就往下淌。母亲坐在旁边,不哭。
我后来接父亲母亲去美国住,他们不习惯,尤其是父亲。我有次带孩子看病,把他也带上了。我们在小单间等医生的时候,父亲抱怨说:“美国看病的房子都这么小。” 我很无语,中国看病的房子是大,可是好多人呢。病人看病是没有隐私的,你说你的病状,满屋子的人都尖着耳朵听。我老婆是个城里人,父母亲第一次来,她就给每个菜盘里加双筷子,说是公筷。 有一次父亲忘了换筷子,我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父亲茫然地看着我。我很想把老婆呵斥一顿,然而我究竟没有,父亲的懦弱像是从空气中传到我这儿。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张木匠家的日子,尽管他从没有跟我们提过。那样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唯有变得懦弱,才能保护自己,只这习惯性的示弱已经深深写在他骨子里,甚至是通过DNA传到我这儿。我悲哀地发现,我在重复父亲,重复父亲的懦弱和隐忍。
父亲住满了六个月马上就走,我心里很内疚,但是我竟然不知道能做什么。父亲回到家就常跟我们提海归的事,说我的中学同学大林学习那么差,复读一年才勉强进入省里的一个二流大学,现在在东莞,做房地产,早发了。“你和你哥也回来吧,国内机会多得是呢。” 我和我哥都不做声。
我去年带着儿子壮壮回国给他做七十大寿,我哥我弟也都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这么多年总算是又聚在一起。我家是在一个小山冲里,在大路上隔一两里地都能看到,可是要绕上一大段路才能走到。我记得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父亲会说一句:“坐稳了!” 然后车子在泥路上一颠一颠地出了山冲。好在后来从大路到家门口的那段泥路改建扩修了,私家车也能开进来了。那天孩子们都跑到老屋里耍,跑上跑下,兴奋得很。我家的老屋很破旧,南方农村典型的青瓦尖屋顶,中间是堂屋,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卧房。厨房还是那种老旧烧柴火的灶台。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田埂上挖水米花,然后捣碎了放在糯米里做糍粑。到了过年我们在灶火上烤糍粑,烤到金灿灿的再撒上白糖,吃起來满口的香甜。我们后来要给他们修新房子。父亲不肯拆老屋,就只好在老屋旁边并排修了一栋新屋。新屋有三层楼,那时候还是附近最高的楼,可是现在也是灰头灰脸,周围好几栋楼都比它高了。那天来了不少人,其实大多是我们兄弟三个的同学来捧场。我们在禾塘里摆了近二十桌,父亲乐呵呵地忙上忙下,看得出很高兴。平日里这两栋大屋子,就他们两个老人住,一定是寂寞得很。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一轮残月挂在天边。父亲看着空荡荡的禾塘,突然跟我儿子说:“壮壮,你要听爷爷拉琴吗?”说着就从大衣柜里找出了他的二胡。壮壮拨弄着二胡,说:“跟我的小提琴有点像呢,也是要拉的。”“是啊,这是中国版的小提琴,等我死了这把琴就给你好不好?”父亲跟壮壮说。“我不要,爷爷不会死的。”父亲笑了,然后他就坐在禾塘的小竹凳上,也不看我们,拉了起来。他拉的是《二泉映月》,调子很悲凉,我小时候听过许多遍,我知道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就会要拉他的二胡。他拉得很入神,我看着他微屈的背影,像一棵被挖空了的老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却紧力地抓着地面。我不知道他这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我站在那儿,心里是月凉如水的凄凉。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