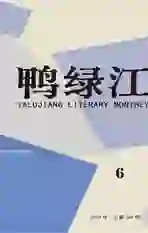必经之路
2018-06-23凌岚
[美] 凌岚
林里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可以看到海。那是95号高速公路在康州南部段,沿着大西洋的长岛内湾一路向北,在布里奇波特市和纽黑文市交界处有一个海港,就叫纽黑文港。那里是康州黄金海岸线上贫困的“下只角”, 那附近几个镇居民中靠政府福利度日的占相当的比重,剩下的是蓝领底层, 学区差,房价低迷不振,空有一片海景和一处处沙滩。
自2001年始,林里一直在纽黑文的工业园做数据库管理。她住在诺瓦克,每天早上,从95号高速公路向北,到了45号出口附近,在你抢我夺的车流外缘道减速,顺辅道下,红绿灯前左转,就是向工业园去的路。
工业园前身是一个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 破产后土地变卖改造成工业园。高速公路上的车声在这条小路上也听得见,变成呼呼的风啸。路的一边是绿化藩篱,初种下去时还是灌木,也有人修剪,现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林里每次车开到这里,就把车窗摇下来,她喜欢海飘来的气味,阿伯塔松散发着金属气的松脂香,冬天是海的寒冷, 带着雪意和海腥的气味扑面而来。
路的另一边,是海, 一个原油港。
沿海湾一圈筑满了巨大的储油罐,铝合金的巨无霸是没有窗户的高楼大厦, 彼此的阴影像一群结伴成群的史前巨人。海面上的船是运油轮和机械修理船,除此以外是巨大的无垠的天空下同色的海水,没有旖旎。这段路比下面的海平面高了几米,十字路口不远处对海建了观景台, 其上可以停车,鸟瞰大海和礁石海滩。一条木栈道从观景台一头铺到海边, 临水的那端原来有个安全门,飓风桑迪袭击时,整个栈道连同观景台下的水泥支架都被时速一百三十英里的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五年后观景台和栈道修复,不知何故,栈道末端的安全门却没有修,也没有人去市政府建议,大家都视而不见,这个海滩是个“三不管”的地方。
那个空缺了门的栈道尽头,经常让林里看着不舒服,她尽量避免目光往那里看, 总觉得会有什么从那里一直走进海里去。
海边在低潮的时候露出嶙峋的礁石,礁石上密密麻麻吸附着像“淡菜”一样的有壳生物,贝壳锋利得像刀子,那里鲜有人行走,“淡菜”生得遍地都是,伴着野生的沙滩玫瑰。初来这里时,林里还曾经穿着鞋在海滩上流连,何曾想连沙滩都有碎贝壳掺在其中,等她觉得鞋中有异, 回到观景台上脱鞋细看,发现两只脚上的袜子都有不止一处破损,她细皮嫩肉的脚,在海滩上走了不过半小时,脚底就已经出现细小的血斑和伤口。等后来那里传出枪击案的新闻,林里就再也没有海边漫步的心情了
海的凶险,即使在风平浪静时都暗藏机锋,这是她这些年来亲身体会的经验,更何况还有老尹的事。
每天早上,“汤姆叔叔”都前来栈道上钓鱼,风雨无阻, 今天也不例外。今天观景台上多了一个穿深红色连帽卫衣的人,背影,不知道是男是女,林里经过时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两个人的背影都是穿GAP连帽衣,像同胞兄弟, 只不过汤姆叔叔比那人高出一个头。
“汤姆叔叔”是一个老人,退休后独自住在西黑文的福利楼里, 每天骑车来海边钓鱼。林里公司的同事大都知道他,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汤姆叔叔”, 来自经典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汤姆叔叔其实是康州土生土长的白人,当过兵,除了跟随美军驻扎过海外,他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州, 跟黑奴历史无搭。他的肤色,经海边多年的日晒雨淋已经变成深棕色,这是称他“汤姆叔叔”的唯一凭证。
下一个路口有一家幼儿园,路边插了“儿童玩耍,车辆减速”的交通标志。这是金牛上过的幼儿园, 那时她还在布里奇波特租房住,每天上班把金牛送进去,下午五点半再接出来, 如此五年,直到金牛从学前大班毕业。幼儿园是一幢独栋的木板楼,外墙漆成奶黄色,红色的屋顶上有一个装饰性的钟楼,上面插着这家全国连锁幼儿园的小旗子。每次看到幼儿园门前阻挡车辆行驶的白色木栅栏,林里的心里都觉得一丝安慰,像低潮时的海浪轻轻拍打栈桥下的礁石,规律,宁静。这家金牛从一岁起待了五年的幼儿园,是她的地标。
这周是儿子金牛上大学后第一天,林里的空巢生活正式开始。今年秋老虎凶猛,到了九月初太阳还是火辣辣的。路边的野莓枝子茂盛到几乎要伸到路上来,那些带细刺的枝条在空中划着弧线往前野蛮生长,争夺着阳光和空间。夏天的时候,午间她还会到这条路上来采红色的野莓吃。 摘了红莓后的枝子会留下一个黄色的蒂头。现在,新生的枝条把蒂头完全盖了下去,林里的目光落在路边立着的一个半米见方的黑板上,上面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坐拖拉机,摘南瓜, 前方右拐。” 旁边插着一个稻草人。
车开到小农场门口了。金牛小的时候,林里带着他不止来过一次。有一年万圣节的黄昏,母子俩周日无所事事来农场转转。那天田地里根本没有南瓜可摘,拖拉机和熬枫糖的摊子也收了。农场管理员认识她和金牛,不忍看到小兒失望,问金牛想不想挖土豆,免费的。管理员借给他们一大一小两把铁铲,让林里把车停在田边,熄了引擎, 把车的大灯打开对着田地,金牛就蹲在那两道狭窄的光里卖力地挖着,他吸溜着鼻子,在冰冷的黑土里饶有兴趣地撅啊刨啊,像在找复活节彩蛋。
十一月里天黑得早,车前灯外的田地已经黑黢黢的一片,临旁的田里原来种南瓜,收获后农场主用拖拉机把地翻耕过,残留的瓜叶被机器绞碎了当肥料埋进土里。黑色的土地在黄昏微暗的天光里像海上静默的波涛,连绵翻滚而来,地中间集中堆放几只卖剩下的大南瓜,半明半暗中看过去犹如一个平卧于水波上的人形,林里站在那里看到,吓了一跳,再细看不过是几个南瓜,但是她还是立刻叫金牛收工回家。 二人坐进车里,她把车的暖气打到最大一档,又拧开车上的无线电,让热闹的流行歌曲充满车里小小的空间,没想到就这一会儿她就冷得瑟瑟发抖了。
林里摇摇头,仿佛要在脑海中抛开那天田里所见的幻觉,她继续往前开,金牛此刻正在大学里上课呢。他宽肩的背影,卡其短裤下健美有力的双腿,是她出了波士顿大学的宿舍开车离开时,从车的后望镜里看到的一切。只那么一个片刻,他的身影就消失在进出宿舍楼的大学生当中,车后往镜里只剩下波士顿大学校园里那个标志性的钟楼, 跟学校书店卖的明信片一样。他们母子在楼外拥抱告别,林里的头只到儿子的胸口,她闻到他熨烫好的衬衫上“汰渍”洗衣粉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她曾经熟悉的体味,林里心里一惊,泪立刻盈眶,她咬咬牙,硬是不让眼泪流下来,一抱后转身就往自己的车方向走。
这是十几年来少数几次,林里在儿子的身上看到逝去的老尹的影子, 她忽然记起,老尹抱她的时候,她的头的高度也是将将抵到他的胸口。
老尹去世后,多年来林里习惯了单亲生活,从来都是单打独斗,她努力不去想老尹,渐渐也就不再记得。唯有在跟儿子告别的一刻,林里仿佛觉得他们一家三口又一次现身,好像冥冥之中, 亡者有灵……林里摇摇头打断脑海里的陈词滥调,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想它做什么用?!
她心里泛起歉疚和伤感的奇怪组合,随之又平静下去,林里瞥了一眼车的仪表盘,发现车的油箱那格已经亮红灯, 车需要加油了,下班回家路上要记得给车加油。她的车已经開进工业园区。
工业园中的大部分办公楼,像加长的汽车旅馆,林里所在公司的办公楼在离路最远的一角,她的办公室在楼的北面。这里的几幢办公楼原来是药物公司“辉瑞”实验楼,“辉瑞”搬离后把这些楼连同里面的设备卖给附近的耶鲁大学,耶鲁转租了一部分物业出去, 承租的小公司中包括林里打工做数据库管理的公司。
停车场上的车稀稀落落,从来就没有停满过,这里的好多办公室多年空置,招不来租客。她沿楼梯而上,走到自己的办公室,楼梯上的照明灯炮一闪一闪地鬼眨眼,需要更换但没有人管,康州的经济自从金融危机的破产潮开始一蹶不振,十年来并没有太大的起色。工业园的物业管理近年越来越衰,有人去楼空之感。
林里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拧亮灯,把空调板上的开关打开,除非夏天最热的几天,她一般只打开风扇那档。她拉开窗上的百叶窗,看一眼窗外的停车场以及停车场以外的天际, 然后坐下来, 打开电脑,电脑CPU 启动的嗡嗡声,像一个被唤醒的动物。二十一寸电脑屏幕亮起,那微蓝的光像人工霞光一样照耀进她的心田, 给她带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她是一个部门经理,林里觉得踏实。
在这个小公司混久了,林里在五年前也混到部门经理的位置,薪水十万有余, 年终经常有分红。对她这个单亲母亲来说,除了薪水满意,她还喜欢这里灵活机动的工作时间,不加班, 金牛学校有什么事,她随时可以请假离开。她的资历,她在公司的年份,让周围大部分同事即便不敬她,至少也保持友好态度。
坐定后不久,上司查理忽然敲门现身,他神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上门聊天八卦的。他简短地告诉她公司已经正式被收购,数据库管理部门最快在一个月之后就会被重组。查理是一个老实人,比林里年长几岁,高大的胖子,他眼睛里忧心忡忡不加掩饰,他宣布完这个消息以后, 双眉紧锁,停了几秒钟,给林里一些时间消化这个关乎生计的重大新闻,问:“你知道‘重组的意思吧?”
林里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重组”呢? 来这个公司打工之前,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互联网Startup, 在她拿薪水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01年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时,这家公司资产重组后解散。被一夜归零的除了她的工,还有她递交了半年的绿卡申请,她紧急需要找工作,也需要找公司帮她办身份,申请工作签证。
查理比她负担更重,他有一个前妻和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需要支付抚养费。查理垂头丧气,多说无益,只把身体转向窗户,目光转向窗外那些看了多少年也不能称为风景的风景,他的宽阔的双肩松垮着,肚子那块的衬衫往外凸出,好像一个篮球被切了一半,掖到他腹部的衬衫下面, 整个人的六尺之躯好像被一个无形的重量压住了,“哦查理,我们都会找到工作的。” 林里喃喃地说,说完她自己都觉得无力。林里伸手去握一握查理的手,很想给他一个拥抱,但他心事重重,站在那里没有反应。
这个共事多年的老板是一个老实的好人,一度老秘书琳达还挺想撮合他们俩,结果……结果他们约会了几次,一顿晚饭,晚饭后亲吻告白的一刻,彼此都停住没有向前一步。但那之后,他们之间多了一层看不见的亲密和信任。
查理说:“十点半公司全体人员开会,人事处会宣布具体的步骤。”说完他转脸看牢林里,眼神可怜巴巴,这么近距离里林里看清他松弛的眼睑下细细的纹路,查理这几年老得蛮快的。林里回答:“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面对了,反正大家都躲不过。”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林里说得铿锵有力,但查理好像没有得到什么鼓励,蔫蔫地离开。
办公室剩下林里一个人,她的恐慌感才一点一点蔓延出来,像慢慢涨高的潮水。她脑海里飞快地算一算丢掉工作后的财务账:靠失业保险那点钱吃饭不成问题,但金牛的学费呢?还有给金牛买新车贷款的钱呢?每个月还贷拿什么来支付?金牛上大学的近五万块学费才交掉, 她银行户头里只剩下一万多块钱了……明年的学费过半年就得交50%,万一一年半载找不到工作,她那点存款哪里挨得过去?好在她在诺瓦克的联排公寓没有按揭, 她省吃俭用, 再加上老尹过世后的一点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在几年前林里把房屋贷款全部还掉了……
林里盘算完财务,再次想到老尹,那时她还在读书,老尹的一份薪水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跟工作连带的还有医疗保险,还有工作带来那种“安居乐业”的心定。老尹下岗,这些安与乐都没有了,他该是多么慌啊……想到这里,她心里不能平静,她对老尹的感同身受迟来了几十年。想到这里,她坐不住了,她借着去厨房喝茶,想去找同事聊聊,她需要人群, 她怕自己一个人待着, 还是和大家一起去等十点半的公司会吧。
公司大会传达的意思,纽黑文这个地点的部门人员全部解散,遣散费按工龄计算,有一个标准公式……人事部的人清晰洪亮有条不紊地讲述,跟平时搞例行培训一个模样和腔调,林里心里的火腾就上来了, 她狠狠地瞪着人事部经理,好像要把满腔仇恨都发射出去,转念想,人事经理不也跟着大家一起下岗嘛!周围坐着的同事大都表情木然,林里泄气了,听天由命吧,美国的兼并潮连带着下岗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回到办公室,林里完全没有心思做正事,拿出手机想跟平时要好的几个朋友短信吐槽,或者等同事主动前来开口,但是大家各怀心事,无论手机上还是雅虎信箱都是一片安静。林里心神不宁地在电脑上翻看猎头网站的招工新闻。
这台电脑是一年前换的新电脑,每次更新,IT部门都帮她把个人文件档的文件全部拷贝下来,再拷贝进新电脑上,多年来积累了上百的文件。林里按日期翻找,其中居然有她进这个公司时的那份履历,还有一组旧照片,是用公司的扫描仪扫进电脑的。看了照片的日期后林里的手指跳过那组照片,她不想看,她知道,旧照片里有老尹的照片:金牛一岁生日,他们全家去海边拍照, 回来全家去西尔斯照相部拍全家福……
林里指尖跳过这些文件,转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那里存着她毕业文凭扫描照片、护照扫描照片、劳工卡复印件……旧日的文件,好像《圣诞歌谣》的“昨日之我”,一张张高清电子版地浮现出来。林里把目光转向电脑边的电子座钟,两个数字之间代表秒数的间隔号有规律地跳动着。时间和距离,林里想起那句俗语,它不停息地、安静平稳地拉开她和老尹的距离,这就是她这些年想要的,越远越好,越久越好。
但再久的时间,都不能让她忘记老尹没有给她留下只字片语就走了。“就连去超市买尿片他都会留下一张字条!他一直挺照顾人的,到哪里都记得留个信……” 这是那几年里林里反复说的话,在心里说,也对朋友,对家人说, 质问,抱怨,感叹。除了坐火车通勤去纽约上班或者面试工作,其实老尹很少到别的地方去,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坐在家里,坐着或者睡觉,林里推他,他才去院子里,也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出门唯一去的地方,就是海边……
想到海边,林里的心被搅动了一下。那个海在她的心里,是一个深渊。林里鼓起勇气打开了旧文件中的全家福照片。老尹的脸,在二十年后的现在,乍一看比林里都年轻,乌黑的头发,光洁饱满的额头,眼角没有皱纹。林里不敢多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抹悲哀,那是镜头前的标准笑容抹不去的。林里把目光聚在坐在他们之间的金牛身上,那个小小的人,胖脚丫勉强套进照相前新买的小皮鞋里,脸上憨憨地笑着,毛衣的领口里还露出忘记摘下的围兜的上角,在拍照的最后一刻被老尹注意到,连忙对摄影师叫停,他没有摘下围兜,而是把它掖进他的毛衣领口里。
这些细节,都没有忘记,林里无奈地叹口气……老尹的样子,记忆犹新的是他找工作去面试时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西装,上装的背部还看得出熨烫后隐约留下的折痕。他手里捏着一个夹履历的塑料文件夹,新西装的肩膀过大,老尹整个人像缩在一个壳里。林里一直记得,老尹脸上的表情,与其说严肃,不如说空洞,没有表情的空洞。林里记得她去拉老尹的手,鼓励他再接再厉,屡败屡战,结果他突然将身体往后一退,躲开林里伸过来的手,说我得快去赶火车,要迟到了,然后转身就走。
她如果当时不那么催着老尹找工作,而是像老尹希望的那样,在家里待个一年半载,做他一直想做的贸易网站,他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也就不至于走上绝路了?这个问题折磨了她二十年,此时又像幽魂一样冒了出来……
一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思前想后……全公司的人好像都心不在焉。熬到下班, 大家立刻取了包往外走,此时门外的天已经乌云密布,全然不是早上来时和风丽日的光景,零星的雨点已经开始往下落, 公司里的人都匆忙地道声再见,闷头去停车场驱车离开, 逃也似的,完全没有以往的说笑,林里心乱如麻。
回家的路比早上要堵,路上全是工业园里出来的车。林里的车在车流里走走停停,她不耐烦地打开了车窗,一股带着雨意的海风拂面而来,她深深地吸口气,发现海风里尽是汽车尾气的化学味道,不得不再次把车窗摇上去。
好不容易到了观景台那里,上高速的辅道已经排了长队,林里心想不是经济不景气嘛,上下班时间路怎么还堵成这样呢?她无奈地把车开上观景台边的停车处,她想对着海站一会儿,透口气。汤姆叔叔已经收起鱼竿,正蹲在地上, 面前铺了一张旧报纸,他拿瑞士军刀把一天钓到的鱼开膛破肚, 把鱼头和鱼内脏切下来,扔进海里去。一群海鸥在他头顶盘旋着,尖锐地叫着,等着他朝海里扔鱼肠。他一抬手,海鸥们就朝海里猛地扎下去抢食,一旦抢到一块儿就拼命囫囵地咽下去,没有抢到的海鸥跟吞咽的鸟争夺那鸟嘴上露出的鱼,几十只海鸟此起彼伏,飞起落下,互相扑打争夺时羽毛落下来,落在汤姆叔叔的身上、头发上,看上去跟下雪一样。
穿连帽卫衣的人还在那里,正在沿着栈道,往海的那边走,林里看到他的侧影,果然是一个亚洲人,海边的风很劲, 吹下连衣帽,露出他的亚洲人特有的硬质的黑头发, 头发乱糟糟的。林里疑惑地看了这人一眼,觉得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汤姆叔叔在叫她。
“林,你想分几条鱼回家吗?马鲛鱼,挺好的,都清理干净了……” 他说,指着那个装鱼的塑料箱,见林里朝他走近,继续絮叨:“我这里有旧报纸,给你包两条带回去,拿盐和橄榄油腌一腌, 撒点罗勒,在烤箱上烤一刻钟,挺好的……” 林里点头谢了, 站在汤姆叔叔身边等他取鱼出来,他蹲下身打开鱼箱, 一股海鱼特有的腥味儿随风飘过来,鱼箱里堆满冰块, 没有头的鱼一条条码得整整齐齐,铺在冰块上面,马鲛鱼的肚皮闪着钢蓝色的光,林里看着很开心,多好的鱼啊!她再次道谢。
“起风了,起风的时候真是激动人心!” 汤姆叔叔取了两条大的鱼,拿报纸包好。
“是啊,佛罗里达来的热带暴风雨呢,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几场大雨。” 林里说。
“大雨好!大雨前钓鱼特别容易,今天是大丰收呢!” 汤姆叔叔站直身子,环顾周围的海,接着说:“下完大雨就是秋天了。你看看这一会儿浪多大啊,这么快,潮就起来了……” 林里喜欢他的声音,男低音,带着好听的共鸣声, 加上他的口音,听着很亲切,好像听老人在说故事, “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个外号不是白起的。汤姆高且胖,站直身体的时候,娇小玲珑的林里就得仰视他,他像一头和蔼的大象。
林里接过鱼,汤姆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们俩一起转向海的方向,海浪像被一架架無形的推土机推动着,一波高过一波地朝岸边滚过来,砸在岩石上,水花被风吹着落在他们身上。观景台建在海边岩石上, 飓风桑迪来时曾经被大浪拍打得散架,现在这座是重建的。天上乌云密布,林里环顾四周,发现刚才那么多只海鸥现在却一只都没有了。
对着一波一波咆哮冲来的海浪,林里不由得伤感,开始跟老爷子慢慢说起今天公司重组的新闻。公司重组,看着工业园死样的颓相,在此地找工不大可能,新工作肯定是在别地儿,甚至在别的州,这就意味着她得搬家,这个地方以后肯定少来了。
说着说着,林里忍不住哭了:“我刚刚替儿子交了大一的学费,就出这种事?!老天就跟我开这种玩笑!” 她的委屈,在大象的身边,已经不需要再掩饰了,汤姆叔叔沉默地听着,用粗糙的手抚平林里的背心,然后想起来,急忙把手缩回来,说抱歉,林,你的衬衫上都给抹上鱼腥味儿了……你现在整个人闻着都像马鲛鱼……
说完他嘿嘿地笑起来,林里愣住,然后也跟着笑,他们笑作一团,这时,雨下起来。
热带暴雨排山倒海从天而降,仅几秒钟工夫,林里的衬衫长裤就湿了,衬衫上的马鲛鱼气味随着她的体温散发出来。
林里跟汤姆叔叔冲刺一样回到她的本田房车里,只这么一会儿已经是落汤鸡般,连她的头发上都滴着水。汤姆坐在副座上,气喘如牛,林里连滚带爬地坐进驾驶座上,探身去取车后座上的毛巾,说先躲一躲吧,这雨下猫下狗一样……
她拿了毛巾,转身递给汤姆叔叔一条,一边猛擦着自己头脸上的雨水。汤姆并没有接过毛巾, 他甚至没有注意车里的动静,他正把身体往前探, 全神贯注地盯着车窗外的海,然后腾地跳了起来,嘴里咒骂一句,猛地推开车门就冲了出去,连车门都来不及关上。
那一侧打开的车门刮进风和雨,再次淋了林里一头一脸。汤姆叔叔直直地朝观景台跑去,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他像一只巨大的海鸥,一只仰脸向人吼叫的海鸥,一双手臂像翅膀一样张开,指着海的方向,语无伦次,林里根本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只见他双目圆睁,嘴里不停地喊help, help。
林里不情愿地推开车门,海风猛烈地推搡她,她几乎被掀倒。只听到汤姆叔叔在喊,hurry,hurry!快!救人啊!林,电话!那个人在海里……说着他大幅度用手臂指着海的方向,然后又往海边冲过去。
他们冲到栈道上,往下看,发现已经涨潮了,栈道对着海的最后一级台阶,已经被正在升起的海浪淹没,白色的浪冲过来,又退回去,像一支军队。林里终于在浪里辨出那个穿深红色连帽卫衣的人,他的一头黑发被海水中深绿色的水草缠着,像海豹的头,这时海浪冲过来,他又消失了。林里间断听到海里传来呼救的声音,不是汤姆的声音,是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普通话夹着英文,这声音从海涛声里传过来,间断着,微不可闻, 像是受静电干扰的电波。
穿红色卫衣的人在水里挣扎,栈道尽头的海水并不深,他努力想从水里站起来,回到栈道上,但是他每次站起来,涨起的海潮就冲过来,狠狠把他摁倒。
林里不敢走下栈道,她站在那里呆住,汤姆已经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那个栈道像一条摇摇晃晃的绳子,在风里和潮水里吱吱嘎嘎地响着每一个木头接口。
汤姆弯腰曲背地走着,在狂风吹打下,一个趔趄滑倒, 几乎一头栽进海水,他挣扎着想爬起来,风带着浪压着他,一波一波涨潮的浪打在他背上,要坚持把他也带进海里。汤姆四肢着地趴在那里,整个人好像在拥抱着栈道,他抬头对上面的林里喊: 打911电话啊,911,有人落水啦!快打电话!
林里惊在那里, 不敢往海边靠近一步, 她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拨打911那三个数字。紧急求护的接线员的声音立刻响起: 请问出了什么事?…… 你们在哪里?……我们马上赶到。林里气喘吁吁,带着哭腔回答着,语无伦次,但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已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911电话打完,这时汤姆叔叔从栈桥上站了起来,他浑身的衣服湿透,贴在身上,凸出他的大肚皮和下面细瘦的罗圈腿,像一个卡通画里的小丑。他没有回到岸上,反而扶着栈道的栏杆再次朝海面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对海里的人喊:你坚持住,救援马上就到达,你坚持住,hang on,you hang on……
林里知道这北方的海水有多冷,即使在初秋,海水里的寒气也会在人落进去的一刻,变成一把把微小锋利的刀子,千刀万剐人的全身,那种痉挛,被称为冷震……
老尹,老尹就是这样死的, 不是吗?潮涨的时候,他跳了下去。最后一刻的老尹跟现在海里这个人,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人看到, 没有一个汤姆叔叔跳起来冲到栈桥上大喊救命,老尹的呼救声只被风接收了,朝大西洋的深处走去, 那时林里不在岸上,不在他身边……林里想到这里心都绞痛了。
老尹,对不起,我没有能救你,我甚至没有想过要说句温柔的话宽慰你。在生存压力下我跟你一样焦虑,但焦虑没有让我抑郁,让我变成一个无情往前冲刺的野兽,我光顾着催促你找工作,我看你坐在家里发呆,我骂你懒, 我从来没想到你的心已经病入膏肓。老尹,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我那时太年轻了我不懂啊,你比我脆弱多了……
林里哭了,她终于明白,她一直想躲开又躲不开,想忘记又不能忘记的歉疚和自责,是老尹和她之间最后的纽带,这么多年它像一场持久的暗恋陪伴着她。现在,连这个苦涩的歉疚都是那么美好,好像嵌进肉里的沙子最后变成了珍珠, 这是老尹冥冥中带她走过的必经之路。
林里不再害怕,她往栈道上迈开步子。虽然冷得浑身直打哆嗦,林里使尽全身力气对着海的方向喊着,help is on the way,help is coming, 来了,救援来了……如注的暴雨鞭子一樣抽打着她的脸,但是她还是一遍一遍喊着,给自己壮胆,直到海上再次传来微弱的声音。
这是一个多么平凡又多么不可知的世界,水里和岸上的这三个人,在这一刻,都想活下去。
【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