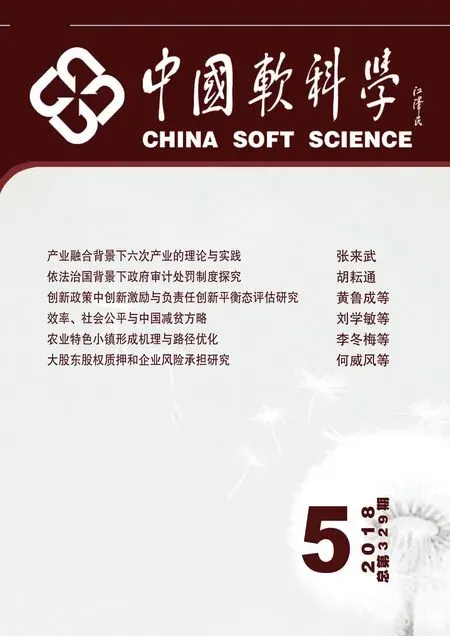效率、社会公平与中国减贫方略
2018-06-22刘学敏张生玲
刘学敏,张生玲,王 诺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效率、社会公平与中国减贫方略
刘学敏,张生玲,王 诺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中国的减贫为全球反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尤其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方略更是减贫方式的创新和升华。在减贫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又遇到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如一些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扶贫效率递减以及绝对补贴对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损害等。因此,应把贫困作为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经济问题和收入问题,把精准扶贫工作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通过多目标推进来解决减贫工作中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冲突。
关键词:减贫方略;精准扶贫;效率;社会公平;体制改革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贫困人口在2020年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在这个背景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无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主题词,它不仅为全国上下高度重视,也为全球所高度关注。近年来,笔者一直参与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以及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中国减贫方略以及社会公平、效率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中国减贫实践与扶贫方式的创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大规模的减贫。到了90年代,《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的发布,开启了制定扶贫计划的先河。经过近4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顺利脱贫,实现了温饱和小康生活,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反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减贫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两份文件,成为引领中国扶贫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纲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人降至2015年的8.36亿人,中国在其中的贡献率超过70%。在国际上,定义为贫困家庭,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其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1]。但不论对贫困做出怎样的定义,最终还是要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这便是贫困线。在中国,2008年国家把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称扶贫标准,初步定为年人均收入1067元,此后又多次上调。到2011年,参考国际人均每天1.9美元的标准,把扶贫标准提升至2300元(按照2010年不变价),比2009年提高了92%。以后又根据物价指数和生活费用进行调整。2016年为3026元,2017年为3200元。
然而,中国的减贫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精神,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2007-2009年三年的人均县域GDP、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基本依据,考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别是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滇川甘青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7年11月,国家又提出“三区三州”(西藏自治区、滇川甘青四省藏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这里是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区域。
针对中国的减贫实际和过去“大水漫灌”的低效率,习近平于2013年11月在湖南省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提出了扶贫“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不断提高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这是首次对于精准扶贫方略的阐释。此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便成为国家减贫工作的指针。在执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方略下,通过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来提高帮扶的效率,通过“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使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由此,中国的扶贫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即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输血”到“造血”,注重脱贫成效;在扶贫资源的使用上,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在考评方式上,主要考核脱贫成效,实施了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尤其是在考核评估中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即引入由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组织机构,就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独立实施外部评价,这是一项重要的体制机制创新。对于申请退出的贫困县,第三方评估主要评估检查4项指标(所谓三“率”一“度”),分别是:“综合贫困发生率”,它必须低于2%(西部地区低于3%);“脱贫人口错退率”,它必须低于2%;“贫困人口漏评率”,它必须低于2%;“群众认可度”,它必须高于90%。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退出。2017年,通过招投标程序,笔者主持了重庆市万州区、黔江区、武隆区、丰都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5个申请退出贫困县(区)的第三方评估检查工作。是年11月国家宣布,全国共有包括河南省兰考县、江西省井冈山市、重庆市万州区等在内的28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这是自1986年国家设定贫困县31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意义非常重大。
在实践中,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每个地方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探索扶贫开发模式,涌现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服水土、接地气的优秀范例,切实发挥了典型示范引领的作用;探索了许多扶贫工作方法,尤其是改变了过去那种“撒胡椒面”的方式,把扶贫资金支持企业,企业扶持农户,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方式,使扶贫资金资本化和永续利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涌现出一个庞大的帮扶带头人、能人队伍,他们业务过硬、能吃苦、肯受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减贫事业,特别值得尊敬。
二、精准扶贫中的效率与社会公平
从理论上讲,减贫过程和扶贫本身就是在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基础上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是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总体上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党的十九大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基于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要求的反映。所以,减贫过程也是社会公平的一种体现,是社会基本矛盾转变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一种方式。
作为减贫方式的一种升华和新时代创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相对于过去“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实现了更大限度的社会公平,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它根据农村贫困家庭的实际致贫原因,精准地实现“点对点”、“一对一”的帮扶,做到了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广大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确实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红利。借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大势,广大农村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会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小康社会。从宏观层面看,这是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的体现。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工作层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仍然存在着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是既损害效率又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
首先,市场经济为所有人创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个人一个平等致富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原则,使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优先使用效率高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参差不齐,一般而言,效率更高的劳动力更容易获得工作岗位并获得高收入,因而他们会更早地远离贫困。反过来看,尽管在现实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是多维的,或因病、或因灾、或因学、或因缺生产要素和资金等,但贫困户所以贫穷,多是因为劳动力质量不高,市场经济“天然”地排斥着他们。在大自然和大市场面前,贫困人群始终是“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2]。从实际调研结果看,许多贫困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大体在50%-70%之间,而且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能够长期务工的成员,就能基本保障稳定脱贫。反过来,遗留下来的贫困户,大多社会参与程度低,保护自我的能力缺失,一些人即使在本地也不受待见。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更弱”[3]。现实的情况是,每个贫困户都是“个案”,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握不住市场机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下激烈的竞争环境。基于此,很多地方为了吸引贫困人口就业,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政府安置一些涉农企业在投资时往往附加了让其优先雇用贫困户的条件,同时政府也给予企业以种种优惠。这样,本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有效雇用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却为了扶贫的公平而使用效率低的劳动力,损害了经济效率。至于说,“贫困者一旦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力军,自主地去解决人口、文盲、发展等致贫问题,自觉地为过上更健康美好的生活而奋斗”[4],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愿望,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其次,减贫效率具有递减倾向。搭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快车,人们的收入水平迅速增长,贫困人口迅速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国家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使更多的人远离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通过更多的机会和有效刺激,使他们“点石成金”[5]。但是,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留下来的贫困人口结构非常复杂,他们贫困程度深,尤其是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使扶贫的边际收益在递减,而边际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图1所示),因而中国的扶贫真正到了攻坚克难、啃硬骨头阶段。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一个二维空间中,横轴为贫困人口减少的量Q(离原点越远,表明贫困人口减少的越多,脱贫成效越好),纵轴表示减贫收益R和减贫成本C。设MR为减贫的边际收益曲线,它具有递减的倾向;设MC为减贫的边际成本曲线,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单位减贫成本是递增的。设MR和MC在E点相交,达到均衡,社会的贫困人口数量为Q0,它对应着某一个贫困发生率(它是贫困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率,以此反映地区贫困的广度),这时为了追求社会公平而进行的减贫是最有效率的。假使社会贫困人口减少的量为Q1,且Q1Q0,它对应一个较高的贫困发生率,这时减贫的收益大于成本,应该继续加大减贫力度,扩大社会公平,直至Q0;同样,假使社会减少贫困人口的量为Q2,且Q2Q0,它对应一个较低的贫困发生率,则这时减贫的成本会大于收益。
如果社会政治哲学是为了彻底消除贫困,如“在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则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贫困发生率为零。附带说明的是,在实际操作时,按照中央文件[6],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姑且不论2%(或3%)按照何种标准确定下来,单就中部地区2%而西部地区3%的确定本身就有些武断。因为有些贫困片区如武陵山区等自然环境几乎一致且犬牙交错在一起,却被分割成西部和中部,又如吕梁山片区的山西(13个连片贫困县)和陕西(7个连片贫困县)沿黄河两岸仅一河之隔、自然条件几乎一致,标准要求却不同等。如果贫困发生率2%(或3%)恰在Q0点上,则这时的减贫是最有效率的。在图2中(它是图1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设横轴为贫困人口减少的量Q(与图1中横轴一致),纵轴表示贫困发生率P。图中N点P=100%,表明这时整个社会处于极度贫困状态;M点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时贫困发生率P=0。图中贫困发生率P0对应的Q0也是图1中的Q0,是贫困人口减少的均衡数量。

图1 减贫成本收益示意图 图2 贫困发生率与减贫人口数量关系示意图
如果这个Q0所对应的贫困发生率恰是2%(或3%),说明国家确定的脱贫摘帽标准是最有效率的。当然,由于人们有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这是马克思所讲的“天然特权”[7],因而劳动能力强的、适应市场的人就会率先脱贫,而那些剩下的不能适应市场、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只能依靠社会“兜底”,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最后,绝对的收入补贴既不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也会损害经济效率。其实,在一个特定农村,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往往不会很大。一般来说,收入分布会呈现出“橄榄球状”即“中间大、两头小”的形式,因而在精准识别中,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从调研结果看,由于很多人都集中在国家确定的贫困线上下,线下的农户(他们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将获得国家的各种帮扶和福利,享受很多国家帮扶政策,而线上的农户(非建档立卡农户)却不能得到,由此而造成非贫困户与贫困户的矛盾;即使是在贫困户之间,他们因实际获得的多寡不同也存在着各种矛盾。这种矛盾还延伸为一些人认为这是因干部“不公平”造成的结果,进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此外,从结果上看,确定的贫困村兑现了各种帮扶政策,其帮扶工作力度、攻坚氛围、帮扶派驻力量、获得的各种帮扶资源、扶贫推动方式以及政策落实力度都更大些,而非贫困村的发展诸如基础设施等反倒不如贫困村(所谓的“贫困村吃撑了,非贫困村却饿的不得了”),形成一种“倒挂”现象和新的发展不平衡。从实际调研中发现,当前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矛盾、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矛盾以及贫困户相互之间的矛盾。设有两个农户A和B,在初始状态下起点一致。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起始状态大体一致。农户A起早摸黑,勤劳致富,积累了财富,盖起了新房;反观农户B,因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而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住房通风漏气,没有保障。为此,农户B变成了贫困户,享受各种政府补贴和帮扶政策,而农户A却什么也得不到,由此造成了不公平。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医院还给贫困户开通了“先诊疗后付费”通道,要求各个医疗机构设立“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贫困人口在乡镇医院住院只缴纳门诊费100元,其余基本医疗费用新农合全额支付;在县域内、市级、省级住院,个人年度自付封顶额分别为1000元、3000元、6000元。更有甚者,贫困户看病还有专车接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反观非贫困户却不能享受相关政策,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由此造成了农户B对农户A的示范效应,似乎勤劳的人矮人一等,而“贫困户永远有理”,出现“我是穷人我怕谁”、“我不劳动,共产党也不会让饿死”的不良心态,有些贫困户甚至被国家的好政策养得“浑身不舒服”。这样,既打击了积极干活的勤劳人,出现“养懒汉”现象,还恶化了邻里关系。在现实中,一些贫困户没有脱贫意愿,成为“永远无法叫醒的装睡的人”。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贫穷和无能高度相关,无能可以导致贫穷,贫穷也可以导致无能。“贫穷会腐蚀人的耐心”[8]。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绝对的补贴不仅损害效率,而且在追求社会公平的时候,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公平。
三、以体制改革促进效率和社会公平
基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考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过程中,跨越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就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首先,解决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社会公平和效率问题,必须多目标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本身不是精准扶贫造成的,而是由于单项推进而相关领域没有相应跟进造成的。譬如,从实际调研的数据看,农户的致贫原因中,约有30%-60%是因病致贫,这些家庭中往往因有一个长期卧床不起的成员的拖累而无法摆脱当前的贫困状态。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措施,确保农村贫困人口住院总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对少数农村特困人口、重特大疾病晚期患者给予特殊帮扶。但是,在广大贫困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贫困家庭脆弱,其他非贫困家庭也很脆弱,他们同样也经不起重大疾病的困扰,一个家庭一旦其某个成员患有重大疾病就会很快进入贫困群体。进而言之,即使是城市的一般收入者也经不起大病的困扰。因此,如果能够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制,则不仅可以解决贫困户的脱贫问题和有效防止他们返贫,也可以解决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而且从可能性上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积累的社会财富使国家完全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同样,通过把农村发展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结合起来,实施振兴农村战略,充分发挥农村的功能,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充分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则就可以解决一系列农村的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贫困问题,就可以根除当下的一些致贫原因(如因学致贫)等。因此,要拓展对于贫困的认知,贫困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在中国也是改革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精准扶贫讲究“精准”二字,每一个农户都是“个案”,其贫困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应关注由此造成的巨额行政成本。由此看来,在既有体制下推进精准扶贫政策,就可能导致效率递减和损害社会公平,还可能使原有体制固化,而只有通过具有“普惠制”性质的改革,才能降低扶贫成本,在有效减少贫困人口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和提高效率。就是说,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是最终解决农村发展和“拔穷根”的利器。
其次,把贫困作为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经济问题和收入问题,才能找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平与效率矛盾的途径和方法。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贫困是个社会问题,要“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9]。在当今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中,都把贫困户当作帮扶的客体,精准扶贫的主体仍然游离于客体(贫困户)之外,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在帮扶贫困户,贫困户仅仅是被帮扶的对象,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贫困户没有脱贫意愿,甚至出现“我脱不了贫你就脱不了干系”的“绑架”干部的行为和心态,把自己的脱贫完全寄希望于政府帮扶,犹如诸葛亮之于阿斗,从而这些人在整个脱贫攻坚中起了很坏的示范效应,既损害效率也危害社会公平。把贫困者仅仅作为被帮扶的对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缺乏脱贫的可持续性,一旦这种“运动式”扶贫结束后,非常容易返贫。所以,在精准扶贫中要注重扶贫同扶志相结合,诚如习近平所说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10]。尽管在精准扶贫中,我们坚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有按劳分配原则,就是每个劳动者应分配的个人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它要求,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劳动,凭劳动获得个人消费资料。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的人则无权领取个人消费资料。正如毛泽东在深刻洞悉中国农民落后的一面后明确指出的那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1]。而“教育农民”首先必须“认识农民”,要把物质条件改善与精神状态改变结合起来,创新帮扶方式方法,从整体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入手,倡导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通过生活质量的提升、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让贫困户在良好的环境氛围下萌生新希望,催生他们的奋斗精神。
最后,把精准扶贫工作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精准扶贫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它通过“歼灭战”和精准施策的方式,使在一个时间段内彻底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然而,它在追求整个社会实现公平的同时,在具体实施中也产生不公平和牺牲效率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把精准扶贫工作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由于贫困人口仅仅是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在贫困县其贫困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一部分,这样,扶贫工作也仅仅是农村工作的一部分(如图3所示)。
某地方政府提出,“一切工作都为脱贫攻坚服务,一切资源都向脱贫攻坚聚集”,把脱贫攻坚当成农村工作的全部,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人们把关注点都放在一个“点”上,都在“精准”二字上做文章——这当然也是国家考核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做到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的制度设计下,省级领导干部及省级部门都有帮扶贫困县脱贫的任务,县及以下的基层干部更是全力以赴,不仅自己的工作岗位是全力帮助贫困户脱贫,而且还有几户甚至十几户的“结对”帮扶任务,他们根本无暇其他工作。这也就造成一个错觉,似乎精准扶贫便是农村工作的全部。如前所言,扶贫工作仅仅是农村工作的一部分,仅仅是可持续发展关注的一个侧面。如果把所有精力和重点都放在扶贫上,就会一叶障目,就会冲淡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工作。由此看来,只有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振兴中国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繁荣提供巨大的动能,让农村焕发蓬勃生机,才能不仅使贫困人口脱贫稳定、持续脱贫,还使所有农村人口都享受到发展成果,才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公平问题。另一方面,要把精准扶贫与改革结合起来。在既有的体制下,精准扶贫工作可以解决短期目标,很多情况下也只能是解决一些面上问题,但却使原来一些问题固化,这就需要通过改革,通过对于旧有的体制和做法或者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而解决由此产生的和长期累积的矛盾。须知,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也是最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体制改革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城市化对于农村发展的冲击问题,使广大农业劳动者也享受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改革而振兴乡村,而不是停留在矫情的所谓“乡愁”上;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使农民能够有恒产从而真正地爱惜土地;通过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保护农业、保护耕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政府更多介入一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的过度介入;通过改革生态经济体制,基于目前14个贫困片区大多位于生态功能区的实际,完善流域上下游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切实能够通过保护生态获得收益;等等。所以,解决好农村的脱贫问题,处理好社会公平和效率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关系问题,而根本解决贫困问题,拔掉穷根,还是要通过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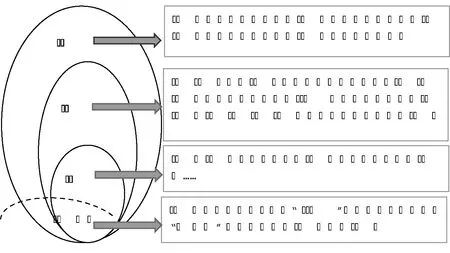
图3 精准扶贫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4-38.
[2][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27.
[3][印]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
[4]虞崇胜,余 扬.“扶”与“脱”的分野: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的战略转换[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1):41-48.
[5][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N].2016-04-28.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4/28/content_5068878.htm.
[7][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8][美]塞得希尔·穆来纳森,坎尔德·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困与忙碌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61-66。
[9][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
[10]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EB/OL].2015: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11/28/c_1117292150.htm.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Efficiency,EquityandPovertyAlleviationStrategiesinChina
LIU Xue-min,ZHANG Sheng-ling,WANG Nuo
(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have vastly contributed to the global anti-poverty endeavor. Through persever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China has developed a characteristic pathwa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innovative and essential strategies, notably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However, hardly c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dodge the issues of economic inefficiency and social inequity such as inadaptability to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and the economic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sts of subsidy. Consequently, poverty issue should be addressed as a comprehensive social issue rather than an issue of merely economic growth or welfare distribution. Therefore, a well-rounded approach concerning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s critical in reducing poverty. Thu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gions and China’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ation will provide a proper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in the war against poverty.
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social equity; reformation of institution
中图分类号:F323.8
A
1005-0566(2018)05-0049-07
收稿日期:2018-02-05
2018-04-08
作者简介:刘学敏(1963-),男,山西襄汾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资源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本文责编:王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