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故乡流落他方
2018-06-12郑远涛
郑远涛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张爱玲写成《小团圆》时在书信上如是告诉好友。加埃尔·法伊的小说处女作《小小国》运用的正是他最深知的素材—童年往事。一九九四年非洲东部国家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殃及邻国布隆迪,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兼叙事者—混血男孩加布里耶(昵称加布)大约十二岁,跟作者本人当时的年龄相仿。动乱不安中,加布和妹妹被送上救援法国侨民的飞机,与留在布隆迪的父母天各一方。无论加布的故事有多大成分属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战乱体验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堪回首的,然而《小小国》不是一本残酷的书,它克制地书写战乱,笔调里常常充满了乡愁与怀恋。
故事开始时,加布十岁,和父母、妹妹一起过着有花园、汽车和仆役的优渥生活。同一条街上还住着几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他们一起偷芒果、跟帮派小头目打架,以为自己在街区里割据一方。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孩子,这是一段伊甸园般的童年。
但是布隆迪当然并非天堂,它遍地穷苦,更有族群对立的政治现状,危机四伏。加布的妈妈伊冯娜本来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小儿子的心目中,她“就像侧影优美的淡水芦苇,身材纤细挺拔……还有乌木一般的黑皮肤和安科莱母牛一样的大眼睛”。一九六三年伊冯娜四岁时为了躲开大屠杀而离开祖国,从此与卢旺达近在咫尺,远若天涯。自从嫁给了法国建筑承包商米歇尔,她便梦想远走欧洲,如此方能得到一份安全感。丈夫却希望留在布隆迪继续做生意,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在这里,我们是有特权的人。回到那里(指欧洲),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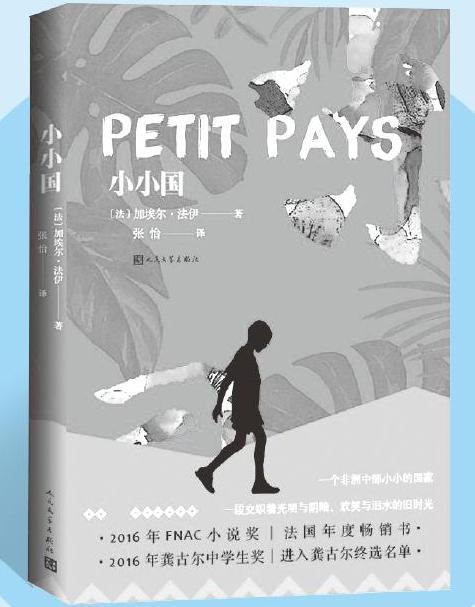
《小小国》 [法]加埃尔·法伊著 张 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加埃尔·法伊在叙事技巧上采用了双重视角,加布的儿童视角自不在话下,细读作品,还能发现一种成年人追忆童年的视角,对父母双方的困境作了公正的评述,使这对异国伴侣的关系具有了某种人类普遍性。故事发展下去,米歇尔、伊冯娜的跨文化婚姻由于双方缺乏共同的生活愿景而爭吵不断,终以分居收场。其实,他们俩都是流落他方的失根者。米歇尔出身法国山村,成年后选择了在布隆迪的特权与安逸,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回到祖国立足渐渐丧失信心。伊冯娜有家(卢旺达)不能归,对政局的败坏若有预感,不甘就此在布隆迪永久安家。然而在残酷的时代面前,个人的计划实在不堪一击,米歇尔和伊冯娜的希望最后都落空了。社会动荡如山雨欲来,加布被小伙伴带去夜间酒馆喝一杯,他在喧哗中听见这么一种议论:“我们生活在一片悲剧的土地上。非洲大陆的形状像把手枪。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就让我们开枪吧。”局势果然很快便急转直下。
妈妈伊冯娜,也许是本书塑造得最复杂多面的一个形象。当太外婆给小加布讲卢旺达传统故事时,妈妈并不赞成这种传承文化的用心,在她眼里,加布和妹妹都是“白人小孩,只是肤色略深而已”,但读者心领神会,这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卢旺达屠杀初起,伊冯娜身为被针对的族群—图西族人,勇敢地回到卢旺达援救亲属,过程中目睹了凶残的杀戮,心灵受创,失去理智。加布的四个年轻的表亲被暴民杀死在家里,尸体三个月无人收埋。妈妈将他们埋葬以后,客厅的水泥地上依然留着擦不掉的几个斑点,是死人躺过的地方,“永远地嵌在水泥地上,嵌在石头里”。伊冯娜像着了魔似的反复对两个亲生孩子讲述她经历的恐怖,我不禁联想到一个反例: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进了集中营的犹太父亲依然千方百计哄骗小儿子,让儿子相信那里的一切全是某种有趣的游戏—在伊冯娜身上,恐惧的本能盖过了护犊的情感,这一点极有力地刻画出她的创伤之深。同样,伊冯娜在疯狂与激愤中辱骂丈夫和小儿子,将过去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归咎于自家男性,说他们俩是杀人凶手,这描写不但增加了这女性角色自身的深度,也反映出标签化思维方式对人的毒害如何超乎想象。一家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两族!
人心惶惶的日子里,加布从邻家夫人的藏书中找到自己灵魂的藏身之所。“人们已经接受了自己随时随地会死。死亡……拥有了日常生活最平庸的面貌。”乱世中岂有安全的避风港,当社会困于族群特征被撕裂为你死我活的对立阵营,加布的小伙伴们也模仿成年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街区”而杀人。最后同辈用压力迫使加布就范,放弃中立,参与了仇杀。在《小小国》里,如果说父母分居是加布童年伊甸园中的第一道裂缝,那么杀人事件则意味着这个乐园化为了废墟。布隆迪最终变成加布和妹妹不得不逃离的人间地狱。后来,布隆迪的战乱持续了十五年,然而加布却由始至终“没有一天不想起那个国度”。哪怕这个栗色皮肤的混血男子早已定居法国,工作安稳,他毕竟并不像他妈妈从前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般的“白人孩子”。人乃是记忆的动物,加布怀着故园之梦流落在巴黎。尽管布隆迪早已物非人亦非,那里毕竟给过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小说尾声,加布为了继承旧时邻家夫人的藏书而返回布隆迪,童年小伙伴大都已流散海外,昔日街区也变了模样,不过再次印证了故乡与童年的双生关系。虽然谁也无法挽留时间的脚步,拥有过美好童年的人是幸福的,因为那种记忆永远可以是我们面对人世波澜的力量之泉。
译者张怡在《小小国》前言中指出小说的谋篇布局仍有青涩的痕迹。在我看来,主要问题在于它穿插式(episodic)的叙事结构不时露出拼合的斧痕,作品尚缺乏浑成的气魄。译者强调《小小国》作为历史见证和生活记录的价值。当然,一部作品自可从不同角度欣赏。加埃尔·法伊生于斯长于斯,下笔寥寥数语便点染出热带生活的声与色。种种孩童视角的观察,经过翻译后依然保有原文不失天真的语调。请看作者写全家过境扎伊尔,道路上眼见的景象:“聒噪的大鹅全身脏兮兮……一群山羊排成一串……一对对母女仿佛玩障碍滑雪似的,在一辆紧挨一辆的货车和小巴士车队间穿行,偷偷摸摸地卖着粗盐浸的水煮蛋和袋装辣花生……乞丐双腿扭曲,乞求路人行行好,施舍个几百万……昏昏欲睡的士兵在锈迹斑斑的岗亭里,有气无力地挥舞着苍蝇拍……路面上坑坑洼洼,仿佛一个个巨大的火山口……”又如描写一个坐困危城的酷热傍晚:“传来蝙蝠成群飞过的声响……它们打算去坦噶尼喀湖畔的番木瓜树上度过一个饕餮之夜。”活灵活现,令人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