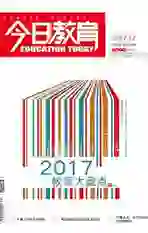“为了上学,我不得不中断我的教育”
2018-06-05刘猛
刘猛
正如药物不等于健康,床位不等于睡眠,房子不等于家一样,学校也不等于教育。有微信好友给我发来标题这句萧伯纳说的话,并说它挺有意思的,但又说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正好我最近阅读了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英汉双语版,2017版,本文部分引文后面加括号注明页码的,皆出自此书),感觉要说明萧伯纳这句话所蕴含的意思,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了伊利奇。伊利奇用一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现代学校制度何以常常扼杀了“真正的教育”?
认真算来,这其实是我与伊利奇的第二次相遇,而第一次相遇则是十五年前在南京师大读博期间。那时,我师从本书的译者吴康宁教授,曾有机会从同门学兄那里得到导师翻译的当时名为《非学校化社会》(台湾桂冠版,1992)复印本一册。只见复印本封面左侧空白处竖行写着:“仅此一本,请归还。吴康宁”。犹记当时我的阅读状态是想读却读不进:一方面疑惑这本名声如雷贯耳的书不能同时出简体版,是不是犯了什么禁忌,从而有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之窃喜;另一方面,“相逢难相识”的不少繁体字也着实让人苦恼,以至于读起来也只能是连蒙带猜,不时叹为天书。
不过,现在想来当时读不太懂这册书的原因除了印刷字体之外,主要的恐怕还是本人的社会学想象力匮乏,就是说自己所积累的中国社会与教育经验还不足以与伊利奇这本书中所呈现的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与教育经验发生勾连,因而难以产生多少共通之处。当然,“饱汉不知饿汉饥”,那时作为“饿汉”的我,也幸亏没读懂伊利奇这本书,否则要是我信了他的学说,并付之于决绝的超前行动——不“去”“学校”(南师大)读博,那么从中等学校教师的位置“下岗(准备)再就业”的我就难以获得如今的高校教师“社会身份”。换句话说,在伊利奇渴望的能“除去(de-)”“学校(化)(schooled)”的“自由社会(society)”到来之前,我只能“再三细思量,宁愿不‘自由”地“先去(go)”高等“学校”接受“教育”,以改变自己不利的“社会处境”。
一
学校控制着文凭的发放,相应地也就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层级的划分。这是伊利奇书中所着力批判的社会现实。伊利奇认为,这种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学是教的结果”这样一种根本的价值观(或信念)。以此价值观为基石,适合于学习的学龄儿童、胜任教儿童学习的教师及设计好的学习内容(课程),学校制度的三大核心部件(即“学校现象学”)就被现代社会建构了出来。为使学校制度更好地运行(或曰“科学化”),一些配套的仪式必须不断地改善。如,学的结果能够准确测量,而没法测量到的人的体验则被归为“次要的、不安全的”;课程逐步变成“一捆商品”,方便师生之间的销售与消费;学校要能激发学生的消费需求,就必须根据扩展课时计划,不断包装和升级教学内容等等。
这一切合理吗?根本不合理!伊利奇的回答干脆利落。伊利奇认为,从根本上说,现代学校之所以得以存在并日益壮大的价值基石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学习是他人操控越少越好的一种活动。大部分的学并不是教的产物,而是不受束缚地参与到富有意义的情境之中的结果。大多数人都是在身心‘投入时学得最好,但学校则要人们把自己的人格与认知的发展看成学校精心计划与操控的结果。”(48页)伊利奇以为,工业时代的学校制度或系统,比较切合于消费社会,它承诺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带来的“预期”,尤其是较好就业的预期,以便求学者将来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但这种预期每每落空,特别是对贫困阶层的家庭子女。受制于已有的文化、语言、求知欲、父母的兴趣等因素,家庭较穷的孩子根本无法同富有阶层子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整个社会一旦接受了学校可以支配的神话,社会资源就会很“合理”地流向学校,从而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教育資源利用效率反而大为降低。伊利奇以当时北美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学校财政增加的实际效果为例,发现其与预期总是出入很大。
如何改变?去学校化,迎接一个自由社会的到来!这是伊利奇这本书的标题所明示的。放在人类思想史上来看,伊利奇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对工业化社会之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之书。学校、军队、医院等现代社会主要组织的制度弊端,都是其要探讨的对象,而学校则是伊利奇选择来进行批评的更为突出的“典型”而已。如把健康托付给医院、将和平托付给军队一样,人们一旦迷信于“教育是由教育者支配的制度化过程的结果”,学习就会变成被迫顺从于外界要求的义务,而不是个体天然具有的可以自主的权利。而真正的教育,就是使学习者恢复自由学习的权利,使学习“一定不能起始于‘某些人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而应起始于‘学习者为了学习想要接触的人和事的问题”(90页),要构建适合于这种真正教育的新制度,必须有四种相关的教育资源以供学习者利用:教育物品查询服务(机器、实物、人工制品是学习的基本资源)、技能交换(技能演示者是唯一的人力资源)、伙伴选配(方便于选择学习伙伴的联系网络)及专业教育者(既有实践智慧,又乐意帮助新人进行教育探索的人)。
二
正如弗拉纳根评说的那样,“伊利奇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质量,而在于他对教育机构自以为是的确定性提出挑战和给予打击的效果”。由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与教育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我们现在要思考中国当下的教育问题,伊利奇这本书可算适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资源。一本书是不是真正的好书,其实就看它能不能唤起阅读者自身的经验,产生共鸣。阅读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的过程中,我头脑里不时地想到:
上世纪末,身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的我曾与一群农村小学校长座谈,其中一位校长说出了他的一个长期难解的情结:“为什么成绩好、后来考上好的中学甚至大学的孩子,离开农村留到城里,日后见面对我们却大多比较冷淡;而常被我们训斥批评的孩子,虽然没有考上好学校,留在了农村(务农),却对我们客客气气。”
十多年前,我的一位侄子初中毕业没能考上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又不愿去,就去了苏南打工。一次我看到他的《初三毕业留言册》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说真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而值得怀念的就是我们初三(5)班这帮好兄弟和小姐妹,将来我肯定会想你们的!”
2003年,北大学子(陆步轩)卖猪肉一事成了持续的热点新闻。而近几年,关于北大毕业生则又流传这样的“段子”:“一对北大毕业的年轻父母拜问禅师:‘如果买不起北京的学区房,应该怎么办?禅师回曰:‘如果北大毕业生都买不起房,那还买学区房做啥?”
记得当时我帮校长分析可能的原因是:“成绩好的孩子认为,他成绩好主要是自己刻苦学习的结果,而不是教师教的结果;成绩不好的孩子,感到教师苦口婆心地帮自己,却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因此总会有些愧对。”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虽与伊利奇此书中的想法相去不算太远,但他说得更为明确,“诚然,在某些情况下,教确实可能有助于某些类型的学。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之外获得他们的大部分知识的。……即使是目的性最强的学习,大多也并非有计划的教学的结果。”(18页)
“对学校而言,最糟糕的状况是它仅仅把全班学生聚集到同一间教室,并以同样的流程对所有学生进行教学。……学校确实向学生提供了摆脱家庭束缚与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向儿童灌输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应当从与自己一起被分在同一个学习群体中的那些人中选择朋友。”(105页)按伊利奇的看法,我的那位侄子所受的学校教育恐怕正是“最糟糕”的一种,而且“注定”了他那几年所能交往的同龄伙伴大多也只能仅限同一个班级的同学而已。
“学校已成为现代无产者的一种世界宗教,它凭空许诺要拯救技术时代的穷人。民族国家通过学校来实施教育,驱使所有国民都循序渐进地学习与拾级而上的各种文凭相对应的课程,这同昔日的成人仪式及僧侣晋升并无二致。”(16页)当你听到有关北大毕业生的故事和段子时,想到伊利奇近五十年前早就有过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有点相见恨晚?!
三
这本书让人读了非常过瘾,是与中文翻译者吴康宁教授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导师22年后重译这本小册子“巨著”,所下的工夫既可以从全篇清通的译文看得出来,又可从其为帮助读者尽可能准确理解伊利奇本书思想精心而写的万言之多“译者导读”与“译后记”看得出来,还可从近180条累计足有2万多字的页下“译者注”看得出来。
当然,本着“爱吾师,更爱真理”之教导,笔者在此愿斗胆指出译文的三处不足:
1.英文“作者序”的最后一句有括号补充字词,即“(schole)”,导师中文翻译时漏译了。它是英文词school(学校)的希腊和拉丁语源,原义为“闲暇”,说明古代“学校”与人的自由、“闲暇”紧密相关,而不似现代“学校”,常常让人有些“窒息感”。这与书中第六章所讲的最重要的建设性观点(即“真正的师徒关系”,“对教师而言总是一种享受,且对教师以及他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休闲方式。”114页)是彼此“照应”的。难处在于此处译成“闲暇”,中文便显重复,应保留括号中的原英文,另加一中文注释说明为宜。
2.关于“卡内基委员会”的名称运用及评论。导师在译文中有两条注释提及,一是第六章开头(85页)的页下注认为,原文有误,“应为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或卡内基基金会”。笔者以为,难下结论,原因有二:一是网上可以查证,英文文献确有“卡内基委员会”的提法;二是导师也没能提供伊利奇所引用那份“报告”出处的更准确信息,因而无法肯定其“有误”,还是暂不下结论为妥。二是第七章后部分(129页)的注释“边际价值”时又提及“伊利奇对于概念的使用有时比较随意”,并以上述“卡内基委员会”为例。笔者以为,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判断,“比较随意”之说恐难成立。笔者这样看,主要因为伊利奇此书讨论的是如此严肃的话题,并且在其序言中也提及有“数十位参与者提出了建议或批评”(4页),看名单,这“数十位”大多也是西方一流的学者(如彼得·伯格),他又怎么能“比较随意”得了!
3.个别地方的译文似有日后改进的必要。如第10页中间有“只有停止……提供财源,才能阻止其产生让穷人无能为力的副作用并因此而导致穷人更贫穷”一句,后半句显得板滞拗口,较难理解,是否可改為:“导致穷人更贫穷的制度副作用(即让其无能为力)才能被阻止”。另外,本人近年粗研了“小学”(即文字学)和繁体字,又有机会对照了一下繁、简中文本和英文本,发现个别之处的翻译,简体本反而不如繁体本准确。如繁体本的“导论”(即简体本“作者序”)中有这样两句:一是“改变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也罢,增加(the proliferation)教育的硬体或软体(hardware or software)也罢……都无济于事”;二是“古德曼的意见最为尖锐,他促使(obliged)我修正(revise)了自己的观点”。这两句简体本中的改善之处是将“硬体或软体”变成现今内地习惯的“硬件或软件”,“促使”变成“迫使”更贴切了一点,但将“增加”改为“添置”,将“修正”改为“改变”,这两处则反而不如原来贴切了。
上面的体会与意见妥当与否,当容商榷,但笔者之意是面对这一内地简体版的双语读本,吴老师的翻译只是方便我们抵达伊利奇思想堂奥的桥梁,而要真正把握伊利奇此书的精髓,就必须能穿越于英汉两种文本之间,并不断与阅读者个体的“己身经验”和所属的“群体经验”相关联,以在“学习网络”中“寻求个人惊奇”(83页)为目的,这或许才是以伊利奇所倡导的自由学习理念来学习伊利奇著作的最为合适的方式。
说到这里,有必要补充的是,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位微信好友,是一位远在北京的网络书店老板。我追问他萧伯纳之言的出处,几天后他进一步查证后告诉我,那句话他记得并不准确,是马尔克斯自传作品《活着是为了讲述》中插入引用的。所在一节的原文是:“去年,我在萧伯纳的鼓舞下从大学辍学(他说:‘很小的时候,我不得不中断教育,去学校上学。),妄想无师自通,靠新闻和文学为生。我无法和任何人争辩,隐隐觉得,我的理由只能说服我自己。”马尔克斯所说的“去年”是1949年,30年后的1980年,中国一位“第一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肄业”的部队作家第一次买了中文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了前面两页就觉得,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怎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他就是后来自称“与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才“终于可以离开他了,同时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的莫言。有不少人相信,如果马尔克斯当初坚持上完了大学,他就不太可能取得后来的文学成就,同样,也有许多人相信,要是莫言能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他的语言才华与想象力可能早就被磨灭了。两位作家的成长故事与人们的这些想法,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伊利奇对现代学校制度激烈批判的背后,是对人的个体生命之尊严、趣味及自我选择权等方面的珍爱。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