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北朝供养人画像浅析
2018-05-29赵世金马振颖
□赵世金 马振颖
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是天水地区较大的一座佛教石窟组群,由四座中小型石窟寺组成,分别是拉梢寺石窟、水帘洞石窟、千佛洞石窟、显圣池石窟,这四座中小型石窟寺均匀地分布于鲁班峡峡谷之中,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色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美妙的画卷。这座石窟寺的内容主要以摩崖悬塑和壁画为主,内容非常丰富,佛教造像有大小百余尊,壁画700余平方米,碑刻题铭十八通,石胎泥塑舍利塔十二座[1]5。由于这座佛教石窟寺的开凿从北朝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石窟的开凿与绘制几乎没有间断过,所以对于研究古代天水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宗教信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水帘洞石窟群中,保存了大量的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以及壁画,其中壁画中有许多供养人画像和题记,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资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宗教、社会文化都提供了许多非常有效的信息。
一、水帘洞石窟群所见供养人画像总录
供养人画像是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土佛教石窟中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于供养人画像研究成果颇多,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考察,都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供养人即出资开窟塑像画壁画的功德主,洞窟完成之后,功德主的形象一一被画在洞窟里,表现他们对佛陀的恭敬虔诚和藏在心里的善良愿望。他们与石窟的关系是互相依存,没有功德主就没有石窟……”[2]113。正是这种重要的作用,所以供养人画像在佛教石窟寺中的地位一直被提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在水帘洞石窟群中也有大量的北朝时期供养人画像,尤其是在其子窟水帘洞石窟与千佛洞石窟壁画中,出现了很多供养人形象,这些供养人都活动于古代天水地区,其社会地位、民族成分亦有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这样就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代天水地区的民族、宗教、社会等问题。
(一)水帘洞石窟中的供养人画像
水帘洞石窟为水帘洞石窟群中的一个单元,位于拉梢寺对面不足500米的莲花峰下,石窟坐西向东,为一个大型的天然洞穴,长约50米、高30米、深20余米。水帘洞石窟群的艺术构造多以壁画与浮塑为主,均为佛教题材,现存壁画136平方米,将其编号为16个。
1.水帘洞2号,位于洞穴中部,崖面敷泥彩绘壁画,高5.5米、宽8米左右。画面的正中绘有一佛二菩萨造型,主佛的足下绘一长颈圆腹宝瓶,其下绘莲台。宝瓶的上方,主佛莲台下方两侧三身男供养人,其中第一身为比丘,身着袈裟,下着裙,手持莲花,第二、三身供养人头戴笼冠,身着圆领窄袖胡服,腰系带,下穿宽裤,足穿圆口鞋,手持莲蕾,虔诚向佛而立。与众不同的是三身供养人均绘有圆形头光 (图1)。原每身供养人头侧均有墨书题名“比丘蕴化供养佛时”,右侧二、三身供养人分别墨书题名为“南安郡丞都□魏洪标供养佛时”、“□□□西县吕运供养佛时”。画面左侧自上而下又绘男女供养人8排,每排人数不等,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或10人以上,现存70身,均侧身向佛而立,自上至下。
第1排:绘比丘,身旁均有墨书题名,现大多仅留痕迹,可辨认者有“比丘须□□□”、“沙弥□□□□”、“比丘□□□□”。
第2—3排:绘男供养人,均着斜领交叉的宽袖长襦,其身旁的墨书题名已经难以辨认。
第4排:绘比丘尼,均着袈裟,身旁墨书能辨认者有“沙弥尼僧晖供养”。
第5—7排:均绘男供养人,戴冠,着圆领窄袖胡服,身旁墨书题记可辨认者有“佛弟子□□□□□□□”、 “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南安郡……”、“杜行供养佛时”等。
第8排:绘女供养人均着“V”形宽领上装,下着长裙,旁有墨书题名,大多数已不能辨认,可识者有“清信女王真供养佛时”、“□□供□□□□”、“清信女王女妙□供养”。

图1 水帘洞2号供养人
这幅组图在水帘洞石窟群中组合有序,内容也相当丰富,涵盖了飞天、佛说法图、供养人、宝瓶、菩提树、菩萨、弟子、力士、熏炉等多种造型,其布局严密,构造思想独特,虽然有后代重修的一些痕迹,但是总体上来说仍然保持了北朝时期原绘的色彩与风貌。
2.水帘洞4号,为一幅说法图的右半部分,主尊佛仅存腿部及狮子座。菩萨束发髻,戴三珠宝冠,余发从耳后下垂至肩部用系带相束。袒露上身,戴连珠纹项圈,下着长裙,身体呈“S”形,跣足立于莲台上。说法图中右胁侍菩萨身后绘两排供养弟子像,上下各两身,均着双领下垂袈裟,足穿云头履,拱手向佛而立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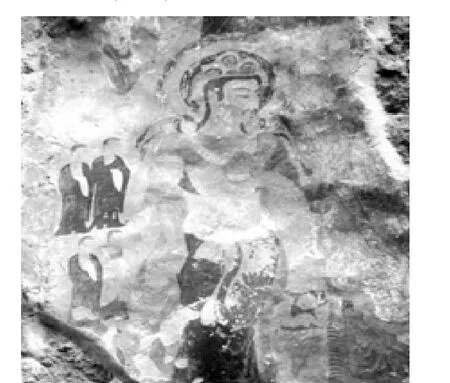
图2 水帘洞4号供养人
3.水帘洞6号,为一摩崖浮塑圆拱形尖楣浅龛,龛两侧泥塑半圆形龛柱,龛内绘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龛外下方为原绘壁画,正中绘一熏炉,其两侧下方各绘一狮,熏炉右侧上方绘一辆单牛拉车 (图3),牛车后方分上下两排绘供养人像,上排供养人已模糊不清,下排五身供养人均系女性。每身供养人旁均有墨书题名,现仅存三身墨书题名,依次为“比丘尼清□/供养佛时”、“□□□□□/供养佛时”、“清信女焦□□/供养佛时”。熏炉之左侧上下亦各绘一排供养人,均系男性,前为比丘,已模糊不清,上排后三身男供养人旁墨书题名,分别为“佛弟子焦阿帛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祥/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善/供养佛时”,其后还有“侍人□□□/□□□□”、“佛”、“佛弟子□□□/供养佛时”。下排供养人旁分别墨书题名为“比丘□□/供养佛时”、 “佛弟子梁□□/供养佛时”、 “佛弟子梁令超/供养佛时”、“佛弟子梁畅/供养佛时”、“佛弟子梁阿罗/供养佛时”、“佛弟子梁阿男/供养佛时”、“佛弟子梁景延/供养佛时”。

图3 水帘洞6号 (供养人所乘牛车)
这座窟龛保存相对较为完整,在石窟中出现了大量的供养人以及榜题,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活跃于秦州地区的梁、焦二姓两个家族的功德窟,壁画由于在后代长期的烟熏导致有一些模糊。
4.水帘洞7号,原绘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像,佛座下左右各绘男女供养人一排。右侧女供养人四身,均方平发髻,外披圆领式长袍,领前结带垂至胸际,下着长裙。左侧男供养人存三身,第一身为比丘,身着袈裟,其余二身男供养人均着圆领窄袖胡服,男女供养人顶部均绘伞盖 (图4)。

图4 水帘洞7号
5.水帘洞11号,崖面上绘有一佛四胁侍菩萨像。佛像为低平肉髻,面形方圆,着圆领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双手举于胸前作禅定印。佛两侧为胁侍,均为世俗装。右侧第一身为女供养人,无发髻,上着“V”形领宽袖长袍,下着裙,足穿云头履,拱手向佛,立于莲台之上,圆形头光,榜题“佛弟子权之女供养”;其身后绘一着圆领窄袖上衣,下穿窄裙,双手举于胸前侧身而立的侍男,圆形头光,榜题“佛弟子权□□供养”。左侧第一身为女性,上着圆领窄袖胡服,腰束带,下着长裙,云头履,向佛拱手虔诚而立,圆形头光,榜题“佛弟子□□□供养”(图5)。

图5 水帘洞11号
佛说法图外下方左右,又各绘一排女供养人像。右侧女供养人现存二身,高髻,上着“V”形领宽袖长袍,下着裙;其中第一身榜题“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左侧女供养人存四身,着圆领窄袖衫,下着裙。
这幅组图保存比较完整,为北朝原作,从题记中可以看出这座窟龛是权氏与莫折氏的功德窟。
(二)拉梢寺供养人画像
拉梢寺的主体窟区开凿于莲苞峰南壁一处高60米、宽约60米的崖面上。现存大小窟龛24个,各类造像33身,覆钵塔7座,壁画365平方米,摩崖题记一方。
1.拉梢寺摩崖题记,位于拉梢寺崖面8号龛下方,开凿一个横长方形摩崖浅龛,龛高1.54米、宽2.25米、进深0.2米。龛内正壁阴刻摩崖题记,魏碑体,共12行,每行9字,每字规格为0.1米×0.1米,共103字。具体如下 (图6):

图6 拉梢寺尉迟迥摩崖题记
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释道□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佛一区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
虽然在拉梢寺石窟中并没有其最大的功德主——尉迟迥的画像,但是这方题记提供给我们许多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座石窟寺的开凿背景以及尉迟迥的一些具体情况。从造像题记就可以看出,这尊造像的题记模式与佐藤智水的第一种造像模式保持一致,没有多大变化。这短短的一百字左右的碑文却为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明确地提出拉梢寺石窟的开创时间以及开创人物等明证以及造像祈愿等。从题记中可以看出拉梢寺摩崖大佛的创建者是当时北周贵族尉迟迥和当地的一个法名为释道□的比丘,拉稍寺的创建的时间是大周明皇帝三年 (559),也就是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在这一时期,北周佛教承袭北魏余韵,发展相对比较快。特别是西魏时期,宇文泰掌握最高权力,对于佛教大力支持,所以西魏北周初期佛教发展一直较为迅速。这一时期北周政权不是特别稳定,而且处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前,佛教的发展并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相对迅速,在麦积山、须弥山、北石窟寺等寺院中都有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
2.拉梢寺11号,为摩崖悬塑,崖面塑一立佛二胁侍菩萨。在左侧胁侍菩萨身光右侧绘有一排坐佛,在坐佛的下方,残存三身供养人画像,均着红色袍服,除了头部及胸部尚可辨认外,其余造型仅存残迹。
根据尉迟迥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座石窟开凿于北周武成元年 (559)。但是从现存壁画以及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座石窟寺在北朝以后的历代王朝中都有过重修,尤其是宋元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但是这座石窟所保存的供养人画像相对较少。
(三)千佛洞石窟供养人画像
千佛洞石窟又名千佛崖、七佛沟石窟,位于拉梢寺石窟西北约一公里的一个天然洞穴内。洞穴南北两崖壁分层开龛造像,北壁造像现已残毁,南壁上下分七层开龛造像,现存摩崖塑像、龛像、壁画等。
1.千佛洞11号窟龛,为摩崖敷泥壁画,在凹凸不平的崖面上绘制,壁画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中部绘两绿色草庐;下部绘数排人物像,均绘出背影,似为武士形象,戎装,戴红色或绿色头盔,肩披绿色铠甲,身着红色战袍,手执武器,下层数排供养人,着圆领窄袖服。
2.千佛洞16号,为平面长方形尖拱浅龛。龛内原塑一菩萨及二胁侍菩萨像。龛基绘供养人像三排,可辨认者为第一排左侧四身女供养人,着橘红色圆领结带长裙,裙带飘于胸前。
3.千佛洞36号,为北周时期所绘制,一共有供养人八身,没边四身相对而立,各手持绿色长茎莲蕾。其中每边为首一身高于其他三身,应为导引僧尼。左侧为男性供养人,穿红色圆领窄袖束腰长袍,右侧为女性供养人,最后一身着V形领广袖服饰 (图7)。

图7 千佛洞36号供养人画像
4.千佛洞44号,摩崖敷泥壁画,崖面上 绘一佛二弟子像,保存比较清晰。在弟子两侧有供养人,前各有一比丘引导。左侧可见七身供养人:第一身比丘穿黄色双领下垂袈裟,榜题为“比丘□□供养时”;第二身男供养人,着黄色圆领长袍,头顶有华盖,榜题“大都督姚□□供养时”;第三身男供养人,穿红色圆领紧袖衣,手执细长柄、黄色华盖;再后三身均着黄色圆领紧袖衣;第七身供养人,着黄色衣裙,榜题为“□□□□供养时”。右侧现存四身供养人:第一身比丘,与左侧同;第二身着红色衣;第三身着黄色衣裙;第四身着红色圆领衫 (图8)。
(三)显圣池供养人画像
显圣池位于通往水帘洞石窟的峡谷公路左侧,距水帘洞文管所约1.5公里,系一天然的“凹”形岩洞,略呈等腰三角形,高约8米、宽约10米。现存造像多以壁画为主,壁画面积大约90平米,将其分为13部分,以隋代开凿为主,线条多以绿色绘制,由于长期受潮等原因,壁画脱色、漫漶等现象特别突出。
1.显圣池5号壁画,画面四周原绘有十字形花卉组成的边框,现多已残毁。正中绘一身交脚菩萨,左、右各绘一身胁侍菩萨,均绘有圆形头光。在交脚菩萨肩部两侧各绘一弟子像,右侧菩萨下方绘五身女供养人,女供养人头部模糊不清,上着交领宽袖长袍,下着曳地长裙,面向菩萨而立。
2.显圣池5号壁画,壁面绘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右侧弟子下方绘有一排女供养人,现存二身。
3.显圣池9号壁画,壁面原绘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菩萨两侧绘有两排供养人,上方绘飞天。左侧为男性供养人,均着圆领窄袖长袍,现存四身。右侧为女性供养人,现存五身。
显圣池石窟的内容以布局在断崖上的壁画为主。从残留的壁画中可以看出,佛的头光大多为圆形,分为若干层光圈。服饰线条勾勒得较为明显,与隋代榆林窟第39窟中的儒童本生人物服饰、造型都比较相似。特别是壁画中的造像具有一些南朝的风格,可能是由于在文帝发兵平定南方陈朝之后,大量地搜罗南方的书画,导致南北文化融合加剧。隋文帝平陈之后,在东都建立了“宝迹”、“妙楷”二台,珍藏于南朝陈所获的八百余卷书画作品另外在显圣池石窟中有一铺隋代一佛二菩萨雕塑造像,但是残损严重,已经不能辨别其面目。隋代时期造像破坏比较严重,据笔者猜测,主要是在隋代中后期秦州、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灾害,导致水帘洞石窟造像的破坏。
二、水帘洞供养人画像所反映北朝秦、渭等地的民族成分
从上文我们即可以看出在北朝时期水帘洞石窟群与权氏、焦氏、梁氏、莫折氏、姚氏等几个家族有关,甚至有其专门的供养窟,那么这些家族在此地一定具有很强的势力。尤其是在这座石窟中,这些供养人画像都略带一些胡风,在衣着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学者对于这些供养人身份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多为活跃于古代秦、渭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大姓[3]。那么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讨论。
1.权氏
水帘洞11号窟龛有大量的权氏题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第11窟龛为权氏家族的功德窟,供养人画像多上着圆领窄袖胡服,而且这座石窟中的造像以一佛四菩萨为主,菩萨着世俗装,从榜题我们可以看出佛的胁侍就是权姓供养人,并且成为供养菩萨,可见其地位比较崇高。在古代天水、平凉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权姓供养人碑铭或者题记,与本文联系,我们可以对这个家族有新的了解。现存甘肃省博物馆《权旱郎造像碑》为西魏大统十二年 (546)造,高181厘米、宽67厘米,碑文中有供养人共计25身。权旱郎造像碑是典型的家族发愿功德碑,从其供养人的姓氏中可以看出权氏与吕、王等姓氏有姻亲关系。[4]54另外,最早发现于甘肃秦安,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权道奴造像碑》其功德主为“荡难殿中二将军都督渭州南安郡守阳开国伯权道奴”。另外在《王文超造像碑》、《王令猥造像碑》、《宇文建崇造像碑》、《诸邑子石铭》等都有权氏的存在,且这些造像碑的建造时间都集中在546—574年之间,与武山水帘洞石窟群中的权氏时间上基本一致。
根据敦煌出土文书S.2052号《新集天下望姓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权氏为天水郡所出二十姓之一[5]210。在西秦时期,休官首领权干城曾担任东秦州刺史、北周名将权景宜、唐代名臣权德舆均出自于权氏家族,是秦陇一带的望族。至于水帘洞石窟群中的权氏是否是氐族,尚未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因为“居于天水境内的权氏,为商周武帝后裔。商高宗武丁封子元于权国 (今湖北宜昌市当阳县东南),后以国为姓,称为权氏。战国末期,权姓子孙迁于天水一带定居繁衍”[6]73-74。所以权氏居于天水历史相当久远,我们尚且不能根据其供养人画像和榜题来确定其为氐族。
2.梁氏、焦氏、姚氏
在水帘洞石窟群中亦有梁氏、焦氏题记,也有其家族功德窟。
梁氏是西羌比较重要的一支大姓,在魏晋南北朝的陇西、天水等地,在敦煌文献中,梁姓乃泾州所出八姓之一。这种姓氏也是较为常见的,例如前秦时期苻生的皇后就为梁氏。另外在史料中有梁希、梁安、梁平老、梁楞等记载,尤其是梁安、梁楞等担任前秦时期的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在前秦政权中地位比较高,而这些人物均属于陇西羌,与苻氏政权关系异常密切。所以水帘洞石窟群中的梁氏题记有可能为羌族一支。
焦氏与梁氏一样,在古代秦州以及周围地区也有非常强大的势力,焦氏在天水南安、武山等地势力极为强大,其中焦遗、焦度等都为南安人。《资治通鉴》载曰:“西秦王乾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后。世子炽磐为太子,仍命炽磐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以屋引破光为河州刺史,镇枹罕以南安焦遗为太子太师参军国大谋。”[7]3620-3621又曰: “秦卫将军吉毗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广结引还,内安诸羌万余人叛秦,奏推安南将军督八州诸军事、广宁太守为主,遗不从,乃劫遗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7]3825从文中可以看出焦遗在南安羌人中地位较高。另外,又《南史》中记载: “焦度,字文绩,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难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杨难当,度父明与千余家随居襄阳,乃立天水郡略阳县以居之。”[8]1152所以焦氏在南安等地的羌、氐等少数民族中地位比较高,焦氏、梁氏均为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姓,他们对于水帘洞佛教石窟的修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姚姓是秦州羌族豪门,十六国后秦即是秦州姚氏建立的羌族政权。姚兴时期对于佛教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曾要求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经,在其推动下,后秦境内奉佛者十室而九,位于秦州地区的水帘洞石窟群自然也受到其影响。
3.莫折氏
在水帘洞石窟群第11号说法图中,右侧的一身女供养人画像旁有“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的墨书题记。由榜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古代秦州地区有莫折氏的存在。莫折,本为关西复姓。在《元和姓纂》中记载:“莫折,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在《西秦录》中记载,莫折姓氏的有西安太守莫折幼春、尚书郎莫折阿胡等。据魏文斌先生的研究认为,大约在两汉之际,莫折氏即内迁,居住于今天的陇西、天水、武山、甘谷等地[1]145。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莫折羌活动也较为频繁,比较重要的有莫折大提、莫折念生等人领导的关陇起义,震动了北魏朝廷:
(正光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9]150
这次起义最终被北魏朝廷重兵镇压。在大统二年的时候,莫折后炽又举兵造反,在原州、庆州等地举行起义:
大统二年,宁自梁归阙,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久之,迁车骑将军、行泾州事。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民,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10]466
这两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都受到当时朝廷与地方官吏的残酷围剿,所以对于莫折羌打击较为严重。在北周时期的水帘洞石窟群发现的这方题记,证明了在当时的秦州地区,莫折氏仍然大量存在,并且也与汉人一样,对于佛教较为推崇,虽然经过屡次起义,莫折羌也遭受到中央朝廷的严厉打击,但是从这些碑记中可以看出莫折氏在秦州等地还具有一定的势力。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水帘洞石窟群的开凿从北周持续到了明清时期,信众的范围涵盖了古代天水很多地区,是一座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信奉的佛教窟龛。北朝时期,水帘洞石窟群已经开始开凿,其中现存最大的摩崖造像的开创者就是秦州刺史尉迟迥,他是鲜卑族人。而在水帘洞与千佛洞等石窟中发现了姚氏、梁氏、焦氏、权氏、莫折氏等供养人的题记,说明在北周时期,武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姓占居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当时水帘洞石窟群开凿的重要功德主和供养人,在水帘洞石窟群中有他们专门供养的窟龛。后来吐蕃入侵,控制了这一地区。宋元时期,武山地区又是比较重要的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出现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说明在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已经走出河湟,在古代的秦州地区有了传播。吐蕃、党项、蒙古等许多民族都在此地生存,因此在武山水帘洞石窟群中的供养人服饰有少数民族的风格。
三、水帘洞石窟群中的供养人的特点及其具体情况
在水帘洞石窟群中现存北朝时期的供养人亦有数百身,从其外形、衣着服饰、车马坐具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一)水帘洞石窟群中供养人画像的基本特征
水帘洞石窟群目前发现数百身供养人画像,当然原绘作品远远高于这个数目。但是我们从供养人画像中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千人一面”,也就是说这些供养人具有非常多的共性特征。我们知道,在北朝时期,这座石窟中存在大量的少数民族特征,尤其是石窟的功德主有很多是少数民族,但是我们却很难发现其具有典型的胡风特征。这种情况似乎与敦煌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保持一致,“通过前人研究归纳,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具有雷同的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就目前刊布的敦煌石窟供养人像图版来看,都表现出这一特征”[11]10。郑炳林先生对于敦煌石窟中供养人画像及其共性与个性有着非常精辟的分析,思路比较独特,他认为“千人一面的现象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去注意:一种是家窟……这些石窟因为具有个人或者家族的性质,绘制的供养人主要是家族成员,因为血缘关系而相貌接近,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还有些石窟是一个社、一个寺院或者归义军政府开凿的石窟,绘制出的供养人相貌接近”[11]11-12。
我们详细观察水帘洞石窟群中的供养人画像特征,也会发现在各个家族窟中,供养人的特征基本保持一致,这可能与郑炳林先生的分析具有相通之处。例如水帘洞2号、水帘洞4号窟都有这种表现,说明在北朝时期,家族窟龛中的供养人画像基本保持一致的模式,共性特征远远大于个性特征。但是正如前文所析,北朝时期这些窟龛多为少数民族家族窟,为什么却很难发现其少数民族风格。主要是由于秦州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所以民族交融相对于其他地区则表现得更为成熟,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服饰以及外貌特征上来说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另外,我们应该将这种原因归之于审美特征的一致性上,在佛教石窟中,佛教造像无疑具有主导地位。佛像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区别于常人的最主要的特征,那么作为石窟的功德主——供养人画像也会与佛像的基本特征交织在一起,形成非常完美的外形特征,这样既有利于供养人对于其形象的接受,也有利于技师对于供养人画像的绘制。在水帘洞石窟群中,供养人画像也是较为完美,供养人身材高大,较为苗条,面部表情比较和谐,服饰也相对比较华丽。
(二)供养人的个体身份
在水帘洞石窟群供养人中,虽然存在“千人一面”这种共同特征,但是仍然具有许多不同因子,究其个体身份而言,有沙弥、沙弥尼、南安郡丞、佛弟子、清信女、比丘、比丘尼、僧人、大都督、秦州总管等。这说明北朝时期的水帘洞石窟群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石窟寺,无论身份、地位高低,都可以成为这座石窟寺的信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北朝时期秦州地区佛教信仰比较普及,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对佛教比较虔诚。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北朝时期秦州地区长期战乱,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也非常担忧,于是将其归之于佛教信仰,以信仰佛教而获取平安。
在水帘洞石窟群供养人画像中,我们根据供养人的排位顺序和装束也可以判定其地位的高低。例如“大都督姚□□礼佛图”,在《水帘洞石窟群》编为44号,图中绘佛说法,以及比丘、大都督姚□□等供养人。从供养人画像中我们就可以明确知道大都督姚□□。这一画像的主尊为一佛二菩萨造型,在菩萨的左右两侧都有一排供养人。左侧依次排列一位比丘六位供养人,前方第一人为比丘,身穿黄色双领下垂袈裟,双手笼于袖中,前有榜题“比丘□□供养时”;第二身供养人头裹巾帻,眉目模糊,上唇、下巴、两腮皆有胡须,穿黄色圆领长袍,腰系蹀躞带,前有题记“大都督姚□□供养时”;第三身供养人头扎巾帻,身穿酱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革带,为前面的供养人大都督撑起伞盖,伞柄细长,伞面是很清浅的明黄色,垂饰銮铃。从这些供养人的特征以及顺序来看,都是围绕大都督姚□□,体现出此人地位的高大。
在佛教石窟艺术中,供养人的地位也可以用其他工具进行衬托,例如伞盖、朝笏、香炉、熏炉等,例如在敦煌莫高窟217窟中就有双手持笏的供养人画像[12]32。在水帘洞石窟群中发现了一辆供养人所乘坐的牛车造型,就是供养人身份的象征。在这幅图案中,牛的体型非常健硕,头部前伸、高昂,在其身后拉着一架方形双轮车,车辕较高,车轮较大。与敦煌莫高窟隋代洞窟中的一幅牛车图极度相似。所以这幅图像中的牛车应该是水帘洞石窟的供养者所乘坐的牛车,反映出这一时期,牛车仍然是主要的出行工具,而牛车可能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当然,供养人的画像也是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水帘洞石窟群破坏比较严重,尤其是壁画大部分损毁严重,在这座石窟群中有关世俗生活的写照相对比较少。

图9 莫高窟301窟供养人所乘牛车 (隋)选自《敦煌莫高窟壁画全集》

图10 水帘洞石窟群牛车 (北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融合的时期,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各领域全面展开的变动,同时也显现了一种融合。既是民族融合,也是文化融合。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融合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石窟作为各民族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化见证,真实地体现了这种交流与融合。这不仅仅是石窟中经常体现的所谓“X模式”。“X模式”体现了某一个地域类石窟寺之间的文化影响与吸收、融合。但是这些“X模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类似的特征。从大体上而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法、僧三宝也都沿着丝绸之路向河西、中原一带扩展,经典也沿着丝路在不断地被译出。石窟的建造与佛教经典的译出几乎同步进行,正是由于经典传播地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文化圈,再加上社会风俗、民族文化、地质地貌等多种原因,因此形成石窟的不同模式。但不能否定的是这些模式的佛教遗迹仍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四、总 结
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是古代天水地区较大的一座佛教石窟寺,距离麦积山石窟较近,在许多方面都受到麦积山石窟的影响,与麦积山石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秦州模式[13]52-57,是陇右诸多石窟中的另一种样式。由于天水地区的佛教石窟寺基本都处于同一个地理单元,所以其佛教文化、思想、佛教造像的流变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这一地区佛教石窟的功德主,无论是民族、身份、佛教信仰均有许多相似之处。
北朝时期,天水地区民族成分相对较为复杂,包含了氐族、羌族、汉族、鲜卑等多个民族成分,这在古代秦、渭地区出土的众多造像碑中都有明确的说明,特别是水帘洞石窟群中供养人画像以及题记也可以作为这种历史观点的佐证。在水帘洞石窟群中发现了数百身供养人画像,这些画像既有相似之处,亦有其个性特征。从画像的外形特征上来看,虽然有的供养人画像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胡风”特征,但是总而言之,这种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在造像中,民族成分的突出特点已远远小于阶级成分,在这些供养人画像中,对于自己的地位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就供养人画像的艺术特征而言,无论是从其构图方式,还是颜料的用色以及画师的技巧上来说,都显得比较成熟,毕竟到了北朝末期,佛教石窟寺的构造与建设都非常成熟。所以水帘洞石窟群中供养人画像以及题记的特征反映出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具体特征。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水帘洞石窟群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 [J].敦煌研究,1995(3).
[3]魏文斌,吴荭.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北周供养题记反映的历史与民族问题 [C]//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张铭,魏文斌.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甘肃馆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J].敦煌研究,2016(5).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敦煌文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6]汪明.石佛镇权氏造像题记简考[M].敦煌研究,2016(5).
[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 [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李延寿,撰.南史:卷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李延寿,撰.北史: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1]郑炳林.敦煌写本相书理论与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关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二 [J].敦煌学辑刊,2006(4).
[12]张景峰.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养人画像调查新发现 [J].敦煌研究,2016(2).
[13]温玉成.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J].敦煌研究,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