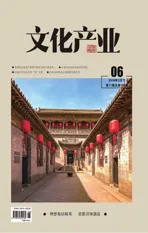从《野草》若干文章浅析鲁迅先生语言魅力
2018-05-24夏玉溪
◎夏玉溪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00)
正如阿摩司·奥兹在演讲中所言,“在所有的意识形式中,文学最不吸引感官”。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美,在不同的美中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独特魅力。
一、从鲁迅的生死观分析语言的刚性美和暴力美
文学艺术通过用语言塑造意象这一桥梁,连接了读者的心理表象和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出对意象的思考与联想,产生对美的感知。朱光潜在《无言之美》中将美分为刚性美和柔性美两种,认为“统观全局,中国艺术是偏向柔性美的”[1],而鲁迅冲破了这种柔软,以锋利的笔调抨击了当时国民的懦弱和愚昧,他的美是一种刚性的美。
借用意象展现刚性美在鲁迅的散文里体现的更为突出,受幼时过早体会世间冷暖和对疾病的长期体验让鲁迅的散文里散布着对生和死的独特感受,在他的笔下,万物的死是象征着突破和新生,死亡并非尽头,生也不尽是开始,生死相生相长,腐朽的死亡是新生的开始。这一点可以从《秋夜》里他对枣树的描写中体会,枣树作为《秋夜》中的象征具有强烈的力量美感,这份美正是通过语言对意象的塑造,将“不可言说”的审美感受尽情表达。此外,文中的“眼睛”“恶鸟”“撞在白纸罩上的青虫”“奇怪的天空”无一不是鲁迅笔下的意象,鲁迅先生笔下的枯枝是要制“蛊惑的眼睛”于死命,他的“恶鸟”是划破天空的主动出击者,“青虫”虽死但他们不断撞击白色膈膜的举动是“英雄”,他赋予不同的生物以不同的生命象征,为了渲染象征物的美感,大量纯色渲染着鲁迅的文章:“非常之蓝的天空”“窘得发白的月亮”“苍翠精致得英雄(小青虫)”等,鲁迅先生让强劲的刚性和绚丽的颜色迸发出一种刚性美,在他的笔下甚至可以看到时代千千万万的英雄,这种象征带来的刚性美是独特的,并非一蹴而成,它融入了鲁迅先生对语言色彩的感知以及其独特的生死观。
在《一觉》里鲁迅似乎直接点明了生死相生相伴的观点:“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受着‘生’的存在。”[2]在这里“生”似乎是因为在死伤后太平的存在,但其实是为后文的悲哀做铺垫。当一个民族的太平需要武器的暴力来维护的时候,哪里谈得上是“生存”?这就引出了后文“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的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是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2],笔锋一转,“活着”是因为死去的为国家前进而不断冲击着封建的青年,“死亡”是因为这死寂的只能由暴力带来的太平,生死不止停止在生命,它更是精神。鲁迅将生死直接运用在植物、人上,最直白、最直接地对生死进行思考,带领读者的思维进入他的世界,仿佛是花朵绽放在坟墓上,直逼人去正视我们的社会,让死不仅是代表死亡,让大众在革命者的死亡中找到更为坚硬和挺拔的生机,鲁迅是在告诉读者为民族而前仆后继的勇者们身上的血性和韧性,在死亡的坟墓上为他们栽培了花朵,这又是一种刚性之下的柔美,鲁迅是在为所有的亡魂找到了他们的归宿。在震撼之外,这语言象征物带来的刚性美更让人动容。
鲁迅把语言的刚性美发挥到尽善尽美的同时,在对生死、血液最直接的描写中给予人还有暴力美感,《复仇》在其散文中是一篇最能将这种暴力展现的文章。“人的皮肤之后,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2]开篇直接描写血液,这是一种对人体脆弱性的最直接的剖析,血液会让人产生各式各样的联想,鲁迅始将血液与“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连接在一起,似乎是要象征着美好,而后文“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2],直接将读者拽入对战争打斗的联想。
看客的表现是贯穿鲁迅创作的一个主要群体,它是滑稽的上层社会群体的形象,也是无知状态下大众群体暴力的表现,而群众的出现正是暴力得以“欣赏”的最主要因素。“衣服漂亮”“拼命伸长”“四面赶来”“舌上的汗和血的鲜”创造出一个和杀戮的严肃场景井然不同的相对愉快的场景,中和了杀戮的恐惧感,是一种对暴力审美的处理手法,在戏剧和恐惧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文末两位并没有杀戮在一起,而是持续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群众一哄而散,结尾在荒诞中又一次点明准备杀戮双方是“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荒诞的叙事与结局、绚烂的场面和色彩描写、戏剧的看客群体共同生发出了鲁迅生死观里暴力美学中的“生命之美”。鲁迅先生的文章常带着血腥的气息和愚蠢的民众。有观点认为这是在抨击无知的百姓,但从暴力美展现的“生命美”来看,鲁迅是要血“活”血,用革命者沸腾的热血浇灌在百姓冰冷的血液上,用革命者的血液活了整个底层阶级,让暴力的美绽放在死土上,他是要让中国人的血性被血腥味刺激到忍无可忍的爆发。
二、从文字的运用上谈矛盾美

鲁 迅
鲁迅在渲染自身文章时,非常喜欢运用语言本身具有的矛盾性来营造人在极端状态的形象,同时运用颜色的辅助来罩染整幅画面。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为刻画一个饥饿女孩的形象,先生写到:“在初不相识的披毛的强悍的肉块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躯,为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而颤动。”[2]肉体是强悍的,即使这只是一个小女孩的身体,她的身体依旧是健壮的,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鲁迅此写的目的: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破旧院落里的女孩们并非是瘦弱无为,他们会跟随父母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来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行,所以女孩的肉体较于同龄贵妇家庭里的姑娘更为强悍,但始终只是个姑娘,再怎么样的强悍肉块,身体始终是瘦弱的,而这渺小则是说明像这样的女孩是千千万万劳动家庭的缩影,是普遍存在不具有特殊性;二是突出饥饿状态中更加瘦骨嶙峋的状态,饥饿是人的肉体无法抵抗的病魔,即使肉体强悍也不妨碍那种深入骨髓的饥饿让人不仅瘦弱更是渺小,在生理状态中,我们展现着最原始的本能,是最渺小的存在。人在生气到极点的时候,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这是人体一种应激反应,同样在饥饿到极点的时候也同样适用。
“欢愉而颤动”用于本应是痛苦、难以忍受的饥饿,但鲁迅是用这种矛盾来描写人在极端饥饿下的状态,不仅让女孩的形象栩栩如生,更让读者透过纸张感受到本能的对饥饿的体验和恐惧。鲁迅是在用这种方式让他的文章更具有感染力和穿刺力,将整个社会的现状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描写方式除体现在对人身体状况的展现外,鲁迅先生还将其衍生到“人”本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在描写奴才的时候运用到了这种矛盾,其次就是整个文章的框架上也运用到了这种矛盾。从语言美感来说,正是矛盾的对比展现出直接叙述达不到的高度和深度,让文字在矛盾中被赋予了生命,展现出文字运用的灵活性和新鲜感。
三、从标点符号的运用上谈留白美
留白是中国艺术作品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极具中国美学特征,也被广泛运用到文学作品中。留白的美感带给人更多的思想空间,让人在作品本身的美感中衍生出自己的美学感受,是一种与观者本身审美能力相关的手法,也正是因为留白的存在,作品才能千古流传,让人在他人感受的基础上添加上自己独特的感受,让这种美穿越了时间,更具有现实意义。
鲁迅作品里的留白美除体现在对话中省略号的运用外,还体现在他分段的跳跃性和语言的戛然而止上,这些在《野草》中篇幅较短的作品中运用得更为典范,尤其是《狗的驳诘》中。文中有十个段落,其中五个段落是对话,每一段字数不超过46个字,全文的内容缘起鲁迅先生的梦境,缘起本身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梦境对鲁迅而言是一张空白的画板,不像任何现实存在的背景带有本身的特征,梦就是白色的,可以说这个背景本身就是一种留白,给读者就留下了很多可以衍生的白色。第二段只有短短的十个字,“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2],随即是用句号结尾。
句号和省略号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决断感,它没有像省略号带给人的悠长,它更像是一把刀切开物体,更加决断和利索,句号就不会给人美感吗?不是的,句号给人利索的美感,它不会拖泥带水,而利索的背后更是给人思考的空间:狗为什么而叫?叫了什么?这个叫声对文章有什么意义?同时句号的结尾更具有跳跃性,它可以让读者的大脑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第八段是狗的一句话,它是以省略号作为结束,这种悠长是鲁迅先生对文章结构的控制,省略号的前面是细数狗认为势利不如人的例子,在揭示丑恶的内容后面加上这个悠长的符号是为了让我们去补充狗想要说什么,这种非常聪明的处理方法让空白的空间非常大,也引出了后文“且慢!我们再谈谈……”[2]。
文中仅有的两个省略号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利用中间的空间连接起来从而引出更大的空间,让读者去思考狗还有可能说了什么。结尾以梦境结束,梦境虽然结束,但留下了一个梦境结束后发生了什么的空白,这个空白承接梦中内容的空白,可以说整篇文章都需要读者的想象带入来写尽鲁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每个人填写的内容不同正是这篇文章的出彩之处,也是留白的出彩之处。
这是留白一般的用法,但鲁迅高明之处更在于他看到了留白另一个用处:表达无意义。在文章《立论》中,作者想要表达怎称赞一个婴儿是最聪明的办法是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2]这里的省略号就不是让人去补充内容了,它就是表达什么都不说,这里的省略号不是代表有意义,而是没有意义,这种用法是非常有趣特殊的,在文学中它将思维的可逆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留白扩展了作者的写作天地,将有限的笔墨化作无限的想象,使读者的思考成为文章的一部分,它的美感诞生在读者本身的审美能力之上,是永远都不会被读得完整的美,只要有读者的存在,这种美的内涵就会一直补充下去。
四、结语
一篇好的文章需要融入一个作者深刻的思想,而文不达意的部分就需要不同的手法去弥补,这种言意的矛盾激发出了创作者创作灵感,从而创造出了不同文字的美感。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瑰宝,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发展了民族语言,他展现的文字美是震撼的,也是伟大的,在给予读者不同阅读体验中,文字魅力的建造与文学的发展相生相伴,文字的美是文学发展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又挖掘了文字的美,这也就是说语言与文学密不可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而中国的文学就这样生生不息地传承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