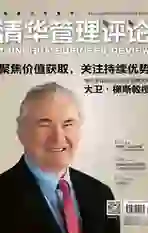聚焦价值获取,关注持续优势
2018-05-23梅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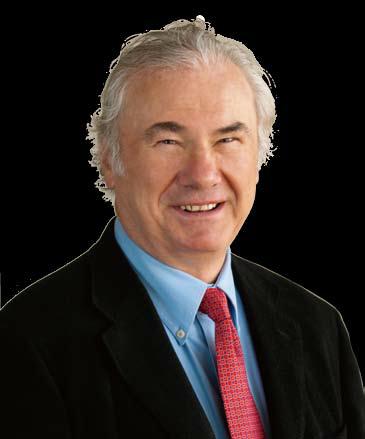
在一个不创新毋宁死的时代,没有一个组织会忽视创新之于公司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如何从创新中获益?如何从创新中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不仅是企业实践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一直以来的核心命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大卫·梯斯先生的“创新收益框架”和“动态能力理论”,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解读,为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价值。
笔者有幸获得大卫·梯斯先生的邀请,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陈劲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一起,对大卫·梯斯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深度了解其创建的“创新收益框架”和“动态能力理论”的思想精髓,并请他对未来的组织管理进行了展望。
梅亮:很高兴您给予我们这次珍贵的访谈机会。这次访谈将会基于您的“创新收益框架”(Profit from Innovation Framework)理论,以及另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理论展开。事实上,作为研究者,我们阅读了大量您的作品,但是产业实践者并非十分了解您的思想。因此,我想从您思想的起源开始提问。“创新收益框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您当初在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最初的深度思考是什么?
大卫·梯斯:“创新收益框架”最早起源于我在新西兰读高中时对英国的观察。当时我发现,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重视科学技术。他们在科技面向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投入比重居全球之首。但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英国如此重视科技却不能通过可行产品的商业化获取收益?这就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层次的问题也源于对英國的观察思考。英国最早将核能应用于气垫船的发明,最早实现了民用喷气式飞机的商业化,最早发明医学成像技术(我指的是“CAT扫描”,这是自“X射线”以来最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之一)。但是,这样一个不断创造革命性技术、并将这些技术成功转化为产品的国家,却在这些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糟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美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美国发明了录像机(Video Cassette Recorder: VCR),但其影响事实上仅限于湾区的几个城市,并没有获得更大范围市场的成功。同样,施乐是最早将个人电脑带入商业市场的公司,其对个人电脑的发明也有许多的贡献,但也没有获得市场收益的成功。
英国这样一个不断创造革命性技术、并将这些技术成功转化为产品的国家,却在这些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糟糕。
所以,我的研究关注于一些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并没有带来商业上的可行性与收益回报的创新。也就是说,创新者并没有获取创新的收益。
通常,创新的线性模型认为:你创造了某项发明,并且证明了发明的概念,你将因为创新而获得成功。显然,线性模型是错误的。
但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能够解释这一种现象。为解释这一现象,我对创新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些关键因素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思考:
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你可以成功地对技术或产品创新应用“许可证”模式,那么问题变得很简单:你发明,并对发明进行许可证保护,你会因此做得很好。然而事实上,一些公司在许可证战略上做得很好,甚至对这一战略展开了大量的投资。但,获取创新收益仅靠知识产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你可以从野中郁次郎先生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中看到,从实验室向工厂转化创新的困难性有多大。你也可以从我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复制引擎”(对创新实现有效、充分的吸收和转化)。通用汽车发明了飞机发动机,但它在市场商业化中失败了,最终通用汽车成为现在的“大众甲壳虫”。
我由此关注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互补性资产”。例如,对于个人电脑刚推出市场的时候而言,个人电脑市场的蛋糕是非常大的。大量的资金从上游流向下游,电脑零售商一般都有五到六个品牌的电脑产品,直到戴尔在这个产业赢得了市场竞争。戴尔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突破这个产业的发展瓶颈,这很重要。我引入了“难以复制的互补性资产”这一概念,来对发展瓶颈这种情况进行表述。
下一个关注点就是时机和标准了。你知道亨利·福特并不是最早的汽车发明者,但他是最早开启汽车大规模市场化的人。时机是指,要思考置身于一个主导性标准涌现的时间点。比如录像机的发明者在早期拥有影响力,能够以昂贵的价格和电视机一起出售产品,但只有在工程师用规模化制造降低了录像机成本之后,大规模市场化机会才来到,但发明者在大规模市场化之前就离开了。
“创新收益框架”就是将标准、主导性设计、互补性资产、知识产权、时机等这些要素进行思考,并整合起来的研究框架。
这是一个可预测的模型,而且相比动态能力而言,是一个更容易测试的模型。虽然这个理论和模型最早是在1986年发表的,但“创新收益框架”在现在依然有其借鉴意义,比如互补性资产在数字经济时代就非常重要。
梅亮:我发现您的“创新收益框架”主要是聚焦创新者(创新公司)的价值获取。如何将其与价值创造相联系呢?或者说基于您的“创新收益框架”,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边界如何界定?
大卫·梯斯:“创新收益框架”是聚焦价值获取的。如果我试图将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都放进来,这会使框架变得很复杂。这个框架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聚焦有限的问题,也即你如何获取价值。关于如何创造价值,像开放式创新、动态能力等研究都有提及。在“创新收益框架”提出以前,没有人关注于价值获取。因此,我对没有涉及价值创造并不感到遗憾。
梅亮:“创新收益框架”本质上是从创新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一方面,创新者可以通过创新推动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创新者无法确保自身的创新价值获得保护。那么从创新的模仿者、跟随者、后发者的角度,这个框架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大卫·梯斯:事实上我的书《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nd Policy Dimensions》(《管理智力资本:组织、战略与政策》)有一个章节专门谈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即使不是一个创新者,倘若你拥有互补性资产,你依然可以获益。所以,后进者或者跟随者可以通过互补性资产而获得创新收益。比如,在录像机产业的商业化过程中,如果你有磁头技术,你会主动希望把他放到录像机上,而不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国内市场来控制国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开展分销的权利。日本早期就是这么做的,现在日本的市场有一些开放了,但是日本对于本国市场的封闭,和对技术许可权的保护与投资,使他们从西方的技术中获取了很多收益。
所以,“创新收益框架”不仅仅对创新者是有用的,其对于互补性资产的拥有者也尤其重要,这也是该框架对创新跟随者的价值。一个最浅显易懂的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年代,最赚钱的人并非是那些挖金矿的人,而是那些出售可穿带的牛仔裤和金笔的人。你能从这里看到李维斯的总部,这是淘金热时代的互补性业务,这些工人和金子相关的业务之间是很近的。所以加州淘金热年代互补性资产的拥有者比挖金矿的人更赚钱。
梅亮:你知道中国一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支持性的国家创新体系、巨大的国内本土市场、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分销体系。在中国情境下,“创新收益框架”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大卫·梯斯: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中国政府清楚地了解如何从创新中获益。他们有限度地放宽准入,很好地管控了互补性资产(如市场)。比如对于滴滴和优步,或是对于阿里巴巴和eBay等都是如此。对于西方的创新者而言,他们很难接近中国本土的互补性资产,中国对这些本土的互补性资产进行了很好的管控。事实上大量的创新价值都基于中国对互补性资产的有效管控而获得了。
梅亮:下一个问题涉及“创新收益框架”面向新的情境的延伸,比如数字经济的兴起,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等。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大卫·梯斯:你应该熟悉“微笑曲线”,其最初是由宏碁的CEO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强调曲线两端的价值增值,如同人的微笑一样,经济回报主要会流向研发端和客户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创新收益框架”也许会承认,很多时候“微笑曲线”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创新收益框架”会关注瓶颈性的资产在何处,复制资产的难点在何处。“创新收益框架”的核心就是:你无法假定结果和稀缺性,你必须关注每一个阶段什么要素是创新所需要的支持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复制吗?这些要素可以构建吗?这些要素可以购买吗?这些要素是公共产品还是很难获取?如果这些要素很容易获取,那么“微笑曲线”就要反转了。
另一方面,假设经济价值主要集中在研发和市场两端,研究并未有效解释企业如何有效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向两端转型的机制。实现转型的机制是学习。以富士康为例,如果富士康开始制造手机了,我认为苹果会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可能有正式的协议规定富士康不能做手机业务,但这样的话富士康战略上似乎是受限的。基于我对一些企业的观察,很多代工厂商在原先的代工业务之外,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自主业务,比如富士康就可以到苹果公司不关心的新兴国家市场,制造并销售手机。但是以上这一些现象背后,其相关的组织学习机制是缺少研究的,也许我可以问问亨利是否有有效的理论解释这种学习过程。
亨利·切萨布鲁夫:当我们思考其中的“学习”机制时,“创新收益框架”变得更有意义了,没有一个框架可以在创新收益上与之相媲美。
大卫·梯斯:“动态能力”理论讨论的是“创新收益框架”遗留的问题。当你开始思考創新,开始考虑如何创造价值,而不是仅仅关注商业模式创新的收益时,你需要弄清楚一些事情,这就是动态能力理论中的感知、抓取等所关注的:一方面要创新,另一方面要开展有深度市场需求的创新。所以要将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和对市场的理解相互联结起来,这就是动态能力思想的核心。
亨利·切萨布鲁夫:对的,动态能力涉及的就是“我”感知、抓住所有内部和外部事物并将其整合起来的能力。
梅亮:我能说这就是动态能力的思想来源吗?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动态能力理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大卫·梯斯:正如亨利刚才所说的,“创新收益框架”非常简单,她聚焦于企业或者个人的产品,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能够获胜的创新法宝。但这个框架没有说什么样的企业会从这个产品的创新演进过程中获胜。所以我需要在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解释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在“创新收益框架”之外提出一个更大的框架了。
动态能力理论涉及到的问题比“创新收益框架”涉及的问题复杂得多。对于企业来说,要在单一创新产品之外考虑更多的创新组合。此外,企业在思考推动创新的动力因素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创新过程相关的演化、匹配、适应等问题。你可以每周创造一个新产品,很多硅谷的公司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如何了解下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呢?你如何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了解下一个风口呢?所以,首要的是你需要感知,然后抓住机会。
动态能力涉及的就是“我”感知、抓住所有内部和外部事物并将其整合起来的能力。

动态能力是一个可行的系统理论,这是别人没有思考过的,我试图弄清楚。我试图回应那些创建管理科学系统理论以及创建管理科学领域的早期学者,达成他们未完成的心愿。之前我认为工程师才有系统理论。比如,如果你要建造海湾大桥,你必须采用系统思考,如何把桥梁线路布置好,如何把他们系统地连接在一起,否则就不能实现。但在管理领域,我们没有系统理论。这不是因为在学术世界,组织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因为我们都试图去测量,希望在组织研究的细分领域深入探索。所以,我认为现在至少应该有一个基于竞争优势的系统管理理论提出来。
陈劲:那么,作为一个管理大师,你是如何思考未来的管理的?
大卫·梯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商学院现在越来越脱离实践了,因为他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狭窄,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概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商学院的。在开始的那段时期,商学院非常像贸易学院。
到了20世纪50年代,伯克利商学院有了伟大的愿景,就是把科学引入商学院教育之中,我们摆脱了那些来自实业界的学术研究者。
现在商学院存在的问题与那时相比正好相反。对于大多数商学院来说,除了一些很小的领域会与商业实践有关,大多数的研究与商业实践已经越来越不相关了。如果企业遇到的是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商业问题,他们才能在商学院寻找到帮助。
未来的管理应该需要我们整合现在拥有的知识,并同时考虑企业现有或未来即将拥有的新技术的发展情境。
在商学院中,具有连续培训经验、且能够为企业高管的管理问题提供解决视角进行思考的学者已经非常稀少,这一类的理论包括切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我所做的动态能力研究。但是,数量屈指可数。
我认为未来的管理应该需要我们整合现在拥有的知识,并同时考虑企业现有或未来即将拥有的新技术的发展情境。比如人工智能,它是可以将公司常规能力转化为动态能力的,直到这个能力被他人再次赶上。
当我们开始考虑所谓的“奇点”这类大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未来10-20年的管理核心在于:创造有意义的框架去解释人们(不仅仅是管理者,还包括政策制定者)如何决策。你看现在的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他有一种本能来识别出目前那些美国经济政策学者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特朗普无法告诉你学者的误区在什么地方,但他的本能让他知道,他们的建议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如果有一个管理框架能够解释清楚特朗普是如何做决策的,一定是很有意义。
另外,企业治理对于管理学也很重要。治理的问题不在于使法学研究者更关注治理、使管理学者更关注管理。在学术界,我们试图实现评价衡量与管理最简单的方法,是尝试回答一个非常狭窄的研究问题,看看人们是否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而对于问题本身是否有兴趣,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重要。所以,在管理学进行企业治理的研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商学院也到了必须实施变革的时候,否则商学院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对管理者而言,管理者必须理解全球化條件下、多利益攸关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管理学的研究方向是应该能帮助管理者应对这样的挑战。
亨利·切萨布鲁夫:在前面的问题中,我们讨论了您重要的两个研究议题:创新收益和动态能力。但与此同时,您又是一个领导1200名员工的成功企业领导者。所以我的问题是,既然你身兼研究者思想家、以及企业家领导者的双重身份,面且您创办了多家公司,这些企业管理的经验是如何影响您的思想和研究思考的?
大卫·梯斯:就管理企业来说,我是有优势的,尽管我个人的经验可能不多,但是我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汇集了成千上万公司管理者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让我在每一天做出快速的决策。因为我没有太多用于管理实践的时间,作为一个身处学术界的企业家,我必须快速思考并做出决策,并需要其他成员有条不紊地推进。商业对话往往需要快速思考,而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慢慢思考,他们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亨利·切萨布鲁夫: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的学术经历和实践经验帮助你思考并构建理论。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你不仅仅需要自己去观察,你也可以从你的经验中提炼应用一些框架,将外在条件与理论进行匹配以快速做出相关的决策。
大卫·梯斯:是的。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有关决策,我可以将所有看到学到的文献应用于我的决策之中。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成千上万他人的研究文献,我掌握的许多知识来源于文献,但是我能在相关的实践情境中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在我的企业中经常发生这类情境,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没有事实发生,但在我阅读过的文献中已经发生过,我就试图快速地到达文献中提到的那些地方。也许这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是很困难的事情,但通常在我的组织内部很容易就达成共识。当你决策的是之后的一至两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需要做的事情会出现模糊和不清晰,这时候我作为思想型企业家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另外,当组织出现固化,我的团队不知道如何推进的时候,我会去做这个关键的决策。很多时候我不需要围绕团队成员,我只需要去做关键的决策,当然这些决策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且关系到很多人的职业。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从学术研究中获益的,其帮助我做出很多艰难的商业决策。
这种困难决策并非每一天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更像是我们没有处理过但需要面对的许多问题,因为组织向许多方向发展。我所面对的不是相同的问题,但是我需要辨别他们,迎接这些长期和持续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我的团队而言,我的工作是让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明确。许多人不能连接到一些关键点,但是对于我的企业来说可以连接到,这是源自于对事物有了普适性、系统性的认识以后所形成的深层次连接。所有这些都影响我,使我能够一直积极主动地来做决策,并引导团队中的管理者对我的决策做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