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贵一人成张岱《石匮书》前言
2018-05-21传栾保群
商 传栾保群
商 传:(一九四五年~二〇一七年),生前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社会史室主任学术委;中国科院大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长著有《永乐皇帝》代文化志等
栾保群:前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整理出版有《日知录集释》、《困学纪闻》等
作为史学家的张岱,他有坚贞的操守、真挚的爱憎、卓绝的胆识。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不钦仰他的史德,服膺他的史识。总观《石匮书》纪、表、志、世家、列传各篇的总论和史赞,约有十万余字,占全书篇幅的二十分之一,是张岱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尤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后集》论赞最为出色。喜欢张岱文章的读者,将从《石匮书》的论赞中看到这位文体大师与《陶庵梦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文章风格。器局恢弘,声情并茂,一言既出,破石断金,史官文化的凛然正气溢于字里行间,而动情之处,真如烈士泣血,寡妇夜哭。人们喜读张岱散文,多由《陶庵梦忆》入手,我至今坚持《陶庵梦忆》中绝大多数文章写于鼎革之前,到了《石匮书》的论赞,早年的花月之情一变而为风霜之气,真喜宗子文章者,不可不读他晚年的史论……
张岱早已是为读书人所熟知的人物了,但他更多的是作为晚明小品文的杰出作家为人们所景仰。如果让张岱给自己定位,我想他大约不会接受「散文家」这个头衔,因为他终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史学家,像司马迁那样以独立精神,完成有明一代国史的史学家,写一部像《左传》、《史记》、《汉书》那样「成于一手」的史学巨著。
早在万历末年,张岱年方弱冠,即开始编撰《古今义烈传》,历十年而于崇祯元年成书,而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石匮书》的写作准备。张岱家中藏书甚富,对他的修史志趣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要修一代之史,他也感到「成、弘而上,杞宋无征;庆、历以来,文献不足」,于是向当地藏书家们发布《征修明史檄》。这年张岱三十七岁,此后直至崇祯末年,张岱的生活记录中多有征歌逐舞、游山戏水,修史之事虽然不是以全力为之,但也未曾间断。不管怎样,到明亡之时,虽然家中藏书尽毁于乱兵,张岱已经有了《石匮书》的初稿,所以他才能在兵燹避难之际「携其副本,屏迹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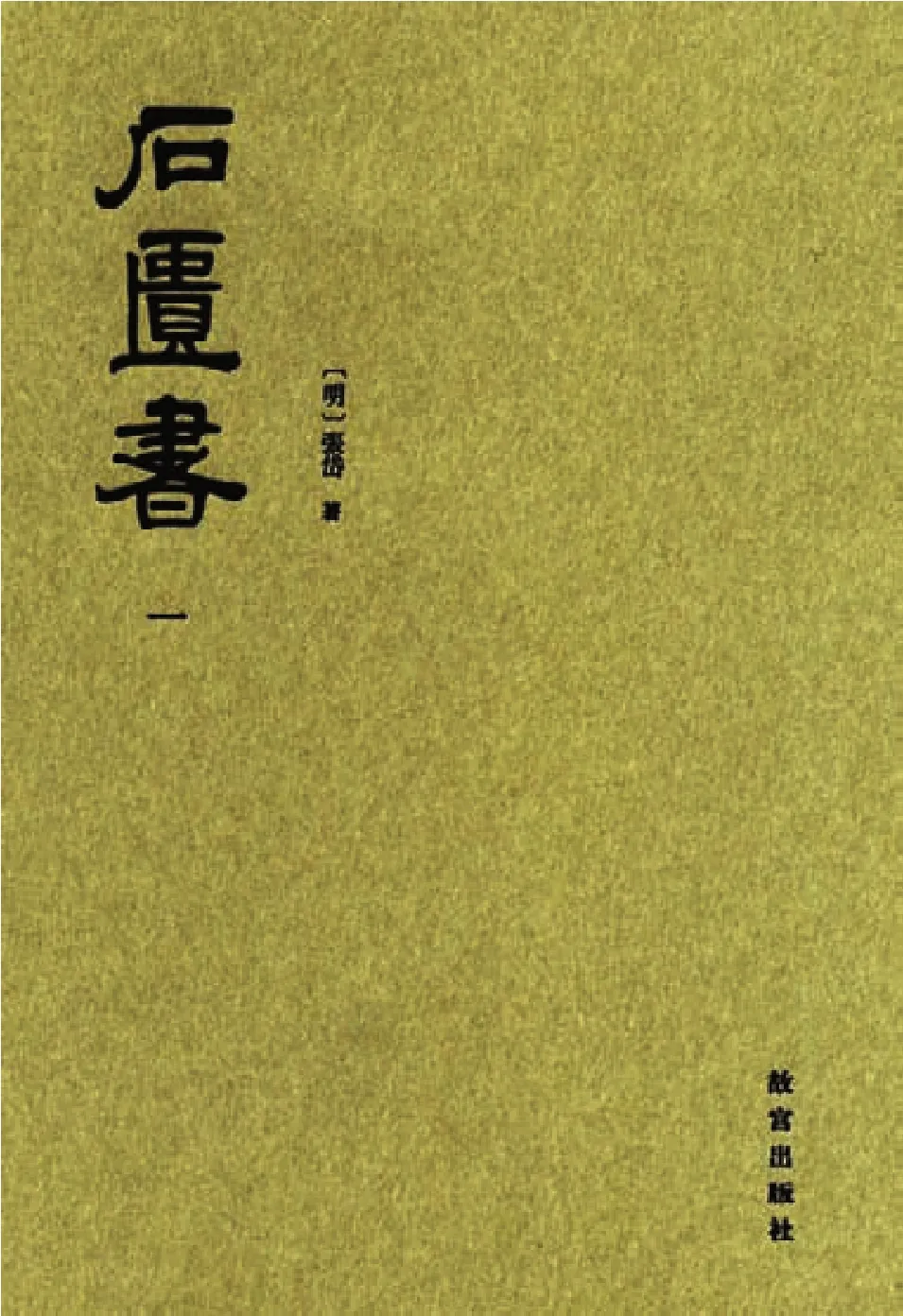
《石匮书》书影
弘光亡后,张岱先是参加了鲁王朱以海的浙东抗清,旋即败散。顺治二年,他避兵入剡;三年,隐身于山阴西南之越王峥,再逃至嵊县;四年,寓居绍兴项里,此间他疲于奔命,困苦劳顿,故旧视之如毒药猛兽,「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几乎「直头饿死」,「每欲引决,因《石匮书》其未成,尚视息人世」。至顺治六年,他移居快园,虽然生活困窘依旧,但总算有了个稳定的写作环境,所以五年之后的顺治十一年,在「五易
其稿,九正其讹」之后,《石匮书》终于成稿。此时明亡已逾十年,虽然东南、西南的抗清政权依然活跃,但崇祯一朝却是尘埃落定,已经可以着手续写了。正在张岱苦于缺乏史料的时候,顺治十三年,丰润谷应泰任浙江学政,欲修《明史纪事本末》,邀请张岱参加撰写。张岱为了利用谷应泰所藏史料,于当年至杭州,把参与《明史纪事本末》的撰稿与续写《石匮书》兼顾并举,居杭一年多,成书数十卷,基本上就是《石匮书后集》的初稿,至此,这部有明一代之史大体成为完书。
这是唯一一部以一人之力完成、完全以《史记》为模板写成的明史。张岱把一个垂老遗民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全部凝结在这部二百余万字的巨著中。他在这部书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最高的尊严和胆气,对清统治者不置一顾,没有一个字流露出对新王朝的归顺或让步。这是一部只要被发现就要获罪的禁书,所以张岱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会梓行于世,但他坚信这书终究能得见天日,为这部本来要叫《明书》的著作重新起名为《石匮书》,就是想让它和郑所南沉于古井的《心史》一样,藏于石匮,但总有一天会被后人发现而流布。
然而严格说来,《石匮书》实为未定之稿。这固然是因为《后集》中有些列传有目无文,但这可以以史料不足或有所等待而解释,并且有些卷目如马士英、阮大铖的行迹已经在《福王世家》中展开。除此之外,全稿还存在着不少本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张岱写传记的文字功力,我们可以从《琅嬛文集》中《家传》、《五异人传》、《王谑庵先生传》、《周宛委墓志铭》等篇中领略其风采,绝对是当时第一流水平,但他没能以生花妙笔施于全书、成一家著作,确实是一大憾事。张岱《与李砚翁》一信中说:「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余载。」以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开始着手计算,此时最早也是康熙九年(一六七○ 年)之后,衰年老翁,仍然修订不辍,可是终究已是「漏尽钟残」了。

商传先生像
虽然如此,以一人之力,于颠沛流离、穷愁困顿之中完成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也足称为艰苦卓绝。列入「正史」的《明史》,清廷开馆六十年,网罗天下名士,聚集天下藏书,成书后公认良史,诸传尚且多有疎漏抵牾。但孟森先生以为,疎漏抵牾尚不是《明史》的最大不足,「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或曲笔,或文饰,对于史馆诸公来说,也就是丧失独立的修史思想,一切服从朝廷,是非全凭圣断,尽其才学,充其量也就是「御用的史料编纂家,而不是史学家」。(先师王毓铨先生语。我问他什么是「史学家」,他说:「要有独立的思想,比如司马迁。」)由此也就看出张岱史学的优胜之处,正在于保持了人格和思想的独立,以事实为依据,以思考为论断,不徇俗,不偏党,不屈服于任何势力的干扰,不屑旁顾,一往直前,直抒己见,大胆论断。
嘉靖大礼议是明史中一大事件,其所以大,是因为一件本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事却引发了官场地震,结果成为影响此后数十年政治的一大变局。世俗之见以为:杨廷和是正人,那么持不同意见的张璁、桂萼就一定是小人。不问是非,先定正邪。「天下后世万口一词,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赵翼《陔余丛考》)张岱对此独持异见,曲原嘉靖帝出于父子之情而考兴献王,「杨廷和辈,不能将顺匡扶,执拗古板,遂致决裂而不可收拾」。(《大礼建言诸臣列传》总论)赵翼言《明史》中的传赞「协是非之公」,即举此案为例,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程颐濮园之说。……未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以为传赞「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张岱早在一百年前就有此识见了。不仅如此,张岱还在《张孚敬(璁)传》中特言其公忠,非谄佞希宠之徒,且赞曰:「孚敬相而中涓之势绌,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里者,谁力也?」杨廷和辈辞朝之后,嘉靖信用张璁,未使权力出现真空而由宦寺乘虚而入,由国计民生大处着眼,这就是张岱史识的高明所在。
张岱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置于历史的大潮中分析判断。在正德谏南巡,嘉靖议大礼,万历争国本诸事件中,无论成败,正派士大夫的抗颜忿争愈演愈烈,皇帝的专制暴虐也随之加码升级,士大夫刚烈正直的名气越来越大,国步民生却每况愈下。那么士大夫以血肉之躯拼死忿争的究竟是什么?动辄叩阍叫号,声彻大内,心里想的是国家百姓,还是只博取个「万世瞻仰」的名声?张岱在《石匮书》的论赞中不严于「非君子即小人」之辨,却要深责「贤者」的历史责任,这与他在鼎革之后,对明朝由盛至衰以至于灭亡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虽然都知道《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但张岱这态度却未必能得到同时士大夫的认可,特别是张岱在《门户列传》中对东林党人的抨击,在友朋中能得到许可的不过一李砚翁而已。
张岱本人极重气节,一部《古今义烈传》贯穿了他半生的写作生涯。对东林前辈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张岱譬之元祐有苏轼、司马光。「光明磊落,出处昭然,不东林者有其节概否耶?」「以三君子言之,亦人负东林耳,东林何负于人哉!」而对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杨涟、左光斗等人,张岱许以「忠烈」,于传中特录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及倪元璐《左光斗行状》。东林在士大夫中名气渐大,诸君子遂高自标榜,互通声气,以致只认门户,不明大义,便给大量「为做官而入党」的投机者开启了方便之门,有野心而无节操的李三才辈,更是把东林当成腾身上位的政治工具;而像刘宗周、王思任、祁彪佳这些有识有节的士大夫,却因洁身自好而与东林保持距离。明末党争的鱼龙混杂,历史走向的变异百出,东林君子起码要负相当的责任。回首天崩地坼之变,张岱追究正人君子的亡国之责,甚至语涉愤激,也许会被人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把历史的责任往那些元恶巨憝和附恶者身上一推,剩下的人都是干干净净的正人君子,难道就对了么?
张岱本人就是正直士大夫的一员,看他为《古今义烈传》写的序,他的性格也是易于激动,一念之间就会舍身取义的,如果他身处大礼议的风潮之中,未必能冷静地不受群情裹挟。但若干年后的历史反思,必须不顾情面,跳出圈子来冷静思考。他对这个政治集团的斗争策略极不满意。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不审时,不度势,不能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极恶的一小撮,反而把那些即使不能成为同盟者,起码也可以争取为旁观者的官僚推到敌对一方,甚至为了沽名售直,对极恶极凶的皇权死磕硬碰,最后鱼死而网不破,血肉狼藉,一败涂地,还自以为这就是可以流芳百世的名节。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角斗中,那种宁折不弯,非我即敌,得志时互相咬啮,失势时自我放逐,对任何妥协和让步都要横加指责,必弄到朝廷一空、豺狼当道而后止,这就是对国家极不负责任的卤莽灭裂。对此,张岱是毫无回避地予以谴责,并追其本原,极端专制的皇权亦不能辞其罪。
作为明代遗民,张岱必须维持对前朝的尊崇,所以他在诸本纪中多有似是而非的溢美及假设之辞,但由全书来看,他对皇权凶残丑恶的揭露不但毫无忌讳,而且是竭尽全力。明朝士风的不振,在张岱看来,最终责任在于皇帝。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对建文诸臣的屠戮侮辱,「破灶扬灰」,把士大夫的忠义正直之气摧残殆尽。此后除了成化、弘治两朝之外,正德、嘉靖以至天启、崇祯,廷杖之惨,胜于凌迟,诏狱之毒,同于屠场,冤死之后,又诬以通敌贪贿,敲剥家属,株连宗族,必至赶尽杀绝而后快,惨刻寡恩几乎到了视如寇仇的地步,君臣之间还有什么恩义可言?崇祯亡国之后,「天下忠臣烈士闻风起义者,踵顶相籍。譬犹阳燧,对日取火,火自日出」(张岱《越绝诗小序》),也就是说,这些忠义之火是来自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并非激于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与黄宗羲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顾炎武之「亡国亡天下」之辨一样,张岱的忠义非由「君恩」,都是对皇权极端专制而导致生民涂炭、自身灭亡之后的反思。
《石匮书》当然不是完美的史著,由于条件所限,张岱为自己设定的「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也很难全面落实。它的缺陷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甚至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但今天来读《石匮书》,是要看它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可学习继承的东西,张岱的史学比同时侪辈有何优胜之处。
论者言及清初浙东史学,首推万斯同,他以布衣身份北上,立志为前朝留一信史,其诚可嘉,而且始终也不失遗民操守。但新朝的功令能让你留一部前朝信史么?在文字狱的罗网下,明廷的「一朝忠奸」或能评判,易代之际的事就难言之矣。论学问渊博,掌握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张岱自不能与万斯同相比,但一置身于矮檐之下,去取由人,一代大史学家就不得不最终成了皇室的数据员。有识必先有胆,张岱能够不受樊笼羁绊,海阔天空,敢想敢写,而且坚信其书必能见天日于后世,其胆其识先占了头筹。查继佐的《罪惟录》和《石匮书》很是相似,一样是私修的,不以示人,也一样坚信其书必能见天日于后世,所以于明亡之后仍用永历纪年,书满兵为虏为仇,痛斥投敌汉奸;但查氏其情可疑。康熙初年「南浔史案」,他是举报人之一,而且受了清廷嘉奖,分得祸主庄氏的部分财产,遂成暴富,人格之鄙,与吴之荣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更无论其遗民操守了。亡国之后,张岱以贵介公子而甘于贫贱,冰蘗之操,皎如白日,而查氏蓄养家妓,耽溺声律,哪里有什么黍离之思、亡国之痛?《罪惟录》装点故国情怀,辞愈激而情愈伪,不过是为身后留地步罢了。顾亭林《日知录》有「文辞欺人」一则,借谢灵运、王维而斥责当代大佬:「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所指应是钱谦益、吴伟业之辈,查氏读此,不知心中有愧否。所以看查氏史学,只一个「伪」字,就先落入下乘。
作为史学家的张岱,他有坚贞的操守、真挚的爱憎、卓绝的胆识。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不钦仰他的史德,服膺他的史识。总观《石匮书》纪、表、志、世家、列传各篇的总论和史赞,约有十万余字,占全书篇幅的二十分之一,是张岱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尤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后集》论赞最为出色。喜欢张岱文章的读者,将从《石匮书》的论赞中看到这位文体大师与《陶庵梦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文章风格。器局恢弘,声情并茂,一言既出,破石断金,史官文化的凛然正气溢于字里行间,而动情之处,真如烈士泣血,寡妇夜哭。人们喜读张岱散文,多由《陶庵梦忆》入手,我至今坚持《陶庵梦忆》中绝大多数文章写于鼎革之前,到了《石匮书》的论赞,早年的花月之情一变而为风霜之气,真喜宗子文章者,不可不读他晚年的史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商传先生于病重中改订此稿,一月后即辞世。本刊摘要登载,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