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以“南京虐童案”为例
2018-05-17胡杰容
胡杰容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2249)
一、问题提出
儿童不仅是家庭的成员,也是国家公民。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享有生存、受保护、发展和参与四项最基本的权利。其中,受保护的权利是指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1]狭义的儿童保护主要是指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和忽视的集体行动,即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救助、法庭命令、法律诉讼、社会服务和替代养护等措施,对受到和可能受到暴力、忽视、遗弃、虐待和其他形式伤害的儿童提供的一系列旨在救助、保护和服务的措施,使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2]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对儿童进行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保护。
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儿童虐待案件说明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尚存在空白。其中,2015年4月初发生的“南京虐童案”引起司法干预,并经过媒体的持续报道,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案件的始末是南京江北区一小学二年级男生施小宝,因为没有完成养母李某布置的课外作业并且撒谎,遭到李某的殴打,学校老师发现伤情后报警。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介入调查,并将施虐者李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浦口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故意伤害罪,并处有期徒刑六个月。①
这起案件被作为一起刑事案件,得到了司法机关的介入。在司法干预过程中,养母李某以故意伤害罪被定罪服刑,其儿童虐待行为受到了刑事惩戒,似乎司法正义得以维护。但从儿童权利的视角来看,这起案件也是关涉多方主体价值观念和利益立场的儿童保护事件。当国家公权在介入家庭领域中的儿童保护时,必然触及案件发生的社会文化脉络,包括当事人之间的情理关系;也要具体而充分地考虑到儿童与家庭之间已经形成的依恋关系、儿童的生活安置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司法干预的出发点是儿童保护,但是否真正做到维护儿童利益最大化、是否达到维护儿童权利的效果尚需深思。本研究将结合这起典型的儿童虐待干预案例,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儿童保护的现实困境和隐含的重重张力。在此基础上,试图讨论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在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的实践中,如何实现国家、父母、儿童三方权利的相对平衡,真正有效维护儿童权利、满足儿童需要。
二、儿童保护中的困境与冲突
(一) 是儿童虐待还是体罚管教
在最广泛意义上,所有对儿童故意伤害的行为都构成儿童虐待(child maltreatment),无论是对儿童的苛刻、过分严厉、拒绝、忽视、剥夺,还是暴力和虐待(child abuse)。[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儿童虐待(child abuse)是指对儿童有抚养监管义务及操纵权的人,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或经济性剥削。[4]这一狭义的儿童虐待界定强调:在不同的施虐主体中,父母是重要的施虐者;在多种虐待形式中,身体虐待是常见的主要形式。在“南京虐童案”中,养母李某因为教育问题多次打骂施小宝,直至2015年3月底,再次因学习和行为习惯问题,她严厉责打小宝,造成一级轻伤。如果参照儿童虐待的界定,显然她的行为构成儿童虐待。我国法律对虐待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相对严格,不仅在主观方面强调主观故意,而且在客观方面要求虐待行为情节严重,具有经常性、持续性和严重后果。在维护家庭团结的立法意图下,虐待案属于自诉案件,不告不管。但在儿童虐待案件中,一是儿童作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无力提起诉讼;二是“家丑不可外扬”等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观使得当事人不愿提起诉讼。因此,对儿童虐待案件,国家介入显得尤为必要。但本案中,司法机关从打击与惩戒犯罪出发,将李某行为的性质认定为故意伤害行为,并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显然,李某殴打施小宝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故意伤害行为,而与儿童虐待问题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机关对李某的行为定性没有触及行为的本质特点。
案发后,李某反复强调,她责打施小宝是为了督促他改正恶习,她的行为属于体罚管教,并坚决否认虐待孩子,拒绝认罪甚至企图撞墙自杀。②③但从儿童福利专业人士的角度看,当事人李某的行为已然构成儿童虐待。到底体罚管教是不是儿童虐待,专业的界定与普通人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即使是遭受责罚的儿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模棱两可。研究发现,儿童对于父母虐待行为的合法性持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在理智上对父母的虐待行为合理化,另一方面,在情感上表现出不接受。[5]52这意味着受虐儿童对父母责罚行为存在认知与情感之间的张力。在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为何难以被认定为儿童虐待?为什么在中国即使是如此严厉的体罚管教也难以被认定为儿童虐待?
首先,对儿童虐待的认识与一定的儿童观紧密相连。人们怎样对待儿童源于怎样看待儿童,对儿童地位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儿童是家庭的私产与父母的附属品,还是国家的公民与独立的权利主体?如果儿童被视为家庭的私产和父母的附属,父母即使再严厉地体罚管教孩子,也是个人行为。反之,如果将儿童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受保护权,体罚责打儿童则可能构成侵犯儿童受保护权。在这一意义上,对儿童虐待的界定是建立在某种儿童观的基础上的。
其次,对儿童虐待的界定要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儿童虐待是一个文化敏感性的概念。在导致对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多种逻辑根源中,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6]28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将体罚责骂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养方式。因此,人们不认为体罚孩子是侵犯他们的权利,而是认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见怪”。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体罚成为管教孩子的一种重要方式,似乎爱之愈深,责之愈严。尽管当今人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和儿童教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亲子权力关系上看,强调家长权威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家长依然认为,打骂孩子只是“体罚管教”而不是“儿童虐待”。体罚管教是否可认定为儿童虐待,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家庭权力关系具有直接关联。
最后,儿童虐待的界定要经历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建构论认为,各种社会现实是在主体间性的互动中,社会行动者之间实现共享性理解的结果;是经由沟通、对话甚至利益冲突与斗争达成共识的产物。[7]从儿童虐待概念在美国的确立过程看,1960年前,虽然儿童受虐现象客观存在,但直到1962年,美国丹佛的儿科医生亨利·坎普(Henry Kempe)等人出版了《受虐儿童综合症》一书后,在医疗、司法和社会服务等不同专业团体的共同推动下,联邦政府于1974年制定的《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法案》才确立了儿童虐待的最基本定义。[6]26这说明儿童虐待要成为一种表现为客观外在性的社会现实,需要人们的思想认知、价值信念等发生变化,需要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透过对相关行动新的意义赋予,实现共享性理解。
正是因为儿童虐待的界定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儿童观和教养观密切相关,所以,不同群体对儿童虐待的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对体罚管教是否是儿童虐待存有异议。在“南京虐童案”中,对李某体罚小宝的行为,司法机关认为是故意伤害,当事人认为只是管教失当,而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的界定,她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儿童的受保护权,构成儿童虐待。在一定程度上,“南京虐童案”折射了儿童保护实践中对儿童虐待行为认知和定性上存在着张力。
(二) 是司法正义还是社会恢复
从欧美国家的实践看,司法、医务、教育和社工等不同专业共同参与儿童虐待的干预,尤其是司法和社工专业。然而,不同专业在价值理念、干预方法、考虑重点上存在差异,这在儿童保护实践中常常是引发争议的问题。从“南京虐童案”的处理来看,强调司法介入,而忽视社会服务,整个干预过程包含着司法正义和社会恢复之间的张力。
首先,司法正义与情理脉络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本案中,养母李某和生母张某之间是感情笃厚的表姐妹,施小宝与李某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依恋关系和归属感。④这种情理脉络可以成为妥善解决问题、维护儿童利益可资利用的资源和优势。但司法机关没有重视施小宝、张某与李某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和被告人,他们不是利益和情感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其司法干预过程强调维护司法正义,拒绝当事人提出的刑事谅解书和刑事和解书,也不愿倾听受虐儿童的心声。这种干预固然达到了惩戒与威慑违法行为的目的,但却使当事人的情理关系和社会团结遭到破坏。本案中,面对养母判刑入狱,生母万分愧疚,甚至跪地道歉。⑤⑥这即体现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儿童保护领域时,司法正义与情理脉络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其次,司法正义与社会恢复之间存在张力。涂尔干认为,违法犯罪行为侵犯的是社会整合,压制型法律以集体意识为主导来维系社会的机械团结,而恢复型法律体现的是以功能依赖来维护社会的有机团结。[8]恰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刑事司法模式建立在适当报应和惩罚罪犯基础上,通过一种规训技术,对案主进行分类管理和监管训练,试图改造主体,保卫社会。这种模式强调司法正义,但却不利于社会关系结构和功能的恢复,甚至对其具有破坏性效果。而社会恢复模式强调在矫正治疗和恢复补偿等非惩罚性的司法理念指引下,通过辅导、矫治、教育、安置、能力建设、恢复关系、补偿过错等措施,一方面实现主体塑造,另一方面恢复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功能,减少纠纷和预防犯罪,最终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9]本案的司法干预具有刑事司法模式的特点,将维护司法正义放在首位,不重视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已经形成的亲子关系,更不重视被告人李某的教养观念行为的矫正、家庭抚育功能的维护,忽视了社会连带关系的维护及其家庭抚育功能的修复。
(三) 是儿童权利还是其他主体权利
儿童保护涉及儿童、父母、社会和国家等多重权利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可能发生权利冲突。在“南京虐童案”中,儿童受保护权和父母监护权、儿童受保护权和社会监督权、父母监护权和政府干预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
1. 儿童受保护权与父母监护权的冲突
儿童的受保护权和父母的监护权都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权利。对儿童的受保护权,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10]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监护既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权利。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11]《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该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10]但由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和立法者的价值模糊,导致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明晰。例如,对父母监护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什么是父母适当的管教行为或适当的教育方法没有具体规定,对父母行使监护权时儿童人身受保护的权利如何体现也没有明确规范,这些语焉不详的地方成为父母监护权与儿童受保护权之间的冲突空间。[12]那么,在维护儿童的受保护权时,如何同时保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监护权?
2. 儿童受保护权与社会监督权的冲突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10]在“南京虐童案”中,媒体的频繁报道和案件的公开审理,完全曝光了小宝的身世及其他隐私。媒体采访时,小宝屡屡被问及案件相关的细节和感受。在网络空间里,他成为网民谈论消费的对象,并被贴上“被虐待儿童”的标签。作为一起典型的儿童虐待事件,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在行使合法监督权,但在推动儿童权利保护的同时,也深深伤害了儿童的隐私权,严重干扰其正常生活,实质是一种二次伤害。社会行使监督权时,如何保障儿童不被二次伤害?
3. 父母监护权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冲突
在父母、儿童和国家三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儿童不仅受父母监护,也受国家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当父母监护行为失当时,国家有保障未成年子女权利的义务,有监督父母等监护人行为的权利。[10]但在何种程度上,父母的监护行为可认定为失当?在何种情形下,国家可进行干预?当父母和国家的认知判断发生分歧时,如何处理?我国相关法律并无具体明确规定。因此,父母对儿童的监护权与国家对儿童的保护权可能产生冲突。
(四) 是儿童受保护权还是儿童其他权利
1. 儿童受保护权与参与权之间的张力
受保护权和参与权是儿童权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儿童观点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即任何事情涉及儿童,均应听取儿童的意见。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儿童参与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应确保能够形成自己看法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儿童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重视。儿童特别享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讼中阐述见解,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1]在“南京虐童案”中,虽然小宝强烈要求回到南京养父母家、希望继续由养母抚养监护,但仍然被带回生父母家。对儿童的生活安置没有充分考虑他本人的意愿,这一司法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受保护权与儿童参与权之间的张力。
2. 儿童受保护权与发展权之间的冲突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尊重儿童基本权利的原则,所有儿童都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和发展。[1]但儿童发展权的维护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可分离,在生活安置上,维护儿童的受保护权和发展权,有时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从“南京虐童案”来看,小宝的生父母是安徽农民,家庭经济压力大,经济抚养能力有限,因此主动将小宝送给李某抚养。而李某夫妻社会经济地位高,是典型的中产家庭,他们为小宝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小宝已经与李某建立了亲密的依恋关系。如果李某能够改变教育方法,将小宝交由李某抚养,在精神、情感、物质等方面,可能更有利于小宝的发展。在小宝的生活安置上,司法机关从维护儿童受保护权出发,裁定由其生父母监护。这种安排不仅忽视了小宝与养母之间已经建立的情感关联,而且不利于儿童发展权的维护。根据媒体报道,小宝离开南京回到家乡后,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学习成绩下降。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尊重儿童基本权利、无歧视、尊重儿童观点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保护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四项基本权利。但在儿童保护的干预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可能发生权利冲突,甚至儿童权利内部也可能出现张力。仅仅从“南京虐童案”的司法实践来看,维护了儿童的受保护权,却忽视了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难以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尊重儿童基本权利、尊重儿童观点的原则,很难说这是理想的儿童保护行动。
三、加强儿童保护的制度创新
对儿童虐待与体罚管教的认知分歧、司法正义和社会恢复之间的张力、儿童权利维护的多重冲突,构成了儿童保护实践的现实困境。走出困境,消解张力,促进儿童权利维护的平衡,需要加强儿童保护的制度创新。
(一) 推动儿童虐待的社会问题化,提升对儿童虐待的共同定义
虽然儿童虐待问题现实存在,儿童受虐致伤致死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但在我国“儿童虐待”至今未被建构为一个社会问题,客观存在的儿童虐待现象还缺乏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的持续关注和集体建构。社会问题具有客观现实性和主观建构性,它的存在不仅依其是否客观存在,而且取决于它是否得到了行动者的关注,是否被行动者主观上接受为社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社会问题是对社会现象的主观定义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问题化的过程,是多方行动者在主体间性互动的基础上进行磋商与对话,逐渐达成一种共同接受的认识与问题解决方案的活动。其中包含着各社会群体对社会现象的不同认识与回应,及其围绕问题认识与社会回应展开的协商、冲突,直至形成对议题的共同定义。[13]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推动社会对儿童虐待的普遍关注,并整合不同的利益、价值、认知的人们对这类现象的理解与定义,才能将儿童虐待现象社会问题化。当社会普遍认识到打骂孩子不是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而是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甚至成为社会问题时,才能形成人们对儿童虐待问题的普遍共识,才能引起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方面的行动。
儿童虐待是一个文化敏感性的概念,对它的界定要结合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处境。正如苏珊·比赛尔(Susan Bissell)所言,对儿童保护的界定必须充分理解儿童及其文化和处境,否则会导致片面武断的界定,而这种武断界定可能使得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儿童保护风险的发生,也可能违背儿童权利,只有基于文化自觉和情境自觉的儿童保护实践才更加有效。[14]正如电影《刮痧》所反映的那样,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样的行动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中国文化认为刮痧是一种中医传统的诊疗技术,而美国文化认定为儿童虐待。对儿童虐待的定义既不能以父权中心主义文化为借口,掩盖儿童虐待的事实,也要充分考虑本土文化和具体情境因素,提出切合中国本土情境的儿童虐待定义。
(二) 倡导支持家庭的儿童福利政策,推动儿童、父母、国家之间的权利平衡
对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干预包含了国家干预、家庭价值、父母亲职权和儿童权利等不同的要素,如何平衡这些要素是儿童保护需要考虑的焦点。儿童保护以一定的儿童福利政策为依托,儿童福利政策集中体现了对儿童抚养和照顾的政府干预。在宏观儿童福利政策上,强调政府干预需要平衡儿童、国家、父母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干预应该重视家庭需要、优势和资源,通过支持家庭儿童抚育功能的发挥,来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
不同的儿童福利政策模式体现了国家介入儿童保护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根据儿童、父母和政府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福克斯·哈丁(Fox Harding)比较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父权主义、父母权利中心和儿童权利中心四种不同类型的儿童福利政策。自由放任主义的儿童福利政策认为,儿童照顾是家长的权责,应该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介入。而国家父权主义强调,国家公权享有维护儿童权益的职责和干预家庭的合法性,当发生儿童虐待的风险时,国家应该积极主动介入,甚至提供替代性照顾。父母权利中心模式主张,国家应该尊重父母的监护权,只对儿童抚养功能失调的家庭提供有限的干预。儿童权利中心模式从儿童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出发,强调维护儿童权利。[15]西方儿童福利的发展已经进入“儿童保护和家庭支持融合时期”,尊重家庭及父母权利成为主导的政策取向,国家干预体现为支持和提升家庭的儿童抚育功能。[16]以美国的儿童福利政策为例,其发展取向越来越强调家庭价值、尊重父母权利与适度政府干预介入,以体现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协调、政府干预背景下儿童权利和父母权利之间的平衡,其实质是国家干预主义前提下,对家庭为本理念的理性回归。[17]概言之,儿童问题连接着儿童、家庭和国家,要平衡父母权威、政府干预和儿童权利三者的关系,儿童福利政策不仅要保护儿童合法权利,还要尊重父母的权威和家庭的抚幼功能。
我国的儿童福利政策正在逐渐从残补式走向适度普惠制,儿童虐待问题的处置也走向有限的国家干预。自“南京饿死女童案”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颁行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八种情形可以依法撤销父母的监护权。[18]这使得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父母等监护人侵害儿童权利行为的司法干预被激活,[10]表明儿童虐待问题被纳入国家干预范围。2016年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遭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纳入困境儿童保护机制范围内,[19]民政部建立了《受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引》。但在工作实践中,会尽力促进家庭完整与融合,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非常严谨慎重,只有万不得已才将儿童带离家庭。这表明我国的儿童保护实践依然非常强调家庭的儿童照顾职责和抚养功能。
如果儿童福利体系不能整合家庭生活背景中拥有的丰富性和优势,这个福利体系就不能有效地对脆弱儿童和困境家庭的需要做出回应。除了保护儿童安全外,维护永久并稳定的家庭联系同样是儿童的需求,要保证儿童是在稳定、持续、永久的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需要通过提供家庭支持预防儿童虐待风险,促进儿童的积极发展。[20]在我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依然相对强大,家庭价值和资源不可忽视。具有中国文化敏感性的儿童福利政策应该以家庭为本,一方面,强调父母是儿童抚育的权责主体,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另一方面,在父母亲职权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上,政府与父母不是一种对立关系,政府不是替代而是支持家庭更好地发挥儿童抚育的功能,推行一种支持家庭的儿童福利政策。
(三) 整合家庭服务和儿童保护,提升家庭儿童照顾功能
儿童保护包括宏观政策和微观模式两个层次,在强调儿童、国家、家庭三者权利平衡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下,需要推动儿童保护和家庭服务相融合的儿童虐待干预模式。即以家庭为干预单位,通过家庭维护服务和家庭重整服务,对受虐儿童及其父母都开展辅导,维系适当的亲情连结,改善父母抚养行为,修复和维护家庭的儿童照顾功能,最终维护儿童权利,满足儿童需要。
儿童保护和家庭服务是西方儿童虐待问题的两种干预模式。前者是政府对儿童抚养角色失当的父母采取司法途径为主的干预形式,政府通过转移或者取代父母监护权来实现保护儿童,容易导致政府与家长陷入对立冲突中。后者将儿童虐待视为家庭结构功能失调的表现,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与家长合作、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帮助家庭恢复儿童抚育功能。[21]在儿童权利的话语下,西方儿童保护模式呈现出综融趋势,即注重发挥儿童及其系统的优势和资源,强调“父母参与”“伙伴关系”,明确国家、社会、家庭等不同主体的福利责任。[22]即使是儿童保护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逐渐走向儿童保护模式和家庭服务模式的整合。从1980年的《收养支持和儿童福利法案》(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建立了“家庭维护与支持服务项目”(Family Preserv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 Program)和“促进家庭安全稳定项目”(Promoting Safe and Stable Families Program),通过了《收养和安全家庭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和《维护儿童和家庭安全法案》(Keeping Children and Families Safe Act of 2003)。这些举措确立了家庭服务在美国儿童福利制度体系中的地位,标志着美国从片面武断地强调儿童保护,转向同时强调家庭服务和儿童保护。[23]
在中国,从当前来看,提升儿童虐待干预方法的文化敏感性,应该以家庭为干预单位,为家庭提供支持、资源和服务等,发挥儿童家庭系统的优势和功能。在我国台湾地区,儿童保护的“家庭干预计划”包括家庭功能与儿童安全评估、亲职教育、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儿童安置评估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方案。儿童虐待的干预主要通过家庭维护服务和家庭重整服务来促进家庭儿童抚育功能的恢复与提升。通过社会工作专业评估,当儿童继续留在家庭内没有风险时,可提供家庭维护服务;当面临高度风险时,可先将儿童进行寄养安置,提供家庭重整服务,以促进儿童回归家庭。[24]虽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针对发生儿童虐待风险的程度不同,但都是以维持亲子依恋关系、降低外部干预对亲情关系和家庭伦理的破坏、恢复和提升家庭的儿童照顾功能及最大限度维护儿童利益为目标。
(四) 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以跨界合作寻求司法正义与社会恢复之间的平衡
儿童虐待问题需要司法干预和法律权威来惩戒施虐行为、维护儿童权利,但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家庭抚养功能的发挥还需要专业社工的参与,通过跨专业、跨部门的合作,达到司法正义和社会恢复之间的平衡。切实维护儿童权利,满足儿童需要,更需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在儿童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在儿童虐待的干预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承担着重要的职责。首先,举报初查。在强制举报制度下,接到学校、医生、社工、邻居、基层的举报后,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要展开调查,筛查是否存在儿童虐待问题。其次,调查评估。儿童受虐风险和儿童保护需求的调查和评估需要社工的参与。儿童虐待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如何降低风险发生率,儿童及其家庭是否有紧急需要,家庭具有哪些优势和资源,是否需要申请紧急保护,需要社工的调查评估和专业判断。再次,制定儿童保护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要召集家庭成员、律师、儿童及其他有密切关联的人员,为儿童及其家庭制定服务计划,商议具体明确的儿童保护方案,以确定给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内容和类型、儿童安置与抚养的方式等。最后,执行儿童保护计划。专业社会工作者依据儿童保护计划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包括通过链接与整合资源,帮助家庭解决经济困难来改善儿童成长环境;通过家庭咨询辅导、亲职教育,提升父母抚养方式和教养观念;通过儿童托育等服务,来补充父母职责;通过协调家庭关系、疏导儿童和家长情绪,解决家庭和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2016年第六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并运行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五位一体的儿童保护机制,这一制度体系的顺利运行需要社工专业的参与及其与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第一,监测预防机制要求强化家庭监护责任,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定期随访等服务,帮助他们改善儿童抚养方式,提升其监护能力。第二,强制报告机制要求学校、医院、村居、社工机构主动报告,社工机构负有发现报告的义务。第三,应急处置机制下,警察依法对监护不当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训诫,对儿童虐待行为开展刑事侦查,专业社会工作者须参与儿童虐待的现场处置。第四,通过评估帮扶机制,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接受委托对儿童安全处境、生活保障、家庭监护、身心状况等开展评估,并提出儿童虐待的干预措施,开展家长的教育辅导和儿童的身心康复服务等。第五,监护干预机制中,当存在儿童虐待的高风险,需要委托监护、临时监护或者转移父母监护权时,司法部门需要参考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以裁定是否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必须转移父母监护权、哪种安置方式更切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由此可见,社工专业的高度介入并与司法部门密切合作是我国儿童保护机制的重要内容。

①案件过程根据央视网法治在线报道整理,“南京虐童案”一审庭审纪实 [EB/OL].[2015-10-16]. http://news.cntv.cn/2015/10/16/VIDE1444972678893820.shtml.
②南京本地宝报道, “南京虐童案”9月28日开审养母李征琴拒认罪[EB/OL].[2015-09-28]. http://nj.bendibao.com/news/2015928/57703_3.shtm.
③“南京虐童案”养母企图撞墙自杀法院决定对其逮捕[EB/OL].[2015-09-29]. http://nj.bendibao.com/news/2015929/ 57751.shtm.
④新华网报道,南京虐童案涉事男童:不恨养母都是为了我好[EB/OL].[2016-03-23].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6-03/23/c_128824578.htm.
⑤中国青年报报道,南京虐童案孩子生母:判决结果太不近人情了[EB/OL].[2015-10-11]. http://zqb.cyol.com/html/2015-10/11/nw.D110000zgqnb_20151011_4-04.htm.
⑥南京本地宝报道南京虐童案养母出狱,生母下跪道歉大喊对不起[EB/OL].[2016-03-13].http://nj.bendibao.com/news/2016313/60703.s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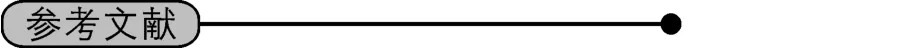
[1]儿童权利公约[EB/OL].[2017-8-30]. http://www.un.org/chinese/children/issue/crc.shtml.
[2]尚晓援. 儿童保护制度的基本要素[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14(8): 2-5.
[3]CICCHETTI D, CARLSON V. Child maltreat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
[4]WHO.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R].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5-16.
[5]祝玉红. 聆听与尊重: 儿童权利视角下对儿童虐待经验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3(4): 50-54.
[6]乔东平, 谢倩雯. 中西方“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逻辑根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1): 25-32.
[7]彼特·博格,托马斯·卢克曼. 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M]. 邹理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27-34.
[8]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0:48-74.
[9]郭伟和. 走在社会恢复和治理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述评[J]. 社会建设, 2015(4): 38-4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主席令第六十号)[EB/OL].[2016-03-14]. http://www.gov.cn/zhengce/2006-12/29/content_2602198.htm.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EB/OL]. (2001-05-30).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1-05/30/content_5136774.htm.
[12]李静, 宋佳. 家庭儿童虐待中的权利冲突及其法律控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5(12): 121-126.
[13]葛忠明, 迟兴臣. 社会问题: 过程及其实践的空间[J]. 文史哲,2003(5): 138-143.
[14]BISSELL S, BOYDEN J, COOK P, MYERS W. Rethinking Child Protection from a rights perspective: some observations for discussion. [EB/OL]. [2018-01-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scientific-contributions/2053964005_Susan_Bissell.
[15]KIRTON DEREK. Child social work polic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9: 7.
[16]乔东平, 谢倩雯. 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J]. 东岳论丛, 2014(11): 116-122.
[17]满小欧, 李月娥. 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94-98.
[18]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等.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EB/OL]. (2014-12-29).http://www.kids21.cn/zcwj/201412/t20141229_308405.htm.
[19]国务院.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EB/OL]. (2016-06-1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6/content_5082800.htm.
[20]JENSON J, FRASER M. Social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family a risk and resilience perspectiv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Inc. 2006: 23.
[21]GILBERT N. Combating child abu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rend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
[22]刘玉兰, 彭华民. 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理论转型与实践重构[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3): 5-11.
[23]胡杰容. 家庭维护服务: 美国实践与中国意义[J]. 澳门理工学报, 2013(2): 149-155.
[24]沈黎, 吕静淑. 台湾儿童保护服务的实践与启示[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5): 7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