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交友:1940年代的夏志清(上)
2018-05-17孙连五
孙连五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1942年,夏志清与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吴新民、丁念庄、陆文渊;后排左起:王楚良、夏志清、张心沧)
在学者夏志清的人生历程中,有两个时期无疑是最关键的,即1940年代和1950年代。目前,学界重点关注的是夏志清在50年代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活动。1961年,夏志清历经数年写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著作不仅开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使得他能够立足欧美汉学界。当然,也正是因为这部著作,确保了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职。此后,尽管夏志清仍然对中国文学有新的思考和认识,但是毫无疑问,对其而言,没有哪个人生阶段能够比1950年代更为重要。如果说1950年代是夏志清在学术上的发轫期与收获期,那么1940年代可说是夏志清学术研究的沉潜期。夏志清本人对1940年代的人生经历十分看重,他接连写了《读、写、研究三部曲》《初见张爱玲 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红楼生活志》《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耶鲁谈往》等多篇文章,回忆他在1950年代的大学教育、文学阅读以及交游活动,这个十年对夏志清后来的人生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2年,夏志清在沪江大学外文系完成学业,在经历了几年迷茫的人生之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宏大志向寻找出路。1947年,夏志清的人生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在北大担任助教的他考取了“李氏留美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此后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为什么夏志清能够取得成功?如果对他在1940年代的人生经历进行综合的考察,我们就能发现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了1940年代的知识积淀对夏志清人生走向的重要影响。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夏志清的相关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夏志清在1940年代的文学活动,对这段时期夏志清的人生经历进行挖掘和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地梳理他在1940年代的文学教育、与西洋文学的关联及其与现代文坛的互动情况,而且能够比较清晰地窥探他在四十年代的文学接受对其嗣后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潜在影响。
一
在1940年代,夏志清完成了从沪江大学到耶鲁大学学院教育的转变,他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上海教会大学毕业生,一跃而成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夏志清在1950年代初完成了毕业论文,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奠定了他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基础。从这之后,夏志清才得以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并把精力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他是如何从一座籍籍无名的教会大学跨入一座蜚声世界的著名大学的?他的青年时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探讨。

1937年,夏志清(后排右)与父母及哥哥夏济安合影于上海
1938年秋,夏志清从上海大夏附中毕业后,考进了沪江大学。这所大学由在华美国南北浸礼会的传道士创建,1900年庚子拳变之际,美南浸信会华中差会及美北浸礼会华东差会的传教士,纷纷逃到上海避难,他们均感觉需要合作兴办高等教育,培养教会及社会急需之人才,拓展事工。随即由两会代表草拟方案,募集资金,在上海东北郊外杨树浦黄浦江畔选定校址,着手兴建校园。1906年,开办神学院并开始招收学生。1911年,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改称上海浸会大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该校建设成了中国水平较高的教会大学,学校环境优美,距离公共租界和上海市中心不远,交通便利,不染繁华。“校园内栽满柳树和四季常青的灌木,铺设草坪,修筑了网球场、足球场和田径跑道。二三十幢高耸的洋楼散布其间,呈现一派充满异国情调的景色。”1930年代,华人教育家刘湛恩任校长,沪江大学迎来了快速发展。刘湛恩1896年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从在东吴大学毕业后,受美北浸礼会资助,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其博士导师是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1928年,年仅32岁的刘湛恩出任沪江大学校长,提倡将沪江大学办得更加基督化、中国化,他先后完成了校名注册、立案,使得沪江大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认可的教会大学,继而起用了大批华人学者担任行政和教职工作,使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学逐步走向中国化。在刘湛恩的领导下,沪江大学的办学规模和社会声誉达到空前的顶峰。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沪江大学的黄金岁月便被这场战争的炮火打断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沪江大学校园被日军侵占,刘湛恩激于义愤,参与反日活动,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领袖之一,遭到日本人的嫉恨。1938年4月7日,刘湛恩在回校候车时,不幸遇刺身亡,终年42岁,他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界为国牺牲的先驱之一。刘湛恩去世后,沪江大学伴随着上海的沦陷走向没落。在紧张的战局环境中,上海各大高校为了坚持办学,不得不转入租界寻求庇护。当时,沪江大学校园被毁,为了解决图书馆、实验室等办学资源缺乏以及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学校与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6所华东地区教会大学达成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建立了联合图书馆实验室。夏志清在1938年入学时,“那时上海郊外都被日寇占据,大学都搬进了公共租界,在办公大楼租两、三层楼面,毫无校园可言。鹿桥《未央歌》里所记载的那种甜甜蜜蜜的校园生活我们都没有享受过,每天上学等于去办公,挤上电车、公共汽车,下了课,再挤上车回家”。夏志清所提及的鹿桥(吴讷孙),1935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后来休学一年,南下游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因为时局的关系,北方很多高校迁往西南地区办学,鹿桥在1938年辗转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外文系,他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讲述了一代年轻人青春和爱情的校园故事,展现了抗战时期年轻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但夏志清没有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在初创时期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抗战大后方的知识青年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也是他无法想象的。诗人穆旦在入读西南联大两年后,曾写有文章谈论学校发展之艰难。第一个困难是穷。西南联大在日军空袭中遭到数次轰炸,设备尽毁,虽然有所增添,但仍无法满足学生需求。教职员工资低,难以生存,很多教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自力更生。学生的生活更苦,一般都是“面有菜色”。另一个是校舍的苦难。由于校舍太少,“许多人睡在一间小屋子里,无法安静是不用说了,而昆明又多流行病,个人健康也无法维持”。不管是身在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抗战时期的青年学子就这样在战争的炮火中开始了对理想的追求。
沪江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特别强调英语作文及会话,在1930年代的沪江大学,“英文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学生对中文缺乏兴趣以及中文能力的低下。沪江大学总共有550名左右的本科生,其中224人学商,70人学教育,134人学化学及医学预科,192人列名文学院。文学院之中,大多数主修社会学与政治学,只有一小部分主修英语,几乎无人主修中文”。对于夏志清来说,他为什么选择英文系?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一方面,夏志清从小对英文就有兴趣,喜欢看英文杂志书籍。举家迁到上海生活后,夏志清又养成了看好莱坞电影的习惯,英文作为一种语言手段,能够加深他对英美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夏志清的专业选择亦有可能受到了哥哥夏济安的熏染。夏济安在1935年入读中央大学哲学系,后来因病休学一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夏济安转学至光华大学入读英文系。夏济安进入光华大学后,所阅读的英文书籍、刊物都对夏志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沪江大学英文系的四年教育,开启了青年夏志清对西洋文学的系统接受历程,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至于夏志清在沪江大学选择了哪些课程,根据《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提供的课程表,我们可略知大概。沪江英文系属于文学院,其设置的主要课程有修辞学、读文、小说、文选、散文、诗选、近代戏剧、演说学、英国文学史、短篇创作、莎氏乐府、文学概要、圣经文学研究、新闻学等。从以上课程设置,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像“诗选”“近代戏剧”“莎氏乐府”等都是夏志清感兴趣的方向,他对英诗、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在此时已经开始萌芽。在沪江英文系所有的授课教师中,有两个外国人对夏志清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令他记忆尤深。一个是贝特女士(Juanita Byrd),教授英语作文课,教书很认真,对美国文学比较了解。曾经在课上把夏志清的作文当着全班读了一遍,对夏志清的鼓励很大,以至于他“以后英文作文,特别用心。直到今日,写起英文论文来,在造句遣词方面,总是精益求精,有时写得顺手,真觉得乐趣无穷”。另一个是夏志清的学士论文指导老师高乐民(Inabelle Coleman),她是个地道的传教士,对文学没有研究,教英文练习、新闻学等课程。夏志清的学士论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英国诗人丁尼生,论文题目是
The Mind and Character of Tennyson
,主要研究丁尼生的心灵和性格。夏志清对丁尼生产生兴趣是在高三那年,他的哥哥夏济安正入读光华大学英文系,师从著名学者张歆海。张歆海很推崇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夏济安在家里常吟诵丁尼生的诗,引起了夏志清的好感。他在1941年暑期修完大三学业后,就开始专心读《丁尼生全集》,并且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是外国人于1854年在上海租界成立的行政组织机构,由万国商团、警务、卫生、教育、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下设法院、监狱等机构,从事市政建设、治安管理等行政管理活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定期出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告》。当时上海工部局图书馆馆藏英文资料显然要比上海其他各大高校图书馆更丰富,时任工部局图书馆主任的是俄裔美国人亚扶锡莫洛夫,根据他在1941年撰述的图书馆报告,可知本年借出书籍共212725册,比上一年多34437册。其中,小说类英文书籍136696册,非小说类英文书籍52473册,儿童英文书籍651册。改年拨发专供购书款共40000元,添购书籍共1837册,其中,英文书籍792册。从1941年12月1日起,工部局图书馆搬迁至福州路567号新馆,面积约8000余方尺,“舆论一致认为本馆历来房屋之占有最佳者”。可以看出,工部局图书馆的借阅量相当大,夏志清在上海时期阅读的不少外文书籍应该都是从这里获得的,他也找到了几种与毕业论文写作相关的研究资料。然而,他的论文后来被同学王弘之借走,所以并无副本保存。据夏志清回忆,沪江大学时期的学士论文参考资料太少,自己对文学批评毫无研究,可能比较幼稚。1943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接收了上海租界,工部局宣告结束。此时,大学已毕业的夏志清也陷入了迷茫之中,前途未卜,人生没有着落,他该去往何处?迫于生计,他于1944年考进了伪政府上海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
沪江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上海,此时赋闲在家的夏志清,因为亲戚徐祖藩接管了台湾航务管理局,于是跟他去台北做公务员。从上海海关到台北航务管理局,这种铁饭碗的工作并不是夏志清所追求的,他人生的转变是从1946年开始的。1946年,成立八年之久的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原址复校,刚任教一年的夏济安在6月返回上海。8月,夏志清从台北辞职回到上海,全家人短暂团聚。9月底,夏志清跟随哥哥夏济安乘船北上赴北京大学教学。夏济安在1943年时就离开上海奔赴内地,先后在西安、昆明等地教英语,1945年才进入西南联大,他在这里教授时间不长,人脉不广,与北大上层似乎往来不多,交情也不深,他结交最多的只是资历比他稍长的卞之琳、郑之骧等人。夏济安在联大教课只有一门大一英文(H组),这门课基本是由资历年轻的教员任教。到了北大之后,夏氏兄弟在北大圈子里仍然属于很边缘的教员,但北大的这段短暂的教学经历,却成为夏志清人生转向的一个跳板。

1942年,夏志清获得学士学位
1948年,著名军火原料巨商、华侨企业家李国钦同意出资设立奖学金,资助北大年轻教员出国留学,全校只有三个名额,夏志清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他写的关于布莱克的研究论文,得到了外文系教授燕卜荪的赞赏。因为燕卜荪是位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夏志清还请他写了申请美国大学的推荐信。但是,夏志清考取奖学金后,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当时有很多年轻教师都参加了考试,但他们对夏志清的录取非常不满,像他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在北大教职员中闻所未闻,有什么资格留美?所以,有很多讲师、教员联袂到校长室找胡适抗议。但胡适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坚持考试录用结果。胡适的这一决定,对夏志清能够获得留学机会非常关键,他也成为夏志清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夏志清详细地记述了面见胡适的三次过程,但他与胡适聊得并不投机。虽然胡适能够力排众议,给予了夏志清出国的机会,但实际他对夏志清并不十分看好,因为夏志清出身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在抗战中已经没落,很难与燕京、齐鲁、辅仁等大学比肩,在胡适眼中,出身沪江的夏志清必定学问一般。胡适也可能出于好意提醒,在择校选取上,他建议夏志清不要选择名校,而应该选择较容易的小大学进修,这样可以顺利毕业。但夏志清偏偏志存高远,他是有雄心和抱负的,可以说,在经历了几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知,对留美生涯也相当自信。另外,胡适还告诫夏志清赴美后要规规矩矩做学问,不要听信艾略特、庞德等现代派叛徒的邪说,夏志清当然不认同,他在这一时期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已经具有了很深的“同情之了解”,对于艾略特的诗歌和诗歌理念,夏志清已经非常熟稔,他认为胡适对世界文坛的认识已经与时代脱节了。夏志清在北平时,尽管薪水很少,还是毅然购买艾略特的诗集《四个四重奏》,这足见他对艾略特的钟爱。
1947年底,夏志清到了美国后,先是投奔到垦吟学院,跟随新批评南方领袖兰色姆。他在国内时就已经与兰色姆通信,并建立了联系。在夏志清看来,尽管兰色姆是一位名师,但垦吟学院却是一座小庙,他并不想在此继续求学,于是有了另投他处的打算。经过兰色姆的力荐后,夏志清最终辗转投入耶鲁大学,师从名家布鲁克斯,这也预示了夏志清与新批评的缘分。1948年春,进入耶鲁后,夏志清开始接受全新的学院教育。耶鲁大学是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1701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一所与哈佛大学并驾齐驱的老牌名校。当时,耶鲁外文系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如语言学家曼纳(Robert J.Menner),戏剧研究专家普劳迪(Charles T.Prouty),比较文学专家韦勒克(René Wellek),英诗专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帕德尔(Frederick A.Pottle)等,并且在四五十年代一跃成为美国新批评的重镇。虽然在耶鲁大学有布鲁克斯、韦勒克、沃伦、维姆萨特等一众新批评的捍卫者,但同样也有像帕德尔这样杰出的旧派学者,新派、旧派并存的学者队伍,也体现出了耶鲁大学兼容并包的名校风范。其中,对夏志清影响最大的两个老师布鲁克斯和帕德尔就是一对冤家,二人曾因为对雪莱的不同评价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很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学术研究以布鲁克斯为榜样,但在选择博士指导教师时却选择了帕德尔。就是在这种新派与旧派并存的学院环境中,夏志清开始了对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夏志清在耶鲁大学
1948年春季学期,夏志清选择了两门课程:一门是由普劳迪教授讲授的“英国戏剧(1558-1625)”,一门是由马兹(Louis L.Martz)教授讲授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从这时开始,夏志清才真正踏入学术研究的大门,他写的一篇论伊丽莎白时代早期剧作家乔治·丕尔的论文,长达47页,这篇研究报告体现出夏志清进入耶鲁后所接受的正规学术训练。他在论文写作中极力模仿布鲁克斯解读诗歌的方法,很快就对新批评的技巧有了充分认识。在夏志清看来,“二十世纪的creative writer大多代表各种attitudes,没有什么系统的思想,把一首诗,或一个人的全部作品,从rhyme、meter各方面机械化地分析,最后总有些新发现,并且由此渐渐可脱离各家批评家opinions的束缚,得到自己的judgment。”夏志清认为,只有把诗歌批评的技巧运用到小说批评中去,才是“正当批评”的路径,可以看得出来,夏志清在1950年代评析中国现代小说的方法,可以追溯至他在耶鲁时期所形成的思考。除了阅读课程指定的书籍,夏志清还非常关注新批评派刊物,比如《垦吟季刊》《西旺泥季刊》《南方季刊》《耶鲁评论》,这些刊物极大地开拓了夏志清的学术视野,他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接触新批评,但其认识毕竟有限。夏志清阅读了众多名家名文,使他掌握了美国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与要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刊物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批评理路。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旧白话短篇小说里的社会与自我》在兰色姆主编的《垦吟季刊》第24卷第3期夏季号刊出,尽管新批评在1950年代后期遭到了猛烈攻击,逐渐从鼎盛走向衰落,但夏志清却仍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新批评刊物上,这十足地体现了他与新批评派之间的渊源。
1948年秋季学期,夏志清选了三门课,分别是“弥尔顿”、“二十世纪文学”以及“古英语”。其中,布鲁克斯所授“二十世纪文学”对夏志清的学术研究帮助最大。这门课主要以艾略特、叶芝、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等现代作家为研讨对象,注重文本细读,着重考察学生对小说内在结构的分析能力。布鲁克斯以诗歌研究成名,他对小说的评析方法与英诗解读技巧如出一辙。在这门课上,夏志清集中精力阅读了不少近代小说,后来,他都拿来用之与中国现代小说作对比。1949年,夏志清在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继续攻读博士的决定,他选择了“华兹华斯的时代”、“乔叟研究”、“古北欧语”三门课,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业之中。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整个国家的时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早已失尽人心,蒋介石的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解放军却势如破竹,相继攻克南京、上海。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新政权的诞生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他们对这个新的国家、新的政权既有憧憬又有忧虑。这时候,同在耶鲁英文系就读的两位中国年轻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
与夏志清的选择不同,另一位年轻人放弃了继续攻读文学博士的机会,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他就是李赋宁。李赋宁与夏志清所做的不同选择,也代表了1949年时代变局背景下,留学海外的知识青年两种人生抉择。他们为什么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与他们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李赋宁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求学经历迥异于夏志清,他出生在一个新派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仪祉早年在京师大学堂学习,后留学德国,主攻水利工程。李仪祉回国后先是在大学任教,广结好友,其中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宓等人。李仪祉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杰出学者,在他就任陕西省水利局长时,极力推动农民修建水渠种植棉花,使当地经济大为改观。1938年,李仪祉积劳成疾辞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他去世后,被誉为“人民的工程师”、“中国现代水利工程之父”。李仪祉在知识界的声誉也颇高,据李赋宁回忆,胡适曾经评价他是一个“great man”。这种优渥、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境,对于少年李赋宁的成长显然有很深的影响。而夏志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夏大栋混迹商界,虽然也有不错的薪水,但是在抗战爆发前,他就将妻子儿女送往法租界,独自一人到大后方经商,要养活上海一家老小,仍然不容易。夏志清也曾回忆那段时期:“我们兄弟手边没有零用钱,即使有勇气找对象,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看电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专心读书。”如此不同的家庭环境也造就了不同的个人性格,从李赋宁与夏志清对耶鲁大学生活的回忆就能够看出来,李赋宁性格外放,人脉也很广,他在耶鲁很擅于交际,与周围的同学、老师交往颇多。而夏志清在耶鲁大学期间,几乎长期处在一种封闭的苦读环境里,除了写信给哥哥夏济安倾诉外,他少有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李赋宁与夏志清在出国留学之前的教育背景差别也甚大,李赋宁出身于清华大学英文系,此后,他还获得了西南联大研究生学历,并留校任教。李赋宁在求学过程中得到过众多名师的指导,其中有吴宓、叶公超、陈福田、杨业志、吴达元等人,这样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堪称顶尖。所以,从李赋宁的教育背景来看,应该说他在国内受到了一流的大学教育,这培养了他很高的眼界和视野。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对他影响很深,尤其是激发了他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李赋宁出国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学成回国尽自己一份力量,把清华大学外文系办成既重教学又重科研的系,与中国文学系看齐”。夏志清出身沪江大学,在教会大学里名气不大,在赴美之前也没有得到过名家名师的具体指导,他的青年时代基本是在上海度过的,这座商业气息浓厚的国际大都市弥漫着各种外来文化,对夏志清影响最大的当属欧美文化,包括各种好莱坞电影、流行杂志等,这种生活环境促成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虽然缺少名师指点,但刻苦钻研、锐意进取的学习经历,使得籍籍无名的夏志清在众多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夏志清之所以出洋留学,并不像李赋宁一样有着崇高的家国情怀,他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个人高远的理想和追求。
1949年底,李赋宁和夏志清对中国的时局做出了不同的判断,最终李赋宁放弃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而夏志清选择继续完成学业,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对于夏志清而言,他的选择奠定了其在美国进入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基础,也确保了他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夏志清的成功正是通过他在1940年代的两次大学教育完成的。
二
夏志清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就抱定宗旨不去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他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英美文学以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在整个1940年代,夏志清阅读了大量的欧西文学,由于他以西洋文学研究为志业,所以对现代文坛不太关注,对现代文学涉猎也不多,哪怕是像张爱玲这样的当红作家,夏志清也知之甚少。可以说,在195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前,夏志清的学术追求和知识储备一直局限于西洋文学,尤其是英诗、戏剧。但是,他的这种以西方文学为资源的知识结构,却深深地影响了其中国文学研究。通过对1940年代夏志清阅读视野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阅读范围主要集中在西洋文学和批评两个方面,这些文学资源构成了他后来学术研究的根基。
夏志清在赴美之前对西洋文学的阅读,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尤其是英诗,他曾有雄心读遍英国所有名诗人的全集。在沪江大学读书时,夏志清就读完了《丁尼生全集》,并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写了毕业论文。大学毕业后,夏志清开始广泛涉猎各类西洋文学著作,他读书用功之勤奋,有两例可兹证明。一是在赴美的轮渡上,夏志清在三天内即读完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菲茨杰拉德的《大亨小传》,又开始读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二是在台北做公务员的十个月里,夏志清利用空闲时间也读了20多本书,种类繁多,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有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林译小说)、梅尔维尔的《白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柯立基的《文艺生涯》、华兹华斯的《前奏曲》、密德尔登剧作三种、布莱克的预言诗等,尤其是布莱克的诗歌,引起了夏志清的兴趣。他谈道:“大学毕业后不出一两年,我即对布莱克大感兴趣,把他的预言诗读了不少,也看了名批评家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论他的专著”,因为对布莱克预言诗的喜爱,他在北平还买了休勒的《威廉姆·布莱克:视觉政治》(
William Blake
:The Politics of Vision
),夏志清也正是凭着一篇论布莱克预言诗的学术论文赢得了留美名额。在北京大学当助教的几个月里,夏志清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重温德文,二是当代英美批评著作,三是莎翁时代的戏剧,四是布莱克研究。这几个方面的规划与努力,对夏志清求学耶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夏志清在大三时就开始辅修第二外语,他一开始打算选法文,但因沪江大学没有专授法文的教师,他只好选择了德文。经过刻苦的自修,大学毕业后,他已经开始有能力读德文名著,如歌德、海涅的诗歌、席勒的诗剧。有一段时间,他在白天读德文版《浮士德》,晚上则读英文版《神曲》,两耳不闻窗外事,沉醉于西方古典文学之中,怡然自得。获得留美奖学金后,夏志清从北平回到上海小住,在赴美前的几个月里,他又开始重拾德文,期间读了大作家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及长篇小说《殿下》、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作品。应该说,在上海时期自修德文的经历,实际为夏志清攻读耶鲁博士学位打下了基础。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学习十分严峻,尤其对于英国文学博士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学校规定学位申请者除了完成博士论文之外,还要通过三门语言口试,即拉丁语、法语、德语,由于夏志清在上海时期就已打下了德文基础,他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另外两门语言,这是他能够在3年时间里就顺利地拿到耶鲁博士学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代英美作家、批评家方面,对夏志清影响最大的当属英诗人T.S.艾略特。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坛的渊源很深,他的诗歌很早就被译介到中国,在1930年代,诸如叶公超、卞之琳、曹葆华等人都对艾略特进行过介绍,艾略特的诗歌观念对中国现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志清在沪江毕业以后,才开始全面接受艾略特,并私淑其为老师,他把在上海能找到的艾略特的诗集、批评集都读了。他不仅熟读艾略特的诗歌,对于艾略特所谈到的作家,也尽力去读。艾略特曾写了一组讨论莎翁时代剧作家的评论,夏志清都找来读,包括克里斯托弗·马洛、韦伯斯特、西里尔·图尔纳、约翰·福特、查普曼等人的戏剧,在读了大量莎翁时代的剧作之后,夏志清认为:“莎翁时代的戏剧是英国文学的顶峰,不仅莎翁超群绝伦,詹姆士一世时代好多位剧作家同样的文字圆浑有力,畅写七情六欲,无所忌惮,同时代抒情诗人约翰邓比起来,也不免近乎纤巧,不够雄伟”。艾略特特别推崇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他在文章中曾引述了邓恩的名诗《遗物》(
The Relic
)中的一句“腕骨上戴着用金发绕成的手镯”(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来说明邓恩诗歌中不同意象、修辞的对照所产生强烈的效果。后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论张爱玲的《金锁记》时,也引用了这句诗,这很能够说明艾略特对他的直接影响。夏志清除了关注艾略特的诗歌和诗论之外,他还对英美批评界关于艾略特的论著有兴趣。夏志清在拜读了哈佛学者麦西生的《艾略特之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T.S.Eliot
)后就很佩服,早在上海研读亨利·詹姆斯的晚期小说时,他就读了麦西生的《亨利·詹姆斯的主要创作时期》(Henry James
:The Major Phase
),并在1951年将这部著作推荐给哥哥夏济安。对于恩师兰色姆在《新批评》(New Criticism
)一书中将艾略特归类为历史批评家的观点,夏志清也不赞同,他认为兰色姆的论证不够充分。从这一时期开始,夏志清对艾略特的诗学观念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判断。对于在美国批评界广受欢迎的著作《武装的视野》(The Armed Vision
,斯坦利·海曼著),夏志清读了后也不以为然,他认为作者在书中大捧燕卜荪、理查兹、布莱克默(Blackmur)等人,却对艾略特不公(unfair)。在青年夏志清的心目中,艾略特不仅是他的精神导师,可能更代表了真理,他逐渐成为艾略特的捍卫者,这种影响直到他进入耶鲁之后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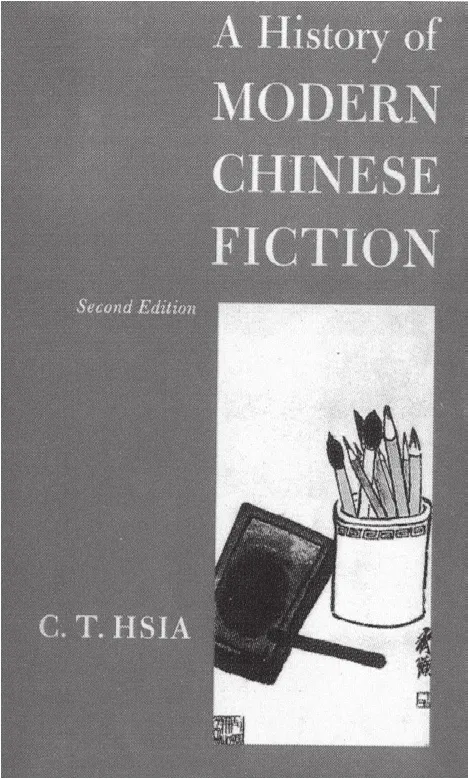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史》1971年增订版封面
除了T.S.艾略特之外,夏志清喜欢的另外一位英国当代作家是阿道司·赫胥黎。他提到:“1942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读艾略特、赫胥黎所有的作品。艾氏的诗集、批评文集能在上海找到的我都看了。赫氏作品丰富,我看了他的长篇小说五六种、散文集七八种,兴致真高。”当时他还应同学之邀写了一篇以赫胥黎为题的文章,名为《赫克斯雷论》,指出:“赫胥黎这个姓氏原是严复为Aldous的祖父Thomas Henry Huxley所音译的,我把它改写成‘赫克斯雷’,不仅音译准确,而且要比文绉绉的‘赫胥黎’响亮得多了。”其实,关于赫克斯雷这个译名,最早的译者应该是张芝联。他曾与好友夏济安、宋淇、柳存仁、徐诚斌等共同编辑《西洋文学》杂志,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洋古代和近代文学。1940年9月创刊,1941年6月停刊,共发行10期,尽管这份杂志创办时间不长,但却是“孤岛时期”上海文坛上一份格调很高的文学刊物。1941年第6期《西洋文学》刊发了张芝联译《赫克斯雷论》,该篇文章译自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先知和诗人》(
Prophets and Poets
)。不仅如此,《西洋文学》杂志早前在第2期刊出的徐诚斌译《曼殊菲儿论》,也是出自该书。这本书介绍了九位英国现代作家,包括吉卜林、威尔斯、萧伯纳、切斯特顿、斯特雷奇、劳伦斯、赫胥黎、曼殊菲尔德。张芝联曾有意要同徐诚斌合力将莫洛亚这本书译成中文,很遗憾,因为战局的关系最终没能实现。由于夏济安是《西洋文学》编辑队伍的重要成员,夏志清对这份杂志并不陌生,他应是读过张芝联的译文。因此可以推断,他将Huxley译作“赫克斯雷”想是受了张芝联的影响。直到很多年以后,夏志清对于赫胥黎的作品依然很关注,给予高度评价:“他(赫胥黎)的散文、短篇小说,没有一篇不是精品,假如我们说赫胥黎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散文家,也不算过誉。”足见他对赫胥黎的喜爱。在北大时,夏志清就读了布鲁克斯的名作《精致的瓮》(
The Well Wrought Urn
,夏译《精致的骨坛》),但他对布鲁克斯的了解可能要更早。1940年,《西洋文学》第4期就刊载了吴兴华的书评,评述了布鲁克斯的新作《现代诗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这部著作涉及到对艾略特、奥登等现代诗人的评价问题,夏志清不可能会忽视。他读完《精致的瓮》后,将之推荐给外文系教授燕卜荪,燕卜荪看后,非常兴奋,因此开始与美国新批评派通信。燕卜荪是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他以《含混的七种类型》(The Ambiguity of Seven Types
)成名,夏志清读了该作也大为佩服。当时,夏志清还读了美国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凯辛(Alfred Kazin)的名作《土生土长》(On Native Grounds
),他对书中论述1930年代以来美国“批评界之两级”一章尤为感兴趣,凯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占据了北极,占据南极的则是比较守旧的、代表传统文化的南方文艺评论家。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1946年就已读了该书,他在当年元月一日的日记里记录:“读Alfred Kazin(卡津)之On Native Grounds
(《论本土文学》),此书详述美国近五十年来之散文文学(189-1940),内容尚充实,我今日读其首三章,关于Howells(霍维斯),Huneker(韩纳克),Stephen crane(柯瑞因),Wharton(华顿夫人),Dreiser(德莱塞)等。诸人中我仅读过Wharton之Ethan Frome
(《伊丹·傅罗姆》),颇喜之,Kazin氏认其忽视现实社会,颇多非议,然其sense of tragedy(悲剧感)与soundless heroism(无声的英勇)有文学上之永久价值,他日多读几本Wharton氏小说后,当可作文辩护之。”不知是否是夏济安将此书介绍给了夏志清,因为他们兄弟二人经常交换读书心得,这也说明了夏氏兄弟有共同的文学志趣和相近的知识背景。凯辛在书中所提到南方文艺批评家,实际就是新批评派,南方领袖就是兰色姆。夏志清读了此书后,就给兰色姆写信,表示愿投其门下。因为夏志清对于兰色姆就职的垦吟学院不太满意,经兰色姆的推荐,夏志清最终辗转进入了名校耶鲁大学。他终生心存感恩,将兰色姆视作恩师。
在耶鲁大学,夏志清以布鲁克斯作为自己学习和超越的目标,他一开始在学术训练过程中所使用的技巧都是模仿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待其对新批评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之后,他便展现出了更大的野心。夏志清曾提及,他计划写一篇文章评论17世纪英国“骑士派”诗人罗伯特·赫里克的名诗《考利纳前去参加五朔节》(
Corina’s going A-Maying
),此诗晦涩难懂,他决心要超越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瓮》一书中对此诗作的阐释。求学耶鲁期间,对夏志清影响最大的一门课程是“二十世纪文学”(由布鲁克斯讲授),该课程主要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作家。夏志清一开始对这门课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早年受艾略特的影响甚深,他的兴趣聚焦于十五六世纪的英国文学,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用功倒不多。因为课程之需,夏志清就找了一些近代小说来读,等读了几个现代作家的作品后,他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读了海明威的一些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战地钟声》后,对夏济安说:“海明威早年故事文笔很干净,你欢喜的Steinbeck的笔调,大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夏济安早年确实很喜欢斯坦贝克,他曾发表书评推介斯坦贝克的小说《摘果记》(今译《愤怒的葡萄》,载《西书精华》1940年创刊号,署名温和),但是夏志清推测斯坦贝克的文风受海明威之影响,则很难断定。对于福克纳的小说,夏志清认为在近代小说里比较特殊,“rhetoric的丰富,为近代人所少有”,这却是事实。对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夏志清认为,“文字很rich,好的地方可追莎翁和Jacobean drama”,将近代作家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与莎翁戏剧、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相提并论,又能看出夏志清早年的文学趣味。对于这些现代作家,夏志清大多是初次接触,他很少参考其他文评家的意见,因而所获得的都是自己的直观感觉,因此,他在将中国现代小说与这些西洋小说作对比时,更多地是靠个人阅读的感觉,至于这种感觉是否可靠,则众说纷纭。当然,在阅读叶芝时,他也参阅了约瑟夫·霍恩(Joseph Hone)编《叶芝的一生》(
Life of Yeats
)以及马克·肖尔(Mark Schorer)等编的《批评:现代文学评判的基础》(Criticism:Foundations of Modern Literary Judgment
)两部著作,这些著述能够加深他对作家的了解与认识。夏志清的阅读范围非常广,除了上述提及的几位名家外,还有一位值得重视,那就是英国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在很多人看来,利维斯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影响很大,这确实毋庸置喙,其实早在1940年代,利维斯的批评就已开始对夏志清产生影响。那时,夏志清在上海读了利维斯的两部著作《诗的重估》(
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和《英诗的新平衡》(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很受触动。利维斯那种锐利、精到的史家眼光,与众不同,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利维斯在西方文坛是一位名气很大、同时争议也很大的批评家,但中国现代文坛对他的介绍似乎并不多。1933年,《新月》第4卷第6期刊出了荪波(常风)的三篇书评,介绍了利维斯(利威斯)的三部著作《英诗之新平衡》《大众的文明与少数的文化》《劳伦斯》,这大概是国内文坛对利维斯最早的介绍。夏志清坦承,对其博士论文写作启发最大就是利维斯的文论。1950年代初,读了利维斯评点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一书之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已经与这位英国批评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夏志清在耶鲁时期的另一项重要的阅读活动,是出于专业学习的需要。为了准备课程论文,他需要查阅大量的参考书目。比如他选了马兹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后,就借阅了与之相关的书籍,如莎翁剧作《维纳斯和阿多罗斯》(
Venus and Adonis
),马洛、查普曼合著的《西罗与里安德》(Hero and Leander
),德莱顿的《恩底弥翁和菲比》(Endymion and Phoebe
)和《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
),乔治·桑兹的《奥维德〈变形记〉的翻译》(Translation of Ovid’s Metamorphosis
)等。为了准备其他课程,他读了大量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弥尔顿的诗歌、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等。甚至在语言学习方面,夏志清也以文学类书籍作为主要的研读对象,他之所以选修“古北欧语”(古冰岛语),是因为他在上海时读过一本古冰岛的小说《聂尔传奇》(Nial’s Saga
),印象深刻,令人难忘。当时,夏志清曾在1944年《天地》杂志第5期以“严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小品文《电影与文化传统》,讲到他读了一部冰岛最有名的小说《火烧聂家庄》(The Story of Burnt Nial
),堪与《水浒》媲美。为博士口试准备法文时,他读了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的《先知和诗人》(如前所述,1941年《西洋文学》杂志就已经提到了此书,夏志清的选择与早年的阅读经历不无关联)、《阿里埃尔》(Ariel
)和瓦雷里的散文,之后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法国学者写的两部《英国文学史》,一部由埃米尔·里格依思(Emile Legouis)和路易斯·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合著,另一部是文学史家泰纳(Taine)独著,通过阅读这些法文书籍,不仅能够提高夏志清的语言理解力,也能够扩大他的文学视野,可谓一举两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