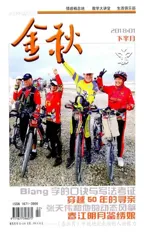狂放贺知章与宽容的大唐
2018-05-15北京丁启阵
◎文/北京·丁启阵

因为写一篇关于贺知章一首《回乡偶记》诗的解读文字,忽然觉得,贺知章简直可以说是唐朝的一面镜子。其人生命运,足以映射出李唐王朝全盛时期的风度与胸襟。
贺知章的狂放不羁
关于贺知章,流传最广的事情有这样几个:一是尚未成名的诗人李白到长安寻求人生发展机会,拜访贺知章。贺知章读李白呈献的作品,读到《蜀道难》诗,大为赞赏,称李白为“谪仙人”,当时就解下身上所佩金龟换酒,跟李白喝了个痛快淋漓。后来又向唐玄宗李隆基推荐了李白。二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写的贺知章醉酒形象,“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三是贺知章的一首《回乡偶书》诗,其中两句疑似诗人自画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大概可以得出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有趣的人。
果然,文献记载贺知章是个有趣的人。他因为善于谈笑,广受士大夫们的爱慕;他的姑表弟、一度做到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陆象先,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这位贺兄真是风流倜傥之人。我跟别的家族子弟分离,再长时间都不会想念。但是,一天没见着贺兄,就会觉得自己变卑鄙庸俗了。”
比有趣更具个性特色的,是贺知章的狂放不羁。《旧唐书》本传说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可见,他年轻时代就已经有狂放不羁、荒诞不经的名声,到了晚年更加随心所欲,不讲规矩。活了七十三岁、原本谨言慎行的孔子说自己“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活了八十六岁、原本就狂放不羁的贺知章,随心所欲那是一定的,不逾矩,大概须改为没有规矩了。
贺知章一直在朝廷为官,晚年官做得还挺大——相当于今天副部级,是高干。但是,他给自己取了个“四明狂客”的大号。在朝廷做着秘书少监的正经官职,却自称“秘书外监”,有不务正业、逍遥自在的意思。更过分的是,他还“遨游里巷”“遨嬉里巷”(分别是《旧唐书》、《新唐书》的原话)。这“遨游里巷”“遨嬉里巷”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是随便出门,在长安的大街小巷里瞎溜达,不顾自己朝廷高官的身份,不乘马坐轿讲究排场,不顾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混迹于市井百姓之间,等等。另一种是特指逛红灯区。唐朝长安位于城北的平康里(也叫北里)是当时的妓院聚集之地,我感觉,贺知章是两种事情兼而有之。
贺知章喜欢饮酒,醉酒是常事。醉酒之后,除了杜甫所说的“骑马似乘船”“落井水底眠”,他还文思泉涌,写诗作文一气呵成。《旧唐书》说他“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看样子,跟李白“一斗诗百篇”情形类似。
醉酒后,还喜欢写书法。有想要他墨宝的人,这个时候只要准备了纸墨笔砚,他一般都不会拒绝,挥毫写上几笔。不过,字数不多,每张纸也就几十个字。就是这样,当时许多人还是把它们当成宝贝,珍藏传世。
八十五岁的时候,因为做了个游览皇帝后宫的梦,上书玄宗请求准许自己出家做道士,并且把老家的宅院舍为道观——千秋观。
贺知章一生命运
对于贺知章,虽然新旧两《唐书》都有传,但因为都不是一人独传,所以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平生经历不是很完整。因此,我们只知道如下一些情况:
青年时代,便以擅长诗文知名于世。三十九岁考中进士。最初得到的官职是国子四门博士,不久转为太常博士。大概因为表弟(姑表)陆象先和张说等人的引荐、擢拔,在丽正殿编辑过几年皇家图书后,转任太常少卿。十三年后,跻身高官行列,升为礼部侍郎,同时加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充太子侍读。高官显爵,位置清要;玄宗本人还亲自给贺知章写了赞词,一时间荣宠无比。
后来,因为一次选人不当,引发世家大族的不满,一度被调任工部侍郎。
大概从六十多岁到八十六岁,贺知章一直在朝廷做着三四品(副部级)干部,不曾降职,不曾外放。到八十五岁时,他决意辞官回乡,玄宗还想挽留,无奈去意已决,只好放他回去。临别之际,玄宗还亲自作诗送别,并且下令皇太子以下朝廷百官,都要参加给贺知章饯行的活动。饯行宴席设在长安近郊长乐坡上,场面极其壮观。
可以说,贺知章的一生,是官运亨通、福禄双全的一生。
贺知章身上的矛盾
作为一个诗人,狂放不羁没有什么问题。但作为一名朝廷高级官员,如此狂放不羁就难免出乎意料。正常情况下,狂放不羁是坎坷不得志者的专利,是隐遁山林或混迹江湖的世外高人的常态。一个官运亨通、福禄双全的人,理应循规蹈矩,谨言慎行,因为他们是社会利益的获得者,心中没有需要宣泄的不平之气,他们应该遵从的是民间训诫“小心驶得万年船”。一句话,如何保住自己业已得到的地位和财富,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但是贺知章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更有意思的是,贺知章的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行得通,而且是大通、亨通,甚至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与信任,长久不衰。太子李亨做皇帝后(史称肃宗),为了报答曾经的老师(贺知章做过多年太子侍读),在贺知章去世后的第十四年,下诏追赠其为礼部尚书,令其官衔百尺竿头更升半级。
有人可能会猜测:贺知章是属于狂放不羁但吏才无碍的非常人才吧。
其实不然,玄宗朝名臣有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贺知章不在其列。贺知章除了诗文方面有一定修养,古书读得比较多些外,政务方面显然是乏善可陈。留下来的,没有什么政绩,倒有两则失败的故事。
早年因时任丽正殿修书使张说的奏请,贺知章跟秘书员外郎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等人一同修撰“六典”及“文纂”,忙活了几年,书并没有修成。
贺知章任礼部侍郎期间,出过差错。惠文太子夭亡,玄宗下令由礼部选任挽郎——出殡时牵引灵车唱挽歌的人。这事由贺知章具体负责。结果,贺知章“取舍非允”即选人不当,引起一帮门阀子弟的强烈不满,聚集众人,闹起事来。情急之下,贺知章竟然不顾体面,在围墙上架了梯子,自己爬上去,露出脑袋冲外边喊话,企图解决问题。他的这一举动,一时传为笑谈。
按理说,犯了这种错误,朝廷应该对贺知章有所惩罚,至少是降职乃至外放。但是,玄宗只是将贺知章从礼部侍郎调任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担任光荣的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升迁为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兼。
贺知章为何得到玄宗的青睐和信任?
乾元元年(758)十一月,肃宗追授贺知章为礼部尚书的诏书,是这样评价的:“……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李唐王朝对贺知章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评价,归纳起来就三点:有学问,修养好,偶尔以开玩笑的方式提点意见。
这不免让我们联想起一个人,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东方朔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滑稽列传》,从中我们了解到,东方朔是善于言谈、爱开玩笑、行为荒诞不经之人。但是,东方朔是以巧妙进谏得到任用、以严肃进谏告别人世(被认为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就是说,东方朔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其实是用心为官的。中间很认真地给汉武帝提出过关于政治得失、农战强国方面的意见。而贺知章是以科举晋身得到朝廷任用、以出家做道士告别人世。相比之下,贺知章则是彻底的狂放不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汉武帝给东方朔做到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位,但实际上并不怎么尊重他,历史上有“俳优畜之”的说法。贺知章跟东方朔的官职级别差不多,都是三四品的官,走的也都是“大隐隐于朝”的路子。但是,他受到的尊敬明显比东方朔多。众所周知,唐朝是引汉朝为自己学习榜样的。不妨猜测,贺知章也有景慕、效法东方朔的成分。从贺知章在唐朝得到的信任、重用情况看,大唐盛世在任用名士方面,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
《新唐书》本传记载,贺知章任太子宾客期间,东宫官员多年没有升迁,当时兼任太子侍读的左补缺薛令之,在墙壁上写字,表达不满情绪。结果被玄宗看到,玄宗写了“听自安者”四个字。意思大概是爱干不干,悉听尊便。薛令之知道后,马上弃官,徒步回了老家。从这个故事看,贺知章表面上行为狂放不羁,其实他内心是有分寸的,他情商很高,至少比同僚薛令之高,尽管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没有什么任性的表现。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贺知章比较超脱,不在乎升不升职。
新旧《唐书》都有贺知章的传,《旧唐书》收入《文苑传》,《新唐书》收入《隐逸传》。这种情况,挺有意思,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后代史家因为自身价值观念的差异,评价贺知章的时候,在重视其诗文才华还是重视其古怪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了分歧。
狂放不羁的贺知章,能够不倒翁似的大隐隐于朝,数十年间岿然不动,官一直做到八十五岁,告老回乡时,最高统治者还对他依依不舍……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李唐王朝全盛时期对于官员的容忍幅度之大。除了汉唐,别的封建朝代,像东方朔、贺知章这种吊儿郎当的人,不是根本就没有晋身之路,就是即使侥幸爬上去了,也会摔得很惨,死得很难看。不是下野,就是下坑,腰斩、灭门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距离我们最近的明清两朝,就是如此。
还是那句老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