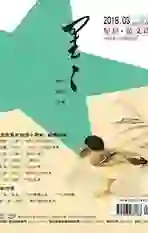很响的月亮(外四章)
2018-05-14马陈兵
马陈兵
我失眠总是因为以下原因: 灵魂的半月过于明亮清澈。
在床上,灵魂一片一片坐起来,未经同意,进出我身体。
暂时这是和平而冷漠的时代。一个中年男人不应该再把自己和太阳联系起来,不应该再和飞鸟经常往来。
“站住!举起手来!”我这样吆喝,但灵魂不理我。这是鬼节之前的第三个秋夜,每一片凉风都鬼一样薄,而灵魂还挡在我前面。
“那个黛臧灰青的河滩有多么无边地温柔!”想起来昨夜我关于夜空的咏叹。河滩上唯一发光的一块石,把水弄得很响。
說 器
人与人语塞话消时,对方寂如眼前一器。
寂中分桠,同干异枝。
或坠薄恶,淡漠疲倦甚而厌,最好眼空无物。
或入清宁,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相看两不厌,山中发红萼。
清宁中有大欣喜。
试以欣喜者论,再投机相得的两个人,一群人,挑灯倾盖或交颈荐席,为长夜饮,为竟夕谈,为三更欢,为白日戏,终不免意足兴阑,静生寂至。
如此,独对三五佳器,或茶盏,或瓦石,或水木,或茵扇,以相得无言之至友佳匹待之,则无一物不为君子佳人,无一器不为木末芙蓉,欣欣遍在,历历自开。
善与器处,客可不来。
茧
从下午五点睡到现在,很着水,如蚕入茧般麻痹的舒畅。真享受。
中间有一段短醒,应该七、八点时吧,雨正好枯树一样细瘦而有力地触地,像一集束一集束哑光的鞭炮,遥远的他乡的庆典。千日酒的余沥或商山荒鸡刚孵的一地小鸡,把感觉的米粒笃笃啄尽。我又睡去。
茧。
农历七月十二日的狗吠
剧烈的落叶突然开始。
一片,一片。一片接一片。像吠。
像刨柴。咒骂。刮锅。喷绘。
其实就是吠。
我闭目看见一条狗为树代言,然后垂死的蝉返魂惊起。白日脉搏微弱,空寂大至。
让秋天来得像狗一样强烈吧。万物皆无归期,白露于我何有焉?大吠就是。
秋 边
秋夜清旷好读书,秋被滑如水皮。晓来人困,一觉浓睡,半在西湖水底,半随芰荷浅欹。
就有鱼鳍的声音,密密集集的猫从月亮上垂下尾巴,村里小芳重新编好的辫子,空山松子从松果腺上不断滴落,渐渐听清,那都是窗外雨声。水漫上眼皮,噢,这和枕簟一样无力的中午天气,你没听到院子里流酒的声音么?谁在会饮?
就想起酒,想起酒伴阑珊,想起自己久不酣饮。此去经年,若总有酒声响于秋边,响于白日,也自糟香满池。
醒了。
空村。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