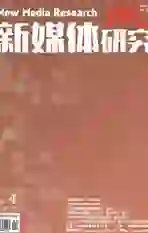匮乏的事件:“社会临场感”在媒介景观中的再诠释
2018-05-08杨浩楠,杨昕
杨浩楠,杨昕
摘 要 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其生产的“表现”与真实世界的事件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体验已经优先于事件的发生,而事件变得匮乏。在充斥着媒介景观的社会中,社会临场感被资本和技术赋予全新的含义。异化的社会临场感为主体带来了更多体验的机会,但这种非真实的活动无形中造成了人们的认知冲突与意见极化。为探求事件贫乏而体验骤增这一矛盾现实的内在原因,文章以社会临场感这一基本概念置于现下的媒介环境中进行考察。
关键词 社会临场感;媒介景观;拟社会互动;伪参与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4-0003-04
社会临场感发源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临场
(social presence)这一概念。Short、Williams和Christie将其迁移到传播学研究领域。他们指出,社会临场感是个体依托媒介与他人交流时对他人的感知程度。在此之后有研究认为信息受者对互动对象的临场感的感知程度来源于对媒介在亲密度(intimacy)、卷入度(involvement)、直接度(immediacy)等维度的判断;这也说明了人机互动的效果也可用社会临场感来解释。
一方面,在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传媒机构着力烘衬的电视名人为观众提供了可互动、交流的虚拟对象;回到当下,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与个人互动的虚拟对象在形式和特质上都发生了改变,这得益于新媒体技术增强了人们置身网络空间时的亲近感和卷入度;但当网络中的用户转换到真实世界中的个体时,疏离感和焦虑却增多了。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社交手段不但赋予而且增加了个体参与陌生人日常生活、社会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线上交流中,互动性同时兼具了单向和双向的特点,使用者既可以选择及时回复,也不会因为必须及时回应互动者而感到压迫感。因此有学者提出,相比线下,用户在线上交流中更有可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有关研究表明,在現实的“赛博空间”中,因为使用者对于预期制裁的无法预见性,其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积极性并没有被提高,甚至是弱化了。
在由媒介技术与资本合力塑造的新的景观中,非真实的临场感和参与感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和焦虑,进一步缩减了普通人参与真实世界活动和社会讨论的欲望。
1 “媒介景观”概念的提出
1.1 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
从媒介环境学视角来看,麦克卢汉思想中的“创造性麻木”(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颇值得关注。媒介偏倚论的创立者伊尼斯认为作为社会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的技术,其形态、力量必然会受到掩盖,身处该文化的人看不到它们,这个遮蔽的面具就是所谓的“保护性抑制”。麦克卢汉延伸了这个概念。
技术通过创造新的媒介不断延伸人的视觉与听觉,这一过程是在人的相关机体的功能极化、失衡、调整与再平衡中完成的。广播延伸了人的听觉,并极大地冲击了视觉。这种冲击是我们以具体的新媒介、新技术的形式回应集体压力和刺激的努力成果。令人惊异的是,在个体“并非有意识地调整各种各样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之后,这种冲击造成的人体感知比率的极端变化被适应了。而这种无意识的适应行为就是创造性麻木,其带来的后果正如麦氏所言,“手术的冲击区和切口区是麻木的”,人们对形塑自己和整个社会文化的技术的力量视而不见。
而在麦克卢汉之后,学派的正式开创者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到了与“创造性麻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论断“媒介即隐喻”。他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所裹挟的意识形态偏向创造了一种“伪语境”,以娱乐性的信息表征形式为遮蔽,冲击了由印刷媒介塑造的理性、严肃之社会
文化。
无论是“创造性麻木”“保护性抑制”,还是“媒介即隐喻”,媒介技术作用于社会个体的形式表现为其塑造的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作为景观社会的表象。从口语传播时代到由网络传播主导的当下社会,技术依托于它所创造的媒介改变着使用者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与行动定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技术的内容、内涵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MR(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等虚拟现实技术的商业化,智慧城市构想的提出……互联网时代不计其数的新技术、新产品无不在印证着这一观点。
1.2 作为表现的媒介景观
景观一词,首次被赋予社会意义是在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作为开篇,这段话对马克思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被物化的论断进行改写,“物的拥有”的重要性被降级,“表现”则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
无数在景观重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过程中,“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这些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成为催眠社会个体的先决条件,而异化产品,也就是表现的不断积累导致了“异域”的生成。在“异域”中,个体被分离,“孤独的人群”进而涌现。
德波对于20世纪社会文化的批判理论,与媒介环境学派众多学者的主要思想不谋而合。有学者指出,景观已经凸现为“媒介时代”的本质。作为景观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媒介,被用来在景观社会中不断展示的精确技术理性也是媒介技术的产物。
美国学者凯尔纳所提出的“媒体奇观”概念,正是借用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并融合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说,使大众媒体成为景观的制造者。他从具体的媒体奇观,如“消费文化奇观”“体育文化奇观”“电视文化奇观”“克林顿奇观”等出发,探讨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演变。
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概念立足于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众传播文化的观察,其理论依托于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环境。而在其代表作问世的短短10年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新的媒介环境,解构了大众传播的主导地位,新的景观已经出现。
随着资本、技术、权力范式的变迁,互联网成为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信息载体;由它主导的信息社会变成了“表现”的集中场域;巨额体量的媒介信息在这里生发、分享、内化,而作为用户的个人,其主体性被激活,自发地承担着优化这一场域的任务。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技术促进了人们对自我存在感的确认。社交性直播等行为成为了这种确认的具体表现,也增进了作为非真实世界里被展示的符号与意象。在互联网占据信息传播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的不断自我确认行为被自动地积累、修饰、展示,构成了媒介环境系统自循环的过程,推动了新的景观的形成。征用大众媒体时代的“媒体奇观”概念解释当下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中的问题显得非常吃力。故笔者建议将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概念在新媒体语境下再次诠释为媒介景观,解释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下个体在社会临场感指引下的社会行为。
2 新媒体语境下的“社会临场感”
胡泳认为,信息创造了事件丰富但体验匮乏的世界。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体验已经优先于事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虚拟现实技术虽然为使用者带来了短暂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但也造成了主体的认知冲突;互联网对“相对无权者”的赋权为个人提供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机会的同时,其内生的极化因素与隐私安全问题又迫使人们放弃参与的实践。如此,人们对日益增进的社会表现产生了焦虑。这种焦虑并非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它所生产的表象,比如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
2.1 卷入度与亲密感——异化的社会临场感
互联网建构了一个缺场社会,符号展示和意义追求成为这个空间的主要内容。为了使用户持续留在“虚拟的天堂”中,营造更“真实”的社会临场感,互联网巨头们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资本不断地对基于“表现”的媒介景观加以改进、修复。
大众媒体时代,观众往往会把电视中的媒体名人看作真实交流的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建立某种关系,这种拟态的互动行为被称之为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身处开放、“连接一切”的网络时代,普通人与媒体名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障碍已经被打破,拟社会互动行为已经由非真实生命体的媒介技术完成。
2018年初有两款现象级手机游戏引发了网络热议——《恋与制作人》和《旅行青蛙》。前者为偏日系女性向卡牌游戏,用户需要在与四位风格迥异的男主角的不断对话、关卡对决中升级、获得新的卡牌。很多女性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都声称“有恋爱的感觉”。后者则是一款养蛙游戏,操作简单,玩法单一,但它的互动性却并不弱。用户给青蛙准备食物、幸运符、帐篷等旅行用品;青蛙在旅途中给主人邮寄明信片,在旅行结束后带回特产。如此反复,用户从简单重复的操作中得到了短暂的卷入感和亲近感。
顯而易见,与用户互动的是媒介技术塑造的虚拟人物,幸福感、归属感的产生也并非来源于真实的社会互动。当失去了用户身份的社会人进入真实世界时,由情境抽离带来的落差感和空虚感对个人的社会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地,虚拟现实技术进一步突破了时空局限,创造了“第二现实”,实现了个人的“在场化”。但这种由AR、VR等媒介技术带来的沉浸感和交互体验是非真实的,并不是主体的客观社会活动,是异化的社会临场感。作为使用者和体验者的个人极易在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中发生认知冲突。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对于孤独的个人来说,媒介卷入(Media involvement)只是暂时的、粗浅的解决方案。而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更加真实的社会互动体验。
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体的心理倾向通过娱乐媒介的心理卷入方式和程度得以反映。而反映的具体形式,则是海量的数据和用户行为习惯。媒介景观将其充分利用,得以制造更多的亲近的“表现”,进一步异化用户的社会临场感,造成主体认知距离与物理距离的分裂。同时,主体在媒介景观中的展示本身也自动地成为媒介景观的一部分。
2.2 已被感知的伪参与
在资本助推之下,不断涌现的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赋予了个人激活潜藏自我意识的手段和工具,也理应增加表达多样化的可能性,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对于个人,特别是作为普罗大众的个人而言,媒介技术内生或被赋予的社会临场感曾给予他们幸福感与亲密度的递升。在社交媒体里,他们可以跨越时空,与相同兴趣者交谈;也可以自由参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更能够释放个人不满与负面情绪;但用户在社交媒体中并非总是以非真实角色进行意见表达和互动交流的。再者,个人在感知到了其他在场者的存在后,便会竭力呈现出与社会趋势相对立或相适应的形象,以降低被孤立或社会制裁的
风险。
作为网生代的年轻人,已经构成了互联网使用者的用户主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各种类型的活动时,往往会受到社会临场感的影响。在对社会议题发表个人观点时,他们总会意识到作为隐藏威权的政府官员的在场,对陌生人的在场体察助推了他们在发表意见时的焦虑感。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媒介平台上抒发个人情绪时,屏蔽功能的使用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在场者的感知。德国学者Neubaum曾做过类似的研究,他对少数意见群体在线上以及线下表达真实观点的可能性做了对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实现话语民主的场域。与面对面的情境相比,用户在其中更有可能被引导着保持沉默。
究其原因,在社交媒体中,社会临场感已然被异化了。威权与风险无处不在,个人对在场者的感知力被不确定性所主导。持有少数意见的个人,意识到自己将面对在体量上更为庞大的多数意见群体,而多数意见的一方将比在真实世界的社会互动中更快、更具体地体察到其群体立场的强势性,进而更为“自由”的生发个人情绪。
身处媒介景观中形成的沉默螺旋,原本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在场者被无限放大或缩小,个体受群体极化及信息极化影响更为深远,而议题讨论的最终目的也发生负面的偏移。
信息极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反转新闻。如“格斗孤儿”事件,最开始多数意见站在谴责当地政府和家长一方,而后来,含泪被迫按下手印的“格斗孤儿”们又带来了舆论的反转。在事件发酵和反转的全过程,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不仅凝聚着其意见的若干拥护者,而且左右着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群体,使得多数意见更具压迫力和统治性。处于弱势的少数意见群体,出于对预期制裁以及被孤立的可能性的考量,往往也会放弃所持观点。
这种由多数意见的压迫力和统治性加剧而形成的舆论环境,是社会临场感异化的表现,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主体参与社会议题讨论时“言不由衷”的现象。话语民主的实现是立足于已经有前进趋向的社会文化的;而媒介景观对于意象和符号的崇拜实质上已经否定了进步的可能性,作为自由表达对立面的威权卫士始终把持着舆论的主导地位,用他们的话语实践着异议者的绝对谬误。但绝对的谬误与绝对的真理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绝对化的
个人。
3 结束语
社会临场理论作为学科融合的成果,本应在我国的传播学科内“占有一席之地”,但对于其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研究与应用却并不多。本文立足于发源自凯尔纳媒体奇观概念的媒介景观视角,将社会临场理论放置在当下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中分析,既给予了媒介环境研究相关的思路,又对网络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建议。总体而言,媒介技术的缔造者必然会在生产新的媒介景观时考虑社会临场感对用户的影响,而作为媒介技术的使用者必须意识到媒介景观中并非客观世界,主体在这种伪语境中生发的情绪是不完全真实的。在现实的媒介生态下,体验优先于事件;看似民主的网络环境隐匿着威权,导致了公众参与媒介所生产事物的虚伪性。
参考文献
[1]Short,J.,Williams E.,&Christie;,B.(1976).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New York:John Wiley&Sons.;
[2]Kumar N, Benbasat I. Para-Social Presence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of a Web Sit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E-Service, 2002, 1(3):5-24.
[3]Ho S S, Mcleod D M. Social-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on Opinion Expression in Face-to-Face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8, 35(2):190-207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8]刘力永.景观社会:媒介时代的一种批判话语[J].北方论丛,2006(6):48-51.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0]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J].国际新闻界, 2016(10):6-27.
[11]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51-56.
[12]彭兰.移动互联网时代“现场”与“在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6(3):142-149.
[1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朱逸.“缺场”空间中的符号建构[J].学习与实践,2015(1):103-109.
[15]雷霞.虚拟现实主动性感知意义探析[J].现代傳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2).
[16]Greenwood D N, Long C R.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Media Involvement: Solitude Experiences and the Need to Belong[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9, 36(5):637-654.
[17]王天娇.社会临场理论的三个内生性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1(6):46-51.
[18]Neubaum G, Mer N C K. What Do We Fear? Expected Sanctions for Expressing Minority Opinions in Offline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17(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