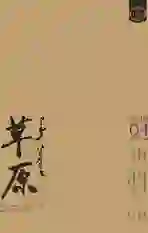商店和书亭
2018-05-08张晓霞
张晓霞
三十多年前,赤峰最大的商店叫作百货大楼,第一天开业时人潮拥挤,像打仗一样,有些人没有看到任何商品就败下阵来,足见人们对新事物需求的迫切程度。
那时我三年级,中意那里的一支圆珠笔,定价是一元零二分钱,上面白色,下面绿色,一按咔嗒咔嗒响。苦心经营了半年之久,终于在一个夏季的中午把一元零二分钱放在柜台上。
这之前,我曾担心它被别人买走,每次来到这里都到文具柜台看看。想来我是多虑了,在那个铅笔和圆珠笔芯都几分钱一支的年代里,谁会昏了头花一块多钱买圆珠笔呢?那时大家的圆珠笔都是用一支笔杆换芯使用,一支笔芯外面卷上几层纸一样写字,几毛钱的钢笔加上一瓶两三毛钱的钢笔水够用一学期。所以这只小葱一样的圆珠笔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当时,偌大的商场里只有我一个顧客,我攥着它转身离开,脚步匆匆,心怦怦乱跳,好害怕后面有人追过来再把笔抢走,出了大门都不敢相信这东西真的归我了,回望这座静悄悄的大楼,心中恍惚得很,顶着太阳往学校跑,路上连人都没有,两边街道静得吓人,路两边高大的树木伸出的阴凉也没能减少我奔跑代谢的汗水。
另一个让我常常光顾的商店是永巨副食商店,它位于上学放学的路上,我经常顺路点点货。这是三东街最大的副食商店,商店里弥漫着酱油五香面的味道,令人心驰神往。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爱吃的:蛋糕永远在柜台里摆着;面包,在出去劳动时会成为令人羡慕的午饭;绿豆糕作为降火的药物一年会吃两三回,可惜到嘴的也是药的剂量;大片酥和饼干,吃的时候常常把它竖起来,一层一层地往下啃,以此延长它们在嘴里的时间,偶尔手里会有几分钱,我能买得起的只有酸枣面和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
夏天,商店会在外面支起防雨帐篷专门卖水果,那时水果品种不好,苹果很贵,味道却令人失望,沙果酸甜爽口,对舌头的刺激比涩巴巴的苹果好得多,而且价格便宜,是我记忆中真正的水果。
有一次母亲买回沙果,分成四份,我守在旁边,实在是难以选择:这一堆儿又大又红,可只有八个;那一堆成色个头都差了很多,可是有十个;介于中间的两份是九个。父亲说如果他选,就选那八个,因为“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我还是为难,我宁可吃一筐“烂杏”,只是觉得“烂杏”不够一筐。迟迟不做选择,是希望父母重新考虑“烂杏”的数量,哥哥们要回来了,我还是选不出来,拧麻花似的在母亲身边蹭,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从“仙桃”堆里拿出一个,连那一堆“烂杏”都抓给我,“咱们要这堆儿”。
满街都是骑着自行车卖冰棍的。自行车后固定着一个白色的箱子,用白色的棉被盖住,边骑着自行车边吆喝:“冰棍冰棍。”五分钱一根,夏季酷热,母亲给我的“降暑费”有限,兜里的五分钱往往要揣好几天才会变成冰棍融化在嘴里。若能隐忍不花,钱会多起来,兜里揣着两毛钱的感觉比吃一根冰棍还要惬意。
有一次揣了一毛钱到商店“点货”,商店门口竟然在卖“红豆冰棍”!一毛钱一根!乖乖,一毛钱一根的冰棍,那得多好吃?我呆了半晌,掏出一毛钱,我也要吃一回“仙桃”!冰棍拿到手,模样令人怀疑,就是普通冰棍的样子,但被污染得像泡了豆包馅的大米粥,里面有两小撮暗红色豆状物!还没吃,就有点后悔了,试着咬了一口,大失所望!豆就是豆,冰棍原有的甜被豆搅和得打了太多折扣!再看看那大白糖冰棍儿,清凉爽脆,一咬还咯嘣咯嘣响,不但有解暑的爽利还有咀嚼的快感!再看看商店里,一毛钱能买到多少好东西!就是什么都不买,口袋里装着一毛钱那也是不小的心理优势。现在全都落了空,真是沮丧到了极点。
转学到一小,可逛的商店又多了,一小对面有一个账簿商店,除了账簿,还有小人书。小人书是那个年代的人美好的记忆,在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小人书慰藉充实了多少人的心灵!当时最贵的小人书两毛六,多是影版的,我尤其喜欢。我大了一点,兜里的零花钱也多了一点,攒够钱就买一本。看着一本一本多起来的小人书,就像看着自己的财富在一点一点增加一样,有财主数钱的快乐。时间久了,攒了整整一书包!到了初中这些书又成了同学交际的工具,用来交朋友、抄作业和考试作弊。
再后来,红山宾馆前的小书亭成为消费主场,我手里的一点钱都交到那里。开放、进取、单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小书亭的杂志里,我到了追星的年龄,我追的星们也在那里。我不但知道大家都熟知的港台明星和日本明星,还看过《苍茫的时刻》,知道默片时代的嘉宝和“嘉宝说话啦”“嘉宝笑了”“让我孤独”等偶像轶事和名言,知道英格丽·褒曼和她的意大利丈夫,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级的偶像是苏菲·玛索、黛安莲恩和波姬小丝。后来,波姬小丝和阿加西结婚,后来又因为志不同道不合离了婚,阿加西和格拉夫结婚这样八卦也被持续关注。整个八十年代及以前的中外电影、两岸三地的娱乐圈,只要是书亭书店有售的书籍杂志报道过的,我都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冠以“青年”的杂志,还有《世界之窗》《世界知识画报》《临窗风》等,在这些杂志里我知道了法拉奇、杰奎琳、赵元任、梦露、第欧根尼等另一个世界的人。我没有脑洞大开,反倒模糊了对人的认识。后来高中遇到了赵琰,也是骨灰级文青,我们一拍即合,一起度过了文艺又追星的正常的高中生活。还有张红、大赵岩一干人等,大家把三毛、琼瑶全部看完,还有亦舒、梁凤仪若干,当然也顺便看了《百年孤独》——吓人吧!某个节日,或是生日,赵琰送我的礼物是一本现代诗集《城市人》。说实话,根本不懂,也看不进去。那时还有一套“五角丛书”,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在其中的一本里我读到了庞德的印象诗——“地铁里的脸和湿漉漉的树枝上的花瓣”,用现在的话说,我也是醉了。那时我对诗的认识是“我愿意是急流……”
按理说,文青文青,有年龄特点,这种病虽然可怕,但只流行一时,但赵琰和我是深度感染者,直接影响了择偶的标准,最后,我嫁了写诗的,她嫁了画画的,我们和文学艺术再也分不开了。
每每聊天至此,我们都只能自我解嘲,像鲁迅嘲笑法海一样,说一声“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