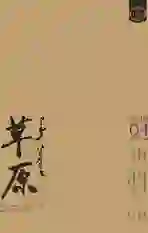随笔四篇
2018-05-08西凉
西凉
巨大阴影处
也许“原罪”不仅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存在在《旧约》里,而是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存在于从远古一直以来的焦虑中。
上帝为什么和他们订立这样的约定?我想上帝明明是知道他们会违背这个约定的。上帝给出的理由似乎总是不那么充分:知羞耻、知善恶必背负痛苦。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上帝是先验的,但他的隐晦和言不由衷总让我产生怀疑,似乎上帝本人对伊甸园的理想设计,是来源于经验和教训。他的胸有成竹,让我相信,此前还有一个世界,而这一个也可能是另一场试验。
前些日子我听陈丹青讲圣马可教堂的湿壁画,讲十四世纪伟大的画家安吉里柯。安吉里柯的神有着劫难之后的平和、单纯、美好和安详。在安吉里柯那里似乎回应了我的看法:伟大的神性深处是人性,而人性的深处也是神性。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但也许都是在不断的试探中,在试探中突破秩序,在试探中前行,并背负由此所带来的焦虑,从而接受来自内心巨大的不安和精神的惩罚。安吉里柯在佛罗伦萨赢得尊重和巨大的声誉,以至于教皇想让他当佛罗伦萨的主教,而他拒绝了。也许我们可以从安吉里柯的绘画中了解他,进而推测他已进入神的内心,并了解到神的本意。
随着商业繁荣、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到来,上帝的约束逐渐被法律和道德所代替,但这并不意味着撒旦和上帝把整个世界交给了人类,在人性巨大的阴影处,他们始终存在,上帝似乎成为观察者,而撒旦却极有可能仍是蛊惑者。
卡佛在《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小说集里,就是在探寻那些潜伏在阴影处的难以把握和言说的人性。就像李敬泽所说:“他让很多很多人感知到了在自己生命中确实存在一种荒凉,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我更樂意把它说成是人性的巨大阴影处。它充满着背叛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像是一个活着的疤痕,原罪一样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是一种焦虑,而不是活着的逻辑。
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这篇小说里,更加直面这种焦虑。比尔和杰瑞在他们的妻子准备午餐的时候,驾车出去,路遇两个骑行的少女芭芭拉和莎伦,她们的美好激起了比尔和杰瑞的欲望,而最终杰瑞用同一块石头砸死了她们。这一切,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似乎每个人都感觉那是一种梦幻般的精神游走,而并不是现实,甚至伤口会愈合,血液会重新流进血管。然而,那的确是现实,的确已经发生。而我们永远找不出他们的逻辑性动机。
这场毫无征兆的游戏般的凶杀,让我想起卡佛的话:“我们已经都知道,人生是一场悲剧,更悲哀的是,这场悲剧的主角还不是你,而是命运。每一个人,都注定了是旷野里的寂寞,都注定要面对生命本身的孤独,甚至还有人性中固有的恶。”
苏童说:“读卡佛不是读前面一大朵一大朵的云,而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
那些山峰投射出巨大的阴影,那里埋伏着多少惊悚的危险,就有多少梦游般的鬼使神差。
像身影迫切的乔瓜那样
像风摧折着荒野的植物那样,死亡的阴影也一直追赶着胡安·鲁尔福笔下的人物,以至于他们都来不及绝望。
我无法确定这些生活在近乎荒原上的人类,是否出自鲁尔福本人的经验,我没有搜寻到鲁尔福的出生地和长期的居住地,也不确定这本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集《燃烧的原野》的故事背景是否在那稍早的年代。比如,墨西哥革命年代。但从人物名字看,可以推测他们是西班牙人的后裔,而不是印第安土著,或者古老的阿斯特刻人。他们应该生活在墨西哥西北部山地和平原的交叉地带。这个地区符合小说里多次提到的风、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一百毫米,而且集中降水,容易造成洪水和土地的板结。就像他多次提到“像老牛皮一样”的土地,雨水过后,土地开裂,留下“水渣”,像土地长出了刺,会割破人的脚。
我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探讨鲁尔福小说的艺术性源泉,而是想推测地理和历史环境是如何塑造或者启示一个作家的,就像当我们了解到南美洲古老的神话,和人们讲述神话的方式,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尔克斯一样,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只是评论家借助说话的方式而已。当然,马尔克斯在鲁尔福那里得到照耀,卡夫卡和鲁尔福使他的写作走出瓶颈。
但,这仍然不是我思考的方向。我相信一个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对那里生存着的一切居民有着最本质和独特的塑造,包括人类和植物。也许,我更想说的是植物,它们比人类更古老,至少那些从别处被风送来的植物比鲁尔福笔下的人物更早地来到贫瘠的原野。迁徙来的植物和原住地植物体现不同的生命状态。是鲁尔福笔下的人物的迫切,让我想到了那些迁徙到荒原来的异乡植物。这种迫切表现在生育的迫切和对死亡的迫切,都有一种被驱使、被催促的感觉。
在我来到乌海很多年,差不多有二十年之后,才见到乔瓜的。它是和我的童年一起生长的植物,它白色的汁液至今还在我舌尖的记忆里停留。当我在二十年之后,在异乡重新见到乔瓜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它们在山谷的沟槽的背阴处,很翠绿,硕果累累。我迫不及待地想尝到它们,像是与童年意外相会。我挑了一个最大的,放到嘴里,但已经咬不动了,它有半个手指那么大,但是已经老了。再挑一个稍小一点的,也老了,咬不动了。那么再小一点,再小一点,一个一个渐次地尝,一直到最小的一个,只有黄豆那么大,但它仍然是老的,不能吃的。我尝试着换一棵,再换一棵,仍然如此。这让我感到颓然,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像一个恶毒的玩笑,把我困在了某个时间里面,同时也有一种缺乏真实之感。
还好,这里强烈的阳光能够唤醒我的意识。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山上的植物,它们有野菊、枝芨、沙蒿,还有可以吃的大黄、泽蒙。
在此之后的日子,甚至延续至今,只要到了野外,我会不由自主地观察这里的植物,比如哪些可以吃,哪些是动物喜欢吃的。哪些是原生植物,哪些是迁徙来的。哪些是来自更远的远古,与古大陆的变迁逐渐成为现在的样子,哪些是地质大变化之后才有的植物。
比如半日花、四合木、裸果木(这个是我的推测),它们是更为远古的孑遗,在地质大变化之前,它们可能是高大的植物,枝繁叶茂,甚至有的植物学家认为四合木曾经像桐树那样的高大,可以蔽日,而现在只有几十厘米高,叶子还没有绿豆那么大。
比如红柳、沙拐枣、花棒、骆驼刺,枝芨、刺旋花、大蓟、梭梭、白刺、霸王、沙蓬、蒙古韭(沙葱)、碱韭(泽蒙)等等,它们应该是地质大变化之后的植物,也属于这里的原生植物,它们现在生机勃勃,花开得艳丽,显得从容和舒展。
而野百合、大黄、乔瓜,以及许多还不知道名字的植物,则属于迁徙来的,它们是外乡人。它们像鲁尔福笔下的人物一样,更敏锐地感知旷野的风和漫长的干旱。它们比那些原住民更显得急迫而紧张,它们匆匆地钻出地面,用很快的速度成长,很急促地开花结果,而后播撒后代。好像是等不及了,好像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同样,它们和身边的那些“本地”植物总保持疏离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植物界的“社会关系”和人类保持着平行的状态,你很难见到这些外来的植物能够成片地长在一起的。尤其百合,也许一座山或者一大片的荒原,也只有矮矮的一株,在那怯怯地生着。也许是因为恶劣的环境,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荒原上的百合花,是苦而咸涩的。有些植物生和死是极其快、极其潦草的。
鲁尔福在《燃烧的原野》里对那里的人有这样的描述:“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全都走了……天一亮,他们就长大成人了。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他们从母亲的胸口一跳跳到锄头上,然后就从卢维纳消失了。”“只剩下老头老太和单身女人,也有的女人有丈夫,却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回来又离开的时候,给老人留下装着粮食的口袋,在他们的女人肚子里种下又一个小孩儿……”它们多像荒野的乔瓜那样,急于老去,以便躲避突如其来的灾难。
如果有一天人类遭遇灾难,大概也会如此,个子变矮,不再美观,生育年龄提前,着急老去,着急撤离。即便现在,也总有一些事物,像身影迫切的乔瓜那样,让我们来不及叹息,就老掉了。
[说实话,《燃烧的原野》并没有满足我的阅读期待,也许《佩德罗·巴拉莫》会好些,马尔克斯曾经对它倒背如流,但我猜测它可能超不过《百年孤独》,尽管是它照亮了通往马孔多的道路。]
那一刻,他肯定是微笑着
走回房间的
这个月,仍然保持一个月四本的速度,卡佛的《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茨维塔耶娃的《新年问候》。《佩德罗·巴拉莫》看完一遍,第二遍看了一半,突然意识到,在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一点它的照耀,于是停下。而茨维塔耶娃,对于当代中国那些优秀的诗人,很少有人逃得过她,不管是二手的,还是几手的,还不能够出现一个和她平行的星座,似乎还都不具备她那样的力量。
鲁尔福和茨维塔耶娃都有重读的必要,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需要保持对它们的陌生感。
应该在1962年,也就是马尔克斯来到墨西哥的半年之后,他才得到朋友的推荐阅读《佩德罗·巴拉莫》,“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的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他能背诵全书,甚至倒背,不会出大错。他把这本书形容像“索福克勒斯一样浩瀚”。无疑,《佩德罗·巴拉莫》让马尔克斯找到了“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这种说服力就是一种敞开式的庞大,一种死亡不是终止而是延续的叙述态度,这种时空交错、死人的魂灵参与当下生活的讲述,产生了奇妙的诗意。我能想象得到马尔克斯当时的激动不已,这可能是他从写作为了讨好友谊转变为充满野心和期待的充满未知的惊心动魄史诗般的旅程,那就是创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
然而,《佩德罗·巴拉莫》之前呢?它之前又有谁触发了这样的方式呢?是哪一束光线无意地扫过胡安·鲁尔福的前额?
茨维塔耶娃还是通过韵律和音步的韵文写作,中文的翻译已无法呈现她语言的现代性和韵律,这可能是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它的对应方式,汉语言的格律诗和词很难达到,即便对应它的韵律,而损失的却是它丰富的现代性和内涵。也许,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文译者已找到最好的妥协办法,在保持诗歌灵魂和韵律方面做了不得已的取舍。在告别洛尔迦、瓦雷里等等之后,中国当代诗歌更多地接受着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雨露。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他们语言的运用,而这恰恰是茨维塔耶娃反对的,她把这种语言的炼金术称为“对大自然的冒犯”。
“我只靠这副皮包骨活着,所有的你们都披戴着盔甲。你们拥有你们的艺术、社会出路、友谊、消遣、家庭、职责。我,在最底层,一无所有。所有都像一张皮一样落下,或处在这张皮下——活生生的血肉和火焰:我,普绪克。我不适合于任何形式,甚至不适合我自己诗作中最简单的形式。”
我很难理解茨维塔耶娃一生的颠沛流离和苦难,在她的诗歌中却很少有个人愁怨的体现。她的小女儿在苏联大饥荒中被饿死,1937年她的丈夫和大女儿相继被逮捕,她和儿子被疏散到叶拉布加,1941年她在那里自缢身亡。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茨维塔耶娃的目光不在尘世,当然這并不是说她没有承担生活的责任,她生前是那个颠沛家庭的支撑,也许我们像她理解里尔克那样理解茨维塔耶娃是缪斯的化身,当然,我想在那些艰难的时刻,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像几颗彼此能望见的星辰那样,给了她温暖和存在的力量。
让我们放松些,像茨维塔耶娃那样调侃一下:“男人们都梦见了塞壬,女人们都梦见了拜伦。”
总之,这个并不快乐的春节,有不快乐的茨维塔耶娃和有少许快乐的鲁尔福在远方的注视,就能把那些巨大的虚无推得远一点。此刻,外面依然有莫名其妙的鞭炮声,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在半个世纪以前为他小说里的角色不能飞上天而踌躇忧虑,直到第五天,他看到搭在晾衣绳上的床单飘起来。
那一刻,他肯定是微笑着走回房间的。
如 果
如果我能站在后面的山包上,我就能看到一个人的一生从这座城市走过,他无数次穿过那条街道,有时匆忙,有时悠然,有时停下来和人讲话,有时走在路中间又折回来,回到那所老房子,然后又重新走出去,穿过那条街道。他穿过那条街道无非为了再回来,就像一只放在桌上的蚂蚁,从一端走向另一端,然后向后转,循环往复,一生不止。你能看到他每天早晨八点准时从一所房子走向另一所房子,然后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回来。
在这些往返的途中,你总能看到他一丝不苟,目的明确。
他用过的东西会逐步扔到垃圾堆里,他的活动很固定,基本在一条马路和另一条马路之间。他的脚步由充满活力、矫健、沉稳到蹒跚;他的头发会由柔密富有弹性和光泽,到渐渐灰暗、稀少,站在这里正好看到他纷乱的头顶。
他的一生显得忙碌,有条不紊,但绝大部分是重复,今天和昨天几乎没什么两样。他的一生流过那么几次眼泪,有几次几乎肝肠寸断,但过一些日子,他还是收拾好行装,继续在这条老街中间穿梭,并渐渐恢复了笑容。
有时看到他领着一个女人和孩子,拿着费半天力气才吹好的气球,在草地上撒几个欢,然后抱抱她们,就再回到那条重复的路线上去,夹着他的越显沉重的公文包。
你不知道他一生在做什么,为什么,为谁,但忙碌好像就是他的工作。他混在那些人中间,像树林里的一片叶子,难以分辨。有时我在垃圾堆里搜寻他穿过的几双皮鞋,那样子带着疲倦、辛酸和难以言明的悲凉,这在他忙碌的身影中是难以见到的。
我注意到他有过那么一些晚上,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我不知道他是否思考过什么,但有那么几次这片街区,就那一扇窗亮着,旁边房间的大床上摆放着一个沉睡的女人和一个梦呓的孩子。他显得安静极了,像在与自己对话,像接受教训,无比虔敬的样子。我知道他不知道我在注视着他,他熄灯的时候已经很晚,他的手显得很无奈,灯关掉的时候,他被深埋在黑暗中。
[责任编辑 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