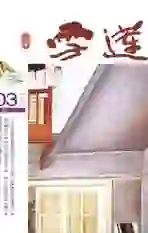牧民的儿子,大地的诗人
2018-05-07刘大伟
刘大伟
一
在阅读辛茜女士的长篇报告文学《尕布龙的高地》时,我刻意不去翻看书中的人物和风景图片,直至在这个安静的下午读完全篇时,脑海里很快勾勒出一位身形魁伟、办事利落、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党的高级干部形象来。只因常年奔波于南北两山之间,他俊朗的面庞可能被山风吹得粗糙而黑红,他挺直的腰身因积劳成疾却又长时间硬撑而弯出了令人疼惜的弧度。回到海北老家,这位党的老干部还牵挂着西宁南北两山的一草一木,终因病痛离开了故土,然而他又把自家院落送给家乡人民,办起了“哈勒景金银滩农牧民医疗合作室”。从此,除了两袖清风,一身病痛,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当我将自己所构想的尕布龙形象和书中的图片逐一对应时,毫不夸张地讲,一种隐痛与崇敬交织着的复杂情绪自心底弥漫开来——不得不说,作家对主人公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叙述得深挚动情、客观公正,对尕布龙这一党的好干部形象塑造得真切生动、栩栩如生。一切文学都是关于“人”的文学,无论是极具虚构性的小说,突出抒情性的诗歌,还是讲求写实性的报告文学,“人”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作家通过对“人”的书写,完成对生活的触摸,对时代的感知,对问题的探寻,对现实的反思,最后达到对世界和人本身的深刻体悟与认知。这一过程可以是侧重形而上的哲思,也可以是极具细节性的描摹,无论是何种方式呈现,只要触动了读者,带给读者诸多啟悟与思考,或者在更深层面上得到了审美的震感,那么其书写的意义便不言自明。显然,报告文学《尕布龙的高地》对主人公的塑造是依据大量的人物细节,一笔一画还原出来的。这些细节主要通过扎实的田野作业取得,无论是来自亲人的讲述、同事的回忆,还是北山上那些草木用大片绿色所做的见证,都因蕴含着强烈的生活真实而饱含张力。在不断的被吸引、被震撼的过程中,每一位读者的心底都能够清晰地显现出一个胸怀博大、忠诚耿直、心怀慈悲的尕布龙形象来。若不是作家用细致精准的笔墨,用非虚构的方式将尕布龙形象定格在读者心中,很多人对尕布龙的认知恐怕还要停留在“传说”和“怀疑”阶段。须得承认,尕布龙做人为官的品质,注定了这部作品的品质——作家无需动用多样化的文学手法,只需将有关尕布龙的生活真实梳理出来,就足以感动读者的心灵。
二
那么,如何概括尕布龙这一兼具生活真实和文学意义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够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层面去更好地理解他呢——通过阅读,不难发现,无论是尕布龙遗留的只言片语,作家采访获取的大量信息,还是不同读者得到的个体认知,以“牧民的儿子,大地的诗人”这一形象来定位尕布龙,我认为比较贴切。
牧民的儿子,无论何时何地,都心牵着草原上的生产劳动和父老乡亲,永远保持着骨子里的朴素、善良和厚道,愿意用一棵草的姿态,面对世间的繁花和风雨。为了确保这样的生命底色,尕布龙近乎苦行僧般地恪守着自己人生信条,连身边的亲友和同事人都被要求遵守。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身为“牧民儿子”的尕布龙说一不二的性格特征,以及在貌似铁面无情的表象背后,蕴含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高贵品质。当17岁的女儿召格力参加完乡里的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会打针、换药、接生孩子后,开始幻想自己能像班上同学一样去西宁卫校上学,希望和同学们一样留在西宁,哪怕是县上、乡上的医院,穿上白大褂在正规医院工作……当她把这个朴素的愿望告诉父亲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召格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你阿妈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阿爸工作太忙,顾不上,你就留在家里放牧,当赤脚医生,好好照顾你的妈妈,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吧!再说,阿爸也不能搞特殊,把你安排在城里工作。阿爸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该用在老百姓身上啊。”于是,我们读到了召格力含着热泪,忍着满腹委屈和父亲在风雪中收拢羊群的感人场景。2006年,尕布龙的孙女达什姐莉从青海大学毕业后,尕布龙给她的建议是:“你还是回到家乡海晏,到最基层的地方工作,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吧!还可以守在妈妈的身边,照顾妈妈。”学医的大外甥东主仁青毕业被分配到砂石厂当修理工时,他又说:“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嘛!”
这就是赤子情怀,工作不求名利,服务一心为民。作为牧民的儿子,草原就是故乡,草原上的百姓就是亲人。尕布龙从海北草原来到青南草原,他的故乡范畴在不断扩大。他教育子女时说——要热爱草原,建设牧区,虽然牧区自然条件艰苦,总要有人来建设。如果牧民都进城,草原建设、畜牧业生产由谁来发展?诚如斯言,这是一个牧民儿女的良知之言,当很多人都奔着远方而去时,总得有人留下来,守护着那些虽然贫瘠但还有着母亲的家园。
尕布龙身居要职却从不以高级干部自居,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牧民的儿子,人民给了他手中的权力,他要把所有的热情和能量传递到人民的心上。工作中这样做,一般人都可以理解,但尕布龙的可贵之处是生活中也这样做,很多人就难以理解了,拿他家人的话来讲,那就是“关心别人远远超过了关心家人”——给牧民搬家,给开会的干部倒水;遇到贫困的农牧民,无论身上装着多少钱和粮票,都要拿出来接济;把家里的新被子拿给受冻的孤寡老人,把女儿召格力的羊群赶到等待脱贫的人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谢绝了省政府办公厅提供给他的省长住宅楼,固守着畜牧厅家属院80平米、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和暖气的平房,四间潮湿阴冷的房子被他用土坯砌成了五间半,半间是自己的卧室,其余五间搭上了11张床,专供从牧区来西宁看病、办事的农牧民食宿。从此,尕布龙的小家变作了一个让农牧民免费吃住的杂乱而又温暖的“牧人之家”。
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个传说,然而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何况这一切都是真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尕布龙内心有个担忧——住在省政府院子里固然方便,而且显得体面,可是省政府的住宅区设有警卫,搬过去以后,那些不会说汉语,找他求医、办事的农牧民不敢进门,怕是再也不会找他了。不找就不找了,又有何妨——且听尕布龙是怎么想的:“到我这里来的大部分是农牧区的贫困群众,城里没有可以投靠的人,不会说汉话,我不管谁管?”直至1982年,省政府大院不再设立警卫,尕布龙才从畜牧局家属院搬了过来,2002年搬至省人大家属院。虽然中间搬过两次家,但每到一处,“牧人之家”的传统从未终止。对于那些急需扶助的弱势群体而言,尕布龙无疑是个神一般的存在。但这个存在并非虚无缥缈,有一项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牧人之家”在畜牧局家属院存在了7年,省委大院20年,省人大家属院4年,作家辛茜和尕布龙的侄子做过详细的统计,“31年来,尕布龙在自己家免费接待来自基层看病办事的农牧民至少达25000多人次”。阅读至此,所以的怀疑和不解都会自动消散,习惯了自私和麻木的灵魂在这一刻也会羞惭得低下头来。老百姓问——这样的党员干部还会有吗……我想,最好的回答只能留给时间去筛选和淘洗了。
三
波兰诗人米沃什说:“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放低姿态后得到的一种人生诗意。视“人民为天”的尕布龙在繁忙的工作中不谈风雅,不会歌唱,“更没有用他的名字,在荒丘之上刻下浸透着他对这片山水情深意长的丝毫印记。”犹如一棵小草,他将生命的根须重新扎进南山脚下并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专注而深情地凝视着天空与大地,蔚蓝的天空和不语的大地因了他一生奉献却默默无闻、心怀大爱又倾尽所有的胸怀而带上了几分歉意与感伤的色调。實际上,他是一个胸怀大地和人民的诗人。笔者非常赞同作者辛茜女士的观点——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浪漫而多彩的诗人!他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高贵品质远远超过了诗人米沃什所说的“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
当下,人们对诗人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偏狭,似乎专注与阳春白雪和孤独抒怀的人就是诗人,似乎语言偏激行为怪异的人就是诗人,似乎能写分行文字的人就是诗人。实际上,诗人不是冠冕,也不能自我认定和命名。真正的诗人是在社会急速推进的浪潮中能够守护着我们日益凋敝的精神家园的人,真正的诗人其情怀与眼光一定超越了尘世的媚俗与现实的功利判断,在众声喧哗的纷扰语境中默默坚持着善良、真诚、悲悯、宽容、感恩和敬畏的“诗歌精神”的人。真正的诗人需要时间为他证明。如果上述这些关于诗人的理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尕布龙无疑是最具“诗歌精神”且心怀大地和人民的诗人。
他为一片不毛之地换上碧绿苍翠的裙装,他把无数陌生的穷乡亲接到家中视为亲人,他在冰雪中、风沙里、困苦中给人带去希望的灯盏与温暖,他把党的事业、组织的重托、人民的信任看得比天还高、比命还重,他把人类的智慧、集体的思想、个人的信念用一肩之力扛起来,竭尽全力付诸实践……这难道仅仅是堂吉诃德,而不是一个时代不可缺少的诗人吗?这个世界上或许有两种诗人,一种诗人寄情山水,喜欢手捧金樽对月高歌;另一种诗人则会扎根泥土,更愿意把一棵柔弱的草木紧紧拥在怀里。两种诗人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但是如果非要做个比较,显然愿意为世间草木分忧解难的诗人更值得尊敬。
毫无疑问,尕布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只不过他把最好的诗篇写在了荒山与大地之间,写在了草原与城市之间,那些绿树成荫的山坡,那些粗糙面庞上绽开的微笑,那些在困厄中涌现的倔强与坚持,都是他亲自写就的诗篇。这些诗篇让冷漠者感到荒诞,让心存私念的人感到汗颜,但也会让每个愿意忏悔的人反省自新,成长为更有担当和情怀的人……这或许就是尕布龙的精神所在,他把一个富有远大理想、执着信念和人文情怀的诗人形象,塑造在青藏高原之上,闪耀着温暖而又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