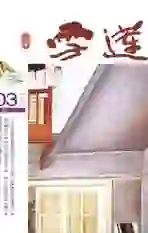花儿和信使
2018-05-07樊健军
跳。
黑豆跳下了石坎。
跳。
菜团子跳下了石坎。
跳。
再一个跳下了石坎。
花栗子在石坎边缘站立了许久,做势要跳下去。
你不许。
叫驴子在石坎下急了,却又不敢大声叫嚷,嘬着嘴,不让花栗子跳下去。叫驴子还不罢休,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来威胁花栗子。花栗子的身体摇晃了几下,稳住了。
跳。
叫驴子鼓励悯若跳下去。
悯若说,不跳,我不做小偷。
叫驢子说,你不做小偷就吃不到枣子。
悯若说,我不吃偷来的枣子,也不吃青枣子。我要等枣花大婶请我吃红枣子。
叫驴子说,枣子都泛白了,快熟了,甜得很。
悯若说,我才不受你的骗,上你的当。
叫驴子说,那你在上面等着,我摘了枣子给你吃。
但悯若不等待青枣子,头也不回走了。
枣花大婶的后院是块场地,场地左右两边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后边是个石坎。围墙上苫着干枯的稻草,稻草雨淋日晒都泛了黑。围墙下靠墙堆放着劈柴,刚码放的新柴散发着树木的清香,时间久了,柴也泛黑了,有一股腐朽的气息。场地的一角架着一扇石磨,另一角是口水井,中央是棵枣树。枣树虬枝盘旋,遮蔽了大半个场地。枣花开时,香气从院墙上溢出来,大半个村子都闻得到。四邻八村的蜜蜂都赶着飞往枣花大婶的后院,去享受枣花盛宴。枣树是同枣花大婶一块嫁到水门村来的,许多年过去,枣树长得比她的主人还要繁茂。枣花的清香勾起了村里人的想象,枣花大婶的枣子又要丰收了。
枣树挂了果,枣花大婶就看得紧了。通往后院的槅门从早到晚关着,不轻易许人进去。后院不放长竹竿,也不放扁担和戗棍。不放高凳子,更不放木梯子。院墙的稻草上放了狗骨刺。石坎抹了三合土,光滑滑的,难站脚。石坎之上用石楠树围起了篱笆,石楠树上的长刺让人生畏。有两年,枣树下还系了狗,狗虽不凶相,可吠声骇人。脚步声响在院墙外,院子里早就叫嚷开了。
悯若走了,叫驴子恍了一下神,很快就恢复了。他像个猫,蹭蹭几下爬上了树。菜团子也想爬上去,爬了几下,结果像个泥团子似的跌回了原地。枣树太高,泛红的枣子都在半空里。叫驴子想爬到更高处,但都够不着,就支使黑豆,去寻根竹竿来。黑豆的溜溜在院子里转着圈,就是寻不见竹竿,也不见别的可用来打枣子的木棍。叫驴子后悔没带根竹棍来,可后悔也晚了,只能在低处捋些个半青不白的枣子。
院子里慌乱时,花栗子将一根石楠树的枝丫扔进了院子,然后像个鹞鹰那样张开双臂飞下了石坎。花栗子擎起石楠树枝,扑楞几下,枣子像下雨,叭啦叭啦,青青白白的一大片。黑豆一个狗扑屎,菜团子也滚了过来。叫驴子见状赶忙从树上跳下来,一头扎进了人堆里。枣子还没拾净,哨兵就气喘吁吁来报告,快跑,枣花大婶回来了。众人就嗡的散了,都往石坎下逃。石坎太滑,上不去,有人急得要哭了。叫驴子就托着个矮的屁股,让他们一个个先逃,独独留下花栗子。花栗子托起叫驴子,叫驴子回到石坎上一溜烟跑没了影。花栗子抠了几下石坎,三合土太滑没能抠住,再抠,指甲缝里都抠出血了,才抠住石坎。幸好快一步,险些就被枣花大婶捉住脚踝了。
花栗子,你个火把鬼。枣花大婶大骂。
叫驴子在来路上守着花栗子,花栗子却从另一个方向走了。叫驴子命令黑豆和菜团子将枣子扔成一小堆,先拣出几颗个大的,泛白的,余下的每人数颗,平均分配。
叫驴子揣着枣子去找悯若,却找不见她。叫驴子找遍了村子,才在水门河边的草滩上找到她。悯若蹲在草地上正看着什么,听见脚步声也不抬头。叫驴子走过去,才发现她的眼皮子下有一簇米粒大小的白花,认不得是什么花。先前还没开花,我刚走到这儿它们就全都开了。悯若的脸上是迷惑的微笑。她是愉悦的。哪有那么神奇的事情,许是早就开花了,你没发现。叫驴子说。是我到它跟前才开花的。悯若噘起了嘴。叫驴子见她不高兴了,慌忙将几颗白枣从口袋里掏了出来,给你枣。悯若将双手藏在背后。叫驴子说,你看,都是白枣子,挺甜的呢。我说了我不吃偷来的枣子。悯若说。叫驴子将枣强行塞在她的手心。悯若扬起手,将枣掷向了河里。
叫驴子愣怔了一下,朝河奔过去,捞回了两颗白枣,没捞着的几颗被河水带走了。
悯若吹牛,她去哪儿,哪儿的花就开了。悯若站在稻田的边缘,稻子就含胎,抽穗,扬花了。悯若去花生地转一圈,花生就绽放出无数小黄花,刨开泥土,就有甜甜脆脆的水花生。悯若在地坎下走一遭,草莓就红嘟嘟的,比小嘴儿还鲜艳。叫驴子不信,娘也不信,可爹相信,那孩子,有些神奇。爹不只相信,还鼓励说,找空让她来家里玩。
娘抗议说,谁都可以,就他俩不行,花栗子和悯若,一个也不许上咱家来。
为啥不能?
那俩,都是来索债的。
谁欠了他们的债?
村里人都欠了。
什么债啊?
生死债。
娘的话不可相信,因为她是水门村的女人。水门村的女人对孩子不待见,没事就来一句,讨债鬼。裤子划破了,咒骂,讨债鬼。谁哭鼻子了,揩干了鼻涕还要挨骂,讨债鬼。谁抢了谁的陀螺,讨债鬼。谁抢了谁的木头手枪,讨债鬼。谁偷了谁家的红薯,讨债鬼。讨债鬼是她们的口头禅。仔细琢磨一下,她们的话没意思,娘的话也没意思。
那个,悯若,可以来咱家。爹坚持己见,说,花栗子就别来了。
都添三张嘴了,万一应验,再添一张嘴,养得活啊你?娘朝爹翻白眼。
没见饿死谁。爹的话硬朗得噎死人。
你有本事别让我娘儿几个遭罪,你不是没长眼睛,看看这过的什么日子,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就差没去做叫化子。娘一脸委屈和鄙夷。
爹遭了抢白,叼着烟斗出去了。
爹和娘拌了嘴,爹的儿娘的女就有可能要遭罪了。花栗子和悯若没这份罪受,花栗子没爹没娘,悯若也没爹没娘,花栗子没爹没娘是娘死了,不知爹是谁,悯若的爹和娘可能还活着,就是不知他们是谁。
悯若在水门村的第一个家是谷大婶家。悯若是晚上出现在谷大婶家屋檐下的。那晚上狗叫了三四回,每一回都没有什么动静,要么狗们肚子饿了,要么觉得夜太长,吠几声给自己解个闷。可狗们一叫,村里的耳朵都支起来了,在黑暗里仔细聆听着,会不会有门响,会不会有羊叫鸡叫牛叫。若不警个醒,招了贼,损失就大了。天快亮时,谷大婶家忽然响起了鞭炮声,村里人都以为谷大婶的儿媳妇又生了,想一想不对,她儿媳妇一个月前才生过,哪能又生啊。鞭炮声也就十几二十响,一眨眼的动静,往后就没响动了。谷大婶的男人一激灵跳了起来,也不穿衣,扯开门,就往门外跑。有个模糊的人影往村口的方向快速移动着,揉揉眼睛就不见了。丢了啥?丢了啥?谷大婶跟着追出门。丢个卵毛。谷大婶的男人瓫声瓫气说。待要关门继续睡觉,屋檐下却咿呀几声,像是人哭又不像人哭。寻着声音找去,晾衣的竹竿上多了一只竹篮,声音是从竹篮里传出来的。将竹篮拎回屋,划根火柴,点亮煤油灯,才发现篮子里是个皱皮皱嘴的小人儿,被一团黑不溜丢的棉花包裹着。
你们都没见过,哪有人形呀,就是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谷大婶每次说到悯若都把她比做小老鼠。
谷大婶养了小老鼠一个星期,就将她送到村后庙里的神台上去了。小老鼠吸干了她儿媳妇的奶水,她刚出生的第三个孙子因此饿得哇哇叫。她不能再养她了,不然她第三个孙子就要饿坏了。神台上空荡荡的,除了一只插着断香的泥香炉,和泥香炉下的一圈香灰,啥都没有了。要有的话,可能就几粒老鼠屎,也是细细瘦瘦的。悯若在神台上睡得香,醒来之后就咿咿呀呀哭,哭着哭着,就没了声音。叫驴子的娘打猪草回来,在庙前歇脚,见神台上有个棉花捆,就想着要把它拿回去,不能铺棉袄,做双棉鞋也行。踮着脚将棉花捆弄到手,却将她吓了一跳,竟然是个小人儿。一瞬间她就明白了,棉花捆中的小人儿肯定是谷大婶放的。造孽呀,造孽呀。叫驴子的娘将小人儿抱在怀里,不知该咋办,想放回神台上不忍心,抱回去送还谷大婶吧又不敢。思想了半天,还是决定抱回家去。她想得美呢,是个女孩儿,养大了可以当儿媳妇,还省了娶亲的花销。叫驴子才三个月大,叫驴子的娘有奶水,不够的话找村里的婆娘讨几口,估计不成问题。
往后的日子,叫驴子的娘一手抱着叫驴子,一手抱着小老鼠,奶了叫驴子再奶小老鼠,奶水不夠了就抱着小老鼠往正奶孩子的人家蹭。长到五六岁,悯若就不乐意了,村里人不叫她悯若,要么叫她小老鼠,要么叫她小媳妇,叫小老鼠没什么,叫小媳妇就不愿意了。只要有人叫了小媳妇,她就不回叫驴子家,一个人跑着庙里睡到神台上去。可能她黑灯瞎火睡惯了,不怕鬼更不怕神。再往后,吃饭也不愿意去叫驴子家,东家吃一顿,西家混个饱。到头来,悯若不是谷大婶的孙女儿,也不是叫驴子娘的儿媳妇,成了大伙儿的囡囡。
悯若不是谁家都去,村后头破絮家,一个老头加一个儿子光棍她不去,村东头上福家,同几个儿子分了家,独独留下上福和上福女人,上福的耳背了,上福女人患了白内障,她也不去。她老是往有小媳妇的人家跑,做小媳妇们的尾巴。她喜欢看小媳妇们的肚子鼓起来,又瘪下去。喜欢看小媳妇们捧出乳房,往刚从身上掉下来的小人儿嘴里塞。悯若的神奇是那些小媳妇传出来的。小媳妇来时我的肚子还瘪瘪的,才多久,就有了这个小壶崽。她们不知是炫耀她们自己会生娃还是夸奖悯若吉祥。
小媳妇们替婆家养了人,婆家就把她们当宝贝样宠着,水果罐头,茶壳饼,麦芽糖,什么好吃的都往小媳妇的怀里塞。悯若跟着受惠了,小媳妇们有吃的,就有她吃的。
哪儿有吃的就往哪儿钻,有奶的就是娘。叫驴子的娘败坏说。
可是小媳们不听她胡说,仍旧把悯若奉为送子观音。
过几天,悯若没有等到枣花大婶来请她吃红枣,花栗子却受到了枣花大婶的惩罚。那一天,摘完猕猴桃下山,碰巧遇见了枣花大婶,原本狭窄的道路被枣花大婶的柴捆占去了大半边,小伙伴们一个个从柴捆前侧身而过,黑豆过去了,菜团子过去了,叫驴子也过去了,花栗子落在了最后。花栗子怕是早忘记了偷枣子的事,冷不防被枣花大婶揪住了耳朵,嘴都咧得像道刀口子。你个鬼伢崽,还偷我的枣子不?说,还偷不?枣花大婶用另一个只手揪住花栗子的腮帮子,花栗子的嘴咧歪了,像个老鼠洞,可就是没法说话。小伙伴们都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叫驴子歪着头在笑。你不说话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枣花大婶不扯耳朵了,两只手同时揪住了花栗子的腮帮子,先前花栗子也许是倔强着不愿说话,可后来想说话也没法说了,只能任由枣花大婶揪着。
花栗子,说呀,不偷枣子了,咱不偷枣子了。悯若干着急。
花栗子的脚踮起来了,还是一声不哼。
悯若转脸恳求枣花大婶说,婶啊,您放了花栗子吧,没人敢偷您的枣子了,谁偷您的枣子谁就变哑巴。
还是小观音懂事。枣花大婶这才放了花栗子的腮帮子,又推了一把花栗子说,鬼伢崽,你得谢谢小观音菩萨,下次再敢偷枣子我打断你的腿。
花栗子得了救,没命似的逃走了,可又不逃远,收住脚回头来气恼枣花大婶,我要偷光你家的枣子,还要偷你家的人,偷你儿媳妇水莲。
你个野杂种,雷打火烧的,看我不撕烂你的屄嘴。枣花大婶被激怒了,像只鹅样划着双手,蹦跳着追赶花栗子。追了几十步,花栗子早不见人影了,只好停下脚,双手叉着腰,边咒骂边喘着粗气。
枣花大婶的枣子没指望了,小伙伴们只有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物上。红薯地有了裂缝,扒开裂缝,就能挖到硕鼠似的红薯。红薯脆嫩,清甜,可老是吃红薯也够腻歪,鼓了一肚子气,半夜里还闹肚子,像有只小兽在肚子里踢腾。
马上有好吃的了。就在小伙伴们没有去处之时,花栗子诡异地说。
哪儿有吃的?除非天上下屎。叫驴子对花栗子的话全是不屑。
过几天就知道了。花栗子不在意叫驴子的鄙夷,一脸骄傲的神秘。
果真,没过三天,村北的有水老汉不知患了什么病,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本来都出门晒太阳了,他儿媳妇还给他熬了两碗粥,不想第二天下午就走了。走了老人村里就有热闹了,报丧的报丧,挑石灰的去挑石灰。道士很快进了村,唢呐悠悠扬扬吹起来了,锣鼓没日没夜敲着。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厨房忙碌了起来,磨豆腐的磨豆腐,做米果的做米果,厅堂里一摆一大桌。神桌上供奉着各式点心,红红绿绿的,哪一种都不稀奇,但哪一种都好吃。
派上活的来领活,没派上活的来吊丧。村里一个男哑巴,不管谁家有了丧事,都派他挑水。哑巴挑两只水桶在前面走,两条狗在后面追着他,哑巴被追不过,从口袋摸出一个肉团子,又放回去了,再一摸,摸出一块豆腐扔在地上。两条狗,一块豆腐,狗就掐起了架。
黑豆他娘在茶房泡茶,泡茶的佐料给黑豆装了一荷包。叫驴子他爹在挖穴,挖过穴就喝酒,叫驴子不喝酒,他爹就抓了一把干果给他。菜团子的爹坐礼房,礼房的吃食就更多,有酒还有烟。这种场合只有悯若是不来的。花栗子不会错失良机,径直钻进了厨房,厨房里正热火朝天,围着灶台转的都是婆娘。最辛苦的是烧火的婆娘,一个人看两只灶的火,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烧火的婆娘敞着胸,汗水从额头上冒出来,流过脸,流过脖子,一直流到奶尖上,才一滴一滴往下滴落。烧火的婆娘正愁没人换手,见到花栗子像见到了救星,不管平日里咋样,这会儿逮住了就逮住了。花栗子只管烧火,吃的毋須多操心,灶台上放着一只脸盆,不管煎的炸的烧的煮的,掌勺的婆娘都会往脸盆里舀上一勺,只要锅里有的,脸盆里就有。三天三夜的道场散去,花栗子也撑了个滚瓜肚圆。
丧事都过去了一个多月,花栗子还在吹牛,我说的没错,有吃的吧。
又说,有水老汉在场地上晒太阳,他的头顶上呼呼冒着白烟,还嚷着要喝粥,我就知道他要走了,这叫,这叫,回光返照。
花栗子的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大人们的耳朵,他们听了也是一怔,有水老汉不是命该绝,而是被花栗子给催命催死了。真是邪门了!
打那以后,花栗子就成了村里人嘴边的催命鬼,阎王爷的跑腿,老人们望而生畏的死亡信使。
晚秋的时候,悯若终于等来了枣花大婶的邀请。但在内心,悯若早已不太稀罕她的邀请,如果早些时日,放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让人高兴。这毕竟是个丰收的季节,不说家里养的,土里种的,单是山坡上的野味就足够诱惑人了。猕猴桃,八月灿,山梨子,金樱子,要什么有什么。秋夏相交的时候,猕猴桃摘回来还得想法子找糖来腌,这会儿却是剥了皮就能往嘴里塞,而且一汪的糖水,让人直咂嘴。八月灿的味道最让人留恋,吃了还想吃。
大人们也不像往日那么吝啬,只要嘴巴甜,总会有意外的收获。守在村口的路边,遇见嫂啊,婶啊,太婆啊,只要喊上几句,说不定她们就会解开提在手上的小包袱,给你抓一把干果子。或者从口袋里给你掏一把花生,有可能还有一两根麻花,甚至几颗糖果。
枣花大婶特意绕道到村口,从孩子们跟前走过。
婶啊。悯若的甜嘴巴最先张开。
婶啊。菜团子立马跟上了。
枣花大婶手里啥也没有,就从口袋里掏啊掏啊,掏出了几颗红枣,给每人散一颗。枣子红彤彤的,很蛊惑人的眼睛。
吃吧吃吧,甜着呢。枣花大婶眯着眼,一个劲地瞧着悯若。
悯若又喊了一声,婶好啊。
哎哎,婶好着呢,明儿个上婶家来吃枣子。枣花大婶眉开眼笑向着悯若说,就你一个人来,可不许带别人。
枣花大婶邀请悯若吃枣子是有原因的,她儿媳妇水莲嫁过来三四个年头了,肚子瘪瘪的,从来就没有隆起来过。这是她的心头病,水莲一天不怀上,她就一天不能抱上孙子。
婶啊,我一个人不去,要去大伙儿一块去。悯若说。
枣花大婶的脸变色了,像蒙了一层薄薄的枣子皮。她瞧瞧菜团子,又瞧瞧黑豆,再瞧瞧 叫驴子,当发现花栗子也在其中时,她的眉头皱起来了,像是长了两个结巴。
都去吧,都去吧,婶的枣子多着呢。枣花大婶故作大方地说,转而又附在悯若的耳边嘀咕,那个催命鬼可不能去,给他吃的枣子早吃过头了。
第二天,悯若和叫驴子,菜团子,黑豆几个一同去了枣花大婶家。枣花大婶比预想的要热情得多,在水莲的卧房里摆了一张四方小桌,桌子上摆满了果盘,有红枣,花生,南瓜籽,还有几个红壳饼,几根掰开了的麻花。
水莲也在屋子里陪着他们吃红枣。她长得并不好看,脸上麻麻点点的,头发枯黄像稻草,细胳膊细腿,身体扁扁的,肚子那块更是瘪得厉害,有可能肚子里没长有蛋袋呢。鸡生蛋有个蛋袋,女人也像鸡,肚子里该有个蛋袋,要不然孩子生下来之前藏哪儿。水莲也吃红枣,吃一颗向他们笑一下,笑的时候就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嫂子,啥时生下弟弟呢?悯若问水莲,不只问,还拿手在水莲的肚子上摸了一下。
就生,就生。水莲嘴里裹着枣子,话也说得不太清晰。
你一爪,我一手,很快小方桌上的果盘就扫荡干净了。再坐下去,小伙伴们都没有耐心了。找个理由,一窝蜂从枣花大婶家逃了出来。
这伙豆子鬼,真能吃。枣花大婶在他们身后嘀咕。
悯若偷偷藏了两颗枣子给花栗子,花栗子不要,还吐了一口唾沫说,我才不吃,说不定还招她的骂。
事情再一次被花栗子说中了。来一年,水莲的肚子隆起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却是个女孩儿。水莲抬不起头,枣花大婶更没有好脸色。那些枣子都给狗吃了。枣花大婶憋闷时忍不住愤愤地说。

村里人没有冤枉花栗子,打他出生起就是个灾星。花栗子他娘本是后山马老汉的孙女,除了马老汉和他眼瞎的女人,家里就没有别人。马老汉养了一匹马,靠马帮人驮东西苟延着日子。花栗子他娘喜欢到村里来东串西串,不知怎么肚子突然就隆了起来。问是谁的种,她啥也不说,不知是真的稀里糊涂,还是有意替那人隐瞒着。这种未婚先孕的事在村里是遭人耻笑的,何况连肚子里的孩子的爹是谁都不知道。花栗子他娘怀上花栗子后极少在村里露面,孩子呱呱坠地后,竟然一头跳进了水门河里,尸体顺流而下,在距离村子三里地的猪婆潭才找到。花栗子长到四五岁,两位年迈的老人先后谢世了,留下他一个孤儿。
如果没有花栗子,花栗子他娘就不会投河自尽。
花栗子生来就不吉祥。
后来,果真印证了村里人的预感,花栗子是上天派下来的索命无常。他往谁家跑,谁家的老人就要注意了,说不定来个回光返照,不出三天老人的子孙们就得披麻戴孝。花栗子无处可去了,几乎家家都给他下了逐客令,不许他登门。谁家没有老人呢,即使没有老人,谁又愿意让个不吉祥的家伙溜到家里来。
也有心思叵测的人家。菜团子他爹虽然村里办红白喜事时坐礼房,但心眼儿一点也不端正。别人家不欢迎花栗子,他巴不得花栗子天天上他家去。菜团子他爷爷瘫痪在床有三四年了,虽然下不了床,人却是清醒的,村子里的事情躲不过他的耳朵。花栗子进了屋,菜团子爷爷先前就骂栏圈里的猪,你哼哼什么,你那点歪心眼谁不知道,有你肥的一天。骂过猪之后,他又诅骂闯进他屋子里的一只老母鸡,你钻进钻出瞧个什么稀奇,有你不下蛋的一天,哪天不下蛋了,就一刀宰了你。花栗子被菜团子他爹诱去了两趟,再也不敢贸然登他家门了。
花栗子更无处可去了。
但村里人无法消除对他的防备,明着不能去,暗地里谁又能掌握得了他的行踪。留着这么个不吉祥的人物在村里总不是件好事。该拿个主意了,不能再让他在村子里转悠下去,说不定哪天又有哪个倒霉的老人要受害了。有些人聚在一块嘀嘀咕咕,嘴巴上含糊其辞,但内里都心知肚明,就是要为花栗子找个去处。花栗子不是姑娘家,不能把他嫁出去。有人就去另外的村子打听,看看有谁家愿意过继儿子,啥东西也不要,将孩子接过去就行了。问了几家,见了花栗子都不乐意了,这么大个人,养也养不亲了,过继了也是白养人。
该另拿一个主意了。最终点子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让黑豆他爹去执行。黑豆他爹不情愿,就有人说给他记工分,一天记十个工分,啥也不用干,还白吃白玩。叫驴子的娘怂恿叫驴子的爹,这事就该你去,把那瘟神送走了,小媳妇就是你儿媳妇了。枣花大婶也絮叨她男人,别说有工分,没工分你也该去,看看后院那棵枣树,受他的祸害还少吗?就该让他吃点苦头。
黑豆他爹几个上路了,花栗子跟在他们身后。水门镇毗邻湖南和湖北,他们出了村径往武汉的方向走。黑豆他爹说要带花栗子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那里不只有各种好吃的,还有好多好玩的,有三层楼高的大轮船,有夜里挂满灯笼的树,有会说话的鸟,会唱歌的鱼。花栗子受了诱惑,欢天喜地跟着去了。其他孩子都眼巴巴地,没有大人们的允许,谁也不敢跟着去。
过了三四天,黑豆他爹回来了,叫驴子的爹也回来了,枣花大婶的男人落在最后。三个男人哭丧着脸进了村,惟独不见了花栗子。后来才知道,花栗子一直跟得紧紧的,可走着走着,谁也没注意,再回头时忽然不见了。他们仨在路上来来去去找了三四天,怎么也找不见花栗子的人影。就这么走丢了。
村子里安静了不少。庄稼人的日子照旧有条不紊,该干啥干啥,没谁闲着。
过了半个月,花栗子才回来。那天黄昏,村口忽然哇的一声有人哭开了,跑去一看,只见花栗子蓬头垢面的,正抱着那棵白果树在痛哭,比死了爹娘还伤心。
花栗子是水门村的花栗子,走哪儿也丢不了。村里人有了感叹,对之前过分的行为嘴上不说,心里暗暗有了自责。这种自责容忍了花栗子继续呆在村子里,但要想上人家的门,人家的脸色依旧难看,毕竟心里有阴影,一时半会抹不去。万一应验了呢,那就太对不起自家老人了。花栗子倒很乖觉,知道村里人对自己不待见,再也不轻易上人家去,多半时间都守在悯若睡过觉的破庙里。闲时没人到庙里去,除了悯若,也许因为同病相怜,经常跑去给花栗子送些吃的。那不见花栗子的半个月,她着急坏了,幸好谢天谢地,他又回来了。
日子像个醉汉,踉踉跄跄地过去。
花栗子不知不觉十五六岁了,虽然缺吃少穿,个头却是疯长,慢慢有了男人相。这么大个子的人,整日游手好闲,村里人看着不像回事。有人就寻思,该让花栗子干点什么,好歹对得起他死去的家人,也别让他再祸害村里人。
谷大婶的男人提议,让花栗子跟着学木匠。
谷大婶说,你不嫌晦气我还嫌晦气呢。
谷大嬸的男人就不敢再多话了。
叫驴子的爹说,让花栗子去做道士。
大家伙都觉得有道理,问花栗子,花栗子说啥也不愿意。
菜团子的爹说,去学劁匠吧。
花栗子更不乐意。劁匠可不是什么好差使,拿村里人的话说是断子绝孙的职业。
有人就冒火了,气愤愤地说,这也不去,那也不去,你到底想干嘛?
花栗子迫于压力,只得喏喏答应了。
花栗子做了几年劁匠,成人了。他做劁匠的师父张罗着要给他说一门亲事,托媒人问了几处,都不成事。正愁着时,有人提醒说,眼前不就有个现成的吗?问,谁?答,小媳妇呀。说的是悯若。叫驴子的娘却不答应了,在内心她早将悯若当儿媳妇了。不管怎样,得证求悯若的意见,问悯若中意谁,悯若也不害羞,大大方方选择了花栗子。花栗子的师父便办了两桌简陋的酒席,谷大婶和她男人坐了上席,权当是悯若娘家人。
婚后,悯若问花栗子,你怎么老是往走了人的地方跑?
花栗子被问得一愣,才说,哪是走了人呀,分明就是过节,欢天喜地地热闹。
悯若想是明白了,这人啊,生是节,死也是节。是节就不得不过。
村里人却隐隐有些不安,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到一块,究意会怎样呢。先是留意悯若的肚子有没有大起来,悯若有了肚子,人们便有了新的担心,悯若到底会生下一个怎样的孩子。那段时间,娘的担忧比爹的担忧更厉害,娘说,我的右眼皮怎么跳个不停。吐了口水去抹眼皮,怎么也抹不平静,跳得越发欢快了。每逢这种时候,爹就闷了头抽烟,让烟雾把自己埋起来。
整个村子的人在忐忑中终于迎来了花栗子家的鞭炮声。悯若生产了,是个女婴。第二天,村里的姑嫂婶姨都去道贺,见了粉嘟嘟的一个小人儿,都高兴得不行。有婆娘问,叫啥名字呢?花栗子问悯若,叫啥名?悯若又回问花栗子,叫啥名?
花栗子想了想,说,叫吉祥吧。
悯若说,就吉祥。
【作者简介】樊健军,江西修水人,中国作协会员,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小说月报》等刊,著有长篇小说《诛金记》《桃花痒》,小说集《空房子》《行善记》《有花出售》《水门世相》等,曾获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小说),首届《星火》优秀小说奖,入选加拿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名单(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