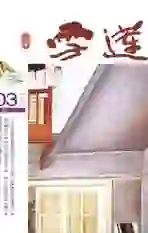西峰札记
2018-05-07李安平
李安平
九龙路
天天从同一条路上走,走的时间久了,反倒说不出它的好了。我要说的是九龙路。很多时候,想静下心来写一写九龙路,但是只要一摸键盘就觉得似乎有些漠然的感觉,也说不清楚漠然在哪里,反正无从下手。
九龙路是这座城市的第二大主干道,纵横南北,当然也是一条繁忙的大道。东站。南站。三中。四中。附小。区公安局。区委。区政府。公园。早市。家具城。九龙路的繁忙是不言而喻的,不知道是这些单位或者场所赋予了九龙的繁华,还是九龙路赋予了这些单位和场所应有的繁华。九龙路一天到晚总是沉浸在繁忙的车流和人流中。
5路车是穿越九龙路全境,是大半个全境,不过也可以这么说。5路车有多少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5分钟就有一辆。5路车上的司机基本上都是外地人,有湖南人、四川人和个别的本地人。其实只要车按时发就行了,哪里人开都是次要的。谁没事会瞎琢磨这些事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进入你的脑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它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就会一股脑的往你的脑海里砸。一个有雨的正午。参加完一个朋友的作品研讨会的午宴,我就站在5路车的站台前等车,要是在往常,这件事平常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等车,上车,坐车,下车,好像都是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可是今天,这一切似乎是个例外。雨滴突然稠密了一些,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没有带雨具,我们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5路车过来了,大家一窝蜂的挤上去了,谁也没有发现有啥异常。可是就在我们乘坐的5路车行驶不到100米的时候,从后面杀出一辆一模一样的5路车,它就像突然窜出的一头豹子,带着随时可以爆炸的愤怒向我们乘坐的车撞来,车上的人都吓慌了,司机匆忙中打了一把方向,车体激烈的摆动了许久,才恢复了平衡,车又继续向前驶去。事情还没有完。没有多大时间,那头“豹子”又窜了出来,这一次的愤怒似乎更猛烈了一些。它直接挡在了路中央,我们的车又是一阵激烈的颤抖,被迫停住了。两个操着湖南话或者四川话的司机对吗起来,大概是前面的司机占了后面司机的时段,后面来的司机挥舞着臂膀,企图进行身体上的接触。旅客也开始不满了,骂骂咧咧了一会儿,就有人下车了,我也跟着下车了。在雨中奔跑了不大功夫,又一辆5路车过来了,我又挤了上去。刚才的不快仿佛还停留在脑海里。
晚上。九龙路灯火阑珊,尤其是树枝上洒下的红红绿绿的灯光和地灯射出的光怪陆离的灯光,照得人眼花缭乱。新潮的男男女女夸张地搂抱在一起,嘴角里亮着星星一样的烟头,他们尖叫着,喧嚣着,身份可疑,行为乖张,不可思议。夜晚的九龙路是他们的舞台,我,不还有更多的我们都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我们只是经过而已。
血迹出现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寒冷像匕首一样,令人不寒而栗。早上一切才刚刚开始,有许多开始正准备开始,可惜有一些开始就被寒冷无端的打断了。一辆摩托车的早上和一辆出租车的早上就面目全非了,预先的程序被粗暴的打断了。它们相撞了。摩托车的残骸倒在路旁的绿化带上,两个受伤的躯体痛苦的呻吟着、抱怨着,血迹从他们的身体里渗透出来,很快就凝固了,像猩红的皮冻。人群簇拥上去,围拢了呻吟传播的半徑。清障车和120救护车像橡皮一样,擦拭了刚才的一幕和破碎的现场。九龙路又恢复了应有的繁忙,又隐匿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管发生了什么,还是将要发生什么,九龙路呈现出来的姿势除了繁忙,还是繁忙。它生发了许多情节,又隐匿了更多的情节。对于我们,他们,你们来说,大家都是匆匆过客,九龙路永远是熟悉的或者陌生的。
炮台巷
我喜欢炮台巷这个名字,二十年前,我曾漫无目的的在这里寻找过炮弹壳,那时候,我真是幼稚的可以啊,坚信这里一定打过仗,有散不去的硝烟味,有散落的弹壳,而且我固执的认为炮台巷一定和战争有关,和硝烟有关。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忍不住要到炮台巷转悠一番,企图寻找所谓的弹壳。当然这种寻找只持续了四年,我就被一张派遣文书送回了故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和生活。
炮台巷像西峰的康复路一样繁华,一样出名,一样令人流连忘返。在二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后还是这样。
二十年前,西峰唯一的商场——大商场,就坐落在炮台巷。那时候,一说到市场去,谁都知道要到大商场,要到炮台巷。诺大的市场笼罩在塑料盖顶的钢筋支架下面,市场被一截一截的水泥柜台分割开来,还用红色的油漆编了号码,水泥柜台根据号码的的范畴,分成了若干个经营区域,显得井然有序。四角的边沿地带都是红色廊柱支撑起的两层或者三层单面楼,是专门开店铺的,里面的货物应有尽有。当然还是以时装店居多。记得我上中专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到这里来,曾经给我买了一件黑色的西服。那是一件后背开叉,前襟半圆的西服,里面是全挂的羽纱里子,提在手里沉甸甸的,穿在身上很是气派。当时是50多元,我穿在身上一试,父亲就乐了。他连价也没还就买下了。那时候,50元是我们一学年的学费,我们两个月的零花钱,我当时都有点心疼了。我还在背地里埋怨过父亲,父亲是个农民,靠力气吃饭,咋就不知道疼钱哩。现在想来,父亲是多么的爱我啊。他自己省吃俭用,到自己身上硬扣,到儿女身上竟是这样的大方,一点都不疼钱。唉,父亲去世都八个年头了,每每想到这里,心里总觉的对父亲有一种亏无法弥补的愧疚。
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啊。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啊。二十年后当我重新面对炮台巷的时候,真有一种久别“乌衣巷”的感慨。二十年物是人非,只有炮台巷的繁华依旧。如今的炮台巷虽然还是那么逼仄,那么拥挤不堪,但是它固有的繁华却是无法更改的。炮台巷是老百姓的购物天堂,昔日的大商场早已面目全非了,塑料盖笼罩的大盖子换成了宽阔的“南亚”室内服装商城了。那些廊柱支撑的店铺则变成了琳琅满目的门市部了。如今昔日老大的位置早已不复存在了,二十年,西峰成冒出了多少商场,商城,购物广场,专业市场,但是无论它们如何的繁华,都取代不了炮台巷的存在。相反,随着西峰的繁华,炮台巷反倒显得更重要了,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息息相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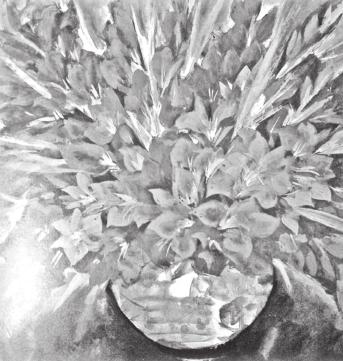
炮台巷由两条细长的巷子构成,一条是三院巷,一条是邮电局巷。它们就像南大街生出的两根小肠,细而曲折。邮政局巷稍微宽阔些,卖便宜书和古玩的摊子非常多,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气候。现在书价贵了,一本定价几十元的书在这里只需要花十元的钱甚至更低一些就可搞定,里面少许的错别字也不碍大事。这些书贩子都和西安兰州的大书市有联系,书的种类都很和潮流,而且里面还有好多经典书籍。至于那些古玩摊点就更妙了,不管你买与不买,卖与不卖,都可以弯下腰抚弄一阵子,主家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会主动和你搭话。虽然赝品和真品混杂,但也从中可以领略一些东西。除过这两大摊点,还有花样繁多的杂货摊点,有些杂货在别处买不到,在这里一找就找着了。三院巷像一把剪刀一样,伸出两条叉。一条以三院住院部为中心,另一条通向三院门诊。以住院部为中心的地带,就是便宜服装的天堂,这里的服装价格便宜的让人难以置信,但它还确实就是这个价。除了密密麻麻的门店,还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摊点。这里的摊子好摆,你哪怕用一根挑杆挑上几双袜子,几双手套,几个口罩,都有人光顾。逢地段宽的地方,商贩们就支架子摆摊,逢逼仄的墙壁,他们就在墙上钉几根长钉,拉几根绳子,把衣服往绳子上一搭,生意就开张了。还有更逗的,既不用挂绳子,也不用挑杆,把衣服往肩膀上一披,胳膊上一纏,扯开嗓子就吆喝开了。通向三院门诊的那条巷子就更窄了,窄的只可以通过两辆并行的出租车,人流多的时候,动不动就堵车。这个地段大都是些吃食门店和一些卖水果蔬菜的三轮车。不要看他们地段狭窄,但生意也是好的出奇,听说这里的一家烧饼店供着全城几家大酒楼的烧饼,面粉一天要用30多袋,试想那要烙多少烧饼啊。至于那些早餐店,小旅社,生意就更不用说了。
炮台巷就是这么一副模样,它乱,它脏,它拥,它挤,但是老百姓都离不了它。老百姓隔一阵子就要到炮台巷采购一些便宜东西,当然少不了上当受骗,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时候还是物有所值的。
火 巷
火巷像这座城市的一截尾巴,显得多余而不合时宜。它被老城庙从中砍断,和市区活生生的一分为二,一截繁华,一截萧条。东面是火巷,西面是市区,柏油马路到了东面自然而然的就中止了,继之而来的是凹凸不平的土路,到处充斥着垃圾,污垢。火巷像城市的弃儿一样,被甩在不远不仅之间,而且显得那样生分,对比强烈。
对于繁华的市区来说,火巷像一块伤疤,毕竟不是多么光彩。好在火巷人对此倒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丝的抱怨和不平。穷的洒脱,穷的心安理得。
狭长的火巷沟像一只瘦俏的旱船,从城市的东北方向斜插进来,形成了羚羊挂角之势,像一位凌厉的入侵者,令这座城市惶恐不安。火巷是这座城市的特殊出口,一则它承载来这座城市东北方向的全部排污功能;二则它的最北边就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火葬场,每一个生命枯竭的城市人都从这里被送往另一个世界;三则火巷毗邻肉类批发市场,所有与杀戮动物有关的血腥粗暴行径都在这里完成,而且那些肮脏不堪的动物下水和抛弃物都被随意的扔在沟底,每天都会有无数的野狗来觅食。因为这三种原因,想来火巷就更叫人敬而远之了。其实,事实还不是那么回事。火巷沟底有一股清冽甘甜的泉水,被火巷人从沟底抽上来了,而且还修了水塔,还建了纯净水厂,一桶纯净水才两块钱。每天早晚,络绎不绝的市区人都会到火巷来买水,买纯净水,买自来水。还有些白发斑斑的大爷大婶见天跑到火巷沟边溜达,看风景,看更北边被苍翠簇拥的火葬场。
火巷像一个毫无怨言的接纳者,接纳了这座城市的一切污七八糟,接纳了这座城市无法接纳的所有肮脏。同时它又是一位圣哲,藏污纳垢之余,对来自城市的鄙夷和嫌弃能默然处之,还向这座城市奉献出了清冽甘甜的泉水,这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