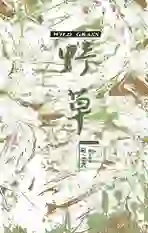唯有幽暗之寂静取之不尽
2018-04-23泉子
泉子

信的偏离
是信的偏离发明出了永无止尽的死,
而我们的确信中
有着那永远无法企及的永生
年轻的父亲
那个在公共汽车上因孩子的顽皮
而一次次将他推开的年轻的父亲,
那个因疲惫而将他的沮丧
倾倒在他无辜孩子身上的
怒气冲冲的父亲,
多年之后,
他是否会像我在此刻一样
为这人世的残缺
而如此羞愧。
密密的荷塘
一个密密的荷塘需远望,
需时间深处
那看不见的锋刃删繁就简后,
这人世的空阔与洁净
再一次为你所见。
感谢
感谢西湖,
感谢白堤两侧的垂柳
与姹紫嫣红的花儿,
一颗孜孜于道,
而依然如此浓烈的心
是需要西湖持续地再教育的,
直至你获得道的柔弱,
直至你获得真理的凛冽,
直至你获得空无的澄明,
直至你获得
一颗历经沧桑后的赤子之心,
直至你获得那伟大的至善
与寂静。
愿力
必须拥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愿力,
你才得以说出
一个如此繁盛而又荒凉的人世。
技艺
技艺是对自由的渴望。
而绝对或终极的自由
只在道中。
尘世的艰难
心正,然后才可事成。
或者说,尘世的艰难
恰恰是我们,以及万物那颗共同的心的艰难,
是我们历经沧桑,终于成为自己时
那从来,直至永远相伴随的喜悦与悲凉。
羞耻
终究是一个人的羞耻
帮助我们找到那通往诗的唯一入口。
一种如此单纯的力
在我成长过程中一个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是我的羞涩与愧疚吗?
是生命深处一种如此单纯的力,
是一首永远无法完成的诗,
帮我安然度过了
人世无所不在的沼泽与陷阱
痛哭失声的点点
小猫妙妙第一次把粪便拉在枕头上后,
点点说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懂事的小妹妹。
当小猫再一次若无其事地向她飞奔过来时,
她迎着它抬起了脚。
小猫逃窜到了门的背后,
然后惊惶无措地望着
突然痛哭失声的点点。
“刚才我出脚那么重,
妙妙会不会恨我,
她会不会因此伤心难过。”
我的安慰是苍白的。
“爸爸,你说过,
小动物,甚至是一棵树、
一朵花都是有情感的。”
而我突然間想起了,
我那依然如此年轻的母亲,
在我的一次恶作剧之后,
当邻居带着孩子来家中告状,
她高高扬起的手,
轻轻落在我的肩头时,
突然失声痛哭的样子。
忧心
不要为技艺或年龄忧心,
我们需要时时警醒的是,
我们是否依然能够
心无旁骛地去看,去理解这人世。
会手语的猩猩
一只会手语的猩猩,
一只这个世界唯一获得大学文凭的猩猩,
一只因唯一一次在课间侵袭
同班女生而被送回实验室,
并在笼子里关了整整十一年的猩猩,
一只说他受伤了,
但不是身体任何具体部位,
而是人类从来不曾真正理解他的情感的猩猩,
一只指着他身边的同类说,
“那是一些黄色的狗”的猩猩,
一只一遍遍用手语说,
“妈妈,你开车带我回家吧”的猩猩,
一只患忧郁症的猩猩,
一只终于死于心脏病,
享年三十九岁的猩猩,
而当他说他既是人类
也是猩猩时,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就像我第一次知道,
我既是诗人也是人时,
来自绝望与孤独的
那么丰沛的赠与。
当我广为人知
当我广为人知,我还是我吗?
而杜甫、屈原、陶渊明
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名,
而不是诗,
不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
那颗为空无与人世之悲欢所共同穿凿的心。
荷花带给我的震惊
荷花带给我的震惊,并非此刻的美与繁华,
而是它终于无可挽回的凋零。
遺憾
一个如此饱满的时辰不能在语言中留痕的遗憾;
一种寂静不能继续成为寂静,
幽暗不能继续成为幽暗的遗憾,
直到你终于理解
遗憾同样是语言,是尘世一种如此美好、珍贵的馈赠。
任何一种剥离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
如果说道在尘世是隐匿的,那么,所有艺术的意义
都在于通过各自的方式将它再一次擦亮与发明,
但不是剥离,
或者说,任何一种剥离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
而唯有注视仿佛一次新的浇筑,一次新的无中生有,
并伴随于道从万物共同之深处缓缓浮出的
永无止境。
古老的敌意
当我一头扎进那片熟悉而幽谧的丛林,
一个陌生的男子已先于我抵达。
我们相隔几棵高大而挺拔的银杏树,
并同时惊诧于对方的出现,
以及两头雄狮从洪荒之远处
通过一道闪电分别传递给我们的,
一种如此古老的敌意。
唯有幽暗之寂静取之不尽
每天,我会来到这片人迹罕至的树林,
和静静的树木站在一起;
每天,我都和这些树一起倾听
与辨认那共同的根;
每天,我们从大地之深处汲取着力量,
而唯有
这幽暗之寂静取之不尽。
当你落笔后
当你落笔后,我知道悲凉已化开了一点点,
我知道——
你已然从大地,从岩石之深处
提炼出
一颗终于为人世所见的墨滴。
庆幸
我庆幸与欣慰的是,在持续了十年对米沃什接近炽烈的热情之后,
我终于没有成为另一个米沃什。
烟云深处的道路
许多在你曾经的写作之路上仿佛不可逾越的天堑与山峰,
包括最初你周围的友人,
包括在你的前行中
不断给你以养分的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
他们已化为你在今天回望中山峦的起伏,
以及曾为你的步履丈量过的,
一条烟云深处若隐若现的道路。
细节
细节是我们必须在精微中才得以企及的圆满。
而我们又必须时时警惕,
以避免陷于那渔网的洞眼般无所不在的桎梏。
年轻的神
他们能认出你吗?
一个一百年前的黄宾虹,
一个一千两百年前的杜甫,
一个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
一个两千五百年前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
一个依然如此孤独,
依然并注定不能为一个时代所辨认的
年轻的神。
即使是最强力者
即使是最强力者,
即使如凯撒大帝
或拿破仑,
即使如秦始皇
或成吉思汗,
其身后依然有着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力——
那径直穿越万有的空无。
人性之暗
在两个前后相续
又几乎雷同的梦境中,
我在一种强烈的刺痛中哭醒过来,
两个向我借钱的朋友,
分别用一张涂改后的字据向我要债,
并通过法院发来了传票。
不,不是恐惧,
甚至不是羞辱,而是人性之暗
在一个明晃晃的梦境中如此触目地显现,
并穿凿出了
一条从心喷涌向眼睛的道路。
辨认
西方近两百年的胜利或者说辉煌
是建立在对人性之恶的辨认之上的,
而西方文明日益深重的危机同样肇始于此,
是这辨认之后的沉溺,
而终于没能凝聚出
一次超越或救赎的契机。
必然
必然来自我们每时每刻的修行,
而偶然是夸克粒子般隐匿起的
一个个永不为我们所见的自己。
永无止境的发明
李白、杜甫、但丁的努力是微不足道,
佛陀、耶稣、穆罕默德的努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不是世世代代的读者与信者
那永无止境的发明。
中医的神奇
西医总体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而往往视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为相互隔绝的存在。
中医的神奇在于追根溯源,
并因此终于重建起
万物之间隔绝已久的联系。
云亭
当荷叶高过你的眼睛后,
云亭还是云亭吗?
它是否依然完整地伫立于对岸,
或是已然恢复为
那个从未为你所见的
砖石堆砌之物?
死亡
这个繁华都市最新一处骇人听闻的死亡现场
是在离我居住的小区几里外的豪宅聚集区,
一个年轻女人与三个孩子的死
让我从母亲猝然离世的悲伤中有了片刻的分神。
这些惨烈的死,
而真相远比死亡本身更惊心,
他们眼中勤劳而老实巴交的保姆,
她的愚蠢、無知甚至比邪恶可怕得多,
她最先点着了一本厚厚的书,
在天空即将放亮,
也是这座城市最黑暗而死寂的一瞬。
她从来没有想要她们死,她说,
而只是试图用一次火情来掩盖之前偷盗的事实,
包括一只手表与两只手镯。
但她们的死还是通过更多的细节
带给了我一种坍塌与倾覆的力。
她们,一个比我年轻近十岁的女人和她的三个孩子:
10岁与5岁的男孩,
以及8岁的女孩。
三个孩子紧紧依偎,聚集在妈妈周围,
在离起火的客厅最远的那个房间,
她们头顶是整面落地玻璃幕墙上只能展开一拳缝隙的
一个小小的窗子,
她们所在的房间没有任何过火的痕迹,
但全身都被黑色烟灰包裹着,
包括鼻孔与嘴巴,
她们共同的死因是窒息,
她拨给同小区友人的求助电话,
半小时后终于被看到,
而在浓烟封堵住她们的喉咙之前,
有人仿佛听见过她们的呼救声。
重逢
如果再孤绝一点,
我就可以重逢那最初的自己。
诗
诗是不可言传
而又终于被语言捕获的一瞬。
是这伟大的,
同样是落入凡尘的一瞬,
是这欢喜着,
同样是悲伤的一瞬,
是这如此饱满、
同样如此孤独,如此绝望,
又如此丰盈
而永无止境的一瞬。
远方
自从我发明出道与真理等词语后,
我以为不再有更远的远方,
直到蓦然回首中,我再一次看见了青山
那仿若静止的奔腾。
那为我们所见的
道是神,是圣经中的上帝、
古兰经中的安拉、
佛经中的“无色、声、香、味、触、法”,
他们的隐匿作为一种共同的禁忌。
而那为我们所见的是耶稣基督,
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
以及佛陀因慈悲
而在这人世一次次地重临。
直到十二小时后
在连续多日的便秘、头晕、盗汗之后,
最后那个周日的晌午,
一种属于东方的古老智慧
仿佛突然间临到我。
妈妈,我给你刮下痧试试?
你随即转过了身,
两条深紫的色块在我手指与你结实的后背相触的瞬间,
从你身体深处浮出。
几乎同时,你身体深处的鲜红
再一次漫上刚刚还暗沉死灰的脸上。
很快,你起身,摇摇晃晃地
并坚持自己穿过客厅去厨房取水,
你脸上的笑容传递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颗心中那绷着的弦渐渐松弛下来。
大家惊叹着一种东方古老智慧的神奇,
并庆幸上午没有坚持把对医院有一种近乎恐惧心理的你
强行送往医院。
中午餐桌边的交谈是轻松而愉悦的,
我甚至拿因多日没有洗澡而在你身上起的汗垢开起了玩笑。
在躺回床上时,
你说,你给我擦擦身吧。
我从热水盆里取出了毛巾,
在姐姐、秀秀、阿朱的环绕中,
擦拭着那厚实、因两个深紫的色块而更为醒目的后背,
随后,你转过了身,
一种迟疑与不安是短暂而不易察觉的,
我手中的毛巾先落在有些松弛的腹部,
然后是那对耷拉下来的乳房。
你把之后整个下午的酣睡
归功于刮痧与我为你的擦身,
直到十二小时后,
你起夜摔倒,遽然离世。
传统
传统是一代代的智者重回万物本源处的勇气和愿力
而终于勾勒出的
青山的起伏与奔流。
顺天意
“尽人事”,是穷尽你所能,;
“顺天意”,是坦然于你所不能。
或者说,唯有那些不能的才称得上天。
或者说,天不仅仅在我们头顶,
它同样在我们体内,在大地,在宇宙,
在万物之共同的至深处。
盛年
茂密,不能更茂密了。
荷花次第结出莲蓬。
而这里同样有着
你在不远处的回望中
一个已然不再的盛年。
天赋
或许,天赋并非是天赋,而是因我们世世代代的修行中
那隐没不为我们所见的部分
一次次获得的赠与。
惊诧
当我恍然并惊诧于知了的叫声时,
是我恍然并惊诧于
那突然从我身体深处醒来的绝望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