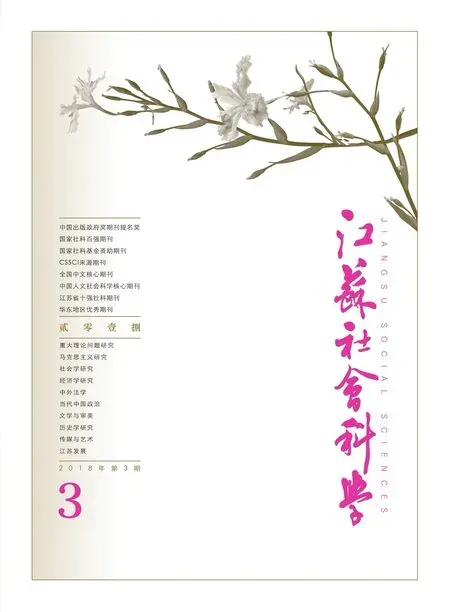《论语》中时间的表述与价值指向
2018-04-15郭院林冯月月
郭院林 冯月月
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它反映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人既生活在时间中,又创造着时间,时间观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西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建立了直线性时间观与循环性时间观,其中有上帝时间观的影响,具有超越性。中国人的传统时间观来源于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具有经验性;也来源于对生命境况的感悟,往往与“时”“运”“气数”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虚无。《论语》中的时间观异于西方,并没有建立宗教式超时间的永恒,而是将生命和历史放在了时间之流中考量。前人在研究《论语》中的时间观时,或追溯它的时间来源,或按程度、性质划分,建立一套时间评估体系[1]柯远在《〈论语〉的时间观念及其溯源》(〔济南〕《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提出,《论语》中所传达的时间观念与天命、天时、人伦息息相关,这种时间观念的来源与上古时期的巫祝们赋予天、地、人的象征意义有关;王琴《〈论语〉的时间与规训》(〔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秋之卷)一文认为,现世人生、礼都是被非逻辑性的时间规范筹划好的,《论语》时间规训的主题范围甚是广泛。。本文从文本出发,剖析《论语》中的时间表述,讨论这些表述背后的价值指向。
一、时间的表述
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体验,往往与日常接触、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密不可分。日升日落,春去冬来,这些变化就是时间流逝的证明。用今天物理学的观点来说,时间的流逝与物质的运动分不开。这种“执有观时”[1]詹冬华:《中国古代三种基本的观时方式——切入古代时间意识的一个维度》,〔济南〕《文史哲》2008年第1期。(即以物观时)的方式,逐渐积累形成了人们的时间经验。“显示、暗示和提示着时间存在的经验,称为时间经验。”[2]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时间经验可分为标度时间经验(对事件定时定位)与时间之流经验(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论语》中表述的时间没有精确的科学划分,而是较常见的粗略直观性的标度时间。“相对的、表观的和通常的时间是延续性的一种可感觉的、外部的、通过运动来进行的量度,我们通常就用诸如小时、日、月、年等这种量度以代替真正的时间。”[3]〔美〕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页。时间的基本单位有年、季、月、日等,又有朝、夕等更细致的时段划分。“朝闻道,夕死可矣。”[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朝”与“夕”一起连用时往往表述时间极短的意思,这种概念直接来源于太阳东升西落的直观感受,“朝”“夕”分别是日的起点和终点,“日”作为时间单位既可实指,也可用于形容时间之短。“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有一瞬间的愤怒,就不能理性思考了,忘记了自身。“吾日三省吾身。”[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也可理解为频繁自我反省。相比而言,月亮盈亏变化则要比日起日落时段要长。“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日与月对比突出的是时间长度的不同,也是毅力与恒心的不同。根据观察天体有规则的运动,大自然提供给人们的时间,日、月往返推移,形成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10]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这里的年岁是约定俗成的日历。生命的长短还与心理体验相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在心情振奋时,孔子忽略了时间的流逝。
“时”是日月运行的节奏,人们将日月星辰的空间位移与生活联系起来,使其具体可感。自然决定的“时”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是自然万物的生命节律。“时节”“四时”是具体的标度时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细致微妙的变化提示着人们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1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有了记时体系,人们就知道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从而规范自身行为,协调人类群体,便于日常活动。“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植物的发芽、抽叶、开花、凋零,生、死有时,栽种有时,万物依时。这些由自然决定的生命形态,它们的变化与存在,皆可视可感。
由于时令季节与万物的合拍程度不同,使得荣枯盛衰俱有时度,从而由此引申到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文化决定的“时”——时机——具有抽象意义,可以理解为机会、条件。“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1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屡次错过时机,怎么能称得上智慧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事讲求实用性,处世灵活,抓住时机。由时间的类似可以推导类似境况,“告诸往而知来者。”[1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第128页,第3页,第198页,第56页,第70页,第189页,第70页,第185页,第4页,第178页,第9页,第17页。以一个时者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将“往”(过去)与“来”(将来)、“故”与“新”等时间词放在一起对照,突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18]《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金景芳认为孔子的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一个是“仁义”。“时”是基本的,偏重自然方面;“仁义”处于从属位置,偏重社会方面[1]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时”为孔子所提倡的一种重要思想,等同于“中庸”。《中庸》里讲:“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2]《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这种“时中”思想,即是随时以处中、与时偕行。另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是“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时光像河中的流水一样,昼夜不停流去,一去不复返。孔子提出了“逝”的概念,这种逝去包括一切过去的东西,比较抽象。上引“告诸往而知来者”与“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的“往”“来”和“逝”一样,不再指具体的时间。
“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和限制因素必然反映在语言和行为里。”[5]〔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第56页。中国讲求人与自然和谐,这种观念注定人们不会产生支配、掌控时间的意识,而是遵循时间的意志。因此,英语里有明显表示时态变化的标志词,汉语里只有“曾”“当”“过”等符号意义的词表示事件发生在过去。“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这里的“始”是先前、起初的意思,表示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与“今”相对。表示过去意思的词还有“古”。“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论语》中有15个时间副词,出现59次[8]孙尊章、徐凌、梁任芝:《〈论语〉〈孟子〉时间副词比较研究》,《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尝”在《论语》中出现10次,8次为时间副词;“将”出现18次,15次是时间副词。古代中国对抽象时间的认识来自宇宙、自然,是最直接的流逝型时间感知,纯粹是经验性的,不同于今天等值、等量的划分。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与存在样式就是一种时间经验样式,虽然不像现代有精细的时间观念,但心理感受外在时令季节变化的敏感性更强,因此《论语》中的时间表述体现了孔子的生活感受与存在状态。
二、时间的延续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孔子的感叹中隐含着时间连续不断、绵延不绝的性质。西方一些思想家强调个体性,而在宗法制的中国,尤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规范,认为人不是单独的,只有在家族绵延、世代传承的前提下,才能正常的面对死亡与生命中的无常。种族的延续,表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就是重祭祀与孝悌。
“对先祖、甚而那些久远的死者的尊敬、赞美和崇拜,在中国人心理和行为中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10]〔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第56页。孔子就守丧三年这一议题与宰予有一场争辩,宰予认为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会耽误礼乐教化,守丧一年就足够了。孔子反对这种功利性的意见,他认为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离开父母怀抱,独自行走。等父母去世了,孩子也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以报答恩情,所以“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真正的过去或源头总在将来与我们相遇。”[1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6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消逝的父母并没有完全地成为过去,一定程度上正参与、影响着后代的将来。生命像画了一个螺旋,盘旋而上。对祖先的怀念,反映在日常行为中,就是祭祀。爱其亲,敬其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孔子告诉弟子樊迟,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以礼服侍他们,去世后,仍要按照礼仪来祭拜,丧葬礼仪也是孝道的一种表达。无违是礼的特征之一,所以《论衡》解释此句说:“毋违者,礼也。”[14]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8页。《礼记·礼运》云:“大顺者,所以养生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页,第30页,第44页,第70页,第91页,第186页,第13页。送死,事鬼神之常也。”[1]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6页,第706页。“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2]《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第62页。在孔子看来,无违父志这样的政治规范才是孝。孝包含感恩、报恩、关怀之意,而孔子强调人自身类的延续与创造的文化传承。
孔子很重视祭祀,《八佾》与《乡党》篇集中讲了祭礼。“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孔子称赞大禹,是因为大禹在祭祀方面的贡献。祭祀的规格、祭器的数量、祭祀人在祭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明确尊卑,确定血缘远近。再如“慎终追远”观念。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认为:“慎终,谓丧尽其哀也。丧为人之终,人子宜穷其哀戚,是慎终也。追远,谓三年之后为之宗庙,祭尽其敬也。三年后去亲转远,而祭极敬,是追远也。”[4]《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朱熹以为:“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5]《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第62页。祭祀祖先是孝的一种表现,也是传统维护与流传的方式。
孔子要求善待在世的亲人,尊敬父母与长者,友爱兄弟。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孔子的“仁者爱人”,即爱其亲。而爱其亲人从爱双亲、子女始。“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亲子以活着的方式关联生与死的距离。父母年长,以其长寿而感到欢喜。与此同时,父母年老,身体衰弱,见其老态又忧惧死亡的到来。“长辈的生命总在以死亡逼临(将要到来)的与再临(活着的过去)的方式构成着这年。”[8]张祥龙:《孝意识的时间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父母、子女的生与养,世代以朝向死亡的方式存在着。这些面对生的欢喜与朝向死的恐惧,并不是当事人独自体验完成的,而是家庭、家族共同经历的。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人重视后代,就是对死亡哀恐的一种表现,因为没有子孙,就没有了血缘的延续。孝,是子女面对衰老着或已消逝的父母,追忆过去。亲辈在我的经历中走向衰老,而我在孝顺亲辈时,正体验着死亡。这种向下的方式,也使我们的“将来”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孝的关键何在?其核心在于未来延续性的传宗接代。《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10]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6页,第706页。《说文解字·老部》说:“孝,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11]《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孝的关键不在于赡养,而在于侍奉父母,其核心是传承,所谓“子承老也”,其意义就是繁衍后代。
孝,是纵向时间的联系。悌,则是共时联系。“长幼之节,不可废也。”[1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1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孝与悌通过文化、制度的连贯,将纵横时间连接,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第2页,第39页,第7页,第194页,第91页,第51页。。于是,无限的宇宙之流与有限的个体生命统一起来,去世的祖先、亲人仍在时间之中,时间记忆的持久抵抗着遗忘。“在中国哲学中,对时间的关切既是一种真实性和存在的形而上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和文化实践的原则。中国哲学因此可以说以时间哲学(在形而上的层面)和时间性的哲学(在伦理层面)为其特征的。”[15]牛宏宝:《时间意识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与西方比较的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祭祖是自己朝向死亡的存在,孝悌是面对死亡做出的事先判断。祭祖与孝悌立足于“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一端连接过去,一端朝向将来。这种生存方式,通过血缘时间观延续着生命的意义。
三、时间的社会性
马克思有许多关于时间的名言,如“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第532页。“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在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第532页。马克思的时间观中,人是能动的主体。人是群居性动物,不同的个体构成了社会,因此时间具有社会性。时间的社会性,也可以说社会时间,即“以社会为主体的时间”[3]吴兰丽:《社会时间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0页,第22页。。社会时间不是观念上形而上的存在着,它具有实践性。“社会时间在文化、制度的中介中达成了社会时间的观念的建构。”[4]吴兰丽:《社会时间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0页,第22页。中国对“正朔”的认同体现出大一统观念,“岁颁其正于万邦,万邦奉之,无敢变乱,以明大统之所在,以一诸夏之所承。自唐虞以来,未之或改,《书》所谓‘协时月正日’是也。周置太史以掌之,六卿于此班治政焉。诸侯受而藏之庙,岁之首则朝庙而行之,谓之朝正。及其衰也,太史失班,诸侯失朝,而天下始异尚矣。”[5]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卷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中华再造善本,第1页。历法一方面是自然时间的记录,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主体意识的体现。历法的统一,一则为生产劳动服务,二则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服务,如何选择历法其实是人的主观行为。“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2页,第23页,第23页。治理国家用夏朝的历法,因为夏朝以农历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春夏秋冬合乎自然现象。出行用商代的车子,因为商代的车比周代的自然质朴,“大辂、越席,昭其俭也。……周之礼文而备,取其纩塞耳,不任视听。”[7]《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朱熹注云:“夏时,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岁首也。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岁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也。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8]《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历法有太阳历和太阴历,夏历更切合我国生产生活实际需求,这是经过历时筛选而胜出的。朱熹的注解中分别以夏、商、周三代的岁首照应人、地、天。之所以如此解释,其实朱熹也是想借天地人这样的权威来强调文化认同的必要性。“显然,《论语》里‘古’的时间是被支配、被秩序化的:‘作事’之人当遵从‘以人为纪’的‘夏时’,不可随意乱纪。如此,方是合乎时间规矩的。”[9]王琴:《〈论语〉的时间与规训》,〔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春秋》开篇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0]《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6页。“王正月”不是简单的时间表述,而是作为春秋公羊学的一大命题提出,其实质是正人伦纲纪,推行王道,达到大一统的目的。《论语》中的时间表述很多时候恰恰体现了华夏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观念。
只有确定了正朔,把握了天道,识得人伦规矩,才能坚守礼乐典章的细节。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式微,礼乐崩坏,诸侯国不合礼仪之处,不可胜数。鲁国使用超越自身等级的礼乐,孔子对此深恶痛绝。“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2页,第23页,第23页。季氏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享有的乐舞,孔子怒不可遏。然而,当时有僭越行为的诸侯不止季氏一家。“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1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2页,第23页,第23页。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祀祖先时,用天子的礼,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原本奏《雍》乐时,天子严肃地居中主祭,诸侯只能立于两侧。如今,三家如此作为,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因礼乐制度形成的文化心态、心理认同,孔子一直致力于“复周礼”。孔子一生好古,克己复礼。“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页,第70页,第28页。“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页,第70页,第28页。孔子沉浸于古代的旧制与文化,他的遗训汲取了前人的经验与教训。知古今之变,才能随时适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也应有所损益,“行夏之时”的主张,便是他对周礼的创新继承。“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页,第70页,第28页。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基而制定的。孔子自身是殷商的后人,却不从殷而从周。孔子宣扬的“礼”也并不是要完全恢复周礼,而是要建立一套崭新的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不是复古论者,只想把当世治理得更道德些。
社会时间具有绝对不可逆性和相对可逆性。“人类历史即社会时间的展开,历史的意义的诠释就是社会时间活动的呈现;而社会存在的发展作为一种未来的规划统摄着曾在(过去)和现在,社会存在与发展在社会时间未来的可能性维度上涵涉了个体生命存在、感受与历史意义的展现。”[4]吴兰丽:《社会时间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1页。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向前的、不可逆转的,人,这一因素改变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合目的性的运动决定了社会时间具有主观能动性,从社会来看,时间仿佛可以倒流,也就是从未来向现在的运动,也可以以现在追溯过去。”[5]赵纯昌:《论时间与空间的社会性》,〔哈尔滨〕《北方论丛》1995年第2期。前、后方位概念在时间隐喻中很常见。前就是过去的,即历史,后就是未来。“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5页。“历史长河”“万古长青”是与空间性相对应的宏观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者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一直为对历史的深切关怀所增强。”[7]〔法〕路易·加迪:《文化与时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对时间的敏感,使时间意识与情感体验纠结在一起,这种对时间的执著体现在历史意识和记忆情怀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左传》中孔子引古志中这句话来评述楚灵王乾溪及难之事,表明此乃古成语。“复”是回到、返回的意思。“先反乎礼,谓之复礼。”[8]《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页,第111-112页。复礼也就是回到礼仪规范。“非礼处便是私意。……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谢氏更为明确:“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9]《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第83页。程子的意思是如果人们都按各自的方式生活,而不顾虑社会公德与行为规范,那就是非礼。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个性偏离社会规范的方面,礼是历史传统流传的规范,因此要复礼。
《论语》中对礼的态度还体现出孔子的历史主义价值指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据刘台拱考证,告朔即班朔,也就是天子“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周礼·太史》)。其意义恰是“以示威于天下”(《孔子三朝记》)。幽王以后,不告朔于诸侯,而鲁之有司循例供羊,至于定、哀之间犹秩之[10]《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页,第111-112页。。在这里,子贡明显看到了告朔礼已经不实行很久了,没有必要再为之每朔犹杀羊进庙。或许子贡考虑到形式和内容不一致,所以索性连残留的形式也想取消。然而在孔子看来,礼是不能少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利益和礼仪形式比较中,孔子选择了礼仪形式。他认为如果连这样的形式都没有,那么礼就会崩坏得更加迅速,以后要考察都没有线索。所以朱熹以为:“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11]《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第83页。这一方面表明孔子是竭力保存现有的仪式,绝不会做损害礼制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孔子对礼制的历史主义态度。如果连饩羊这种形式都不复存在,那么告朔之礼如何能够恢复呢?正如他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这是对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饩羊和文献都是历史的遗留,没有这个遗存作为线索,历史就会断裂,礼无从考索。“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这句反映了孔子对礼的因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说礼承载着文化,不同时期的礼反映了文化的传承。商继承夏的礼仪,周继承商的礼仪。“虽然周代的文化总体上是‘礼乐文化’,而与殷商的‘祭祀文化’有所区别,但礼乐文化本身来自于祭祀文化,而且正如殷商的祭祀文化将以往的巫觋文化包容为自己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包容连续性’,这是古代文化演进的基本方式,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维新道路’相对应。”[2]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1页。
“社会时间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3]赵纯昌:《论时间与空间的社会性》,〔哈尔滨〕《北方论丛》1995年第2期。对混乱现世的不满,促使孔子对先王、先贤无比地崇拜。“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对尧舜禹的功绩和人格赞叹不已,大加推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尧作为君主很成功。舜无为而治,不扰百姓。“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周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仍向殷商称臣。孔子虽然盛赞尧舜禹的“先王之道”,但实际操作中他推崇周代的礼乐文化制度。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孔子自命是周公的文化传人。“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孔子对制礼作乐的周公可谓魂牵梦绕。尧、舜、禹、周公等这些不受时间限制的道德楷模,是世人学习的典范。承先贤之志,启子孙万代之祉,远古时期成为人们向往的时代,这些先贤通过人们的传颂,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被转化成历史。
“我们称历史为‘人的科学’,这还是太过含混。必须说:‘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然而,历史的时间却为具体而有生命的实体,而且一往无回顾。它是浸泡时间的血浆,也是使时间成为可以理解的场所。”[8]〔法〕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3-34页。时间是塑造历史的动力,铭记了人处在当时环境下的表现。历史并不是大量事件的简单堆积,这些历史当中隐藏着孔子修身齐家治国的大道。
四、时间对当下的意义
西方对死有先验的执著,基督教提出上帝创世说,人是上帝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人具有神圣性,时间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所以要重视死;希腊思想中,虽说人类也会死亡,但有不死的神族,这种宗教式的对永恒的追求,实际是人类对死的逃避。中国传统时间观与西方迥异,我国古人对生命的体验不着眼于死,不寄托希望于未来,不追求彼岸世界,而是关注当下,重视现实,对待世界“乐天知命”。
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农耕方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关注的是现世,不是来世,也不是宗教式的长生,所以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论语》中的人文时间有明显的政治社会倾向,注重人生与现实。死不可言说,但有对死的领悟,向死而生。“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66页,第112页。孔子回避对死的讨论,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飘渺,没有道家视死如归的洒脱,也不像古希腊和基督教追求虚幻的永恒,而是对时间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说苑》载:“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防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说苑·辨物》)“死不是一切生命体验的先验根源,而反倒是诸生命现象之一种。”[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中国思想家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生命,人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小个体,个体的生命体验,只是万物蓬勃生机中的一段插曲。不着眼死,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生的问题最重要,死的问题可以存而不论。儒家重视生的价值,时间最终指向人的情感体验、历史遭际。
“自孔子至戴东原,大多哲学家都承认变化是实在的,一切物都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如川的大流。西洋及印度的哲学家,有认为变动是虚幻者,在中国似乎没有。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之一个特点。”[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对万物不断流逝、生长、变化欣然接受。孔子在川上的流水之喻中,“不舍昼夜”,是对时间流逝的从容不迫,表面上是大自然的河水在时间中流逝,深层暗含着生命像流水一样昼夜不停消逝。这并不是孔子对时间流逝的妥协屈服。相反,时间是连续不尽的,在这种绵延中蕴含着生机,日日新,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时间与万物联系在一起,体现物我相融的生命情调。夫子见川水之流迅速,兴言时事往者皆像川水,生命似流水奔腾不息,最终也会消亡,这是动态的过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3][4][5][6][7][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生命时间流逝不可逆转、不可抗拒,面对未来之死与当下之生的选择、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的无限,孔子密切关注现世生活,把握时机,对流逝的时间进行抗争与挽救。在有限的时间中建功立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就增加生命的密度。
个体生命都将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孔子重视这个大时间的始终,合理规划每个动态的时间点,以便创造“个人时间”。孔子这样把握人生中的每一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这并不是简单地用年岁把生命分割成一小段一小段,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心理也应在“一日三省”中有成长的过程。正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孔子把握生命的契机,将人生划分为少年、壮年、老年三个阶段,每一个时段都严谨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创造的欲望与时间的流逝冲撞,最终在规制中实现生命价值,得以流传千古。“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周易》穷尽命理,预示吉凶,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学习《周易》要结合生命的发展,去长时间体会。“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到四十岁了仍被人厌恶,这一生也不会有大作为了。“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8页,第12页,第174页,第70页,第189页,第93页。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名望,那他就不值得畏惧,因为后来的年轻人会追赶上来。
《论语》中的时间表达程度有所不同,对过去的时间概念表述相对模糊,对现在的时间规划很清晰具体,不涉及对未来的讨论。时间的延续性与社会性包含着儒家的道德伦理,这些具有规训意味的仁、礼涵盖整个社会,对现世人生有多种意义。